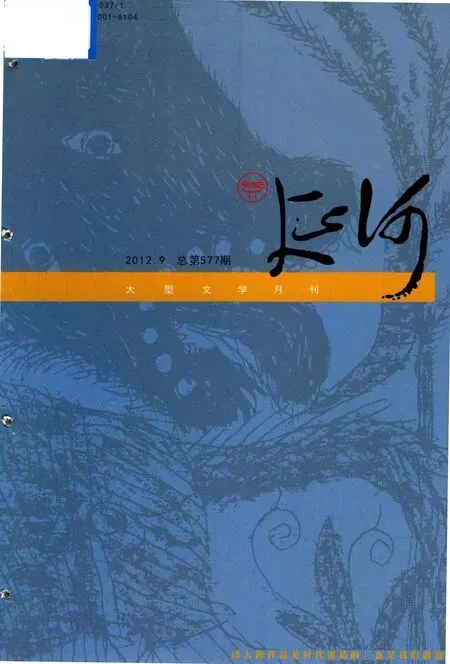拉哥们一把
2012-12-18和军校
和军校
魏明新拿到组织任免的红头文件以后,躲进洗手间里,裤子也没有脱,就那么干蹲着,咬着自己的袖子,任泪水飞扬。魏明新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他不会露一丝声气。最先,是郭头儿给他吹的风。郭头儿说,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你熬成了,祝贺!魏明新知道郭头儿跟组织部长是牌友,他的话向来不是空穴来风。办公室的同事们陆续逮着了风声,嚷着叫魏明新请客,魏明新硬是撑得稳如泰山。后来,组织部长找魏明新谈话了,魏明新知道他的这个副处级八九不离十了,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该干啥干啥,不张不扬。公示之后,红头文件下来了,直到这会儿,魏明新悬在半空的心才算落到了肚子里,他知道,这个副处级已经是他袖筒里的鸟儿了,再也飞不了了。魏明新的眼泪越淌越欢,心里五味杂陈,只有他清楚,为了这个副处级,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悄悄地哭了一气,魏明新用袖子把眼睛沾干净,用凉水洗了脸,抿着嘴唇,然后一点一点地把两个脸蛋吹大,再一点一点把气放出去!往事如烟。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一去不复还。他魏明新副处长的幸福生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了。
魏明新走马上任后,郭头儿原本想给魏明新安排几个出头露脸的活儿,但魏明新提出他先去基层走一走,跟基层的同志见见面,熟悉一下。魏明新的理由很充分,容不得郭头儿不同意。魏明新知道,郭头儿是他命中的贵人,他现在的一切都是郭头儿给他的,没有郭头儿,就没有他魏明新的今天。他不想跟郭头儿拧着来,但他也有自己一点隐私。
魏明新决定先去乌尔禾。这一决定,连魏明新自己也吓了一跳,天大地大的克拉玛依,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乌尔禾?平日里,太多的琐事总是让魏明新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乌尔禾进入思维和梦想的时间越来越少,亦无牵挂,直至忘却。此时此刻,乌尔禾第一时间跃入他的脑海,且越来越清晰,随之清晰的还有师傅、小初、阿福。乌尔禾,是魏明新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那会儿,魏明新刚从大学毕业,他的师傅在乌尔禾,他的初恋在乌尔禾(如果那还算做初恋的话)。魏明新恍然明白,不是他忘了乌尔禾,而是他一直回避着乌尔禾。二十年弹指一挥,物是人非了,他可以坐着属于自己的专车风光无限地回乌尔禾了,他要大声地告诉乌尔禾:我魏明新又回来了!他还要告诉整个世界,没有靠山的人照样可以功成名就飞黄腾达光完耀祖。他要去见见师傅,见见小初,见见阿福。
乌尔禾的天还是这么高,还是这么蓝,乌尔禾的空气里还是飘荡着浓浓的牛羊肉的馨香。魏明新视线模糊了。魏明新和阿福同一天来到乌尔禾采油厂报到,同一天给小初的父亲当了徒弟。师傅是个锉墩墩,四方大脸,爱下棋。收下魏明新和阿福为徒的当天下午,师傅就把两个人请到家里吃饭了。师傅端着酒杯说,在我这儿,有个老规矩,收徒弟的第一天,在家里摆个收徒宴。往后呢,我肚子里有多少货,给你们倒多少货,看你们不顺眼了,也打,也骂,打了你,你担着,骂了你,你也担着。如果你们愿意担着,就端起酒杯,这一杯酒下去,咱们就是情同父子的师傅和徒弟了,如果不愿意,拧身子走人,我不拦。魏明新和阿福不约而同地端起了酒杯,叮当一声响,三个人一饮而尽。就在那次饭桌上,魏明新见到了小初。小初漂亮得像仙女一样,声音像银铃一样,魏明新一个劲儿地咽着口水,他实在想不明白,师傅这样丑陋的男人怎么能有小初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儿?他拿定主意,一定要把小初追到手。魏明新没有把阿福列为情敌。阿福毕业于另一所高校,是个农村娃,性子温和,貌不惊人,衣着不讲究,走路低着头,开会坐角落,人多不开腔,一副与世无争安于现状的模样。魏明新和阿福住同一间宿舍,魏明新巧舌如簧,阿福笨嘴拙舌,魏明新喜欢夸夸其谈,阿福是大事小事都搁在心里,性格的差异,使两个人成了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情同手足的好朋友。魏明新说,逛去?阿福说,走。魏明新说,喝酒?阿福说,成。魏明新说,去师傅家玩?阿福说,走。魏明新问,你说小初长得漂亮不?阿福说,嗯。魏明新问,你说我跟小初般配不?阿福说,嗯。众所周知,师傅没有多少文化,却是一名天才棋手,每次厂里举行棋类比赛,师傅都是第一名。每次比赛前,师傅往棋盘前一坐,咬一根烟,不管对面坐的是谁,他都用食指敲一敲棋盘右下方的车马炮,说你随便拿掉一个吧。有人拿掉了车,有人拿掉了马,有人拿掉了炮,不管拿掉了啥,结果还是师傅胜。当阿福坐在师傅的对面时,师傅还是老话老动作,阿福说,师傅,不用。师傅抬头见是阿福,呵呵一笑说,还是拿一个吧。阿福固执地说,师傅,不用。比赛就这么开始了。第一局,阿福胜;第二局,师傅胜;第三局,阿福胜。阿福笑着说,师傅让我呢。师傅连声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说毕,师傅用拳头拄在了桌子上站起来了,那一拄,似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师傅丢了冠军,丢了威风,也丢了“棋圣”的名号。魏明新直看得牙根发痒,心下说,瓷乎乎的,你就不能让让师傅?但阿福不让。阿福就是这么一个人,实诚,也犟,犟得像牛!
可是,后来和小初手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不是魏明新,而是阿福。魏明新捶胸顿足后悔不已痛不欲生,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大意失荆州。
魏明新奇怪的是,在阿福面前受挫的师傅不但不生气,反而越发地喜欢魏明新和阿福了,得空就叫他们去家里吃饭,吃罢饭,师傅就和阿福摆上了棋摊子,魏明新看不懂棋谱,对下棋也没有兴趣,他就陪着小初干家务,洗锅呀,涮碗呀,扫地呀,一块去沙漠里看月亮呀,一块去看露天电影呀……魏明新是幸福的,从小初的笑声中,魏明新判断得出来,小初是喜欢自己的,也是幸福的。魏明新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他开始憧憬以后的幸福生活了。
师傅突然给阿福和小初订婚了。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师傅没提过,小初没提过,阿福也没提过,怎么就订婚了呢?魏明新很失落,很伤感。酒席上,师傅笑得很开心,小初笑得很开心,阿福也笑得很开心,魏明新悄悄地把眼泪往肚子里咽。那一刻,魏明新恨师傅,从里到外,阿福没有一点比得上他的,师傅怎么就相中了阿福呢?由此,魏明新又联想到师傅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技术培训,师傅让阿福去了,阿福在大城市逛了半个月;技术比武,师傅让阿福参加了,阿福得了冠军;生产中有了疑难杂症,师傅也让阿福去了,阿福总是手到病除……魏明新不服气,如果让他参加培训,让他参加技术比武,他照样拿冠军,如果让他解决生产中的疑难杂症,他也能做到手到病除。可是,师傅把机会都给了阿福。魏明新明白了,师傅是偏心的,他爱的是阿福。或许,师傅、小初,还有阿福,他们共同都在嫉妒他的聪明能干。魏明新思谋着跳槽了。技术干部虽然吃香,但技术干部越来越多,想出人头地,比登天还难,思来想去,魏明新打算逆流而上。魏明新探听到郭头儿要来乌尔禾检查工作时,他对郭头儿的基本情况了解了一番,找郭头儿毛遂自荐了。
魏明新双手把自己的简历呈上去,一脸诚恳地说,郭处长,我想干宣传。
郭头儿看罢魏明新的简历,说,你给我一个理由。
魏明新说,念大学的时候,家里穷,我就靠当家教补贴学费,也一直想当老师,但受专业的限制,只能到采油厂来,但我还是想当老师,想搞宣传,我的兴趣和特长就是爱写爱画。魏明新之所以这样说,是他了解到,郭头儿的儿子正在念初中,学习一般。
郭头儿把魏明新端详几分钟,意味深长地“噢”了一声。
一月后,魏明新的调令来了。
离开乌尔禾时,魏明新一直没有回头,这是一处伤心地。
干上宣传以后,魏明新像许多的宣传干事一样,写广播稿,写通讯报道,办橱窗,贴标语,挂横幅……和许多宣传干事不一样的是,魏明新还是郭头儿孩子的家庭老师,还是郭头儿的服务员。鞭炮纷乱年气浓浓家家团圆的时候,魏明新陪着郭头儿和郭头儿的朋友走进沙漠腹地“放松”——靠近农家乐搭起自己的帐篷,吃抓饭,吃烤肉,喝烧酒,然后就是打牌。郭头儿爱打牌,爱得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魏明新并不参战,他只是做服务工作:搭帐篷、泡茶、找零钱,点菜。郭头儿说,所谓放松,就是远离老婆娃娃,专心致志地打牌。节假日了,魏明新要陪着郭头儿“一条龙”:泡澡、捏脚、按摩、喝酒、卡拉OK……郭头儿说,人嘛,不仅要会工作,还要会生活,生活嘛,就要丰富多彩。郭头儿嘴上的活儿很讲究,鸡蛋要吃土鸡蛋,面粉要吃新麦磨成的面粉,土鸡蛋哪儿来?新麦磨成的面粉哪儿来?都是魏明新从300公里外的老家源源不断地运来……幸运的是,郭头儿没忘魏明新的这一番苦心,把他扶上了副科长的位置,又扶上了科长的位置。年龄渐渐大了,专业忘得一干二净,魏明新怎么甘心在科长的位置退休呢,他做梦都想“进步”。如果不进步,怎么对得起自己的一辈子?魏明新心里明白,要想进步,他就得有让郭头儿张得开嘴的资本,所以,他在陪郭头儿之余,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博览群书上,再一篇接一篇地写着“大块”文章,发表在油田的报纸上。办公大楼下有一块公示牌,机关有什么活动呀,通知呀,人事变动呀,都会在公示牌上公示。魏明新最关心的就是那一块公示牌了,暗想,他魏明新的名字总有一天会出现在那块公示牌上。有一天,魏明新的媳妇出差了,他中午泡了一碗方便面,就没有下楼,下午上班以后,魏明新见办公室的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咬耳朵,他问老宁,啥事呀,神神秘秘的?魏明新跟老宁年龄相仿,也是“进步”路上的竞争对手。老宁说,祝贺你,上公示牌了。魏明新的心呼地一下就悬了起来。但他故作镇定地说,又拿我开涮呢。老宁说,真的,不信,下楼看看不就明白了?魏明新没有下楼,他在网上溜了一会儿,然后装作去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后,直接下楼了,公示牌上确实有新内容,确实有魏明新的名字,公示的却不是干部任免通知,而是迟到早退名单。魏明新像是被人抽了耳光,低着头,匆匆从公示牌前消失了。他知道老宁等着看他的笑话,他发誓要打败老宁,不能让老宁看他的笑话,不能让师傅、小初、阿福他们看他的笑话!
住进宾馆以后,魏明新想先去拜访老黑。老黑不姓黑,生得黑,就挣得了老黑的绰号。魏明新跟老黑是校友,老黑比魏明新高两届,属师兄,实干家,升得也快,现在是副厂长。魏明新在乌尔禾时,就跟老黑走得近,两个人喜欢端着老碗喝烧酒,还喜欢吃烤羊腿。魏明新拨通了老黑的手机,问,师兄,在哪儿潇洒呢?老黑说,打兔子呢。魏明新说,师兄真够腐败呀,上班时候打兔子?老黑嘿嘿笑着说,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了?魏明新抬腕一看,窃笑自己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原来今天是星期六。魏明新说,师兄你多打几只,晚上就吃你打的兔子。老黑说,怎么,衣锦还乡了?感谢师傅来了?魏明新打着呵呵说,什么呀,搞调研嘛。老黑说,好,晚上见。收线以后,想起刚才的一番对话,魏明新觉得老黑一句话说对了,一句话说错了,说对的一句是:衣锦还乡。说错的一句是:感谢师傅。自己的升迁跟师傅井水不犯河水呀!
宾馆很整洁,很寂静,独自呆着的魏明新百无聊赖,就出去在街道上溜达,街面上的商店、餐馆、理发馆、招待所,都似曾相识,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亲切劲儿。走着走着,魏明新陡然发现眼前的一切竟然是这般熟悉,这几株槐树,这一片草丛,这两条石凳,这……不是师傅家属区的那栋楼吗?自己怎么不知不觉地走到这儿来了?楼已经很陈旧了,师傅还住在这儿吗?一个老太太正坐在树下的石条凳上摇扇子,魏明新向老太太打听师傅是不是还住在这儿,老太太扬手朝上一指说,四楼,靠东那一家。听到这一声,魏明新的腿就软了,心里泛起一股酸楚。二十多年了,师傅还住在这栋55平方米的小楼房,他们的生活可想而知了。想当初,师傅要是把小初嫁给他,一切都是另一番景象了。魏明新打算回宾馆去,等买一些礼物,再正式地前来看望师傅。魏明新一拧身,怔住了,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四十岁光景的女人,手里拎着菜,愕然地张着嘴巴。
明新,真的是你吗?女人情不自禁地问。
果真是小初。二十多年过去了,小初的轮廓没有变,声音没有变,肤色没有变,只是头发没有了往日的湿润和光泽。
魏明新叫了一声小初。
小初兴奋地说,我爸和阿福都说你这几天要来呢,果真就来了。
魏明新笑着没吱声,也没有把小初的话往心上搁,这次乌尔禾之行,除过郭头儿,没有人知道的。难道师傅和阿福会算卦?小初之所以这么说,或许是出于客套。
小初扬着手里的菜说,我爸和阿福钓鱼去了,走,家里去,我给咱做饭。
魏明新迟疑着。
小初说,怎么,刚当了官,就摆官架子呀?
魏明新一头雾水,她么知道自己当官了?他急忙摆手说,不不不,我想……
小初说,别想这想那的,快家里去。
师母走得早,师傅一直没有续弦,师傅又守了小初这么一个女儿,所以一直跟小初过活。师傅家的布局还和过去一个样,简单,整洁,过去的木头沙发换成了布衣沙发,18英寸的背头电视换成了32英寸的液晶电视,木头小圆桌换成了玻璃茶几,墙上还挂着两张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一张中国地图。小初给魏明新泡了一杯茶,系上围裙,坐在茶几前,一边摘菜一边和魏明新拉家常。
魏明新问,师傅还好吧?
小初说,好着呢。
一杯茶装进肚子里,魏明新彻底放松了,他想从小初的脸上中捕捉一点后悔的神情,他却失望了。魏明新说,小初,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不知当问不当问?
小初说,看你,当了官就变得这么生分了,说吧,啥事?
魏明新问,当年,你怎么突然就和阿福订婚了?
小初说,这事呀,我给你说。有一天,我下班后,我爸突然对我说,你也不小了。我明白我爸的心思,说爸你想赶我出门呀,休想。我爸说,就算我不赶你出门,你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我说,这是你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你看上谁就是谁。我的脾气你知道,打小就被我爸惯坏了,大事小情都靠着我爸。我爸点燃了一支烟,半天没言语,直到把那支烟抽完了,我爸才说,阿福的母亲病了,按关中的风俗,想讨一门亲事,定个婚,冲个喜,爸知道,这是说不出口的事,也是迷信的事,但是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我想给你和阿福订婚,你想一想,你要是同意,就点个头,要是不同意,权当爸没说。我说,爸,我听你的。我爸喜出望外,问我,你同意?我表态说,你同意我就同意。你知道,我打小就是一个乖乖娃,遇事没主意,大事小情都听我爸的。
魏明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他问,就这些?
小初说,就这些。
小初并没有征求魏明新的意见,和面、切菜、拌馅儿、擀皮儿、包饺子,韭菜鸡蛋馅儿。魏明新心里暖烘烘的,小初还记着他的最爱。
魏明新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愫。小初是善良的,是纯净的,是无辜的,只要从师傅的脸上看到愧意,只要从阿福的脸上看到自愧弗如,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就算看在小初的情面上,他也应该拉阿福一把的,他给老黑说句话,把阿福调进机关还是有可能的,当个科长副科长也是有可能的。魏明新比自己的想法吓着了,原来,“给师傅、小初、阿福他们一点颜色瞧瞧”的想法盘踞在他的心头。
小初保持着往日的麻利,包完饺子,又拌了三个凉菜,一碟炝莲菜,一碟老虎菜,一碟尖椒变蛋。小初把凉菜摆上桌,说明新,你先吃。
魏明新连连摆手说,要不得要不得,等师傅和阿福回来了一块吃。
小初笑道,他们呀,天不黑是不进家门的。
小初告诉魏明新,父亲是退休后爱上钓鱼的。每天天一放亮,左手渔具,右手小凳子,晃晃荡荡出发了,风雨无阻。小初还告诉魏明新,阿福就是一个跟屁虫,父亲爱上钓鱼,他也爱上了钓鱼,每逢周末,他就跟父亲一块钓鱼去了,起早贪黑的。
魏明新问,那吃饭怎么办呢?
小初说,上班的时间,我就给父亲带点吃的,周末了,我就做点好吃的,给他们送过去,和他们一块吃,孩子在念大学,周末也不回来,我一个人呆在家里也无聊,就出去跟他们吃个热闹。
魏明新喜出望外,说,走,我跟你一块给师傅送饭去,我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小初推辞不过,就收拾了行礼,跟魏明新一块给父亲和阿福送饭去了。
大自然很神奇,人类很伟大。竟然能在浩浩荡荡的沙漠中竟然能建起一个鱼塘!有了水,便有了灵气。一方碧水,几株绿树,一群水鸭,鸟儿的啁啾声在枝头跳跃着。
树荫下铺了一块硕大的塑料布,师傅和阿福两个人赤着脚盘腿而坐,每人跟前放着一个大塑料杯子,里面是颜色不正的劣质茶叶。中间是棋盘,两个人正杀得全神贯注。
小初说,哪是钓鱼,完全是挂羊肉卖狗肉。
小初又说,他们每天每人只钓一条鱼,然后就下棋了,我不送饭,他们不吃饭,我不叫他们回,他们就死坐在这儿。
魏明新心里泛起一股悲凉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两句“俗话说”,头一句是:破罐子破摔;第二句是:棒槌敲肚皮——自己给自己宽心。
魏明新恭敬着叫了一声师傅,师傅瞅了一眼魏明新,说明新回来了。阿福也跟着附和了一声,明新回来了。师傅和阿福都没有表示出他所期盼和想象的欣喜,他们的表情和口吻都淡淡的,仿佛他们早就知道他要来或者说他压根就不曾离开过这里,更像过去他给师傅当徒弟时出门打了瓶酱油又转身回来了一样。随后,师傅和阿福又急不可待地把目光和注意力转移到了棋盘上。
魏明新心里有几分失落。
小初说,别下了,吃饭吃饭。
师傅伸出一只手掌阻拦道,别着忙,别着忙,这一局,我倒是要看看鹿死谁手!
阿福不动声色地说,是啊,鹿死谁手还真说不准呢。
师傅哼了一声说,不服输,咱们就骑驴看画本——走着瞧!
阿福嘿嘿笑道,走着瞧走着瞧。
小初着了急,蹲下身,三把两把把棋盘上的棋子儿拨拉了乱七八糟,边拨拉边说,瞧个啥呀,瞧个啥呀,再瞧黄瓜菜都凉了!
师傅和阿福不约而同地伸手保护棋盘上的现状,无奈不及小初的手快。
小初命令道,快洗手吃饭。
两个人不满地咕哝着在鱼塘里洗了手,小初从塑料袋里拿出一条干净毛巾递给师傅,师傅拭完了手,递给阿福,阿福拭完了手,递给小初,小初又叠得四方四正地装进塑料袋里。师傅和阿福又一次赤脚坐在塑料布上,小初也学着两个人的样子,把鞋丢在一边,盘腿坐在塑料布上,她拧头招呼魏明新,明新,快来坐呀。
魏明新犹豫着,他很想像师傅和阿福一样,赤脚坐上去,但他又很想表现一下“领导”的矜持和大城市人的文明。
明新,快来坐呀!小初又叫了一声。
魏明新只好脱了鞋,在塑料布上坐下了。小初把三个凉菜和饺子摆上“餐桌”,开始分发餐具,一人一个小木盘、一个小碟子、一双筷子、两张餐巾纸,分发完毕,两手一拍,喊,开饭喽!
师傅抄了一筷子凉子,边嚼边说,有点酒就好了。
小初瞪父亲一眼,冷腔道,都‘三高’了,还酒酒酒,往后少跟我提酒!
阿福说,没那么严重,少喝一点不碍事。
小初又瞪了阿福一道,扬了声说,你个马屁精,少在这儿装好人,都‘三高’了,还不严重?啥算严重?住医院里就算严重了?往后,你也少跟我提酒的事儿。
阿福举手投降,说,好好好,我也不提酒的事。
小初并没有动筷子,她在剥蒜,剥一瓣儿,扔师傅碟子里,又剥一瓣儿,扔魏明新碟子里,又剥一瓣儿,扔阿福碟子里,再剥,再扔。这一家人都爱吃蒜,餐桌上一年四季都有剥好的蒜瓣儿,师傅说过,大蒜是天底下最好的消炎药。魏明新跟这一家人学会了吃蒜,那会儿也觉得大蒜香,解馋。自从调到克拉玛依,魏明新就不吃大蒜了,那冲鼻子的味儿,漱口漱不净,刷牙刷不净,嚼口香糖也于事无济,他要给郭头儿汇报工作,他要跟着郭头儿检查工作,他要开会,他要在电梯里上上下下,薰了郭头儿和别人可怎么办呢?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这话说得有分量,在大机关工作,不讲究细节怎么行呢?
鱼塘边,树荫下,塑料布上,一片香喷喷的咀嚼声,这般和谐,这般温馨,这般幸福。魏明新突然想起了他的妻子,那个性格怪异的小出纳,魏明新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应酬,应酬完了都是摇摇晃晃回家的,回家就跌在沙发上喊水——水——水——,可恶的小出纳不但不给他倒水,还恶声恶气地骂,有本事就喝死到外面去,有本事就不要回家!往往,魏明新都是在小出纳的骂声中走进梦乡的。
饭毕,师傅和阿福还要下棋,小初说,下什么下,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师傅“噢”一声,说,钓鱼。
阿福朝魏明新扬了扬渔具,魏明新摆了摆手。
师傅和阿福坐鱼塘边了,两个人一人咬一根烟,一切都寂静下来,知了的叫声格外嘹亮。
魏明新和小初相视而笑。
魏明新在心里感慨,淳朴的小地方人,他们是多么容易满足啊!
返回的路上,魏明新心事沉沉,一句话也没有说。
晚上,老黑给魏明新接风洗尘。这是魏明新“爱得要命恨得要死”的场所,这是魏明新熟悉又迷恋的气氛,在这里,魏明新如鱼得水。老黑请来的都是校友,还有魏明新往日的几个好朋友。老黑原本也是请了师傅和阿福的,师傅说他不能碰酒,拒绝了,阿福说他有事儿,也拒绝了。
魏明新坐在“上席”。坐在“上席”的感觉真爽,魏明新的眼神和抬手动足的做派都有了居高临下的意思。老黑站起身,举着酒杯,干咳一声,正要讲开场白,随着“吱呀”一声小心翼翼的门响,探进来半拉脑袋,是阿福。老黑急忙招呼阿福快来坐,又吩咐服务员加一套餐具。
阿福把一个剪贴本递给阿福,说,你们喝你们喝,我还有事呢,走了走了。
阿福说走了,真的就走了。
魏明新翻开剪贴本一看,惊呆了,这是他发表在油田报纸上的“作品集”,有“豆腐块儿”,也有“大块头”,一篇一篇贴得整整齐齐,每篇文章下都标注着发表的日期,从字体上看,有的是师傅写的,有的是小初写的,有的是阿福写的,无一例外地都是一笔一划写上去的,公公正正。魏明新曾经让小出纳把的“作品”收集整理一下,说不准那一天要出一本书的,小出纳不以为然地说,溜须拍马的玩意儿,谁看呀,还出书呢,不够丢人现眼的!没想到,师傅一家人默默地替他做好了这一切,魏明新鼻腔发酸。
沉默了片刻,再仰起头来,魏明新又是一脸灿烂的笑容了,他举着剪贴本说,人嘛,就要自强不息,就要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功成名就,否则,只能落个像阿福这样的下场。
魏明新一席话,说得满桌人面面相觑,大家都把目光集集在老黑的脸上。
老黑嘿嘿一笑,带头鼓了掌,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魏处长说得好说得好,来,咱们共同为魏处长敬一杯。
魏明新站起身,却没有像惯例那样挨个儿跟大家碰杯,他说,师兄啊,在座的都是自家人,我也就不见外了,俗话说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给我一个面子,咱们共同拉阿福一把,你刚才也看见了,阿福就是那么个实在人,给一个不长进的师傅当女婿,有点儿自暴自弃,有点儿不求上进,但咋说也跟我‘共患难’过呀,把他调进机关如何?给他一个副科长如何?
老黑被说得一愣一愣的,但他很快就换上了一副轻松的表情,把大家瞅了一遍,笑着说,听见了吧?魏处长明明知道阿福一直是咱们这儿的技术尖子,也知道厂里几次想把阿福调到机关来,油田机关也想把阿福挖走,这个阿福呢就是不去,说他就喜欢在基层做点具体工作。还有,这个阿福是有点死心眼儿,不喜欢当官,如果喜欢当官的话,肯定在我和魏处长之上。可是,魏处长刚才为啥要那样说呢?你们不懂了吧?这就是幽默,魏处长的幽默!
魏明新瞠目结舌。
老黑继续说,还有,咱们魏处长的师傅,阿福的老丈人,你们都知道的,也都认得,在乌尔禾,哪个敢不尊着敬着?还有一个小秘密你们都不知道,想当初,魏处长的师傅发现魏处长的性格不太适合搞专业,才一步一步把魏处长推到现在的位置,你们都傻眼了吧?想不通一个老工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告诉你们也不妨,郭处长你们肯定都听说过,很牛皮的人,他也是从咱们乌尔禾出去的,他也是魏处长师傅的徒弟,也爱下棋,师徒两个情同父子,每年春节,他都要来乌尔禾给师傅拜年,从不例外。可是,魏处长刚才为啥要那样说呢?告诉大家,还是幽默,魏处长的幽默。闲话说得多了,来来来,咱们喝酒喝酒。
魏明新手中的酒杯慢慢倾斜,酒一点一点地洒出去。
这一夜,魏明新酩酊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