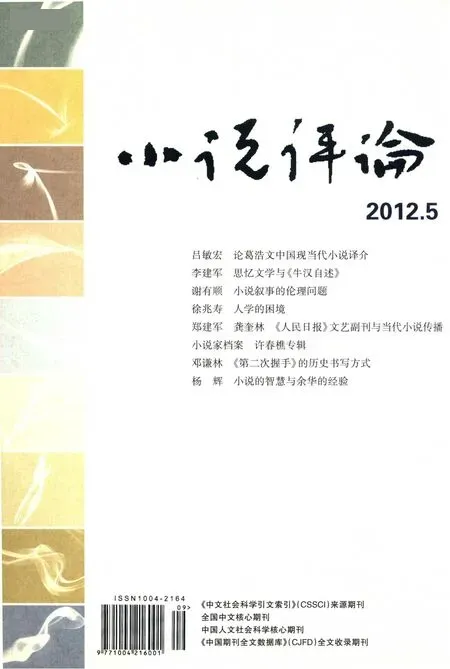一位灵智长者的精神探索
2012-12-17徐兆淮
徐兆淮
自打从编辑岗位上退休之后,已有多年未闻何士光的讯息了。如今忽然从《钟山》2011年5期上读到他的长篇纪实散文《今生》,不禁再次勾起了我与士光书信交往及组约稿件时的情景记忆。而一旦走进记忆的深处,便顿时感到阵阵的暖意与亲切。我知道,内中不仅有老编辑对老作家的怀念,也有评论家对作家的友谊与尊重。而这种感觉一旦走进一个年过七旬的长者的心田,浮现于脑际,便往往会产生一种非诉说不可的愿望,随后我便沉潜到对士光其人其文的记忆中。
诚如一位学者所说:“聪明的老人,应该是对个人的经历与社会有静观与思辨能力的人。”如今我们读着何士光的《今生》,便能感悟到,一个灵智的老年长者对往昔生活的慨叹与感悟,对人生旅途上遇到的邻里亲友的追忆与反思。追忆反思不免有叹息,有遗憾,有欣喜,也有悲苦,还有宗教般的虔诚,灵智者的顿悟,真可谓是人生苦短,百味杂陈,一股脑儿涌上心头。而这或许正是老人旧忆散文的优势与特点。只有具有丰富人生阅历,又经过历史时光的沉淀,耐得反复咀嚼的人,才有资格有能力,写出这类灵智、清纯又耐人寻味的忆旧文字。读之犹如在品尝一杯醇厚清香的人生佳酿。
士光的《今生》没有小说的曲折情节,也不讲究戏剧的矛盾冲突,更毫无眼下正在流行的低俗化倾向。作为一种非虚构性的叙事作品,它除了在淡淡的背景上,缓缓地叙事之外,似乎更注重在真实地诉说真切感人的人生感悟,散发出浓郁的人生慨叹,还有灵智而深沉的哲理妙思。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在作者看似平静舒缓的笔下,童年直到大半生遭际中所见到的各色人等,所经受过的各类事件,尤其是作者五味杂陈的人生体验,自然这也勾起了我这个老读者人生各阶段里,或苦涩或幸福的诸种记忆。
记不得是哪位名士说过一句带有一定创作规律的话:青年人适合写诗,中年人适于写小说,老人适于写散文。我以为,虽然这话不能概括或适合所有的作家或所有的创作规律,但却也不乏一定道理。士光的前期创作委实主要写小说,他的有影响的代表作品如《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和《远行》,还有一些影响不大的长篇小说,均写于80年代,他正值40岁左右的年纪。而他年过半百之后所写《如是我闻》,则属于带有哲理意味的散文随笔类,在这之后,读者确实很少见到他再写虚构体的小说了。如今年近七旬之时,他写作并发表长篇散文《今生》,也就并不奇怪了。仿佛记得,在中国古代作家中,喜好专研宗教、佛法的人,本就少得可怜,而沉潜其中,甚至深深入迷者,恐怕也只有何士光其人了。
我不知道现代青年读者是否喜欢读士光所写的这类抒写人生积累、表现人生体验的长篇散文,依我猜想,那些心境浮躁的人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大约是读不进这类书籍的。而作为走过人生大半旅途的老人,我却颇喜欢读这类长篇散文,并自以为读懂了,其中的一些内涵,读通了蕴含其中的某些感情的。我以为,对于那些具有一定阅历和体验的中老年读者而言,士光的《今生》确实具有另一番风情,另一种吸引力。这情形恰如我年轻时只喜欢读那些情节惊险的武侠小说一样。可见,年龄对于阅读的影响,确实不可小视。
看来,老作家与普通老人回忆、梳理自己往昔的生活岁月时,本就有些不同之处,而何士光的忆旧文字又自与其他作家迥然相异。如果说,一般老人忆旧时总喜欢絮絮叨叨说些发生在亲友间的日常生活琐事,一般老作家更关注于人生变故中社会、时代的政治氛围,那么,何士光在追忆往昔岁月,咀嚼寻常生活中不寻常的滋味时,往往更喜欢注入宗教文化的审视意味,因而不免常令人沉潜到难以捉摸的玄思冥想中去。如此,一般读者读后一时间恐怕尚不能获取到较清晰的印象,但仔细想来,往往倒也能为读者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这情形,我想凡是读过他写于1993年的《如是我闻》者,大约便更能理解他写作《今生》的宗旨。他仿佛是在叹息生活的变动不居,又好像是在感慨生命之无常。
也许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佛家经典很容易进入走火入魔的境界,而何士光写作《今生》原本就意在“为我的今生今世的人生寻找一种归依。”亦即,他所苦苦寻找的,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这是古老的哲学、宗教命题,亦是文化长者对人生和生命的临终叩问。由此观之,《今生》的笔墨,几十年似乎一直未离开自己的今生,也未离开邻里的那位姑娘。他始终专注的兴奋点,乃是在对今生与来世的考量中,讲经说佛,修习道义。在他看来,探究世界和生命的真谛,认知世界的本质,原有两条路径:哲理科学与宗教佛法。或是两者的融会贯通。只有如此,才能进入“众妙之门”,弄清精气神的本源与特质。于是,我们终于看到,90年代之后,站在我们面前的何士光,仿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作家,而几乎成了一个传经布道的宗教文化学者。
显然,《今生》的副标题似可作这样的解读:“经受”的是今生磨难,“寻找”的是人生归依。在一个灵智长者的眼里,人生磨难也许各不相同,而精神的的寻找,却总是难以超越的。
何士光在《今生》的写作中,别开生面地将今生的现实生活与来世的精神寄托融汇为一体,用讲经说佛,传经布道的方式,将宗教文化的玄思,与文学的情感力量熔为一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何士光在当下目迷五色精神萎缩的现实世界里,从拓展、探索宗教文化里寻求出路方面,所作出的可贵努力。尽管,刹那间作为凡夫俗子,寻常百姓,人们并不能完全读懂,也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佛法与道义,但对士光的良苦用心,对他创作走向的蜕变,当能有所体悟认可。如果说,在中国的古代佛教文化中,原就有普度众生拯救灵魂的传统,那么,在当代作家中,何士光或可算是倡导佛教文化的第一人了。当然,何士光的这一探索与倡导,究竟是走火入魔,还是拓展宗教文化,终究还要由历史来作结论。
是的,古往今来,文人学士中主张离经叛道者甚多,而真正皈依佛道,走火入魔者,或许就鲜为少见了。作为年近七旬的老作家,何士光近几年来所作所为,却大有遁入佛法禅宗之趋势。这不能不引人注目,并给以探究的兴趣。由此可见,《今生》这一新作的主要特点或许就在于沿着何士光的小说笔法与《如是我闻》的读经随笔,将两者粘合在一起,将文学笔法人生哲理融入谈经说佛、传经布道之中,甚或可说,以道佛之说来阐释寻常生活现象,并注入到社会观念里。力图将宗教文化贯注到散文创作中去,正是近几年来何士光的文学追求与创作特色。
近几年来,正有些作家在多年创作虚构体小说之后,不时地将笔力转移到非虚构体的长篇纪实散文创作中来。在我视线之内的,就有阎连科与他的《我与父辈》,贾平凹与他的《定西笔记》,还有南帆与他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林那北和她的《过台北》,现在又有何士光的《今生》。如果说,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在真实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背景上,对父母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家庭命运的叙述与书写之中,贾平凹的《定西笔记》的落笔点,在于记录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底层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情绪,那么,何士光的《今生》的题旨则在于,以一个文化老人的目光和灵智,去探索一部分文化长者的心灵深处的隐秘,尤其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去解析自己毕生的精神困惑。或者说,力图将自己今生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与近乎走火入魔般的宗教文化的融汇结合处,寻求超凡脱俗的精神出路。
也许,限于一般读者的生活经历,限于我的阅读体验,一时间,我仍尚不能完全读懂作者的内心体验,也不能领悟其中的全部内涵,尤其是其中关于谈经说佛部分文字的玄机、妙方,但我以为,若以长远的宗教文化处着眼,籍以时日,也许这种探索自会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毕竟,当今人类在创造、追求和享受丰澹的物质生活而忽略、轻慢精神困窘之际,有人致力于精神方面的探索,当是不乏益处的。封建迷信自不足信,宗教文化却是值得探究的。虽然,作者在《今生》追忆、审思的是今生今世,而在讲经说佛中,着力探究的,却是人和灵魂依归和来生来世。
在经历了人生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之后,作者在《今生》中写道:“一切都已经改变了;但是你在这街市之间行走着,心思又还是会渺茫起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已经改变了的日子,又并没有什么改变”。你看这街道两旁,不管是布满大字报专栏,或者布满广告灯箱,又有什么不一样?“是的,在一个灵智长者的眼中,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如同转瞬即逝的变化,原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确是灵智长者的发自内心的心灵体验,也是谈经说佛者对生活真谛的领悟。在士光笔下,这番体验,这番领悟,竟是这般晓畅,又这么深奥。
这情形,恰似作品所写的“我”与那位邻里姑娘的几次人生遭际一样。从邂逅相遇擦肩而过,到机缘巧合的再次偶然相逢,直到终老人生,真是隐隐约约,若接若离,充满了变数与机遇,又仿佛是前生注定一般,让人不由地发生如此这般的慨叹:生活就像是变幻不定的万花筒,又像是前生命定一般,陷入一种不可捉摸无可猜度的境地。经过这么几回深度迷惘之后,好像你便只能到佛法道义中去寻求答案了。当然,因文学语言来解读佛法道义,毕竟要比品味咀嚼生活要困难得多。由此何士光的灵魂探险,是自讨苦吃,恐怕也不为过。
读着年近七旬的士光在《今生》一文中,对今生今世的追忆与审思,对来生来世的宗教参悟,还有他那从容不迫忧伤缓慢的叙事语调,不由地便令我想起20多年前与他的交往,以及与他的文字联络。捡读他在1986年给我的两封应约稿件的信函,再次目睹着他那谦和认真的语态,及娟秀工整的字体,一般倍感亲切和怀旧之情,便顿时泛上心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何士光以一个文学新星带着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从西南边陲冉冉上升之时,我即以《钟山》编辑的身份关注着他的创作,随后读了他的短篇新作《远行》,我即以评论工作者的眼光反复打量这位文学新人,并着手撰写这位作家的作品评论,这就是80年代中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一篇论文《时代性·人性·个性》(何士光小说纵横谈)。紧接着,我与士光,士光与《钟山》这才有了书信往来与见面的机会。
1987年,经过多年的交往,士光终于在《钟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作品《踪迹》。其后,2001年又发表了另一篇散文。再后,他有机会来宁,我曾陪同他游览过南京的秀丽风光,度过欢畅的美好时光。大约就在此前后,他还寄赠二本书《烦恼与菩提》与《如是我闻》(走火入魔启示录)。可惜,我的佛缘甚浅,加之世事繁杂,心境纷乱,终于未能细读下去。每每翻检旧书,见到何士光的题辞,总觉得有负于士光的好意了。而士光也曾两次致信于我,表达他未能给《钟山》寄小说的歉意。在他1986年12月12日来信中曾真诚地写道:“在方今人们对刊物日见冷淡的时候,《钟山》是蒸蒸日上的,以至把新的一期接到手里,都似乎也许着什么希望,让人有些兴奋。……您说的很对,‘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人们似乎都在重新面对一次文学,然后拿定主意。……总之,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努力好了,争取完成任务,并再与你联系。”
依我之见,我以为,士光确实是很想为《钟山》写篇力作的,但最终还是未能兑现夙愿。其中的缘由,或许是因为继《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和《远行》连获三次全国大奖之后,他一时实在拿不出精品力作供《钟山》发表;或许是因为其后,随着世事和心境的转型,他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宗教文化的研究上去了。应当说,对于一个成熟作家来说,这种转移远非一般意义的位移与求变,而近乎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蜕变与新生,是涉及文学观与人生观的一次重大改变。
对于发生在士光身上的这种蜕变与新生,我们固不能简单地用宣传宗教迷信、走火入魔之类的词汇来妄加褒贬,但对士光的创作,究竟是祸是福,一时间只恐我也无法说得清爽。或许这一切已不仅是士光对自己今生今世的思考与概括,也是对当今社会生活中诸种目迷五色的不良现象的一种宗教式的解读与领悟,一种尝试与探索,也未尝不可。如此看来,这种尝试与探索早在《如是我闻》中已见端倪,而今所写的《今生》只不过是何士光创作发生的重大蜕变的标志而已。在世事纷繁价值迷乱的现实影响下,士光终于从纯文学创作转入了宗教文化的写作。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读者,抑或是曾经的责编,我真不知说什么是好。
仿佛就在一晃之间,与士光分别相隔竟有20多年的时光了。尽管如此,我依旧相信,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之间虽然关山重重,相隔几千里之遥,但我仍然挂牵着这位远方的作家朋友。我愿在此遥祝这位小我两岁的作家在未来的创作中,能将文学与宗教融会贯通起来,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景观与精神境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