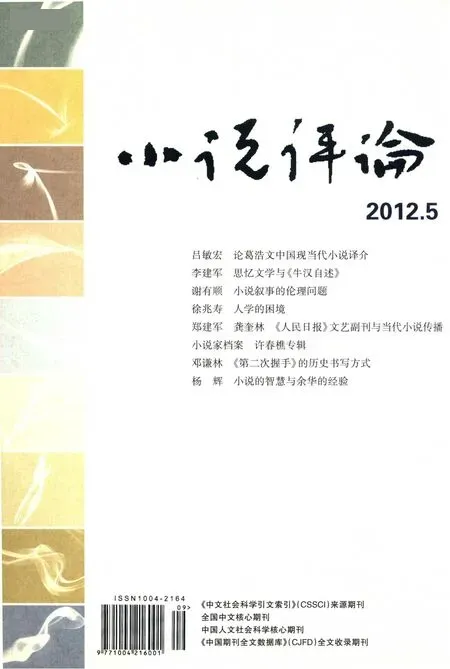论《向延安》及海飞的小说创作
2012-12-17郑翔
郑翔
2011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的长篇小说《向延安》是海飞的新作,这是一部向建党90周年的献礼之作,可纳入红色叙事的范畴,所以从题材上来看,这是海飞对以往小说创作的一次“越位”。那么,这一“越位”和海飞以往的创作之间是否仍存在某些可以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涵?与传统的红色叙事、新历史小说相比,《向延安》又是否具有某种属于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和叙事策略?如果有,那么,它是否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70后”作家对于社会、人生、历史以及文学的独特理解?
本文试图以海飞以往的创作和传统红色叙事、新历史小说为参照,对《向延安》的文化内涵、叙事策略作一个扼要的分析和评论,并通过它来折射“70后”作家创作的某些独特性和文学史意义。
一、悲凉中的温暖
纵观海飞以往的小说,我以为,其最为核心并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涵是:必须在这个充满悲凉的人世间发掘人性的温暖,虽然这种温暖并不能改变人生的悲凉本质——因为这是一种宿命,但它却能滋润普通百姓孤独的灵魂,支撑他们艰难的人生。海飞是一个凭经验写作的作家,这种对悲凉人生中的温暖的发现,应该来源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普通百姓生存状态及其坚韧的、质朴动人的灵魂的细致观察,来源于他对这块土地上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深入挖掘,而且,在发现的过程中,还包含着海飞对于人性,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审视,同时也表现了海飞对于人性善的理想主义情怀。
在海飞的小说中,温暖的人性总是绽放在阴冷的背景上,无论是在农村、城镇还是在城市。海飞笔下农村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这里有飞扬跋扈的村干部,有恃强凌弱的地痞,有因贫穷、嫉妒、愚昧而时常磨擦、争斗的普通百姓,有大量习惯于伸长脖子看的“看客”,有对权力与金钱的普遍迷信以及由此诱发的人性之恶。这样的环境在《温暖的南山》(后改为长篇《花满朵》)、《到处都是骨头》、《看你往那儿跑》、等小说中被反复书写;而《金丝绒》、《医院》、《自己》、《蝴蝶》等小说中的城镇生活,也是由诸多的不如意和阴暗纠结起来的;城市的生存环境甚至更加恶劣,《城里的月光把我照亮》和《我叫陈美丽》中的打工妹都必须把身体、尊严和生存一起打包,即便是杭州城的原住民国芬(《像老子一样活着》),也必须面对生存和尊严的压力。而且,在海飞几乎所有的小说中,主人公除了必须面对生存中有迹可寻的现实的艰难和痛苦之外,还经常要忍受无迹可寻的命运降临给他们的人生错位或灾祸,以及精神上无所依恃的疲惫与孤独。
海飞对人物生存环境的这种处理,包含着海飞对二三十年来我们的时代、社会、文化与人性的阴暗面的深刻体认,同时也包含着海飞对人(尤其是底层人)的命运的某种感想。从空间上来看,海飞的小说概括了农村、城镇、城市三级行政区划,从时间上来看,海飞的小说覆盖了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个别作品还把笔触延伸到新时期以前),所以可以说,新时期三十年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丑恶、阴暗与荒诞面,在海飞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但海飞的小说又非纯粹的写实,因为通过对现实与人生的阴暗面的描述,海飞也试图表示他对人生的某些感想,那就是人生的宿命感。无论你生活在何时何地,你所遭遇的都必然是如唐小丫(《医院》)所说的“阴差阳错的人生”,所以,在海飞的很多小说里,饱经磨难的主人公终于都会像李小布(《自己》)那样认识到“这人生本来就该有悲凉的”,从而使人生带上了宿命的色彩。这种处理当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现实批判力量,但也使小说对于丑恶、阴暗与荒诞的反复书写获得了一定的隐喻性,使小说的内蕴更加丰满。
描写人生的悲凉当然不是海飞的目的,在悲凉的背景上反衬普通百姓坚韧、质朴的灵魂,展示人性、人情最深处的温暖光华,才是海飞“乐此不疲”的母题,也是海飞小说中最打动人的部分。海飞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无例外地都遭受了生活的艰辛与命运的磨难,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因此而损害别人,他们总是选择默默的忍受与承担,且仍能表现出对他人的无私、宽容与友爱——这真是人性的至善至美的体现。《城里的月光把我照亮》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芬芳到城里打工,生存极为艰难,她却自愿承担起照顾受了工伤的前男友和一个弃婴的责任,为此不惜重回发廊,到街头卖唱,甚至为了弃婴的病而入室偷窃,当她费尽心力找到了孩子的母亲时,却发现她是一个无力领回孩子的学生,最后芬芳只好将孩子送给一位好心人(因为她已患了不治之症),在一个充满月光的晚上回到了故乡(她长大的儿童福利院),在洒满落叶的故乡的土地上静静地死去——一颗极度卑微却至善至美的灵魂曾经在这里生长,现在回到了它该安息的地方。这篇小说还代表了海飞小说的另一个特点:生活、生命的艰辛与疲惫来自方方面面,但阴暗与悲凉的生命旁边,始终存在着光明和温暖(虽然往往也弱如萤火),它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宽容与友爱。发廊里的小姐妹们的重新接纳,男友牛娃曾给予过的体贴和照顾,医院护士长的温和态度,中年男人对她偷钱行为的宽容和支助,市容监察对她乱贴寻母启示的网开一面,都是芬芳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而儿童福利院的黄阿姨则是照耀芬芳的温暖的光源。
海飞对现存世界的运行模式和价值规范是持悲观和怀疑态度的,尤其是对“城市文明”的扩张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他始终坚信,人性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宽容与友爱是永存的,它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底层百姓心灵的最深处,在历经磨难之后它将显现,在看破了人生,看破了尘世之后,它将得到提炼和升华。海飞的很多小说,写的就是这个过程。《到处都是骨头》是表现良心战胜邪恶的典型,《为好人李木瓜送行》是一个真诚、无私战胜权力的温暖故事,类似的还有《城里的月光把我照亮》、《遍地姻缘》、《金丝绒》、《医院》、《蝴蝶》等等。《金丝绒》中的唐丽最后竟能和情敌崔曼莉住在了一起,帮助历经磨难的后者一起照顾一个由国外带回来的小黑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女性)最终都能看透人生悲凉的本质,并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可怜人”。既然如此,那么彼此间的争斗和煎熬还有必要吗?于是,宽容与友爱就升华为一种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人性就会散发出金子般纯洁的光华。《医院》对饱经磨难后的唐小丫是这么描写的:“唐小丫后来出现在病房,她像一枚亲切而温暖的金子一样,替病人料理着一切。”人生的底色是黑夜,所以应该有月光,虽然它不能颠覆黑夜的底色,却足以照亮人类的灵魂,我以为这就是海飞反复书写温暖的目的和意义。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以为,《向延安》的潜在主题仍然是海飞以往小说的延续:展示人物“阴差阳错的人生”和“悲凉的”命运并从中挖掘人世间的温暖。只是它把展示人物命运的背景放到了更为遥远的战争年代,这是海飞在小说题材和认识上的一个突破。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战争无疑是最为纷乱、阴暗和难以把握的事件,也是展示人物“阴差阳错的人生”的最好舞台,有如钱钟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小说主人公向金喜一心想当厨师,结果却身不由己地参加了地下工作,他一心向往延安,结果却怎么也没去成,他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传递了那么多重要情报,最终却因失去了上线而无法得到证明,这岂不正是“阴差阳错的人生”和“悲凉的”命运的更充分的演绎?而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人生和命运,基本也是如此。
从“温暖”的角度来看,向金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不断地寻找并力图给予他人温暖的过程,仍是《向延安》中最为感人的部分。和海飞之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向金喜的一生都被纷乱、阴暗和孤独所包围。这个本来家里开着药店,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大群亲人和同学中间的三少爷,从小说开头就开始陷入了灾难与孤独。战争开始了,父亲死了,家空了,同学散了,他也因热衷于做厨师而被大家疏远。于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上海,我们看到向金喜一次次骑车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一次次站在已人去楼空的罗家英家的门前向里眺望,一次次在内心等待延安发给他的通知,一次次独自登上三楼的屋顶用望远镜向远方瞭望……但这一切都无法排遣战争带给他的内心的孤独,相反,他还必须不停地面对旁人的误会和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去的悲凉。寻找一份能够依恃的温暖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对曾经的邻居日本特务秋田一家的感情,和假扮妻子的表嫂袁春梅之间的感情,都异常珍惜。但是,缺乏温暖并不意味着就不能给予温暖,这正是海飞对于人性、人情的独特理解。寻找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望和空虚,但给予却必定可以获得对方温暖的回报,这也是足以抚慰人心的。所以在《向延安》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可怜人”之间的相互协助和关爱。最典型的是向金喜对二哥向金水的相好凤仙的照顾。一开始,向金喜对凤仙并无好感,但当向金水被除奸队除掉,凤仙被卖到了妓院之后,他却毫不犹豫地赎出了凤仙,并安排她开了一家面馆。那么为什么要赎凤仙呢?“我要替我哥赎凤仙”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是他对袁春梅说过的另一句话——“她很苦的”。这是一句体现海飞小说的核心精神的话语,可称之为“海飞式的温暖”。“海飞式的温暖”不但要照顾被照顾者的生活,还要照顾被照顾者的心灵,于是向金喜不但安排凤仙开了面馆,还一大早就起来去做面馆的第一个顾客。类似的细节遍布于海飞的所有小说,是构成其小说细腻、动人品质的重要因素。
而且温暖是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的。小说中的德国人饶神父,在战乱中竭尽全力照顾中国难民之时,自己的亲人也在国内遭遇了纳粹的杀戮,即便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特务秋田,他一家人的命运又何尝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呢,所以他们同样也是“可怜人”。不幸是向金喜与他们之间产生情感上的亲近的重要原因,而只有在类似于战争这样的灾难面前,整个人类的共同宿命和温暖主题才能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现。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向延安》首先是一部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以及地下工作者对于革命的卓绝贡献的小说,但是,它的更深层却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展示个体及人类的悲凉命运,寻找人性、人情之温暖的小说。其实,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始终有着自己的某种坚持的作家来说,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这种坚持,是很困难的,不过,对于海飞来说,由于选题的改变,《向延安》把他之前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底层百姓的人生、命运以及人性、人情的体悟,扩展到了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人类整体命运的审视和关怀,可以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对“温暖”主题的书写在新世纪的文坛可能是一个文学现象。根据近些年的阅读和了解,我发现,新世纪以来,不单文学期刊上有大量以“温暖”为主题的作品,文学评论也一直以比较高的密度关注着这类作品,单从《心灵深处的温暖》、《发掘人世间的爱与善》、《以悲悯情怀观照人生》、《用诗意的目光温暖世界》、《人道主义情怀映照下的苦难命运展示》等题目上就可见一斑。那么“温暖”主题为什么会在新世纪受到如此普遍的关注呢?谢有顺评论铁凝小说的一段话恰好从作家和评论家两方面解释了这一现象:“我特别看重她对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视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因为在此之前,我不知还有哪一个有现代意识的年轻作家能如此执着地去发现人性的善,积攒生活的希望,并以此来对抗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丑陋和不安。”①当然,每个作家用以对“抗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丑陋和不安”的现实和文化资源肯定会有不同,海飞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他所生活的民间的仁爱,其中并含着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海飞是向后看的,过往的乡村文明中那些最美好、最温暖的部分,都是海飞所念念不忘的。有评论家说:“痛惜与爱怜、温暖与爱意,在迟子建那里差不多长成一种‘信仰’了”②。在海飞这里也是一样,而这种对于温暖(善、美、爱)的理想主义情怀,正是文学存在的重要理由,也是海飞小说存在的重要价值依据。
二、在“红色叙事”中还原日常人生
《向延安》是一部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作品,它显在的故事脉络和主题确实都属于红色叙事,但与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传统红色叙事和新历史小说相比,《向延安》在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价值观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因为在这篇小说中,日常人生已成为其历史叙述的真正中心和重点。这不但是新世纪以来日常化写作在历史领域的一个延伸,也是“70后”作家表达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和文学的独特理解的一个叙事策略,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同样以历史为叙述对象,《向延安》与传统红色叙事、新历史小说的话语样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红色叙事是给革命历史作合政治目的论的意识形态解说,在这里,“社会历史全部的丰富性往往被抽象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形式出现于历史小说之中”③。其叙事的“时间模型”是“集体时间”,是革命进化论、政治历史阶段论,所有的革命叙事在其结束之时,必然呈现为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主人公成长的完成、光明与美好未来的最终定局④。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是对传统红色叙事的历史观的颠覆,在其中,历史的合目的性和必然性被打破,社会历史开始呈现出世俗化、零碎化、日常化的趋向。在叙事的“时间模型”上,“古典叙事中永恒与循环的理念、人本主义与生命感伤主义的时间尺度”,即“个体生命时间”,得到了复活⑤。但是,由于过度放大了社会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新历史小说最后在放逐了历史的确定性的同时,也放逐了历史本身。
《向延安》的历史观与前两者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其话语样式和“时间模型”都存在内在的双线对立结构。从显在的也就是红色革命的层面来看,《向延安》的话语样式呈现的是与传统红色叙事相一致的合目的论的形态,采用的是“集体时间”:随着历史的推进,日本人被打败了,国民党被打败了,革命按部就班地走向了胜利。但是,从小说人物的日常人生的层面来看,《向延安》走的又是略近于新历史小说的路子,因为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主人公成长的完成、光明与美好未来的最终定局”没有实现。历史的前进和个人命运的停滞形成了双线对立。比如向金喜,在参加革命前,他是厨师,在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之后,他仍是厨师,新的生活并没有开始。而且,在小说中有一个被叙述者反复强调的细节,即向金喜子承父业不断地登上三楼楼顶用望远镜远眺,这实际上正是一个时间循环论的隐喻。所以,“古典叙事中永恒与循环的理念、人本主义与生命感伤主义的时间尺度”同样在海飞的《向延安》中复活了,所不同的是,《向延安》并没有放逐历史,而是试图从两个层面同时抓住历史。
由于历史观的不同,《向延安》的价值观也与传统红色叙事和新历史小说有别。“红色叙事类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并以“革命为意义中心来组织全部的生活”,“只有统领到革命的旗帜下生活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意义”,“革命不仅在重组着个体的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对个体从精神到肉体的完全征用”⑥。在这种二元对立一元论价值观主宰的话语样式中,历史的本体真实将不可避免地被遮蔽。新历史小说的出现就是试图解构传统红色叙事的价值观,恢复被其遮蔽的历史的本体真实,所以,“它大胆突入政治目的论历史观形成的某些‘遮蔽’,将笔触楔入了‘正史’之外的‘野史’题材之中”,“突破旧有的政治目的论价值观,在个体生命、民间生活、传统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多元的价值关怀”⑦。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由于对历史的先文本性的认识,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以相对主义阐释、解构历史的狂欢之中,于是,随着历史的确定性和纵向维度的消失,新历史小说在带给读者“个体和普遍的共同悲剧”的同时,迎来了循环论迷雾中的价值虚无,而个体也终于蜕化为阐释虚无的手段。
《向延安》的价值观同样存在双线对立的结构。称《向延安》为红色叙事,除了它把革命历史当作自己的叙述对象之外,还因为在显在层面上,它没有否定历史前进的意义,也没有取消革命组织社会生活的意义,而且总的看来,在《向延安》中,个人的情感、命运也都是服从于革命这一集体意义中心的。比如武三春起先是不想把表弟向金喜拖进来做地下工作的,因为他不希望向金喜也和姨父一样死于日本人之手,但最后他还是服从了革命的要求;向金喜并不喜欢地下工作,但他觉得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不能不加入;而且,无论在小说的开头还是叙述行进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群青年一起谈论延安的热烈场面和向金喜向往去延安的内容,都表明,革命或它的代名词“延安”是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合理性的。但这只是一条线,其实单从谈论延安的场面来看,只要稍微留意就可发现,除了用“热烈”等词语简单地形容一下谈论的场面,外加“宝塔”、“延河”、“窑洞”等几个有限的地标性词汇之外,小说从未叙述有关延安的具体谈论内容,所以也一直没有解释延安为什么值得青年们向往,为什么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合理性。相反,小说里倒是经常有这样的话:“金喜认为,延安就是罗家英的代名词”,“延安在金喜的脑海里,只是一个十分向往的图案”。所以,即便到了最后,延安、革命对于向金喜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遥远而模糊的对象,对他来说犹如“一个梦”,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向金喜正曾对恋人罗家英说:“家英,延安太远了,我们都是养家糊口过安分守己的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他内心里遵循的人生目标就是安稳的日常人生,和革命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所以,小说对革命、延安的价值合理性的设定实际上是先验的,革命历史实际上只是《向延安》的一个叙事背景,是它用来展示普通人日常人生的一个舞台,是一种叙事策略。
所以,《向延安》虽无新历史小说那种颠覆革命价值中心的主观意图,但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普通人的日常伦理、情感才是小说真正的价值元点。从“个体的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的角度来看,《向延安》中个体的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并未如传统红色叙事中那样的被革命所重组。比如,虽然在情节的发展中,做了汉奸的向金水杀了表弟武三春,后来军统除奸队的姐夫国良又除去了向金水,看来似乎是立场、理性主宰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但在向金喜心中,这些事情都是违背他的价值标准的,所以一向懦弱的他才会暴怒地责问向金水:共产党多了,你为什么偏偏要杀他?同样,虽然认可国良杀死金水是一次“正义的锄奸”,他心里也“总是放不下”。显然,是否符合人的日常生活伦理或者说自然的人性、人情,才是向金喜心中真正的价值标准,它是可以超越政党、阶级、甚至国界的,他和日本特务秋田一家的感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两者的对比中,革命伦理违背自然人性的一面倒是显示了出来。日常的自然也就是世俗的,所以向金喜觉得,就国良挺拔的男人之感和才干而言,姐姐向金美的离开国良去延安实在是不明智的。而对日常、世俗伦理价值的认定,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民间、传统价值系统的认定,这与新历史小说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从革命与个体的关系方面来看,《向延安》也与传统红色叙事中革命“对个体从精神到肉体的完全征用”很不相同。在《向延安》中,向金喜的家人、朋友、同学有着各不相同的价值立场,但小说对此并未作过多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信仰固然是一种选择,日常生存未必不可以成为另一种选择。小说对主人公身份的设置则集中体现了海飞对于革命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向金喜喜欢做饭,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好厨师,在他看来,只要能做好饭,他的人生价值就能得到实现,所以他说,“乱不乱世,用不用武,都和我关系不大”,所以他说他去延安,仍是想给那里的人们做饭。这里其实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乱世、用武或者说革命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都只是偶然事件,而吃饭、生活才是人类更根本也更恒久的事情。所以向金喜始终没有放弃厨师这一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事体”。而对于他的这一选择,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他缺乏血气,但谁也没有强迫他放弃自己的选择,所以,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向金喜都仍是自由的,他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其中也仍包含着自己的意志。在小说中,其他个体的人生选择也是自由的,而且个体的日常生活理想和情感与革命事业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可以多元的。这一切在传统的红色叙事中是不可想象的,这都说明,“红色”并非《向延安》的叙事目的,而革命历史中普通人的日常人生或者说他们的自然情感和人性,才是小说更重要的叙述内容。
当然,在革命历史中还原普通人的日常人生的事一部分新历史小说已经做过,但日常人生在那里主要是作为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而非目的,而像《向延安》这类在革命历史叙述中真正把普通人的日常人生当作叙述重点的小说的出现,主要是新世纪以来日常化写作潮流影响的结果,可以说是日常化写作在革命历史领域的延伸。日常化的革命历史叙事是对传统红色叙事和新历史小说在历史叙事层面的双重反拨,使历史叙事摆脱了理念先行的模式,回归到更加琐碎但也更加真实可信的日常生活状态,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已触摸到了历史本体,但无疑是对过往历史叙事的一次丰富和补充。同时,从创作个体的角度来看,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尊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创作个体对自身而非某种理念的尊重,表现了个体要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参与历史、阐释历史的欲望。而这也是70后作家试图争取历史话语权的一种表现。
但《向延安》并不止于对革命历史的日常还原,对被还原的日常人生的荒诞感的揭示才是其与海飞之前小说一脉相承的思想内涵。如果从更长的历史常态的角度来看,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也是增加人类生存的荒诞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向延安》中,人物无不因为战争的到来而增加了人生、命运的动荡感,对向金喜来说尤其如此。参加地下工作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命运的错位,他所一直向往的延安对他来说竟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参加革命的结果对他而言几乎是一无所有。对个体与他者(包括革命)之间关系的反思,以及对个体命运的虚无感、荒诞感反复揣摩,是70后作家创作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正如贺绍俊所说:“荒诞感可以说是时代留给70年代出生作家的印记。”⑧
以个体的日常经验来阐释当下生活或还原历史并从中揭示个体生存和命运的荒诞感,应该是70后作家对当代文学的一种贡献,但与西方现代派和中国先锋文学激进的精英姿态和强烈的批判意识所不同的是,70后作家在感受和叙述个体生存和命运的荒诞感时,显示的是一种比之前者更为平和的精神状态。不过,同样是70后作家的日常化叙事,他们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也有差异,有的选择退回自身,叙述个体的日常烦恼和内心荒凉;有的则采取向普通百姓的审美喜好靠近,在与官方文化、大众文化的合谋中,加入一点精英文化的内涵,以一种调和的姿态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海飞的《向延安》显然属于后者,他也从不讳言自己的这一叙事立场。我以为,这种日常化、平民化、市场化的叙事立场对日益边缘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必要,但也必须以丧失文学的深邃性、超越性和经典性为代价,所以几乎也与“如何通过小说的本体话语来重建人文价值”等问题关系不大。
注释:
①谢有顺:《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关于铁凝小说的话语伦理》,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②何平:《重提作为“风俗史”的小说——对迟子建小说的抽样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4期。
③舒也:《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
④⑤张清华:《时间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文艺研究,2006年第7期。
⑥郭剑敏:《当代红色叙事作品中的中国革命历史形象》,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3期。
⑦舒也:《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
⑧贺绍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山花,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