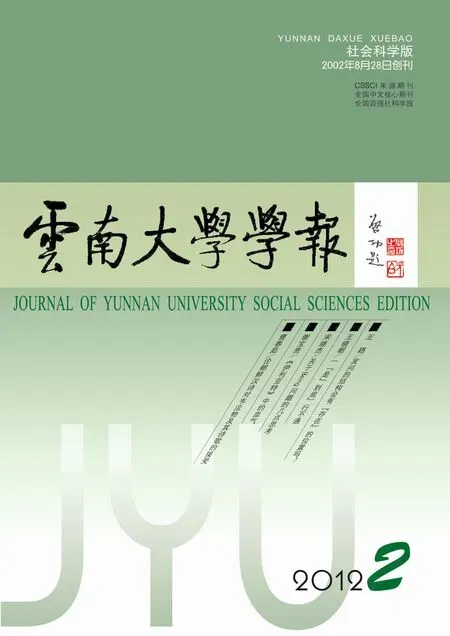亲亲与尊尊:先秦儒家对父母服三年之丧礼意解读的再检讨
2012-12-08郭晓东
郭晓东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制度建构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丧服,而其核心则在于对父母的三年之丧。然而,正是三年之丧的问题,在后世却令人聚讼不已,莫衷一是:作为制度,三年之丧起源于何时?作为礼意的解读,儒家何以要主张三年之丧?对前一个问题,《礼记·三年问》称“未有知其所由来”,虽然时贤亦有颇多的讨论,但至今仍无定论。[1](P22~52)至于后一个问题,先儒之说则屡见于经传,似乎已不须辞费。《礼记·大传》云“服术有六”,而首推“亲亲”与“尊尊”。崔述以为:“《丧服》一篇,两言足以蔽之,曰尊尊、亲亲而已。”(《五服异同考汇·五服余论》)凌廷堪亦称:“亲亲、尊尊二者,以为之经也,其下四者,以为之纬也。”(《封建尊尊服制考》)则圣人为父母定三年之丧,制礼之义不外“亲亲”与“尊尊”。不过,细绎先儒之说,相互之间则似乎颇有抵牾之处。曾亦曾经指出,关于三年之丧在先儒那里就有两种解释,“或因亲亲而三年,或因尊尊而三年”。[2](P111)即便如此,无论是因“亲亲”还是因“尊尊”,其具体的内涵也仍然不是非常的明确。本文即是从先秦若干讨论三年之丧的文本出发,试图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梳。
一、从《仪礼·丧服》经传看“尊尊”作为三年之丧的主导性原则
关于中国古代的丧服制度,最经典的文本莫过于《仪礼·丧服》及相传子夏所作的《丧服传》。按《丧服》,为父服斩衰三年,所以然者,《丧服传》曰:
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
而对母亲之服则相对复杂,若父在,则为母服齐衰一年,《丧服传》曰:
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
而父没,则可为母服齐衰三年,郑玄注曰:
尊得伸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先儒将父母之丧泛称为三年之丧,但父母之丧并不是对等的,为父服斩衰,为母服齐衰,是因为“父至尊”。而父亲在世时,为母只服齐衰一年,是为父之至尊所屈,而不敢“伸其私尊”,则母亦可尊,只不过是较之父之“至尊”而为“私尊”而已。*所谓母为“私尊”者,贾公彦说:“父非直于子为至尊,妻于夫亦至尊,母则于子为尊,夫不尊之,直据子而言,故言私尊也。”曾亦则以为,“母惟尊于内,故为私尊。”[2](P125)只有在父已没的情况下,才可为母亲伸其“私尊”而得服齐衰三年。可以说,按《丧服传》的理解,完全是从“尊尊”的立场来解读为父母的三年之服。
然而,父何以为至尊?按《丧服》经,斩衰有八,“父,诸侯为天子,君,父为长子,为人后者,妻为夫,妾为君,女子子在室为父。”在笔者看来,对其中任何一种的理解,都应当从一个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这八种斩衰服看起来似乎表现的是诸多层次的关系,但实质上它们还是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相连接,那就是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凌廷堪于《封建尊尊服制考》对此论之甚详,其称“所谓尊尊者,皆封建之服”,而“尊尊”之所尊者,在于“尊承重者”,即其“所受于大宗之宗庙、土地、爵位、人民之重也”,可谓是卓有见识。*曾亦以为,“凌廷堪尊尊之义尽出乎封建之制,实未必然”,又认为丧服所言八种斩衰服中,诸侯为天子,大夫为君,父为长子,为人后者,固与封建有关,但其他四种,如子为父,妻为夫等,不过是后世之“子道”与“妇道”。[2](P94)此可备一说。然将子为父、妻为夫等纳入宗法体系来解释,恐怕更为合理一些。子为父,女子子在室为父,则因父为宗庙之主而为宗统之代表者。妻为夫服斩,妾为其君服斩,恐怕也不仅仅是“妇道”的问题,夫对妻妾之“至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可以认为是由其宗统地位延伸而来,或者说,是以父系为本的宗族伦理体系所决定。从《丧服》“外亲之服皆缌”的规定中亦可看出这一点。王国维亦认为服术当与周人的宗法制度有关,其于《殷周制度论》中认为,殷周之际在制度层面最大的变化在于立子立嫡之制,“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3](P291)父亲之所以为“至尊”,完全是由其在宗法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即其作为宗子而具有大宗的地位。*曾亦以为,宗法制的实质在于“以兄统弟”,“父子关系中的尊尊之义与宗法制度无关,其精神殆与母系制下尊母之义无二。然宗法制度自有尊尊之义,只不过不是在父子之间建立尊卑关系,此为后世‘弟道’之所出也。”[2](P94)按:在兄弟行辈,宗法制确实表现为以嫡长子统众子与庶子,而嫡长子所以尊于众子与庶子,则在于其“正体于上,又仍将所传重”,(《丧服传》)即其当先祖之正体,又将代父为宗庙主,故长子得以尊服服之。由此推之,父作为现任宗庙之主,理所当然具有“至尊”的地位。其实,服斩衰三年之父亲,有时未必就是本生之父,《齐衰不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丧服传》曰:
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大宗者,尊之统也。
由此亦可看出,“尊尊”之原则,完全是由宗法所决定,而不是由血缘所决定。*张寿安先生指出:“宗法关系虽以血缘为基础,但宗法关系并不等于血缘关系。正确地说,宗法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此说是也。[4](P90)如果仅依据血亲之关系,对生父无论如何当服斩衰;但是,当一个庶子被立为大宗之后时,他的角色与地位就与原来完全不同,因为他“持重于大宗”,所以,原先建立于血缘之上的父子关系就要为宗法上的父子关系所压降。不仅父子关系如此,即便是母亲之为“私尊”,亦由宗法所决定。作为“私尊”之母,亦未必即是生母,而毋宁是作为父之正室的嫡母。《缌麻三月章》曰:“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丧服传》曰:
何以缌也?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
尽管都是压于父之“至尊”,但嫡母称“私尊”,而庶子为后者于所生母则曰“私亲”。“私尊”与“私亲”这一表述上的区别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嫡母被视为与君一体,故其虽曰“私尊”,但毕竟可以尊服;而妾母则不得体君,故只能称“私亲”,而不得称“私尊”。由此可见,《丧服》经传所规定的为母之服,亦是由宗法所决定的。
总之,从《丧服》与《丧服传》的立场来看,父母之服,完全是以“尊尊”为原则,或者说,是以“尊尊”原则凌驾于“亲亲”之上,并没有后儒所以为的“亲亲”与“尊尊”并重之意,凌廷堪以“封建尊尊服制考”为其书名,即已明显地透露出了这一消息。*按照张寿安的研究,凌氏主张回归到封建制度中去了解丧服的尊尊观念,其用意在于厘清后儒将尊尊之礼意曲解为尊君,即尊尊之旨是“尊承重者”,而非尊后世之帝王,同时建立一种尊尊与亲亲之间的平衡性。[4](P86~143)虽然凌氏在《封建尊尊服制考》中亦自称“《丧服》经传当封建之世,合尊尊、亲亲而制者”,但细绎其书,内在的精神仍在说尊尊,而亲亲者,不过旁涉而已,用意并不在此。在笔者看来,凌氏所以并言尊尊、亲亲者,或是狃于《礼记·大传》和《礼记·丧服四制》诸篇的成说而已。而颇有意思的是,作为凌廷堪的论敌,清儒夏炘在《三纲制服尊尊述义》中认为,“制服之本”不在“亲亲”,而在“尊尊”。我们且不管凌、夏两人论述的用意所在,仅从《丧服》经传的相关文本看,尽管两人的立场迥异,但其以“尊尊”作为丧服原则的结论,还是能得其实际。*张寿安指出,夏炘作《三纲制服尊尊述义》,目的就是要斥凌氏之非,其以为丧服之尊尊就是后世三纲之尊尊。[4](P130~133)就此而论,凌氏用意在于批判当下以尊君为尊尊的误读,而夏氏之用意在于维护以尊君为核心的三纲说,然其对丧服的讨论,却均得出“尊尊”的结论,至少可以认为是与《丧服》经传的论述相一致的。对于夏炘的说法,曾亦亦认为,“考诸周制,则颇得其实。”[2](P114)
二、从《论语》与《三年问》看“亲亲”之为三年之丧的主导性原则
就《丧服》经传而言,“尊尊”是当然的主导性原则,而在《论语》中,我们则可以看到对三年之丧的另外一种解读,即因“亲亲”而三年: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以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也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宰我欲改三年之丧为一年,而孔子只问他“于女安否”,按孔子之说,为人子者之所以要为双亲服三年之丧,是为了心安,或如崔述所说的,是“情之不得已”,*见崔述:《五服异同考汇·五服余论》。其又曰:“礼本乎情,非强人以所不能行者也。若亲初丧而即能饮酒食肉,恬然不以为事,是其心已死矣,强之使必疏食,夫亦何益?故孔子曰:‘女安则为之。’”更何况“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为人子者,岂能不服三年,以见其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可见,孔子完全是从亲情与报恩的角度来看三年之丧的。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贯穿于《丧服》经传的那种“尊尊”原则,而反过来,较之《丧服》经传明确因“尊尊”原则而对父母之丧的丧制作出区分而言,在孔子与宰我的问答中,所谓的三年之丧,父母并没有被加以区别对待,对此,姚际恒指出:
孔子与宰我论三年之丧,并言父母;《中庸》引“子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则为父母之丧,皆三年也。《论语》两言“见齐衰者”,孔子对滕文公言齐衰之服,皆无斩衰之名。则为父母之服,皆齐衰也。不知何时,尊父抑母,别加斩衰于齐衰之上。(《仪礼通论·丧服》)
其又曰:
然考之《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皆以父母并言,则皆三年可知也。且生子劬劳、而三年在怀者,非母乎?父反若因母而带言者,若是者何也?言人情也。(《仪礼通论·丧服》)
在丧服学说史上,姚际恒的这些观点可谓是极端而另类,如称父母之服皆齐衰,又如称父因母而带言者等等,这些观点在主流学界大概都是不会被认同的。但是,孔子以父母并言,这是事实;特别是孔子以三年在怀来论证三年之丧的必要性,则母亲的地位定然不低于父亲,此等推论大概也可以认为言之成理。因此,姚氏以此证明尊父抑母为后起,虽未必就能够成立,但从亲亲之情的角度来论三年之丧,应该说至少是符合孔子的本意的。而若单从亲亲之情来讲,父母之恩爱既同,则子为之服理所当然不该表现出有所区别。反之,若单从《论语》所记载孔子与宰我的对话来看,则孔子对三年之丧的理解完全是以“亲亲”为原则的。
孔子之后,进一步发挥孔子之说,并更加系统地从“亲亲”的角度来论证三年之丧的则有《礼记·三年问》。*《礼记·三年问》全文除了个别字句外,又见于《荀子·礼论》。故学者多以为《三年问》袭自《荀子》,如任铭善先生即以为“为《礼记》者刺取而钞合之”。[5](P81)沈文倬先生则认为是荀子抄录《礼记》。[6](P49)王锷先生详细比勘了两种文本的异同,亦认为《礼论》录自《三年问》。[7](P149~152)我们在此亦从沈、王二先生说。
从人之常情而论,父母之于己,正如《诗·蓼莪》所载:“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因此,为人子者面对此类人事之剧变,那份椎心刺骨之伤痛可想而知。《三年问》说: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就孔子而言,不服三年不足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而就《三年问》来讲,服三年之丧,是因丧亲之创巨痛甚而日久愈迟。二者角度虽异,但孝子对父母之深爱则毫无二致。进而对孝子而言,至亲去世之悲伤,永远难以磨灭,或致终身之痛,故有《系辞传》中所说的:“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而《三年问》则说:“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亲也,至死不穷。”又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驷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然而,人又不能永远生活在悲伤之中,若一昧放任情感的发泄,因毁而灭性,以死而伤生,则又是圣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对于因毁而灭性,《礼记》批评说:“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曲礼上》)孔疏云:“不留身继世,是不慈也。灭性又是违亲生时之意,故云不孝。”故《三年问》以为,先王定以三年之丧期,是“为之立中制节”,使君子小人之情感皆得以节制与调和。*《檀弓》记曾子执亲之丧,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而子思则不以为然,其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丧服四制》亦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这些都是《三年问》中所谓“立中制节”之意。
“立中制节”的提出,与《论语》的说法相比显然多了一层内涵,然而,《三年问》对三年之丧的解读并不仅于此,其又曰:
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则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
这段话最重要的部分当属“至亲以期断”这一原则的提出。关于这一原则的解释,郑玄与孔颖达颇有出入。郑玄以为,文本既言三年之丧之义如此,而这里又言期者,是“为人后者”与“父在为母”者,虽为至亲,而尤以期断之,故“至亲以期断”,是指至亲或有因尊服而受压降,但仍然当断之以期,因此,对郑玄而言,这是针对特殊情况的一种表述。孔颖达则认为“是经义不据为人后及父在为母期”,而只是“明一期可除之节”。对郑、孔两说,当代学者多不取,任铭善先生认为,其意当是“三年之丧推本期服”,[5](P81)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解法,现代学者的理解大多同此。*如王文锦的《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杨天宇的《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均持这一说法。吴承仕先生极其重视“至亲以期断”这一原则,称之为“原则之原则”,认为它是“晚周以前久已盛行的一种礼文与礼意”。[8](P317)然而,对于“至亲以期断”的说法,我们如果假定它在孔子的时代已被普遍确定,那么,当宰我提出“期可以矣”时,孔子似乎不当批评其“不仁”。《三年问》论证“至亲以期断”的理论根据是,“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而这一说法正同于宰我之说,即“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以矣”,然而,孔子径斥之为非,由此可见,“至亲以期断”的说法为后起。*沈文倬先生认为,“至亲以期断”的说法“是战国时期主张短丧者企图修改《丧服经》的理论。三年丧既是由期丧加隆起来,那么,不要加隆就很自然地缩短到了一年”。参见沈文倬著:《汉简〈服传〉考》,载《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173页。
既然“至亲以期断”,而父母之丧又须服三年,于是,《三年问》又提出“加隆”说,即认为为父母服丧三年是“加隆”的结果。曾亦以为,其所以要加隆者,是“取诸尊尊之义”。[2](P113)然而,就《三年问》的文本来看,其论“九月以下”,是“恩不若父母”,是恩之杀,则三年当是恩之隆,故郑玄注说:“言于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而该文最后引述孔子语,则更是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之所以要从期加隆到三年,同样取的是孔子三年在怀之意。*任铭善先生对此说颇不以为然,其以为据《论语》,三年丧本诸三年免于父母之怀,则固无加隆之义。[5](P82)
通过比较《论语·阳货》与《三年问》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贯性,两者都只是讨论父母之丧的问题,且两者都是从亲亲之情来理解三年之丧,是以章景明先生称:“这些都是基于情感、道德、功能而发的理论,最能代表儒家对丧服制度的观念和态度。”[9](P20)而这一观念与态度,“其出发点乃在于‘仁爱’两个字。”[10](P167)在这一意义上讲,有学者认为,《三年问》“当由《论语·阳货》推衍而出”,[11](P152)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在《三年问》那里,由于“立中制节”、“至亲以期断”、“加隆”等诸多观点的提出,使得在孔子那里相对泛义的“亲亲”原则有了许多更为具体的内容。
三、从《丧服小记》、《大传》与《丧服四制》看亲亲、尊尊并重的二元结构
后世论丧服之原则者,多“尊尊”与“亲亲”相提并论,然而,从前面的若干陈述看,对三年之丧的理解,或偏重于“尊尊”,或偏重于“亲亲”,二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事实上,将“尊尊”与“亲亲”作为丧服共同原则而同时被提出的,最早见于《礼记》之《丧服小记》、《大传》与《丧服四制》诸篇。《丧服小记》称:
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而《大传》则直接将“亲亲”与“尊尊”列为服术之首:
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
更重要的是,对“亲亲”与“尊尊”的具体内涵,在这两篇文献中也得到了相当明确的说明与界定。《丧服小记》曰: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郑注曰:
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论的“亲亲”,已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论述与自己亲人的亲亲之情,而是有了一个特定的内涵,它是一个宗法制度框架之中的亲亲关系,故丁鼎认为这样的一个“亲亲”原则与宗法制度相辅相成,并称之为“《仪礼·丧服》制定各级丧服的依据”。[1](P188)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再看《大传》中的说法:
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
又曰: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
宋儒陆佃认为,“亲亲,下所谓自仁率亲是也;尊尊,下所谓自义率祖是也。”(《礼记集说》卷八五)而对于“自仁率亲”一句,郑注曰:“自,犹用也。率,循也。用恩则父母重而祖轻,用义则祖重而父母轻。恩重者为之三年,义重者为之齐衰。”那么,按照这一说法,《大传》中所谓“亲亲”,指的是从恩爱的角度从己一代一代往上推,越往上亲情越淡,此正合《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之意;而所谓“尊尊”,是从义的角度,由祖先一代代往下数,一直至于父亲,越是远的祖先则越是受到尊重。在这一意义上说,正如孔颖达言:“亲亲,谓父母也。尊尊,谓祖及曾祖、高祖也。”也就是说,亲亲的原则,主要针对父而言,而尊尊的原则,则主要针对祖而言。对父而言,因亲亲,故恩重为之三年;对祖而言,虽尊尊,而义断以齐衰。这样,《大传》就以“亲亲”与“尊尊”两个原则奠定了整个宗法观念的基础,*丁鼎以为,“‘亲亲’是宗法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尊尊’是宗法制度的主导性纲领。”[1](P186)而二者之间,又以“亲亲”为出发点,故《大传》又曰:“是故人道亲亲也,言先有恩。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尽管吴澄认为《大传》是“通引《丧服传》之文而推广之”,也有人认为《小记》与《大传》“说明丧服理论而与之完全相应”,[8](P317)但很明显,《丧服小记》和《大传》赋予了许多《丧服》所没有的内容,它们不仅提出了《丧服》经传所不甚着意的“亲亲”原则,同时,它还被列在了“尊尊”的前面,或如孙希旦对《大传》的理解,“尤归重于亲亲”(《礼记集解》),而正是这一点与《丧服》经传中的“亲亲”原则要服从于“尊尊”的主张截然迥异。*也许正是有这样一种截然迥异的分歧,清儒夏炘对《大传》与《小记》相当不以为然,其曰:“然后知《大传》之服术有六,《小记》之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诸说,皆后儒覶缕推测之言,实未得周公制作之本原,孔门传受之要领也。”(《三纲制服尊尊述义》)即便是所谓“尊尊”者,其内涵与《丧服》经传相较而言,亦似乎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此,“尊尊”只是尊祖而言,相对祖而言以父母为轻;而据《丧服》经传,拥有“至尊”地位的并不是祖,而是父。
在《礼记》论丧服诸篇中,同样涉及“亲亲”与“尊尊”两个原则的,还有《丧服四制》,其论曰: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这段话同样是后儒论三年之丧之礼意的经典文本。为父斩衰三年,按《丧服》经传,是因为“父至尊”也;而这里称“恩厚者其服重”,则显然是以“亲亲”原则为基础。然而,对母亲之服,《丧服四制》又曰:
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
也就是说,如果纯粹按照“亲亲”的原则,那么,“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则对母亲理所当然要和父亲一样同服斩。但是,《丧服》经传以父为斩而母为齐,是因为父为至尊,于是,《丧服四制》又取《丧服》经传中的“尊尊”原则,从“家无二尊”的角度,称“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就此而言,《丧服四制》是以“亲亲”与“尊尊”相结合的方式来处理对父母之丧的理解,一方面,所谓“门内之治恩揜义”,“亲亲”的原则高于“尊尊”;但另一方面,正如任铭善先生所说的,“门内之治有恩不能揜义者,父在为母则屈而服期是也。”[5](P101)这也就意味着“亲亲”的原则不是唯一的,在“亲亲”的基础上,仍需要有一种“尊尊”的礼序。很显然,《丧服四制》的这种说法,虽然承袭了《丧服》经传的部分内容,但总体而言,却是对《丧服》经传的重要修正。
除此之外,对《丧服》经传作出修正的还有对“尊尊”的理解。《丧服四制》称“门外之治义断恩”,又曰“资於事父以事君”,则所谓“尊尊”者,又被特指为尊君,郑注即称:“尊尊,谓为天子诸侯也”,郑玄又说:“尊尊,君为首”,后世学者即多据此而以“尊尊”为“尊君”。*“尊尊”演变成“尊君”,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张寿安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作了相当深入的探究。详见张寿安著:《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第二章,《亲亲尊尊二系并列的情理结构》。然而,专从君臣关系论“尊尊”,已与《丧服》经传之说相违,按《丧服》以尊服者八,而“天子”与“君”仅占其二,而其所以尊者,就《丧服》经传而论,恐非其位势所决定,毋宁说是其“受重”所决定,或说是由所谓“宗统与君统的合一”这一宗法结构所决定的。*凌廷堪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君”字的理解。郑玄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而孔疏认为,“士无臣,虽有地,不得君称。”然而,凌氏认为注疏之说与经传相违,其引敖继公之语曰:“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并认为《丧服》尊尊之义全系乎“士有臣”的说法上。这样,正如张寿安先生所解读的:“君不必指天子,也不必指诸侯王,凡是领有土地、人民之管辖权者皆是‘君’。故此,君被视为‘至尊’,并非如后世所言的‘尊帝王’,而应该是‘尊君责’。”[4](P116)不过,“尊君责”之说似乎也不是太到位,毋宁说所尊者是其在宗法体系的礼序地位。而《丧服四制》中既以事君为尊尊,又以“家无二尊”论父在为母服期,则其对“尊尊”之理解,前后之间又显然自相抵牾。*张寿安把这两种“尊尊”分为“家族范畴内的尊尊”与“政治范畴内的尊尊”。[4](P91~92)丁鼎则区分了“宗亲之尊”与“君之尊”,认为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前者“在政治关系上的扩展和延伸”。[1](P190)
四、小结
通过上述简要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对为父母服三年丧之礼意的解读,先秦儒家论丧服诸文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讲,其根本原则不外乎“亲亲”与“尊尊”。就文献而论,我们已经有三种基本的立场,《丧服》经传中显然主“尊尊”说,《论语·阳货》与《礼记·三年问》主“亲亲”说,而《丧服小记》、《大传》与《丧服四制》这些《礼记》中的文献则主尊亲并重说。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于此。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尽管所讨论的都是“亲亲”与“尊尊”,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又颇有出入。就“亲亲”而论,《论语·阳货》中只是从一般的人情意义上讲,认为亲情与报恩是人子服三年之丧的主要依据;《三年问》进一步发挥了《论语》中的这一思想,但诸如“立中制节”、“至亲以期断”与“加隆”等说,使得“亲亲”的原则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在《丧服小记》与《大传》中,“亲亲”作为一个原则被正式提出,但与《论语》和《三年问》所不同的是,这一原则被赋予了相当深厚的宗法色彩,成为了奠定宗法社会的基础。就“尊尊”而论,《丧服》经传之所尊者,主要是在宗法社会中因“受重”而拥有“至尊”或“准至尊”的地位;*我这里所谓的“准至尊”,指《丧服》八种尊服中,除子为父、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妻为夫、妾为君、女子子在室为父六种被《服传》称之为“至尊”之外,父为长子、为人后者两种,传文不以“至尊”称之,但言“以尊服服之”,故称“准至尊”。而同样是以宗法制度为出发点的《丧服小记》与《大传》,其所谓“尊尊”者,则指上治祖祢而言,“尊尊”的对象主要不是父而是祖;至于《丧服四制》,则从“资於事父以事君”的角度来理解“尊尊”,故又被特指为“尊君”。因此,当我们论及“亲亲”与“尊尊”之原则时,恐怕不可一概而论,而当根据其具体的文献背景来厘清其内涵。
那么,面对诸多文献中的纭纭众说,我们又当如何从中取舍呢?或者说,何种论说才是最合乎这套礼制应有的意义呢?事实上,这里最大的困难也许在于对这些文本本身年代的断定,因为事实上至今对它们仍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丁鼎在其《〈仪礼·丧服〉考论》中专门有一章讨论了《丧服》之经、传与记的关系,参见该书第53~107页。按照最正统的说法,《丧服》经是周公所作,或者如今文家的说法,《丧服》经是孔子所订,不管何种说法都意味着《丧服》经代表的是周代的制度,或者至少是周人的遗俗,这一点大概学界都可以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套制度的解读。直接解读《丧服》经的是《丧服传》,相传《丧服传》为子夏所作,或子夏传孔子之教,然而,孔子明显是从“亲亲”之义论三年之丧,作为孔子弟子的子夏何以在《丧服传》中没有体现?*按《礼记·曾子问》中记载了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假如这一记载可信,则孔子曾当面授子夏以亲亲之道。此不能不启人疑问。因此,《丧服传》中的“尊尊”之说,到底是代表着古典之义,还是战国诸儒的新说,亦不能不加以考虑。当然,正统的观点多认为《丧服传》之说最合古义,虽然不合俗情,却正是周尚文的典型表现。曾亦即持这一观点,认为“三年服制重在尊尊之义,不在亲亲之情”。[2](P128)同时,曾亦又认为,孔子说亲亲之道,是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此乃《公羊》家的说法。就理论层面上讲,此或能自圆其说。然而,儒家之学既自孔子而立,则当以孔子的立场来裁定诸礼,并赋予其意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亲亲”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而成为儒家的正统观念,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般被认为是成于战国时期的《礼记》论丧服诸篇基本上一致以“亲亲”为首要原则。当然,从儒家的一般观念出发,孔子主文质彬彬,故于礼则求情义兼尽,是以,如皮锡瑞于《三礼通论》中所说的:“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
[1]丁鼎.《仪礼·丧服》考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曾亦.论丧服制度与中国古代之婚姻、家庭及政治观念[A].洪涛,曾亦,郭晓东.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A].观堂集林[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M].济南:齐鲁书社,1982.
[6]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与《礼仪》书本的撰作[A].宗周礼乐文明考论[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7]王锷.《礼记》成书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吴承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A].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9]章景明.先秦丧服制度考[M].台北:中华书局,1986.
[10]章景明.儒家对丧礼的基本观念及其态度[A].三礼论文集[C].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
[11]邱衍文.中国上古礼制考辨[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