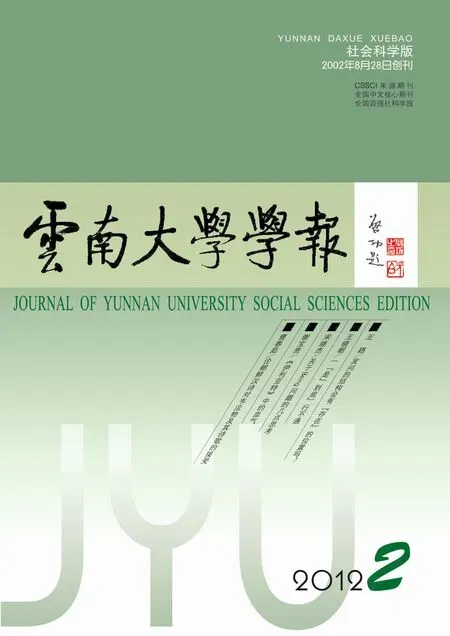“一‘是’到底”行不通
——评王路教授的新著《读不懂的西方哲学》
2012-12-08王晓朝
王晓朝
[浙江大学,杭州 310028]
关于“是”的讨论牵动了众多学者的心,让中国学术界纠结了十几年。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王路教授最近出版了他的新书《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我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他的馈赠,也参加了为这本新书出版而举办的讨论会。
与王路教授以往已经发表的相关论著相比,他的这本新书坚持了他在“是”的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基本论点,而在注重文本研究方面有新的增强。该书选取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西方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的核心段落展开具体分析,指出这些段落中出现的各种西文的being均应译为“是”,而不应译为“存在”,否则就与该哲学家为了证明其一般结论所举的例子不符,并以此证明“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应该以‘是’来翻译being,并且应该把这样的翻译贯彻始终”。[1](引言P4)
王路教授的这本新书作为一个整体所采用的基本论证方法是归纳法。他通过对他所选定的具体文本的分析,把关于“是”的一般理论层面的讨论转化为具体语境(文本)中相关语词、语句、段落的解读,从而在原有对相关语词作“存在”解的译文之外提出了新的理解和新的译文,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以这些文本分析为基础,进而以小见大,王路教授提出了他自己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另一种理解。
然而,这种具体方法运用上的成功,并不能保证王路教授所设定的论证目标的实现。因为他想要证明所有的being都应当译为“是”,如果不将相关的语词理解并翻译为“是”,那就是错误的理解和翻译。可是我们看到,迄今为止,他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但仍是不完全的,因此不能保证他得出的结论是必然的和正确的。这就好比他想要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不可能有黑天鹅或其他颜色的天鹅一样。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柏拉图那里的天鹅是白的,不应当把它看作黑的(不应当译为“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天鹅也是白的,也不应当把它看作黑的。可是这样的举证无论再增添多少,都无法穷尽所有的例证。且不说历史上已经生成的文本汗牛充栋,当今信息化时代新文本的生成更是爆炸式地涌现。所以王路教授想要证明古今往来天下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反过来,王路意见的反对者们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或灰天鹅,王路教授的命题(所有的being都应当理解和翻译为“是”)就已被证伪。
王路教授在该书中使用的基本证明方法是归纳法,想通过个别的例证来获取一般的结论。这与他先前相关论著中对“是”的问题进行一般性理论探究时所使用的方法有异。他在以往著作中非常强调逻辑证明应当“必然地得出”。[2](P237)所以,他的这本新书在“是”的问题的讨论中所取得的实际进展,是指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西方大哲学家的某些重要著作的某些核心段落中的相关语词应当作“是”解,不应当作“存在”解,而在关于“是”的问题的一般性理论的讨论上,他只是重申了他以往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没有取得其他进展。他在书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西方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核心段落的解读是精细的,富有启发性的,但他的解读不是惟一的解读,而是诸种解读之一,其是否正确仍可具体讨论。在此顺便一提,王路教授这本新著的英文标题“How to Understand Western Philosophy”是名不符实的,与他这本新著的内容相符的英文标题应当是“An Understanding to Western Philosophy”,或者“Wang Lu’s Understanding to Western Philosophy”。
包括王路教授本人在内的中外学者的前期研究早已表明,西方文字中的being是一个多义词,它本身除了具有系动词“是”的意思以外,还有“在”、“真”等多种含义。若想证明所有的being都应当理解和翻译为“是”,在我看来最佳途径应当是从源头上、从根本上否认西方文字中的being除了有“是”(系动词)的含义以外还有其他含义,再进而告诉中外学者们,being只能作“是”解,只能翻译成“是”。可惜的是,王路教授在以往相关论著中没有这样做,在这本新书中也没有这样做。我认为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西方文字中的being从源头上就是一个多义词,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今后若这样做的话,会与他本人前期研究的部分成果产生矛盾,因为我们都知道,王路教授本人也是承认希腊文的“是”字的多义性的。
读了王路教授的这本新书,我一方面对他能始终坚持自己在“是”的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主要观点表示钦佩,但另一方面我也实在不明白(读不懂)他为什么要坚持“一‘是’到底”?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摘下“一‘是’到底”的帽子(因为王路教授本人也没能做到“一‘是’到底”或者实际上做不到“一‘是’到底”)?近年来,出于对“是”的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我内心是在期待着他能对自己的这一基本立场有所修正,因此也写过一些论文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过质疑,但他的这本新书中没有对我的这些意见作出回应(尽管他不一定非要这样做)。为能进一步推进相关的讨论,我把这些意见综述如下:
我在《读〈关于“存在”与“是”〉一文的几点意见》(《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中指出: 现代国人已经把“是”主要当作系动词来使用,坚持用“是”来翻译on不一定是上策;译名只是一个表象,任何翻译实质上都是一种再解释;我们可以佐以定义和加注的手段来接近原义,但不一定非要坚持用“是”来翻译on;在译名问题上应当根据不同的语境对同一语词选用不同的译名。
我在《如何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史》(《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0月31日第12版)这篇书评中指出:王路教授的整个思想有三处“软肋”:(1)他的思想以西方学者卡恩对古希腊文“eimi”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和起点,假如卡恩的观点有问题,那么他的思想基础也会发生动摇;(2)他对中西思想文化传统的理解着眼于“异”,而忽略了“同”,他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他的这一看法仅限于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理解,目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西方哲学,但若进入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那么王路教授这一类似斯宾格勒的观点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3)“是”与“真”的问题被他视为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史的主线,而以往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也已力图从别的问题入手来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史的主线,怎样使更多的学者信服他说的这条主线,这是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我在《绕不过去的柏拉图——希腊语动词eimi与柏拉图的型相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卡恩强调eimi有三种基本用法,其中系词用法占核心地位。卡恩虽然高度强调自己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主张西方学者必须用be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来对应翻译希腊语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更没有说过用exist来翻译eimi就是错误的。卡恩同时强调,eimi的哲学用法和含义有一个发展过程,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分析eimi及其各种变化形式和语法结构的含义,以便达到比较正确的理解和翻译。对eimi的语词和句法的逻辑分析虽然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西方本体论的源起与发展,但不是选择译名和理解西方本体论思想的惟一依据。语言分析是哲学思维的前奏,概念反思才是真正的哲学。
我在《用“存在”翻译being的合法性不能剥夺》(《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学术界关于being的争论是在中外学者互参、互动、互释、互译的背景下展开的。用esse的各种变形来对译希腊文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用exsisto来彰显eimi的存在含义,这是拉丁学者对eimi的理解和译名选择,也是延续至今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的理解和译名选择。面对希腊文献,西方学者或是用相当于希腊文动词eimi的英文动词be的各种变化形式来翻译和表达“存在”之意,或是用exist/existence来翻译,面对拉丁文献,他们既用exist/existence来翻译existo,也用exist/existence来翻译拉丁文esse的表存在的含义,总的趋势是用exist越来越多,整个希腊哲学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exist本身也有多种含义,但“存在”之义凸显,它与eimi虽然没有词源关系,但用来翻译eimi的“存在”含义在语义上并无不合之处。拉丁文和各种现代西方语言用exist翻译和表达“存在”观念有其合理性,是西方诸种对eimi的理解和翻译之一,与此相仿,用汉语词汇“在”或“存在”翻译eimi的存在含义同样是合理的。
我在《eimi——卡恩的希腊ontology的语言学导论》(《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王路教授对卡恩研究成果的介绍与卡恩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表述之间有一些差距。王路教授的介绍重点放在那些对他自己的翻译主张(一‘是’到底)有利的方面,而对卡恩研究成果中那些不利于他这种主张的成分着墨较少。卡恩的研究目的是阐明希腊文动词be的日常用法和意义,为解读希腊文动词be的哲学用法奠定了语言基础。鉴于on在希腊哲学本体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我们可以把eimi称为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文化基因,但它还不是哲学范畴本身。如果我们在注意eimi的系词用法的同时,又用eimi的系词用法遮蔽它的存在用法,那么这样的译文离开文本的原意不是近了,而是远了。在中文“是”字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语境下都已经系词化了的今天,“是”与希腊文eimi的系词用法最接近,但与希腊文eimi的存在用法相距甚远,远远不如“在”或“存在”更能贴近希腊文eimi的存在用法。
我在《西方哲学基因eimi的跨文化移植——译名与词义》(《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王路教授的译名主张犯有“词义漂移”的毛病,即在思考eimi问题时看到了eimi的多义性,概括总结出它的基本或主要含义,进而认定eimi的多种含义中有一种是原初的或最重要的,因此持有一种比较强硬的使用单一译名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感到译名不通,不顺,不合中文习惯,要么表面上用的是“是”字,实际上指的是其他含义。
我在《论“是”与“在”的可互换性——以波埃修斯为例》(《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拉丁教父哲学家波埃修斯的现存文本充分体现了“存在”与“是”的互换性。中国学者面对希腊文eimi时所产生的困惑源于这个词的一词多义,也源于希腊哲学在拉丁语使用者中的传播。拉丁语esse及其变化形式的“存在”含义与exsisto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如果想要在中文的理解和翻译中消除这种可互换性,正确的办法不是以系动词“是”为核心去创造一系列译名,如“是者”、“是之所是”等等,用它来替换一切与eimi有词源关系的西文词或词组,并要求人们不要用“存”、“存在”来理解和翻译之,而应当具体分析一词多义的eimi在具体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根据不同的语境采用不同的译名。
我在《波埃修斯〈同者相求〉篇解析——兼答王路教授对“语境论”的批评》(《清华哲学年鉴》2006,河北大学出版社)一文中指出:通过对波埃修斯文本的分析,本人增强了要在译名问题上坚持“语境论”主张的信心,单一用“是”或“存在”来翻译esse无法道出波埃修斯的本意,也会遮蔽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在译名问题上,“一‘是’到底”是错误的,“一‘在’到底”也是错误的,只有根据具体语境给出恰当的译名才是正确的。
我在 《拉丁语词esse的语境化处理——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第1卷第6-7章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哲学文本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译者的“前理解”决定了译者选用和构造什么样的译名。翻译哲学文本必须对原文的语词作语境化的处理。惟有根据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哲学范畴的含义,方能选择正确的译名,从而达到对哲学文本的正确理解和表达。
我在《对“是”必须作语境化的处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有关“是”的讨论发生之前,大多数中国学者确实都在用“在”或“存在”来翻译being,然而通过争论,他们已经认识到不能简单化地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学界已经看不到有什么人主张“一‘在’到底”了。但与此相反,经由若干学者的大力倡导和竭力论证,用“是”来翻译being似乎成了一种可以完全替代“在”的理解和译法,其中较为极端者还主张 “一‘是’到底”,并且反对结合原典对相关语词作语境化的处理。对“是”作语境化处理并非我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大部分争论者的实际看法。甚至连几位比较坚定地主张用“是”来翻译Being的学者,在他们的相关思考中也提供了许多材料和思想,有走向对“是”作语境化处理的趋势。王路教授坚持要以“是”(以系动词为其首要核心含义)为主线来理解和翻译西方哲学论著,同时也批评了包括本人在内的国内若干学者的“语境论”的译名主张。但实际上,王路教授本人也有对语境作分析的看法,而语境分析必然会导向“一是到底”的译名主张的瓦解。对“是”作语境分析,不能止步于语词的层面,而应向语句、段落、语言、语族等层面扩展。
我在《“是”的用法和意义不能混淆》(《世界哲学》,201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对“是”字的用法和意义进行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词义和选择译名,对原文进行理解和选择译名的最终依据是语词的意义(词义),而不是语词的用法(词性)。在相关讨论中说“是”的功能是系动词,这是对的;而说“是”的意义(意思、含义)是系动词就是错的。执着于“是”的一种意义,并主张在翻译中“一‘是’到底”,其思想误区就在于混淆或混同了“是”的用法和意义。
我对王路教授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批评综述如上。但我认为,王路教授的这本新书对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阅读它将推动我本人深入思考和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尤其是他在该书第一章“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引为分析对象的文本的中译文便是我的译文。这一章有三万字左右,我粗粗读了几遍,感到自己对王路教授的想法有了初步的把握。要对他的整章文字作出回应,需要我再读柏拉图的原文,再读我自己的译文,并在这个过程中消除我的译文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篇幅,这显然不是这篇笔谈文章所能完成的。我相信自己今后能抽出时间来完成这个回应,在此则略说几句。
与王路教授整部新著想要实现的理论目标相比,他的第一章的具体任务是试图证明;在柏拉图的重要对话《泰阿泰德篇》的相关文本中,所有的eimi及其相关词汇都应当作“是”来理解,将其译为“存在”或“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在对《泰阿泰德篇》解读时的基本论证套路是:哲学家想要证明的观点与他本人在文中所举的例子应当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就是译文出了问题,阻碍了人们对柏拉图思想的正确理解。王路在对第一段译文作了解释以后评价说:“例子是清楚的:因人而异,风可以是冷的,也可以是不冷的。所要说明的问题也是清楚的:以风为例,人可以是风存在的尺度,也可以是风不存在的尺度。问题是,这个例子如何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呢?”[1](P4)“这些例子无法说明所要说明的问题,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含有存在一词。由此可见,这里举的例子与所要说明的问题似乎是完全不匹配的。”[5](P5)
概括起来,王路教授认为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并翻译错了的理由有两点:(1)这段原文根本就没有出现“存在”一词;(2)人的感觉(风是冷的或不冷的),只能证明“人是”,不能证明“人存在”,或者只能证明“风是”,不能证明“风存在”。“以人感觉到风是冷的或不是冷的为例怎么能够说明人是存在的事物存在和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呢?”[1](P4)王路教授将此论证套路运用于整个“第一章”,且运用于全书。这个例证是他在这本新书中要抓的第一只“白天鹅”。我对这只“白天鹅”的回应目前只有两点:(1)这段原文不仅没有出现“存在”,而且也没有出现“是”,原文中出现的是一词多义的希腊文eimi及其各种变化形式;它们究竟应当理解并译成“是”,还是理解并译成“在”,要放在具体的语句和段落中来确定,我目前认为它有“存在”的意思,因此是有些地方译成“是”,有些地方译成“在”,有些地方不译,有些地方译成其他;(2)柏拉图到底是在用人的感觉证明“人的存在”,还是在用人的感觉证明王路教授所说的“人是”?我目前认为柏拉图的论证目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从一般证明的角度来说,我对前一点只要说明eimi及其相关变形可以译为“存在”就行了(对此,包括王路教授在内的众多学者已经说明了许多次了);对于后一点,众多的哲学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存在的)沿着用感觉证明存在这条路径已经证明了多次了,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马赫的“物是感觉的复合”,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王守仁的“心外无物”,不都是在用感觉证明存在或不存在吗?如果王路教授认为柏拉图在这里想用感觉证明的不是“人在”,而是“人是”,我想说的是,这是因为王路教授刚好中了他自己制造的“语言圈套”或落入了他自己造成的“语言困境”。他说的“人是”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人在”。他在抓这只“白天鹅”的时候又一次犯了我在《西方哲学基因eimi的跨文化移植——译名与词义》一文中指出的“词义漂移”的毛病。
关于“是”的讨论在中国学术界还将持续下去,中国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将随着这种讨论进一步深化。在理解和翻译西方哲学文本的过程中,对同一文本有多种理解和翻译是常态,不是特例。仅就译名的主张而言,我感到“一‘是’到底”是行不通的,但王路教授对若干西方大哲学家的重要文本的解读仍是一种重要的见解,值得学者们予以高度重视。
[1]王路.读不懂的西方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王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