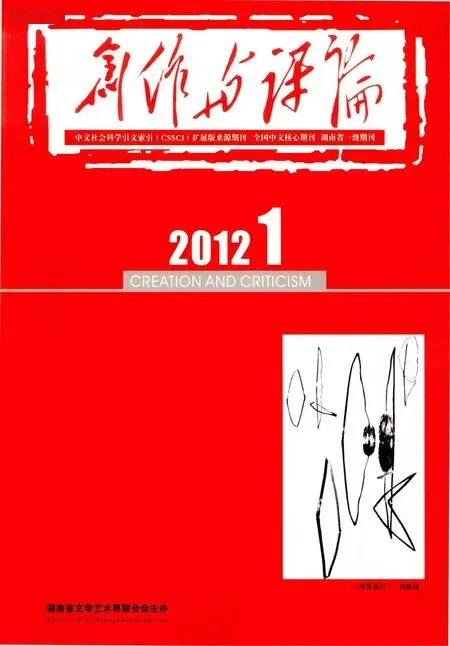意象诗学、徐则臣及现代中国小说*
2012-11-24李徽昭
■ 李徽昭
一、“意象”及小说意象诗学的可能
杨义曾指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的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地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①这里的叙事文学主要指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由古典小说出发,延及现代小说,“意象”及“意象叙事”扩大了本土中国小说叙事理论的边界。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从“意象”角度对中国小说做了较为深入的发掘,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本土中国文学叙事的“意象”诗学。作为解读现代小说的一把钥匙,“意象”范畴及其诗学特征对现代中国小说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意象”范畴由“象”而来,是中国传统象思维的一种体现,《系辞·上》开篇就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象”指的是事物可以感知触摸到的外在表象。《易经》中的“象”既有外在的万物所感知表象的意味,也是一种无法直接感知的抽象性符号。庄子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②庄子赋予“象”以哲学本体含义。庄子“从人的更为普遍直接的语言经验出发,说明语言之外尚有一些东西为语言所不能传达”。③庄子的“不可以言传”的“意之所随者”是指万物本源及难以言说的“道”。王弼则对“言、象、意”做了辨析:“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固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④重申了“意”的本体内涵,由“言”抵达“象”,进而由“象”再达“意”。王弼概括并确定了“意”的本源性地位,以及超越了“言”外与超乎“象”外的“道”的存在。
刘勰说:“是以陶均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脏,澡雪精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烛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⑤刘勰的“意象”可解读为“意中之象”。唐代,“意象”范畴大量介入诗歌批评。王昌龄强调诗歌作品的“意”、“象”与“言”、“意”的相互交融,他批评诗歌“有象无意”或“言”而无“意”的弊端,认为:“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⑥。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观点:“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⑦将“象”和“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可望之“象”或“景”,其次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我们看到,传统中国诗学中,创作主体“意中之象”的获得与创作主体心与外物相感后形成的“志气”陶养有极大关系,强调了创作者身心修养以及意象所容纳的思想与文化意蕴。传统文论中,“意象”多指创作主体和世界万物感应交会,从而形成创作主体独立的“意”和“象”。因此,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层面上,“意象”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近年来,“意象”范畴在文艺学界得到了广泛关注,叶朗、彭修银、汪耀进、王泽龙、胡雪冈、夏之放等先生既有考古式的文学阐释,也有开拓学术疆土的大胆界定。欧美学界也从自身文化出发对“意象”范畴做了阐发,庞德、韦勒克、沃伦等均有自己专属的“意象”范畴。应该说,“意象”范畴的重新征用是21世纪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
作为一种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意象”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艺术思维及文本阐释方式介入到现代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中。20世纪以来,尽管西方文化思潮不断冲击中传统中国,但作为潜在的思维与文化“无意识”,“意”与“象”互动咬合,形成了现代中国作家文本创作时内心所欲表达的“意”与文学思维中呈现的“象”相互沟通呼应的独有的中国文艺创作思维模式。“象”带有模糊的文化特征,其主要的症候便是随类赋形,可以散发更多的意蕴,中国传统文艺语境中的“意象”是中国文化情境所生发的具有多重阐释意蕴的一个独特范畴。中国小说的艺术媒介是中国语言文字,是“象”,也是“意”。小说创作中的作家生活与社会体验积淀而成的内心“意”与“象”落到实在的语言中,形成了小说文本的另外一重“意象”。读者阅读小说文本,形成了由个人生活与文化体现出发形成的再造“意象”。也就是说,“意象”有作家内心意象、文本呈现的文字意象,以及读者阅读所感受到再造意象这样三重“意象”。在当下中国语境下,面对西方文化思潮冲击,现代中国小说意象诗学理应对中国式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意象诗学可以成为中国本土小说理论体系,本文无力就此深入阐发,但认为可依据不同特征及意象在小说中承担的叙事或文化功能做出界定和分类,比如动象、静象、事象、物象、潜象、实象、自然意象、文化意象、身体意象等,由此可以细致解析意象诗学之于现代中国小说艺术与美学的意义。
由于小说叙事的起点和归宿大多集中在空间与人物上,我认为,空间意象和人物意象是小说叙事的起点,也可以说是小说意蕴提升的焦点,对空间与人物的命名往往寄托了作家文学与人生的理想。所谓的作家书写的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正是空间作为意象对小说所产生的独有魅力。因此,现代中国小说的空间意象体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既具有指向现实世界的文化象征意义,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国小说面向世界的民族意识。人物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人物行动及其特征共同构成小说人物意象,将人物在空间中的活动结构起来,便是人物意象与空间意象共同构成的小说意象诗学的一种可能。
二、“意蕴”与徐则臣小说意象
小说意象诗学是一种文化存在,在具体作家的文本中可以阐释的空间较多,本文以徐则臣为例,对意象诗学在年轻一代作家中的运用情况做文本细读式的解读。徐则臣比较认同的方向是“学院派”作家。对21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学院派”指的是作家对学院知识体系中的文学理论、历史的谙熟,在对古今中西多个层面文学知识系统了解的基础上。徐则臣曾在大学讲授过美学课程,有着中文系本科、硕士研究生的良好学院履历。他个人也乐意认同学院派的评价,尽管现在他游离学院体制外,但论读书之丰、涉猎范围之广,许多同代作家未必在其上。我的意思是,正是在对中外文学知识系统了解、比较的基础上,徐则臣对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现代中国小说的基本立场、中国小说的未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徐则臣新近出版了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他对外国名家以17篇小文字做了精到评点,涉猎了卡佛、帕默克、福克纳、奥兹等众多现、当代西方小说大家。这样的分析或可以说,徐则臣对西方小说大家有着堪称透彻的了解。他也表达了建构“文字乌托邦”的宏大野心,这是他对中国式的好小说的一种宣言。比如,“世界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坐标系,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创作都分属于一个具体而微的点——你的坐标”、“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然后才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面对这样的坐标系,他认为“最好的小说要以实写虚,经典皆如此”。他理想的小说是“意蕴复杂多解,能够张开形而上的翅膀飞起来。”“意蕴”指内在的意义,“复杂多解”的“意蕴”与“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象”有着不言自明的美学关联。在徐则臣无意的两种表达中,形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即:通过世界文学坐标系的定位,徐则臣潜在认同了传统中国“意象”诗学对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价值。
这或者可以说是笔者透过徐则臣随笔做出的一厢情愿的阐释,那么,以“意象”诗学视角对其小说文本做出阐释应该是具有实证价值的。短篇小说一般篇制短小,艺术性要求较高。短小的叙述篇幅中,空间、人物等意象属于核心意象,可以显现小说无穷琢磨的文化与哲学意蕴,集中展现小说家的思想、情趣、技巧。徐则臣早期“花街”、“谜团”系列多是短篇,透过这些文本的审读,可以看出在其小说文本中意象运用的实际情况。
徐则臣是有历史意识的作家,或许正因于此,其早期“花街”系列小说中出现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意象多沾染着历史的风尘味。比如《花街》中“杂货铺”、“花街”、“老榆树底下”、“修鞋摊子”、“豆腐店”;《失声》中的“石码头”、“肉摊”、“老槐树”、“石板路”;《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中的“乌龙河”、“柳树底下”、“石埠桥”;《弃婴·奔马》中的“田埂”、“松树”、“沙堆顶”、“小葫芦街”、“五斗渠”、“瓜地”;《养蜂场旅馆》中的“左山”、“旅馆房间”等地点成为小说重要的空间意象,这些空间有着浓厚的历史与生活气息。我们可以想象,古典诗歌中的“枯藤、老树”、“小桥、流水”,与徐则臣小说中所感触的空间意象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这样的空间展示了作家对历史的某种认同,或者是穿越历史的某种渴望。在某种意义上,徐则臣早期小说中的空间意象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有机联系,触动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机制,使得小说的行进沾染上了风尘仆仆的中国气息。
透过作者的叙述,这些空间意象开始弥漫现代生活气息,它们是作家日常生活经验积淀出的感性印象,也是作家想传递的可无限延伸的小说意念空间。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的空间意象贯穿了徐则臣早期的小说文本,对爱情、遗忘、命运等诸多主题的展开形成有效的推进机制。“花街”中的老默与麻婆的相互守望的爱情及其悲悯和老旧的“石板路”一样,“花街”的繁“花”及其惹眼的风云让人叹惋;赶鸭子的小艾在河边与“我”轻松戏耍,在“我们”共同的世界里都要面对意外切入“我们”生活的“陌生人”;“松树下”的“坟堆”边,“我们”追过田鸡,看到如玉的弃婴,过些年后,在消失的“坟堆”边,如玉轻松的说笑让故事时间的改变得到了意蕴上的升华。“石板路”上的陈旧与麻婆的昏老、河岸边的轻松与坐在桌边吃着鸭肉的讶异、消失了的坟堆与轻松说笑的如玉构成了生活中的对冲关系,使得故事有了飞翔的可能。这样的空间意象便可以说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小说家在空间意象架构的语言机制中隐藏了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可说是“象”中有“意”、“意”中味“象”,使得小说的阅读体验有了更多的飞翔期待。这样的空间意象使得故事的主题与其语言构成了统一的心理接受体系,提升了徐则臣小说对历史、人性及命运思考的深度。
小说人物既是故事推进的主要动力,也是故事意蕴承载的载体,人物意象的穿插集中体现了小说艺术的形式与思想。人物命名从来不是随意产生的,往往暗含着某种宿命般的寓意。小说家对主人公的命名凝集了作家对人物命运、小说主题的诸多思考。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人物姓名集中体现了人物意象与其姓名的关联。同样,徐则臣小说的人物意象与其姓名都有内在某种关联。“老默”是修鞋匠,一生默默陪伴在麻婆身边,远远地,隔着距离的审视着麻婆的生活。屠夫名叫“冯大力”,他的失手为自己的命运买了单。追赶田鸡的是“我”和“马小毛”,而“如玉”则是弃婴的母亲。《西夏》中那位仿佛天外飞来的女子“西夏”将历史和现实勾连起来。《啊北京》中无比热爱北京的“边红旗”最终要漂泊在北京。这些姓名是小说人物的第一意象,他们与性格、命运、爱情有着内在的关联。人物姓名构成了与主题相关的另外一种意蕴,和小说的空间意象相映成趣。这些人物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小说创作主体和现实经验生活中与各种人接触后不断地感应交会形成的人物意象,这些人物意象在叙事推进中逐渐变得独立、丰满,具有了承担作者及小说之“意”的可能。
徐则臣的中短篇小说中,故事展开的空间相对较小,人物性格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展示,带有浓郁文化气息的空间意象和人物意象相映成趣,构成了自足的小说意象。在这种自足的意象运用中,故事所承载的文化意味更多,容易对读者构成心理上的阅读认同,而小说家的个人趣味、文化取向与传统中国文化有了某种共通。无作为学院出身的年轻一代作家,徐则臣接受的古今中外多层面的知识熏陶构成了独特的知识结构,这一结构中,我们认为意象诗学应该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可以说,徐则臣的短篇小说艺术集中地体现出对意象诗学的自觉运用,显示出年轻作家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隐在承续,而这种承续既可以看作是年轻的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化的有效回应,也是作家的中国思想与文化主体在新世纪中国经济与文化崛起之后对西方现代小说的积极应对。
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意象”诗学已经渗透进了现代小说家的文学思维中。与短篇小说不同,长篇小说中的意象除了承担了独特的叙事功能,在小说人物性格及作家的审美取向上也有抒情表现功能。在徐则臣的长篇小说中,也有独到的意象诗学运用。空间意象和人物意象如此,比如《午夜之门》中模糊了历史的空间和人物命名,“青石街”、“左山镇”、“茴香”、“花椒”、“沉禾”、“红歌”等。《夜火车》中,“出走”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陈小多三次夜火车的描写成为这部小说与标题相关的重要意象。在第二次小城通火车的夜晚,陈木年追赶火车时,“耳朵里灌满了风声和灿烂的阳光,他听到的声音只有火车的汽笛和自己的喘息”,当爬上火车,陈木年“不由自主张开双臂,从内心到身体瞬间感到了飞翔的快意。他看到巨大的风裹着阳光象雨一样满天满地地落下来”。这与第一次大学毕业出行有了本质区别,是陈木年在现实压抑中的释放,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的生活突围,可以说是陈木年一种独特的自我理想与命运的放逐方式。在这部长篇中,“夜火车”意象承担了抒情功能,是小说故事演进的关键,无疑也提升了小说的诗意与韵味。
长篇小说的长度与难度是约略相等的,长篇小说如何抒情,意象起到了关键作用,意象的有效运用理应丰富长篇小说的意蕴。从《午夜之门》、《夜火车》来看,意象可以说是徐则臣小说的艺术形式,意象的结构、形式、风格与作家主体、审美流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意象也是其小说文本内容,不同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体现了时代与徐则臣个人生活经历所造就的审美风貌与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意象在形式与内容间搭建了恰当的桥梁,由此实现了70后这一代作家立足中国传统对外在世界、内心与形而上世界的沟通。
三、现代小说意象运用及其未来
“意象”是由中国本土文化生长出的一个范畴,经历20世纪现代思潮的淘洗,这一范畴及其可扩展的文化与哲学内涵对徐则臣等年轻一代中国作家产生了积极影响,文学批评也应该看到这一范畴所蕴含的本土文化因素,或者说是“嫡属性”内质。嫡属性(filiation)是由故土文化所产生的,属于自然和生命领域,而相对的“隶属性”则通过批判意识和学术研究所表现出来,其属于文化和社会。若将这一概念缩小使用,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嫡属性生命文化,也有产生于离开故土文化后所受学校与社会教育所形成的隶属性文化。那么,可以说“意象”诗学对中国作家而言则是嫡属性效用,在嫡属性语境上生长出来的“意象”范畴更有独特的阐释价值。因此,关注“意象”范畴远较西方文化所关注的“意象”诗学更有意义。我注意到,文艺理论研究界对意象范畴关注多处于理论层面上,而未能在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中得到更多、更深的应用。尤其对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批评与研究而言,意象的理论征用远远小于“象征”、“现代性”、“后殖民”、“女性主义”等西方血统浓厚的理论范畴。
中国古典小说在漫长的文学叙事中积淀了鲜明的中国文学叙事风格,并潜在地影响着现代中国小说叙事艺术。我认为,现代中国小说的主流——乡土小说的生成有现代思想文化推动的原因,但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意象诗学的影响及中国古典美学的内在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现代小说意象诗学建构中,新时期乡土小说主流之一——寻根小说以独特的意象书写呈现出反先锋的意象诗学特质。李陀认为寻根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在现代小说的水平上恢复意象这样一种传统的美学意识,就是使小说的艺术形象从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意象的性质,就是从意象的营造入手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建设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⑧汪曾祺、韩少功、何立伟、阿城、莫言、郑万隆、贾平凹、张炜等寻根文学代表人物以意象营造为核心书写了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生活,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中,传统文化与生活氛围浓郁,不同的意象中蕴含着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精髓。如果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⑨那么“意象诗学”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小说艺术的“根”。因此,寻根小说意象诗学的运用才真正能显示出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审美意识的普遍性,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也才能以其独特的小说叙述风格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寻根小说对意象诗学的运用体现出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化主体意识,显示了现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也为徐则臣等70后作家提供了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隐形资源。
意象诗学作为一种带有传统中国文化与思想胎记的理论范畴介入了现代小说,这是对现代小说艺术本土化的尝试。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规避中国传统意象诗学的潜在影响。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贾平凹、莫言、苏童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意象诗学成为支撑其现代小说世界影响的有效支柱。徐则臣等70后一代作家,面对古今中西的多重文化与思想挤压,他们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与思想意识,传统的中国意象诗学也应成为他们文化身份确认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徐则臣的“花街系列”、“谜团系列”及有关长篇小说都是在现代小说的意义上继承了寻根小说一脉的意象叙事艺术,对意象诗学做了现代运用和有效阐释,使得现代小说焕发出了中国古典文化与思想的曼妙光芒。
新世纪中国小说已经产生新的质地,乡土小说的边界逐渐模糊,其主题及艺术呈现日渐被无所不能的中国城市化浪潮席卷而四散飘零,“乡土”逐渐退隐,以城市化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也还在迷茫之中。底层小说、京漂小说、新历史小说、乡下人进城叙事等与新生代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等范畴相互混杂,乡土小说的经典面貌被颠覆得面目全非。以徐则臣为代表的70后作家以对意象诗学的有效运用使我们看到了现代中国小说新的美学风貌,他们注意到了“不可言传”的意象表意作用,通过对意象“表意”特征与“象外之意”的美学追求,传达了现代中国小说家对文学意旨的追求,满足了现代中国人对小说形式之外的“道”的独特感受与表达。他们对历史与生活意象的精准表达使我们在现代生活情境中看到了中国古典意象美学的光芒,这一光芒的闪耀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在新世纪得到升华的一种先兆,或许是中国小说参与世界文学的一种可能。
注 释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第289页。
②[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1页。
③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页。
④楼禹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⑤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⑥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⑦肖占朋:《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7页。
⑧李陀:《意象的激流》,《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