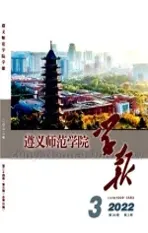略论疾疫视域下的抗战时期贵州城市公共卫生建设
2012-11-18王肇磊
王肇磊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56)
城市因人口聚集,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频频被各种疾疫所侵扰。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公共卫生历来为城市管理者所重视,采取诸多措施以保障城市居民的卫生安全。学界关于近代沪粤京津青岛等西化程度较深城市的公共卫生研究颇为深入。①关于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的相关研究,可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南开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8年第3期;刘佳奇:《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轫》,《历史教学》2009年第2期等。相对而言,西部城市因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其公共卫生问题则远没有取得足够的关注和认可,尤其是地处僻壤的多民族聚居的贵州省。
在贵州城市发展史上,抗战时期是贵州城市现代化取得突破性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深受疾疫影响的一个阶段。因此,研究抗战时期贵州城市疾疫问题对于研究贵州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史无疑很有启发意义。目前,关于贵州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一些问题与抗战时期贵州城市公共卫生的专题研究有直接的关联。但从整体而言,关于抗战时期贵州城市公共卫生的专题研究还较为零散,不够系统、深入。①因此,还有强化相关研究的必要。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拟以抗战时期贵州疾疫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为视角,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作一些探讨,并冀望抛砖引玉,深化此领域的研究。错谬难免,敬请方家斧正。
一、抗战背景下的贵州城市疾疫问题
自古以来,贵州便是“瘴疠之地”,疾疫类型多样,主要有鼠疫、霍乱、天花、麻疹、疟疾、伤寒、麻风等。[1]p532~535据相关资料表明,贵州有记录的最早疾疫可能发生在新莽时期,“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2]p8后屡有记载,如“万历六年播州大疫;十七年春饥,大疫”。[3]卷21,《祥异》《药言随笔》因之评说:“滇黔两粤向有时疫”。[4]p100到抗战时期,疾疫发生的域度、频率呈增加趋势,尤以霍乱、疟疾与天花最为严重。如贵州在1937年6月发生了全省性的霍乱疫情,一年后仍大肆流行,致使很多人丧失了生命;[5]p68~711938年贵阳“近日霍乱极猖獗,蔓延亦速”。[6]p3~91939年铜仁县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率平均约占百分之三十”。[7]p481942年沿河县全县霍乱流行,驻县城川主庙数十名新兵,死亡近半。同年,思南县霍乱流行,死者数以千计。1944年贵州苗族地区霍乱流行。[8]p88~4001944年的《剑河县志》记载:“每年春季……天花流行,婴儿死亡率极高,……一般苗胞唯有乞灵于鬼神,……贻误死亡更众。”
疾疫的频发,与贵州城市环境不佳密切相关。从宏观上讲,多数贵州城市因居民缺乏现代公共卫生观念,而致使环境污染严重。市民多“‘愚’而不注意卫生,因其‘私’而缺乏公众利益观念,驯致随处便溺、唾涕、污垢不除、秽屑乱掷,其影响健康,为害民生,良非浅鲜”。[9]像省城贵阳贯城河“沿河染坊林立,居民不少,致污水流入河内,河水溷浊,妨碍市民卫生”[10]p31的现象在贵州各城市均普遍存在。同时,城市因人口集聚,一旦疾疫爆发便会迅速蔓延。此外,抗战期间,大量沦陷区的流民在城市间频繁的迁移,在无形中进一步扩大了疾疫扩散的范围,加深了贵州城市受疾疫侵害的程度。
就微观而言,因经济落后,贵州大多数城市普通居民身居陋室,居住环境相当粗劣。在黄平县城内,“欲觅一完整之屋宇俱无”。[11]p55~62独山“房屋多为旧式”。[12]p17~22桐梓县城“荒城寥廓,城中居民不过百户,徘徊其间,惟见苍凉满目而已”。[13]卷40其它中小城市因战争、灾荒的影响也多残破不堪。即便是省城贵阳的民居房间一般都较“矮小”,“显得太寒怆”。[14]卷4房屋居住环境一般,连贵阳省主席吴鼎昌主持修建的平民住宅区也只有草屋、瓦房两种。[15]p31~36这些矮小、采光不足的民居在贵州城市多以“低洼巨壑填平以作街市”的地理布局条件下,[10]p31叠加“天无三日晴”特殊的气候环境,极利于疫菌滋生,极易“感染传染病以及肺结核”。[16]p2~5
再者,贵州城市卫生事业极为落后。“民国二十六年前,卫生建设,止于一省立医院而已。全省医师仅有12人,殊无事业之可言”。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无法有效地治疗频发的疾疫,当然就更谈不上进行积极的预防了。“民众疾病”,往往“听其自然。每遇疫症流行,辄致病死累累,……几遍全省”。[17]公共卫生事业的落后,既极不利于抗战前贵州城市防疫工作的开展,又没有为抗战时期贵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二、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
疾疫频发,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贵州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出于抗战大后方建设的需要,除了大力发展经济外,提升人民体质也为各级政府所重视,并开展了以卫生防疫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事业建设。
1.组建专门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贵州卫生行政管理在抗战前仅由民政厅第二科兼理,无专管机关,仅在省城贵阳设置健康教育委员会。为加强抗战时期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与管理,1938年4月成立了贵州省卫生委员会,直辖省政府,综理全省卫生行政。1941年7月,复遵中央颁布的省卫生处组织大纲改组卫生委员会为贵州省卫生处。在卫生委员会(卫生处)之下,贵州省先后在省城贵阳组建了贵州省健康教育委员会、贵州省卫生实验所、贵阳卫生事务所、卫生用品经理委员会等机构,其中专设防疫机构有贵州省抗疟所(1939年)、贵州省立传染病院(1940年)、贵州省防疫队六队(1942年)。[18]p91~94各县级城市随之也组建了相关公共卫生管理机关以直接管理疫政。1938年沿河县改戒烟所为县卫生所,兼负责城区防疫、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印江县于1943年4月成立县防疫委员会,编制6人。[8]p400在疾疫流行时,贵州省还临时设立应急机关。如1942年霍乱大流行,省卫生处迅速成立了临时防疫委员会,组织防疫队深入各地,并实行疫情报告机制。[19]p387~388甚至一部分城市还特设卫生警察。[18]p104这都为贵州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行政保障。
2.颁布公共卫生法规
为促进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和贵州还颁布了相应的公共卫生法规。1940年,行政院相继公布《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和《省卫生处组织大纲》。1942年贵州省政府又颁布《各县、区、乡(镇)卫生院组织规程》,具体规定了医院收容传染病人办法、医院治疗病人呈报制度。此外,贵州还颁布了《贵州省管理开业医师暂行规则》(1940年)、《奖励医药技术条例》(1941年)、《修正管理成药规则》(1942年)等一系列法规,使贵州省的卫生制度渐与他省趋于一致,从而为贵州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3.设立医院与卫生所、培养医护人员
在抗战前,除省城贵阳省立医院外,其它各县城皆无卫生院(所)。卫生委员会成立后,“除于各专员公署所在地、或交通重要县份,设置县卫生院,使为推进卫生事业之核心。其他各县,分置甲乙两种卫生所,甲种卫生所设备以能适应地方需要,办理医药救济及防疫工作等为目标;乙种卫生所则仅担任各种医术简易工作”。[18]p94经过努力,贵州各县级医院与卫生所得到了较快发展。1938年沿河县将戒烟所改为卫生所,有所长、医士各一人。[8]p399是年全省成立了5所县卫生院,后逐渐增加,至1942年县卫生院发展到78所,约占县级城市的96.3%(见下表),到1945年,除县城外,还在各区设区卫生分院21所,乡镇卫生所69所。[19]p385

表:抗战期间贵州城镇医院、卫生所数量简表
以上医院、卫生所还不包括专门防疫治疗机构。如为防治回归热,一些县城还专置了灭虱治疥站等。[18]p104
除举办医院、卫生所外,贵州省也相当注重防疫医护人员的培训。抗战期间,贵州为解决本省防疫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积极利用各种条件加强防疫医护队伍的建设。1939年成立了贵州省立高级医事职业学校。1944年在遵义创办了贵州省第五区各县联立高级医事职业学校,[20]p72~75招收本省籍学员,为各级卫生机关培养各科基本医护人才。同时,还在国立贵阳医学院和西迁至贵州的湘雅医学院根据贵州实际需要培训中级卫生人才,并商请在黔中央卫生实验院贵阳卫生干部人员训练所,为贵州设班训练,“以应需要”,[18]p106~107从而为贵州省各城市培养了一批专门防疫医护人员。这都为贵州城市预防、治疗疾疫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4.积极开展各项卫生防疫活动
一般而言,疾疫预防重于治疗。故“本省(贵州)自二十七年成立卫生委员会后,对于各种传染病,如天花、伤寒、霍乱等,均按其流行季节,积极预防”。[19]p387“自三十三年春,即一再令饬各县市加强检疫及环境卫生工作,并规定各县注射疫苗人数应为各县全人口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贵阳市则应为全市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21]p90据何辑五统计:1938年共有169072人注射了疫苗,1945年则增加到616136人。另据1944年《黔政概况》记载,除凯里、兴义、郎岱、镇宁、金沙、丹寨、黎平等县外,贵州“注射霍乱疫苗者”36678人;“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者”25698人;另外,各防疫队注射霍乱疫苗75424人,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6636人;各检疫站注射霍乱疫苗215627人,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35898人,总计共注射693027人。[21]p91其中仅贵阳市“霍乱预防注射,计六万六千余人”,[10]p74约占1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疫苗的注射范围因受贵州交通环境和经济落后等因素的制约,多囿于贵阳、遵义、安顺、兴义等大小城镇,很少涉及乡村。[20]p72~75在疾疫流行时,成立防疫站、检疫站,积极防治。如“本省二十七、八年先后发现霍乱,势甚剧烈,均经设立临时防疫处”,并与“邻省联络疫情报告,及积极举行普遍预防注射,严密检查车辆。凡旅客无霍乱预防证者,一律不准购票乘车,其外如举行饮水消毒,禁绝冷食摊贩,均得先后扑灭”。[18]p1041942年,贵州再次发生霍乱。卫生处迅速成立了临时防疫委员会,组织防疫队深入各城镇,在玉屏、独山、盘县、松坎等边界设置检疫口,并且建立了疫情报告机制。[20]P72~75在防治天花时,“于二十七年春秋两季,办理大种痘工作,派遣多数种痘员,分赴各公路沿线重要城市办理、宣传及指导种痘事宜”。[18]p105贵州“疟疾盛行”,如民国三十年,疟疾“流行达二十余县”,患病者80余万,抗疟队立即派遣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分三路进行巡行治疗。[18]p106贵州省府为治疗肺结核,还于1943年7月发起了“防痨运动”,设置防痨团,直属卫生处,在各医院、卫生所专设防痨门诊和痨养院。此外,还对回归热、鼠疫等疾疫进行了初步的防治。这些措施的实行,对防控贵州城市疾疫的发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整治城市环境
贵州城市疾疫频发与其城市环境不佳密切相关。作为战时陪都重庆的南方屏障,联络湘、桂、滇、川诸省的交通枢纽的贵州,在大后方占有相当地位。于是,国民政府将大力发展贵州包括卫生事业在内的各项事业、巩固后方作为其中心任务之一。同时,此期的贵州地方政府与市民对城市环境问题也深有感触,要求“修筑道路、改良建筑、讲求卫生”。[22]p151937年主政的吴鼎昌也要求“卫生行政必求普遍推行”,[23]1939年1月1日,第1版本着“清洁、整齐、朴实、安详”的原则,[24]p9~12对城市环境进行大力整治。贵阳市政府“剴切告诫市民,利用劳动服务彻底整顿市容”,并举行清洁比赛运动,“挨户严格检查,使市面日臻整洁。此外更饬警局挨户劝导”。整治内容包括“上下水道之建筑,厕所之改善,街道之清洁,有关卫生商店之管理”等诸项,组建清洁队,进行“街道清洁,垃圾处理”。[18]p103~107罗甸县城规定“凡街道两旁住户门前自己清扫”,并在1942年由县政府专雇一名清道夫,每逢赶场天当晚清扫一次。[1]p532、540
抗战时期,贵州城市认识到洁净水源对防疫的重要性,开始讲求饮用水的卫生,并对城市供水进行了改良,如兴建给水工程、改建水井、禁止污染水源、饮用水消毒等。[19]p386~388此外,一些城市还对饮用水进行消毒,并加强了公共厕所和粪便的管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8]p104通过环境的整治,使贵州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疾疫滋生的土壤。
6.进行公共卫生宣传与教育
民众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的养成,也是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抗战时期,贵州各社会阶层采取多种形式对城市居民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宣传与教育。各级政府和疾疫防控机关制作环境卫生手册,印制关于房屋卫生、饮水改良、厕所管理与垃圾处置的“四程挂图”,并分发各县以宣传卫生知识。贵州省卫生处下设的健康教育委员会编订卫生健康教材,对学生进行卫生习惯训练。通过《修正贵州省种痘暂行办法》,专门规定各县政府或者卫生院所(队)在每次接种牛痘前,必须先期分别督促该管各乡镇保甲长向其所辖境内民众讲解相关卫生知识。各县健康教育委员会,订有各县卫生院(所),举办社区健康卫生教育实施的纲要:“设置卫生展览室外,并与其他社教机关合办失学儿童保健班四班,仍随时作文字及图书之宣传”。[18]p102学校还主办暑期卫生研讨会等会议,以促进学生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内迁的高校与医疗机构则通过文艺演出、办报刊等形式,向民众宣传新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理念,[25]p65~68利用《贵州卫生》等杂志刊登当时名医诊断疾疫的方法,向城市居民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并为民众就医提供方便。①详见贵州省卫生处卫生月刊编辑委员会:《贵州卫生》1942、1943年各期。经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贵州城镇居民的公共卫生观念比抗战前有了较显著的提高,社会效果良好。
三、成效
经过努力,贵州城市以防控疾疫为中心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初步遏制了疫情的发生、发展
随着各项防疫措施的执行,贵州初步遏制住了城市疫情的发生、发展。1938~1939年贵州霍乱大流行,经过积极防治,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以致1940年、1941年“本省未发生霍乱”。自1941年7月始,加强了对来自昆明的霍乱疑似患者的检疫,贵阳市受检者59452人,并对霍乱疑似患者采取隔离治疗措施,贵阳市隔离治疗了19人,[26]p22~23使输入性霍乱疫情也得到了初步控制,到9月则“完全平息”。[18]p104预防天花则推广种痘。贵州省向中央防疫订购牛痘苗1500打,分赴各公路沿线重要城市办理,[18]p105据各县在1944年秋呈报,共施种人数254536人,[21]p91其中贵阳市春季种痘28700余人,[10]p74有效地阻滞了天花的蔓延。
此外,省抗疟队在1941年共治愈二十余县疟疾愈患者80余万人。[18]p1061943年7月贵州省在“防痨运动”中,各防痨门诊共救治了134人,[21]p92从而初步遏制住了贵州省城镇各类疫情的发生、发展。
2.初步建立起了以防疫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体系
抗战时期,贵州省各级政府在预防、控制、治疗疾疫过程中,结合贵州实际,本着预防、救治相结合的原则,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城镇公共卫生体系。首先是建立了以省卫生处为地方最高卫生防疫行政管理机构为核心,结合各县级卫生防疫机构与一些专门防疫机构的一个有机的公共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其次是组建、完善了疾疫预防、控制、治疗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综合性医院(所)、专门医院(所)及专设防疫机构等医疗机构为中心,根据疾疫流行的特点,采取积极预防、疫中治疗、常规防治与应急防治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起了一套从省城到县城(镇)的较为完整的城市疾疫预防、控制、治疗体系,使之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城市环境得到初步改观
抗战时期,贵州出于防控疾疫的需要,加强了城市环境的治理,使之得到了初步改善。
首先是市容的改观。如贵阳在抗战前“以连年兵燹,市街建设,成绩未著”,[10]p32“是苗彝遍地贫瘠不堪的处所,他们真梦想不到抗战以后,贵阳会形成西南诸省交通的中心枢纽,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的。不要说交通、政治,就是一切建筑、人物、风俗、人情也都为之一变”。[27]城内“建筑颇巍峨,街道亦宽宏。临街的老铺面多属楼房”。[28]p17~24“旧街市狭巷,已不多见”,“环境清幽,宿舍清洁,身心为之一爽”,[29](《贵阳管窥》)“市容因而改观者不少”。[10]p32安顺“街道极佳,是石铺的,很平整,很宽大。我在任何省,没见过除了省会之外,又能有这样好的县城。即地方上一切建设,也都叫人只有赞叹”。[30]p9~20遵义“有个现象最惹我们注意的,就是遵义街道之清洁”。[31]p13~19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面貌都有改观,那些像独山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城市的市貌几无改变,街道仍是“龌龊不堪”。[12]p17~22
其次是城市饮用水日渐洁净。贵阳在抗战期间兴建了给水及贯城河工程,初步解决了居民日常用水不洁的问题。安顺、遵义两县城关也进行了饮用水的改良,“均获得当地民众之热心赞助”。[18]p103~104各县城“于二十七年卫生委员会成立后,通饬各县,按其所采之水源,加以改良与保护。改良之道,如改建水井,建筑汲水码头,简易净水池等;保护之方,如使污水污物,远离水源。汲水用水者,不得污染水源等。并考察具有特殊情形之县份,派员代为计划兴建给水工程”。[19]p388其居民饮水条件日渐改善。
市容与饮水的改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疾疫的流行,而且还促进了贵州城市市政现代化的发展。
此外,抗战时期的贵州公共卫生的宣传与教育,使城镇居民逐渐改变过去不甚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开始讲究个人卫生。如贵州城镇居民一改抗战前视疫苗注射为“畏途”为“自动请求注射者,亦络绎不绝”。[19]p387从而加快了城市居民新风尚的形成与发展。
四、特点
纵观抗战时期贵州城市以防疫活动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始终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政府主导性强。无论是组建各级卫生防疫行政机构,设置各级医院(所)和各专业防疫所,还是进行疾疫的预防、治疗,公共卫生的宣传教育,都是在贵州各级政府主导下完成的,较少看到民间力量的存在;二是暂时性。抗战结束后,部分战时迁黔医疗机构、医科院校陆续迁走,特别是卫生防疫人才的流失,使贵州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宛如昙花一般;三是不平衡性。以疾疫防控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事业虽然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但由于受各城市自身条件的限制,那些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城市,如台江、剑河、丹江、泸山、施秉、松桃、紫云、关岭等,公共卫生条件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传染病仍到处流行、发病率高。[8]p88而那些处于交通要道和区域行政中心的城市,如贵阳、遵义、安顺等城市在公共卫生工作推进中受益最大。
总之,抗战时期的贵州以防控疾疫为中心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虽然因抗战的需要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达到城市发展对现代公共卫生的要求。尽管如此,此期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还是为后来贵州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不可避免地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1]罗甸县志编纂委员会.罗甸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Z].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3]郑珍.遵义府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56年.
[4]冼维逊.鼠疫流行史[M].广州: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
[5]李仕波.抗战时期贵州医疗卫生政策探析[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1,(2).
[6]吴传钧.赴川历程[J].旅行杂志,1938,(10).
[7]贵州省档案馆.贵州档案史料[Z].贵阳:贵州档案馆内部版,1988.
[8]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Z].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9]吴鼎昌.勖卫生工作[J].贵州卫生,1942,1(1).
[10]航建旬刊编辑部.贵阳指南[M].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38.
[11]陈志雄.湘黔滇旅行记[J].旅行杂志,1938,(11).
[12]张琴南.入川纪行[J].旅行杂志,1936,(6).
[13]朱偰.黔游日记[J].东方杂志,1944,(12).
[14]茅盾.茅盾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5]金琼.抗战时期筹建贵阳平民住宅区档案史料一组[J].贵州档案,1991,(6).
[16]尚傳道.城市住宅问题[J].贵阳市政,1941,(9、10 合卷).
[17]姚克方.今后之贵州卫生设施[J].贵州卫生,1942,(1).
[18]贵州省政府.黔政五年[Z].南京:南京印书馆,1943.
[19]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Z].南京:南京印书馆,1947.
[20]李娇娇.抗战期间贵州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5):72~75.
[21]贵州省政府秘书处.黔政概况[Z].贵阳: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44.
[22]何德川.建设刍议[J].贵州建设月刊,1946,(1).
[23]吴鼎昌.本年工作,兵役第一[N].西南日报.1939-1-1.
[24]郑一平.贵阳市政设施新姿态[J].新市政,1943,(2).
[25]李仕波.抗战时期贵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其历史影响[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2).
[26]张崇德.贵阳市卫生之回顾与展望[J].贵阳市政,1942,2(1).
[27]顾君榖.贵阳杂写[J].旅行杂志,1939,(3).
[28]宇周.蜀黔湘游记[J].旅行杂志,1941,(10).
[29]张恨水.独鹤与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30]李长之.西南纪行[J].旅行杂志,1938,(11).
[31]同济.千山万岭我来归[J].旅行杂志,19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