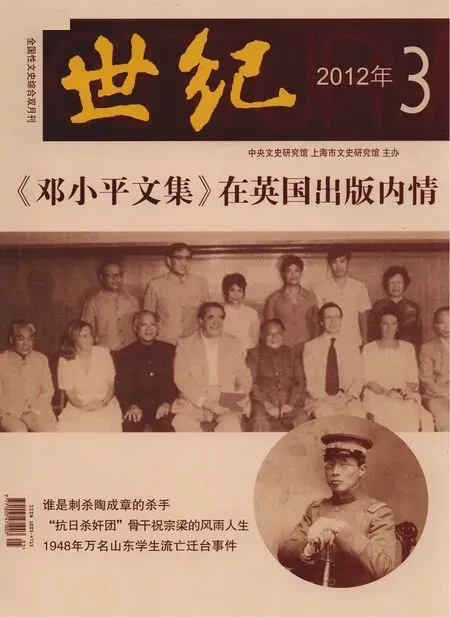“抗日杀奸团”骨干祝宗梁的风雨人生
2012-10-29周峥嵘殷之俊
本刊记者 / 周峥嵘 殷之俊
近两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和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相继播出《刺客使命》和《杀奸团》访谈录,早已在历史风云中湮灭的“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逐渐受人关注。轰动一时的1939年“周作人遇刺案”的幕后策划者和杀手均来自“抗日杀奸团”。一位上海中学校友无意间在电视中看到五十多年前的老师祝宗梁老先生的身影,了解到祝老师还有这么多传奇的人生故事,特意找到我们杂志社。于是,我们在这位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上海上中西路祝宗梁的住处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
祝宗梁今年92岁,满头银发,高大瘦削,温文尔雅,面带微笑,随和可亲,身体硬朗。初次见面,让人很难将这位老人与当年令日寇和汉奸闻风丧胆的书生杀手联系在一起。聊起自己的过去,祝宗梁很平静,也很坦荡,在一旁的快言快语的女儿张梅格则说爸爸可以用“无党无派,没有教师职称”来概括。
天津“抗日杀奸团”的重要骨干
祝宗梁是河南固始人,1920年出生在北京。祖父曾做过清末道台。父亲祝毓瑛,曾在美国留学,读的是经济,回国后曾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工作过,后到天津北宁铁路局任职。九个兄弟姐妹中,祝宗梁排行老二。他最初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被炸后改读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这所学校是法国天主教中学。那个年代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学生家境一般是比较优越的。如果在和平年代,祝也许沿着父辈的足迹升学、出国留学,然后回国效力,然而,爱国抗日的时代潮流改变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占据平津。天津南开中学、耀华中学等学校的一群中学生,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命运,奋起反抗,组织起“抗日杀奸团”的民间秘密组织,惩戒汉奸,袭扰日军,在沦陷区勇敢地掀起抗日风潮。

1945年抗战胜利后祝宗梁(后排右)与向传纬(前排左)、申质文(前排右)、马树棠(后排左)合影
1938年,刚满18岁的祝宗梁在弟弟祝宗权的介绍下,加入到“抗团”。此前的他,只是一个内向、喜欢照相、捣鼓无线电矿石机的学生。1938年1月,祝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抗团”机关里参加了宣誓活动,为保守秘密,他化名为祝友樵。祝宗梁当时参加“抗团”宣誓时的主持人是曾澈。曾澈另外还有个身份,就是军统派在天津站的秘书。
最初的天津“抗团”主要成员是一群十四五岁到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后来有很多社会名流子弟也加入其中,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和孙女郑昆仑,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书,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等,他们完全是凭着血气方刚的爱国热情,在对家庭保密的情况下自愿加入“抗团”的。因为年少缺乏经验,“抗团”在敌后沦陷区发起的行动中也曾数次遭受失败,被捕关押坐牢的成员很多,有些人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在八年抗战过程中,这个组织扩展到北平、上海,前后参加的成员约500人。
关于“抗团”的组织管理问题,据祝宗梁回忆,建有两个小组:行动组和技术组。技术组由祝负责,组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钱致伦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技术组的具体工作,“制造燃烧、爆炸器材,使用的是非安全火药,危险性很大,要特别细心。抗团在这方面曾发生不幸事故多起,深感痛心。祝宗梁细心、灵巧、思维敏捷,负责技术工作能推陈出新,有所改进。他把乒乓球穿孔,注入二硫化碳和黄磷的溶液给我们小团员”。
在天津,祝宗梁陆续和“抗团”成员们参加了火烧日军仓库、棉花站,刺杀河北省伪教育厅厅长陶尚铭、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等一系列行动,成长为一个胆大心细的“神秘杀手”。
说到程锡庚案,可以说不仅仅是“抗团”一次普通的惩戒汉奸的行为,对祝宗梁后来的人生影响也很大。正因为此案,祝离开天津,到了重庆,见到戴笠、蒋介石,也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为此后的人生际遇埋下伏笔。那是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一部美国影片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这位神勇的枪手就是祝宗梁。
刺程案后,重庆打来贺电,并汇来奖金六千元。这些奖金都留作团体经费。那时“抗团”全体人员都是义务性的,连津贴也没有。只有几位离开家庭,没有生活来源的才有生活费。后来因程案其中涉及到白俄和一位瑞士人的死,引起国际交涉。五六月间,曾澈带来重庆的命令,要参加程案的全体人员到重庆去。那时因为离学期期末很近,祝宗梁他们拖到7月份才动身。到重庆后,戴笠在海关巷一号接待了祝宗梁一行。8月上旬,戴笠引着祝宗梁一行在曾家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8月中旬,戴笠为程案要求祝宗梁和袁汉俊到香港自首。因为在天津有四个军统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这四人被日本硬说是“刺程犯”,并要求引渡。祝、袁去自首就是为了营救他们。戴笠还承诺:他与王宠惠(当时的外交部长)研究过,顶多把祝、袁两位送到伦敦。无论到哪里,他都会设法营救。还说此去不要暴露来过重庆。为了家属安全,会设法将祝、袁的父亲接来重庆。

1937年前后,曾澈在天津留影
祝、袁在香港一切自首的手续都是军统代办的。同时还向各通讯社、各报馆都发了通讯稿。当时祝宗梁曾详细地写了一篇程案的经过和有关的证据。事后英国香港当局一直未予答复。可是在天津,四个假刺程犯的引渡问题,一直都没解决。后来这事闹的不止是地方问题,扩大到英日两个政府间的事情。1939年底,日本不再理会天津英租界直接向英国政府提出苛刻条件,如立即引渡四个刺程犯;将李汉元(天津英工部局负责人,当初反对引渡的关键人物)撤职。与此同时,日本还照会英国政府立即封锁滇缅公路,否则就出兵占领英租界。最后,英国因欧战自顾不暇,对日屈服了。四个假刺程犯被引渡给日本。
近几年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对于生活环境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对环境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园林建设是人民所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国城市绿化建设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面积也在扩大,但是建设中依旧有一些夯待解决的问题,不利于城市环境的优化。所以,必须要提高重视程度,把树种的选择与色彩的搭配放到首要位置,增加生物多样性。我国对于这一项目的重视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并且给予了非常多的优惠政策,优良树种的引入给城市增添了新的生机,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所以说我国彩色树种在园林绿化中的配置具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祝宗梁和袁汉俊因英国香港当局不受理两人的自首,11月就回到了重庆。后来天津“抗团”屡遭破坏,元气大伤。1940年春,孙若愚到了重庆,与沈栋、袁汉俊、祝宗梁相聚。大家都为天津“抗团”被破坏感到无比惋惜,决定在上海开展新战场。
1941年10月孙若愚在上海试验炸药时炸断左臂,后又被捕。原定祝宗梁和袁汉俊、申质文、向传纬四人补充,后来因祝宗梁要参加暑训班,所以他们三人就先去了上海。关于这次暑训班,祝宗梁回忆说,在1942年8月间,因为在沦陷区“抗团”屡遭破坏,在内地的“抗团”人员就想大家聚会一次商量对策。我们设想举办一个夏令营。这事由杨国栋与军统商量,结果就成了暑期训练班了。地点在贵州息烽,并按照军统训练班的方式举行。我去上海半路折回到了息烽。有人不愿参加这次活动,以为这就是要参加军统。我们曾澄清,这只是借地举办,“抗团”与军统性质不同,但在抗日这方面是一致的。最后二十六人参加了此次暑训班。在此期间,“抗团”领导小组共同拟定了一个规划,主要内容有在重庆建立“抗团”总部,暂由祝宗梁负责,在安徽界首建立联络站,由沈栋等负责。
暑训班结束后,这年秋天去沦陷区工作的人员陆续出发。此时孙若愚从上海回到重庆,以后改为由孙若愚任“抗团”总部书记。祝宗梁为办理军统取款事宜前往上海,他到河南商丘买了张“良民证”改名张志宏,在1943年1月8日到了上海。结果因从天津来的郑有溥叛变,襄阳南路的联络点暴露,祝和申质文、向传纬等三人相继被捕,关押在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审讯。也正因为郑有溥叛变,天津“抗团”与上海“抗团”同时遭破坏,袁汉俊被捕牺牲。上海被捕的三个“抗团”成员受尽酷刑后,日本人依然一无所获。到了4月底,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毛森保释。祝和其他人则被 “教育”释放了。
1943年冬,毛森告祝宗梁说,戴笠要祝回重庆。后来杨国栋、夏逸农两人到上海,祝宗梁将上海“抗团”移交给杨国栋,回了内地。
“抗日杀奸团”与军统的关系
关于“抗日杀奸团”与军统之间的关系,“抗日杀奸团是军统的外围组织”这一说法长期流传,为此祝宗梁一再叫屈。他说,“抗团”内的确有过军统人员参加,而且在“抗团”担任过重要职务,但这不能说明“抗团”隶属于军统。关于这一点,当年军统的“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恭澍在《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版改名为《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中对军统与“抗团”的关系作了比较准确的分析。此书1984年2月在台湾出版,登载在《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二期。他认为,在《戴雨农先生传》和《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抗日杀奸团”的大段记载,只是衬托之作,不足以表达该团的基本精神,也没有突出该团精义之所在。军统为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抗日杀奸团”则是青年爱国组织,属于民众团体。两者构成关系的基础在于爱国青年分子需要国家抵御外侮的方针导向,而政府方面则在于增加一份抗战力量,并没有所谓的“外围”和“核心”之分。青年学子既无名义也不受薪,与军统局所运用的情报路线性质完全不同。
祝宗梁一再申明:“抗团”与军统最大的区别是“抗团”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军统除此外还有是内战的工具。在抗战期间,“抗团”从未参与军统指派调查学生的各种党派活动,而且自觉抵制这种工作,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目的。日本投降后,“抗团”就解散了。只有几个人仍与军统有关系,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抗团”无关。
1946年春,祝宗梁请求军统同意,将孙若愚、杨国栋调来重庆研究“抗团”去向问题。会议决定“抗团”解散。这时戴笠乘飞机失事,这对解决“抗团”去向也是有利的。“抗团”解散条件是:(1)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活动。(2)为了解决一些暂时找不到公职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暂发十八人的工资,在上海六人。
关于“抗团”解散后自己的去向,祝宗梁说,“‘抗团’的解散会议还没结束时,军统方面叫我到美国去,于是剩下的任务由孙若愚和杨国栋完成。1943年旨在共同对日作战的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军统与美国方面有过协定,规定将来任务完成后,由美国出钱送四十个有功人员去美国深造。这第一批二十人中就有我的名字。我不是中美合作所的,只是军统方面考虑到因抗战我荒废了学业,为我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军统就假造一个报表,要我照抄。我就跟着去了。这二十人到了美国,有的去受训,有的什么也没做。我选的是读书,学校是堪萨斯城大学(Kansas City University)。只读了一年就通知我回国。1947年夏我回到上海。那时陈泽永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教书,地点在上海复兴中路1195号。由于他的介绍,学校也同意我去任职。随后我去南京见到毛人凤,当面向他请求去教书。他同意。出来后又遇到潘其武,他要我去警察总署工作。我拒绝了他,我说我决定去教书。
祝宗梁也谈了他回国后不愿再与军统来往的原因。他说,在抗战期间,参加抗日工作是应尽的义务,现在胜利了,军统这种工作不适合我。何况军统的名声又是那样的坏。再有国民党又是这样腐败无能。我觉得我必须急流勇退。回上海后,军统(这时已改名为保密局)来信要给我诠叙中校的军衔,还寄来一张假造的填表的内容叫我照抄。我未填表,也未寄回。以后又寄来一个通知,叫我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室报到。我也没去。最后寄来一枚抗战纪念章和一枚六级(或七级)云麾勋章。这件东西我收到了。从此以后,我与军统没有任何来往,更未接受过一分钱。
长达十六年的牢狱之灾
抗战胜利后,祝宗梁与同为“抗团”成员的张同珍喜结良缘。张同珍又名张龙桢,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萧山。她在天津耀华中学读初三时,校长因拒绝日本人把英文课改为日语课的要求,在回家的路上被日本特务枪杀惨死,因此张与同班好友孙惠书、冯健美、夏志德一同加入“抗团”,决心以一己之力为抗日效力。1944年,祝从上海去内地的半路上遇到张同珍。她是从天津去内地。于是两人同行,逐渐熟悉了解,互生好感。
1947年祝宗梁在上海教书后,张同珍也从天津来到上海生活。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已久的祝宗梁,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他说,抗战期间,知道了国共合作。在解放军进上海时,对共产党印象很好,因为亲眼看到解放军进城睡马路,住学校临走时还打扫得干干净净。
也正是对新生政权的拥护,祝宗梁利用自己之前的关系,为新政权的巩固出力。对这段经历,祝并不愿多提。我们只是隐约知道他除了自己做工作外,还向有关部门推荐“抗团”的旧友叶纲骞(以前是天津航业公司小开)到香港做工商界有关人士的工作,在抗美援朝期间遭遇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从香港运送重要战略物资铜到大陆。也许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在解放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祝均“幸免于难”,1953年,他被有关部门安排到上海中学担任高中数学教师。虽然仍属于“受控制使用”,不能担任班主任,但此后的六年间,祝还是过了相对平静的日子。夫人张同珍1953年也响应动员家属出来工作的号召,报读中师。后来她一直在家附近的朱行小学教书。

但好景不长,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越绷越紧的强化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祝宗梁平静的教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了。1959年9月25日,刚开学不久,他正在上课,被临时叫走,说是有人约请面谈。当时祝根本没想到会被捕。一开始他被关在车站南路第一看守所,关了9年都未判。最初审讯员让他交待当年接到军统三封信后,有没有别的情况隐瞒未报。几次下来,审讯方对祝说没有别的情况不相信,质问 “军统对你这么好,怎可能没有往来”。两年后,审讯员才说出了所谓的“疑点”,一是家里有张学生证,是祝迫害学生的铁证。其实,那张学生证是一个叫崔铎的学生暂留在祝家的。这个学生当年因交不起学费请求祝代为向校方求情缓交或免交,祝几次请求校长未果。后来崔铎中断学业回了苏北。他求学时为买米上交学校的学生证被退回,暂时留在祝家,祝准备以后还给他。第二则是解放前祝曾和杨国梁去上海市政府调查室领制服布。这两个疑点祝宗梁解释清楚后,持续四年的审讯也告一段落,但既不结案,也不放人。1968年,祝被一个审判员宣布判决——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从第一看守所转到提篮桥监狱。祝宗梁在提篮桥刑满后被送到安徽白茅岭监狱劳动改造,做泥瓦工。
当时祝宗梁住上海中学住宅区7号,他被抓后,家里一下子乱了。他女儿张梅格说,只记得放学后的一天,一批人到家里把窗帘都拉起来,抄家,她看到逮捕证上写着“祝宗梁”,而爸爸平常用的名字是祝子云,妈妈当时坐在一边发呆。祝家的厄运并未结束,“文革”爆发后,一直小心谨慎地教书持家的张同珍又因 “破坏毛主席宝像”的罪名被造反派揪斗,被游街示众并关押十年,1979年才平反出狱。祝家姐弟俩在父母均遭牢狱之灾后,无所依靠,只能靠远在外地的大姑妈、六叔、七叔的接济度日。张梅格曾报名下乡,因小时得过支气管炎,体检不合格,只好在社会上游荡,做临时工养活自己。比姐姐小5岁的弟弟当时才念初中,也只能到郊区的吴泾江川一带下乡。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很高兴,让公安部释放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1975年12月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祝宗梁也在1976年出狱,拿到 500元安家费,回来分配到上海县环保设备厂工作。上海中学1978年复校后,祝宗梁想回上中教书,但受“左”的思想干扰,未能成功。祝出狱后,曾不断写信申诉。 1980年6月2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原判认定祝在解放前夕召开反革命应变会议,解放初期包庇特务分子潜逃的犯罪情节,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原判对祝宗梁处刑不当”。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68)沪军审(预刑)字第175号判决,澄清事实真相,还了祝的清白。

晚年撰写抗团回忆录
祝宗梁后来一直在上海县环保设备厂工作直至退休,虽然有人提出重新为他安排工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1977年恢复高考后,祝在工厂办厂校,教青工补习高中数学。上海县工业局系统其他地方的青工也闻讯赶来,祝还请了上海中学的老同事来上课。其中很多青工后来都考上大学,他们至今对祝老充满感激,在博客中写到对祝当年的教育 “终生难忘”。
值得一提的是祝宗梁在1981—1989年任上海县(后与闵行区合并)政协常委时,有多个提案,其中一个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最具“含金量”。
祝宗梁在晚年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搜集“抗团”资料,撰写“抗团”回忆录。他说,抗战时期曾发生的事情,应该把它写下来给后人留作纪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钱宇年就曾搜集整理过部分资料。可惜未曾整理成文,钱就因病去世。2006年在美国的沈元寿和孙惠书来信说,他们认为大家都已是风烛残年,这项未竟工作,再拖下去,可能有永久丢失的危险。于是他们找到在天津的刘永康、马桂官和在北京的叶于良、孟庆时等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将钱宇年过去搜集的资料加以补充整理,并由祝执笔编写成 《抗日杀奸团回忆录》。2007年在七七事变七十周年时,把它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有关人士和“抗团”同志的后代。当时因无力承担公开出版的费用,这本书只能自费印了200册。祝老女儿告诉我们,因为父亲的“慷慨”,这本册子家里目前只剩一个孤本了。最令祝欣慰的是2011年8月,在“关爱老兵网”的大力支持下,祝到天津、北京等地拍摄口述历史纪录片,得以到南开中学、工商学院附中等地故地重游,并与老战友刘永康、马桂官、叶于良等人重聚。本来还有到台湾与几位旧友聚首的计划,可惜10月的一天在小区外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坏了股骨头,此计划只能放弃。善良的老人尽管收入拮据,看那小伙子可怜就让他走了,自己承担了所有医药费。对于自己面临的困难,如退休金少,老伴因患老年痴呆风瘫在床已过花甲之年的女儿照顾两个高龄老人力不从心而又请不起住家保姆等,祝保持着一贯的淡定,他说很多人的苦难比我的那点遭遇不知沉重多少倍。这令人感佩。
回顾自己充满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祝宗梁感到无怨无悔。他说,“抗团”的那点事,在抗战历史中只是沧海一粟。但他们在敌人侵略面前,不甘受辱,勇于斗争。他们无所企求,不怕牺牲,威武不屈的精神,应予称赞。还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国过去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岁月,即使将来祖国强盛了,周边也未必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