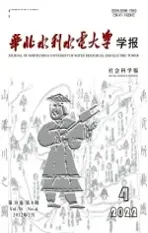禅宗行为艺术公案浅析
2012-08-15刘冠美
刘冠美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四川成都610072)
禅宗行为艺术公案浅析
刘冠美
(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四川成都610072)
通过对禅宗行为艺术公案的解剖,指出不立文字、不离文字是禅宗行为艺术的基本原则,其显著特点是启发式教学、截断思维、肢体语言与口头语言相结合,道具的合理使用。
禅宗;行为艺术;特点
一、“不立文字”、“不离文字”是禅宗行为艺术准则
对行为艺术通常的解释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行为艺术必须包含以下4项基本元素: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
佛教开创之初,就为行为艺术定了调,释迦牟尼“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1](P1)。在这里,释迦牟尼不仅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行为艺术的基本纲领,而且亲自做了行为艺术的示范:“拈花示众。”有时间、有地点、有动作、有交流,四大要素齐备。随后“拈花微笑”这一招牌动作不胫而走,为芸芸众生所膜拜。实际上,“拈花”者,释迦牟尼也,“微笑”者,迦叶尊者也,通过动作、交流,施者、观者、环境融为一体。
慧能不识字,在《坛经》提出“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同时又说“不立两字,亦是文字”,已有“不离文字”之意。不立文字是不拘泥于文字、不执着于经典,“教外别传”重在启发式教学,“不立文字”是“教外别传”的核心。禅悟不可说、不能说,而禅宗的行为艺术是靠肢体表达思想,靠语言对情节串接、解读,言语文字是表意的工具,要得意而忘言。“心之妙不可以言语传,而可以语言见。”不立文字,忘言得性,是遮诠;不离文字,得性忘言,是表诠。
二、禅宗行为艺术公案
公案既是挡住去路的铜墙铁壁,又是截断后路的万仞悬崖。禅师们的行为艺术公案,或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槌;或持叉张弓,辊球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问一答,一唱一提;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等等机用,莫不备载。分宗列派,各有门庭,目击道存,指掌意喻,合宗门妙旨,得教外真机,各类行为艺术公案花样百出、精彩纷呈。
(一)达摩的一履棺
“后三岁,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祖于糙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祖曰:‘西天去!’云归,具说其事,及门人启圹,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举朝为之惊叹。奉诏取遗履,于少林寺供养。至唐开元十五年丁卯岁为通道者窃在五台华严寺,今不知所在。”[1](P46)“履”者,道也。“携履西归”和“空棺遗履”均着眼于道。后世对此行为有疑问:“达磨西归,手携只履。当时何不两只都将去?”回答是:“此土也要留个消息。”又问:“一只脚在西天,一只脚在东土。着甚来由?”[1](P763)留待后人思考。履履各异,“携履西归”的“履”是东土文化,“空棺遗履”的“履”是西土文化。
(二)傅大士的时装秀
中国维摩禅的大师——傅大士在讲解儒、释、道之区别时,着实玩了一把时装秀和行为艺术,《五灯会元卷2》有如下记载:“大士一日披衲(僧衣)、顶冠(道冠)、恿履(儒履)朝见。帝问:‘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恿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1](P118)傅大士打的哑谜是:“冠”表示思维,“履”表示方向,“衣”表示生存。傅大士颇有些指鹿为马的味道,但他最终亮的相是儒、释、道“三合一”的法相,儒为基,道为首,佛为心。如果说“桥流水不流”是“参话头”,那“披衲、顶冠、恿履”则是参行为、布迷局。傅大士活学活用这两种参悟手段,已经达到炉火纯青、挥洒自如的境界。
(三)当头棒喝
禅宗有棒喝传统,“临济入门便喝,德山入门便棒”[1](P634),棒喝即不立文字,是一种强刺激,截断思维。禅宗用棒喝否认经典、横扫权威、解构语言。
“喝”有四种形式:“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罕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1](P642)“喝”法各有不同,“金刚宝剑”,当头截断,不容粘搭,摧毁疑情;“踞地狮子”,不立窠臼,毫无依倚,振威一喝,令人丧胆;“探竿影草”,修行测试,双向探究;“一喝不作一喝用”,对以上三喝总结,意在一喝中,实出一喝外。
“棒”也有四种形式:“有时一棒作个漫天网,打俊鹰快鹞;有时一棒作个布丝网,遭蚬捞虾;有时一棒作金毛狮子;有时一棒作虾蟆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么生商量?你若缁素得出,不妨拄杖头上眼,开照四天下。若也未然,从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画图。”[1](P705)
对棒喝的作用,志璇禅师有说法:“德山入门便棒,意旨如何?”师曰:“束杖理民。”曰:“临济入门便喝,又作么生?”师曰:“不言而化。”曰:“未审和尚如何为人?”师曰:“一刀两段。”[1](P1080)
“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1](P373)“道得也三十棒”是不许学人直接说出悟境,以免触犯自性不可说之忌讳;“道不得也三十棒”,是要截断学人之心识活动,使其在急遽仓促间不假思索,于当下见性。棒喝之法往往交互在一起使用,后来,禅林逐步发展出一套相对稳定的接引学徒的手段和方式,或表达自己的见地,或唤醒他人自悟,达到舍执除偏、是非两忘的绝对圆融的境界,以至师徒互棒互喝亦蔚成风尚。
(四)刀断一指
“其夜山神告曰,不须离此山,将有大菩萨来为和尚说法也。果旬日天龙和尚到庵,师乃迎礼具陈前事。大龙竖一指而示之,师当下大悟。自此凡有参学僧到,师唯举一指无别提唱。有一童子于外被人诘曰,和尚说何法要,童子竖起指头,归而举示师,师以刀断其指头,童子叫唤走出,师召一声,童子回首,师却竖起指头,童子豁然领解。师将顺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言讫示灭。”
同样一指,为何大龙竖得,天龙也竖得,唯独童子竖不得?大龙示范在前,天龙悟道在后,而童子就是单纯模仿。天龙一指禅也是直指人心的一种方法,“一指”本身没有意义,只是象征“直指本心”,断指使童子明白,竖指只是一种提示,提示返见自性。指头的妙用不在指本身,而在指头所示的对象。若“寻指而亡月”,则与道相背。
(五)打地、打坐具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领旨,常晦其名。凡学者致问,唯以棒打地示之。时谓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后致问,师但张其口。僧问门人曰:‘将如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地,意旨如何?’门人即于灶内取柴一片,掷在釜中。”[1](P181)
以势示禅,以棒打地,棒虽藏但口却在,照样可以口打地,打地和尚的门人深得其精髓,用掷柴釜中作答。这里“打”的含义、“地”的含义值得深究。《说文》对“打”的解释是:“击也”,由此衍生出多种释义如:攻击、放出、做、造、拨动、揭破、提起、涂抹、开出、捆扎、结合、获取、除去、计算、使用、玩耍等。管子在“水地篇”中对地有明确定义:“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显然地者也是所有问题、疑虑的答案荟萃之所,打地和尚的“凡问皆打地”的行为艺术就可理解了。
瑞州九峰希广禅师,游方日谒云葢智和尚,乃问:“兴化打克宾,意旨如何?”智下禅床,展两手吐舌示之。师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风力所转。”又问石霜琳禅师,琳曰:“你意作么生?”师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只是不知落处。”又问真净,净曰:“你意作么生?”师复打一坐具。净曰:“他打你也打。”师于言下大悟。净因有颂曰:“丈夫当断不自断,兴化为人彻底汉。已后从教眼自开,棒了罚钱趁出院。”后住九峰,衲子宗仰[1](P1158)。
同一动作,不同的禅师的解释完全不同。葢智禅师着眼于动作的过程,在开打到将触及坐具的这一时段,对空气的扰动,即有“此是风力所转”之说;石霜琳禅师着眼于动作的对象,即有“好一坐具,只是不知落处”的言论;真净禅师着眼于动作的主客体,你打坐具,坐具打你,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方有“他打你也打”的妙论。
(六)圆相
仰山有九十七圆相,画圈加字、加图案,后人明州五峰良和尚总结九十七圆相共有六义:“曰圆相,曰暗机,曰义海,曰字海,曰意雨,曰默论。”圆相为体,其余为用。曹洞宗的基本理论的“五位”,是以理为正位,事为偏位,“正”、“偏”组合成:“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正中到”,并分别以五圆相对应“五位”:□□⊙○●[2](P100),其象分别是:上阴下阳、上阳下阴、阳中阴、全阳、全阴。
“马祖令人送书到,书中作一圆相。师发缄,于圆相中着一点,却封回。”(忠国师闻,乃云:“钦师犹被马师惑。”)[1](P68)画圈者,圈为法界,圈内万物皆空,圈外空皆万物;着点,应是点在圆心,构成向内收缩,一即是佛理,一即是禅道,“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也。忠国师的看法是,道钦中了马祖的圈套,道钦正确的作法是回函一张白纸: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一切无相,何来圆相?进而索性无信纸无信封,令弟子空作递交状作为回信,类似慧能对神秀的回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师入园取菜次,乃画圆相,围却一株。语众曰:‘辄不得动着这个。’众不敢动。少顷,师复来,见菜犹在,便以棒趁众僧曰:‘这一队汉,无一个有智慧底。’”[1](P144)此公案有点类似脑筋急转弯。
禅师画圈围菜,并交代不准动菜,徒弟们照此办理,反被暴打一顿,斥之为弱智,聪明的做法是去圈取菜,保证获得禅师称赞。禅师的正命题是“圈在菜在”,显然他力图让徒弟悟出的反命题是“圈失菜去”。
(七)张弓架箭、空弦三响
抚州石巩慧藏禅师,本以弋猎为务,恶见沙门。因逐鹿从马祖庵前过,祖乃逆之。师遂问:“还见鹿过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猎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个。”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几个?”祖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无下手处。”祖曰:“这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师掷下弓箭,投祖出家。[1](P160)
袁州崇胜院珙禅师,上堂,举石巩张弓架箭接机公案,颂曰:“三十年来握箭弓,三平才到擘开胸。半个圣人终不得,大颠弦外几时逢?”[1](P1248)
马祖深谙启发式教学的真谛,一反历来宗教呆板的陈腐气,合理运用逻辑与概念,张弓射箭,由“射一”到“射群”,再到“自射”,在逻辑推理上,先将命题进行量的扩张,动摇提出命题者的信心,再抛出反命题,最终完成开悟。
“漳州三平义忠禅师,福州杨氏子。初参石巩,巩常张弓架箭接机。师诣法席,巩曰:‘看箭!’师乃拨开胸曰:‘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又作么生?’巩弹弓弦三下,师乃礼拜。巩曰:‘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遂拗折弓箭。后参大颠,举前话。颠曰:‘既是活人箭,为甚么向弓弦上辨?’平无对。颠曰:‘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1](P182)
石巩禅师继承马祖的衣钵,不讲繁琐、玄奥的道理,专用“张弓架箭”接引学人,并把“张弓架箭”的公案推演为“空弦三响”的公案,把对箭的射的动作分析:“射一”、“射群”、“自射”,转为对射的效果分析:“杀人”、“活人”。而大颠禅师对石巩以空弦三响解释“活人”不以为然,其禅理是即是“活人”,没必要在弓箭上做文章。
(八)“杖”的学问
智海本逸禅师道出“杖”的妙用:“这拄杖,在天也与日月并明,在地也与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御恶。在衲僧也昼横肩上,渡水穿云,夜宿旅亭,撑门拄户。且道在山僧手里,用作何为?要会么,有时放步东湖上,与僧遥指远山青。”[1](P1017)
对杖而言,王侯代鞭,百姓防身,僧侣挑担,渡水夜宿,撑门拄户,显然这都是杖的实用,“放步东湖”是眼界,“遥指山青”是境界,而这些就是杖的妙用。
“杖”的运用在《五灯会元》中有精彩描述:“日芳上座,僧问:‘如何是涵盖乾坤句?’师坚起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断众流句?’师横按拄杖。僧曰:‘如何是随波逐浪句?’师掷下拄杖。僧曰:‘三句外请师道。’师便起去。”[1](P999)日芳禅师用杖的“竖”、“按”、“掷”解释云门三句。
为了检测新系统的运行效果,于某煤矿生产企业内针对新系统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试运行,结果发现,应用新系统后,皮带机电控系统的设备故障率显著降低,使用期间内,并未出现由于电控系统故障而导致的设备停机情况,且相较于老系统,新系统的平衡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原系统在启动或变速的过程中会出现由于震动导致的煤屑散落情况,而新系统运行下此类问题并未再次出现,有效降低了故障发生概率。
就动作的方向性而言,“竖”是直立,“按”是水平,是控制;“掷”是无方向、去方向、不控制。
“涵盖乾坤”是乾坤并万象、大地即真如,“竖”是指向,即指理又指事。理事互彻,理在事中,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截断众流”是阻绝意路、意象对峙,最终顿悟,“按”的方向与“竖”的方向垂直,是对“竖”的截断,“按”和“竖”构成对峙。
“随波逐浪”是随缘适性、随机接引,“掷”的动作类于“随”和“逐”意涵“去”和“无”,杖掷自然阔,随缘天地宽,应机宇宙通。
三、禅宗行为艺术的特点
(一)启发式教学
禅宗的启发式教学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过程具有发散性和层次性,途径具有多元性和反思性。透过宗师举止、语言文辞的暗示性与多义性,去领会宗师的悟心。棒喝交驰、打地画圆、刀劈断指等方式是无语之语的另一种传释方式。禅宗大的行为艺术公案是富有原创性的思维体操,善于坚持禅宗的既“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传统,善于把遮诠与表诠巧妙地结合起来。
(二)截断思维
“截断众流”指截断奔驶疾驰的情识心念,指示参禅者不用语言意识把握真如,而要返照自心,痛激性灵,以获得顿悟。毛泽东对禅宗的棒喝之法情有独钟,在“反对党八股”中对喝的解读是:“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深谙喝的真谛。
(三)肢体语言与口头语言相结合
西方的行为艺术仅有肢体动作和道具,没有口头语言相配合,往往让人看不懂,如堕十里云雾。禅宗的行为艺术讲究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紧密配合,两者是场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时口头语言点破动作的真谛,有时动作对口头语言作注脚,两者有机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教案,所谓“图文并茂”是也。在傅大士的时装秀中,一问一答,问用口头语言,答用肢体语言,梁武帝的设问对逻辑的展开、情节的演绎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梁武帝的设问,傅大士一个劲不停地做动作,人们很难理解他借行为艺术对儒、释、道的诠释。
(四)道具的妙用
在行为艺术中道具是必不可少的。它加强了意蕴的表达,更生动、更形象,有助于学人的体察和领会。禅宗的道具,既是随机取物,天地乾坤,信手拈来,无一不可;又是因境制宜,有的放矢。禅师在用“杖”解释云门三句,源于杖的细而长、便于指向的功能,若用粗而短的道具,则指向的功能就减弱了。
有道具无动作是死道具,有道具有动作是活道具;有动作无道具是干瘪的动作,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动作有道具是有生命力的动作。如“杖”的道具使用,会把学人的注意力吸引、集中在道具上,从而使学人开悟,破解谜题。禅师们把动作与道具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教学服务。
(五)故弄玄虚、票房毒药
由于有“不立文字”的金字招牌,又是释迦牟尼开先河,一时间禅宗教学中,行为艺术泛滥成灾,大家群起仿效,你喝我打,怪招迭起。
一些清醒的禅师开始反对胡喝、乱喝、盲喝:“师应机多用喝,会下参徒亦学师喝。师曰:‘汝等总学我喝’,我今问汝:‘有一人从东堂出,一人从西堂出,两人齐喝一声,这里分得宾主么?汝且作么生分?’若分不得,已后不得学老僧喝。”[1](P642)这里提出“喝”要分宾主,宾看主,主看宾。宾看宾,主看主。
建州崇梵余禅师对胡喝、乱喝颇感汗颜,“僧问:‘临济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难逢作者。和尚今日作么生?’师曰:‘山僧被你一问,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1](P1031)黄檗惟胜禅师却对花样百出的“行为艺术”颇有微词:“临济喝,德山棒,留与禅人作模范。归宗磨,雪峰球,此个门庭接上流。若是黄檗即不然,也无喝,也无棒,亦不推磨,亦不辊球。前面是案山,背后是主山,寒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门。于此见得,得不退转地。尽未来际,不向他求。若见不得,偌俸上味,翻成毒药。”[1](P1116)
一种倾向总是掩盖另一种倾向,做任何事情都有个度,超过这个度,事情就走向反面,变了味的禅宗行为艺术,不但不能促进对禅理的参悟,反而成了票房的毒药。
[1][宋]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方立天.禅宗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Art Cases of Zen of Buddhism
LIU Guan-mei
(Dongfengqu Management Office,Dujiangyan in Sichuan Province,Chengdu 610072,China)
Performance art of Zen of Buddhism is indepenndence-of-words and depenndence-of-words that it is the basic principles.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re the heuristic teaching,truncated thinking,combination between body language and verbal language,rational use of props,based on anatomy of the performance art's cases of the Zen Buddhism
Zen of Buddhism;Performance art
B946.5
A
1008—4444(2012)01—0030—04
2011-10-20
刘冠美(1946—),男,辽宁黑山人,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教授级高工。
(责任编辑: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