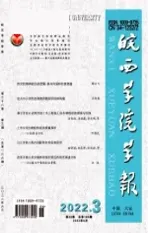鲁迅的翻译特色探析——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
2012-08-15汪龙平沈传海
汪龙平,沈传海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009)
鲁迅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也是杰出的翻译家,是一位希望通过翻译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思想型翻译家。鲁迅一生翻译并介绍了大量的外国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的翻译涉及到14个国家的100多位作者,近300万字。但国内学者冷落了对翻译家鲁迅的研究,国内研究专著仅有3本,根据《鲁迅研究数据索引》,至1981年12月,有关鲁迅翻译研究的文章只有54行[1](P265),1981-2005年间仅发表了30多篇文章。鲁迅翻译思想的核心是“直译”,此策略遭到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鲁迅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普通的读者很难喜欢。面对他人的误解和非难,鲁迅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用自己的实践行动寻求“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想。
本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从译者对需要的适应、选择这一视角出发,探讨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特色,以期对作为翻译家鲁迅的翻译思想做出一种全新的探寻和挖掘。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主张“译者为中心”。该理论是建立在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基础上,也就是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认为翻译活动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适应——是译者选择性的适应;选择是译者适应性的选择;译者集“适应”与“选择”于一身[2](P101)。“译者为中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适应和选择——对内和对外,即对能力、需要和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发挥译者能动性,实现译者目的。
一、对译者自身“能力”和“需要”的适应和选择
胡庚申教授认为,“为了提高译品‘整合适应选择度’的目的,译者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那些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相匹配的作品翻译”[2](P101)。在文本的翻译方面,鲁迅灵活、创新地使用各种翻译策略,显示了鲁迅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超群的能力。如鲁迅翻译对话,有时用白话文,有时却用文绉绉的文言文,可以看出鲁迅在翻译时充分考虑到了说话者的身份地位和说话者的语言风格,这种游刃有余地驾驭语言的能力,与鲁迅深厚的古文功底、渊博的知识和对白话文的感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不只翻译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需要什么,他就输入什么。无论从第一部科学幻想译作《月界旅行》的《辩言》里的“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还是到《域外小说集》序中提及的“改造社会”[3](P151),鲁迅把翻译同社会变革和国民命运联系到一起,时刻以社会需要、国民需要为己任。他认为改造国民思想、挽救民族危亡,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文化,摒弃陈腐的中国传统文化。于是,鲁迅翻译并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希望翻译“弱国”的文学作品具体生动地向国人展示面临“亡国”危机的可悲境遇,唤醒国人正在沉睡的灵魂,引起大众对作品产生共鸣,激发人们对革命的热情和信心。对鲁迅而言,翻译不仅是其生存、发展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本能需要,也是多维度地适应社会、读者和时局等内在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以及对翻译事业的兴趣,对理想的追求等等各种需求。
二、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外在的因素是指“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译者和译文需要适应的多种因素的集合”[4](P174)。翻译过程如同语言交际一样,是个动态过程,是个不断选择、适应的过程,鲁迅翻译活动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特殊地位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一)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
由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性也随之逐渐丧失甚至被抛弃。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洗礼的国人认为,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东西,包括先进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等。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开始提倡直译,并践行直译。从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始到1935年《死魂灵》的翻译,鲁迅都明确指出自己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直译”。“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二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5](P287)
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国“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当时,许多新文化人认为应当大力倡导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抛弃古奥难懂的文言文,若白话文表述无力,要向“欧化”开放,“欧化”国语。傅斯年曾在《性命古训辨证》引论部分提到:“思想不能离开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要想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欧化,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欧化,这是倡导欧化语言和翻译腔的一个深层原因。这里的“欧化”就是“直译”,鲁迅强烈地意识到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从异质文化中吸取力量,“直译”毫无疑问是首选翻译策略。鲁迅的“直译”表明的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语言符号的尖锐否定和对西方文化及其语言符号的基本肯定而提出来的。只有“直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才能引进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6]。这也表明翻译策略是由一定的历史文化决定,反映出译者优先考虑的因素,选择性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意在适应,适应意在生存。
(二)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特殊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时期。一向处于边缘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第一次占据着中心位置[7](P1),著名以色列作家也是翻译家埃文·佐哈尔在多元系统理论中提到,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会带来翻译规范、行为模式、方针策略等一系列变化。当翻译从边缘转向中心地位时,模糊了翻译和创作的界限,译者乐意打破本国的文学传统规范,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更接近原文。鲁迅作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代表,以“直译”为主要的异化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关注的是翻译本身之外的政治状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
三、对汉语言发展的适应和选择
通过“直译”,把外国的语言形式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改造传统汉语,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以弥补早期白话文在思维和表达方面的不甚精确的缺陷。当代法国著名的理论家、拉美文学及德国哲学的翻译家贝尔曼指责以往翻译对“异”成分的压抑,他认为优秀的译文应该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中的“异”怀有敬意。正因为这种“异”的翻译让我们有幸领略到原语的语词,以古希腊悲剧为例,如果利用各种变形系统翻译古希腊悲剧,我们就无法欣赏古希腊悲剧的语词。德国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荷尔德林直译了希腊诗剧,给德语带来了优美的音调、节奏和韵律,使德语更具美的风致和曲折丰富的表现力[8](P218)。通过“直译”,吸收外来语的长处和精华,能给本国语增添新的质素,从而扩大本国语的“界域”,让本国语的表现力更加丰富。
文言文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新的白话文还不够完善,有必要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创作出新的词法和句法。鲁迅的译本中夹杂了许多东洋新名词和欧化的词,如“学术”、“进步”、“文明”、“哲学”、“教授”、“造物主”、“名誉”等;在词法上,鲁迅秉承“悉如原音”的理念,音译了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如“伊凡洛夫”、“斯巴达”、“波士顿”、“俄罗斯”等。在句法上,鲁迅采用了欧化的标点符号,引入了破折号(——)和省略号(……)。!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他用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用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9](P157)。
清代文章小说里已经使用了句读,熟悉逗号、句号的使用。问号(?)、感叹号(!)的运用也“近已习见”,但仍激起了时人极大的反感。可想而知鲁迅重点输入前所未有的破折号和省略号在当时是多么大的勇气和创举。有人甚至说是欧化的标点符号拖累了《域外小说集》的命运。为了更好地揭示鲁迅引入欧化标点符合对现代汉语发展的贡献,我特地搜寻了不同时期两位译者鲁迅和陈之对《死魂灵》第四章里同一句话的翻译,并重点对比了对标点符号——省略号和破折号的使用。
就是有用……这是我这边的事情了——一句话,我有用处[10](P165)。
有用就是了……这是我的事情,——总而言之,有用[11](P85)。
发现鲁迅和现代译者陈之对标点符号的使用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句话发生在奇奇科夫请求诺兹德廖夫把许多已经死了还没有注销名字的农奴转到自己的名下,可又不想说出要这些死农奴名字的真正用途。在诺兹德廖夫的一再追问下,迫于无奈,奇奇科夫说“有用就是了……这是我的事情”。省略号“……”形象地揭露了奇奇科夫的狡猾,别有用心,不想说出要死农奴名字的真正缘由。破折号“——”表稍有停顿,跳过要说的话题。对鲁迅输入的“欧化”标点符号由反感到现代汉语的普遍使用,无疑是鲁迅勇敢的坚守。正因为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丰富了原有的汉语语言知识,促进了汉语语言发展,为现代汉语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四、结束语
鲁迅的译作,虽然读者态度冷淡,同行抨击,然而译者鲁迅的坚守,选择性适应了当时的特殊翻译生态环境,能动地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译者有所为,作为译者,不仅要培养个人能力,提高整体素养,还要适应整个翻译生态环境。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资料索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鲁迅.月界旅行·辩言[A].鲁迅全集(第1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A].鲁迅全集(第1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贺爱军.鲁迅“硬译”的文化解读[J].上海翻译,2009,(4):73-73.
[7]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社,2006.
[8]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9]鲁迅.域外小说集[A].鲁迅全集-略例[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鲁迅.死魂灵[A].鲁迅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1]陈之译,齐豫生.世界文学名著宝库[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