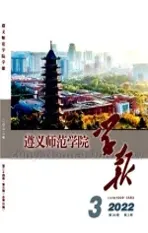语言视差的多维理据及其翻译策略
2012-08-15杨司桂李华琴
杨司桂,李华琴
(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所谓视差(Parallax)是指“人们的大脑对所观察事物产生的判断与实物有所不同”[1]。视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用一把尺子去测量木头的长度永远达不到绝对的精确,得到的测量结果与实际长度总存在一定的误差;用秤去秤一个物体所得到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也存在一定的误差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视差”现象,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另一种“视差”,即“语言视差”,却被人们所忽视。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不仅表现现实,还扭曲客观现实”[2]。扭曲客观现实也就意味着语言与客观现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视差”。作者将从符号因素、语言因素以及认知因素对语言的视差进行诠释,并就如何翻译带有“视差”性质的语料提出与之相对应的翻译策略。
一、语言视差的符号因素
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是对客观现实的表征,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使用的汉字便是如此。例如,“人”,就像一个人双腿叉开站着,“雨”字有“四点”,像似在下雨;而“日”和“月”酷似天上的(⊙)和()。拼音书写文字亦不例外,根据希伯来语的早期记载,字母“a”就是对牛头的写实,“b”是对马的模仿,“g”像骆驼的头像,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日久天长,就很难看出早期图像对文字留下的痕迹。这样,语言符号对客观现实的表征关系势必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或曰“视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以及法国符号学家德里达(Derrida)的语言符号学对于解释语言视差的成因有一定的说服力。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清晰、完整、有声,另一方面则晦暗、残缺、无声[3];他认为人们通常在命名、形成或使用某个概念时只注意到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前者常常掩盖或压制后者,后者就不为人所注意。这里提到的“晦暗”、“残缺”、“无声”就说明人类的命名和概念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进而对客观现实的表征便存在一定的“视差”。而德里达对语言符号的独到见解,对语言视差的解读也自有其道理。德里达首先对传统的符号学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符号并不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并非像索绪尔(Saussure)比喻的硬币的两个面那样密不可分。他认为符号的出现并不等于它所意指的东西(客观现实)现时在场,而是意味着所指不在场,是推迟了的在场,人们从符号中寻找意义时所得到的不过是能指的能指,解释的解释,例如,“树”常被释义为一种“植物”,而“植物”又需要其他词来解释。不仅如此,德里达还认为每个符号都是由无限延续的符号的意义构成的。德里达把语言作为能指的集合体,与所指无关,这样,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表征的距离就更大了。虽然德里达的看法有点偏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语言与现实客观世界的对应关系存在着偏差,有时偏差还挺大。
以上两位符号学家对语言的阐述,说明语言符号的表达和认知功能是有缺陷的,不能全方位地表征“客观现实”,出现了扭曲客观现实的现象。对于这一点,陕西师大文学院教授韩宝育在“语言符号的局限性[4]”一文中也进行过相关论述。他认为“语言符号在表达认知内容时,具有粒散性的特点,如果我们要用语言来勾画一个未知事物,只能得到一个疏略的框架,这个框架的颗粒是很大的。单凭语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颗粒以下的细部”。在这里,“颗粒”是指对语言细部的假象。以照片为例,颗粒大的照片模糊,颗粒小的照片清晰。语言有类似的特点。我们说语言颗粒很大,是指纯语言符号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和意义是很模糊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颗粒”构成的,因而都有一个颗粒大小的问题。纯语言所提供的图像虽然模糊、粗梳(清晰度以下),但我们感受却很具体、很清晰。而“颗粒以下”就是指清晰度以下语言符号所漏掉的内容。语言既然类似颗粒结构,线形排列中的各个语义点之间,在其前后左右,就都会有空白,这就是所谓的粒散性,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语言“视差”现象。
简而言之,语言符号与客观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映,或语言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现实世界,从而导致语言视差的产生。当然,除了因对映不一致而产生语言的视差外,语言符号的不足或贫乏也会产生语言的视差。
二、语言视差的语言因素①
①语言因素其实属于符号因素的一部分,为了更好阐述语言视差产生的缘由,加上语言不足是视差产生的重要原因,故单独作为一部分来阐释。
我国翻译家胡以鲁认为,“天地之始无名也。名之起,缘于德业之模仿。”意思是说,宇宙起源时有物无名,名是人类模仿自然的结果。在古代,由于原始初民的语言简单,或相当贫乏,不能想出更精确的新词语表达他们周边的新概念及新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用现存的词语或短语来表达,有时把两个实际不同的事物当成一个。至今,人们还在使用这一方法,不过美其名曰“隐喻”,它既是一种修辞格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符号学家皮尔斯(G.Peirce)区分了记号(icon)的三种情况,而隐喻就属于其中一种,表达的是一种平行关系,即通过指出某物与另一物之间某方面的相似来表达某物,此表述本身就意味着语言表达与客观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即“语言视差”。
即使到了现在,语言还是显得非常贫乏,总落后于现实,新的事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而语言中的新的与之相应的表达却不可能立即跟上。此时此刻,隐喻便趁虚而入,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缺。隐喻中的本体与喻体是一种平行的喻指关系,这种表述就意味着语言与现实存在着一种“视差”。这种“隐喻”性的视差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例如,在中国,某人要辞职去经商,我们称之为“下海”,而“经商”与“下海”从表面上看不存在任何联系,而现存词库中没有合适的词语来描绘“辞职经商”这一现象,于是乎,人们只得使用“下海”这种“视差”语料来表达。其它相类似的情况还有:泡妞(court girls)、熔炉(melting pot)、晒太阳(bathing sun)、打扫卫生(do some cleaning)等等。因囿于篇幅,不再赘述。
总之,语言总是滞后于现实,导致语言符号不够用,不能与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一对应。中国人常说“词不达意”、“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用言辞表达”、“这样说是挂一漏万”等说法,就是对以上现象的生动写照。人们为了准确描述客观世界及人类情感世界,隐喻便应运而生,而隐喻来身就是一种平行关系,故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视差”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三、语言视差的认知因素
认知语言学认为客观现实是语言的源泉并对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不过,人的认知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能反映现实,但不是直接的,在反映的过程中,人的认知因素不可避免地介于其间,也就是“心生而言立”,其模式是:
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语言符号
可见,认知发展先于语言表达并决定语言的发展演变,也就是说,语言是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被理解了的客观事物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
这一点在古代,尤其是原始社会尤为突出。古时候,人们的思维能力是很有限的,或曰“思维贫困假说”,其思维能力处于低水平状态,他们只使用简单的方法来了解周围的客观事物,通常把实际上不一样的事情当作了同一种事物,或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代表一定场景的某些模糊指称。如,单词“sea lions”,表面上看来似乎指的是海中的狮子,其实不然,指的是大耳朵海豹。不过,人们还是以“sea lions”对该动物加以指称,因为他们常用些普通的词来描绘一些模糊但差异明显的不同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单的词语及表达便成了固定语言表达,从而导致语言表征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差异,或曰“语言视差”。又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古代人认识和描述事物的一个基本原则,因而身体活动便成了当时人类思维活动的典型活动,那时的人们易于根据自身的部位来认识周围的事物,例如:他们认为山有头,于是便形成词语“山头”。类似的还有“山腰,山脚,桌腿,树身”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表达便慢慢地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但我们知道山和树不是“人”,因而不可能长有头、脚、腰等等,这样语言与现实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视差”。又如,我们所熟悉的“sunrise(日出)”和“sunset(日落)”这两个表达亦是如此。古时候,人们对他们周围的事物用自身的部位来命名,而对于遥远的事物,他们就只有用附近的物体来命名,也就是说,他们了解事物的规律是从近到远。当早晨太阳升起来时,由于他们把自己所处的位置作为参照点,因而误认为是太阳在运转,便有了“sunrise(日出)”与“sunset(日落)”两词,后来我们知道实际上地球绕着太阳转,而根本就不存在“太阳上升”、和“太阳下落”这两种情形。然而,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那种扭曲现实的词语表达,也不刻意去改变这些表达。因为有些表达在某些社团一旦形成,就不易于改变,即便为了接近现实而临时改变,人们也不接受这些新生的词语表达。
总之,人的认知因素在“语言视差”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知先于语言表达。当人们还没有获得“温床”的概念及其特性以前,就不会出现“温床”一词;当人的认知能力尚未发展到被动概念时,人类就不会使用被动概念的语言结构。而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因如此,在古代,也就会出现语言对现实的“锚定”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视差”,我们也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现今的语言表达在将来也会被认为是对现实的一种“扭曲”,存在着“视差”。
可见,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存的语言中有着大量的语言视差现象,这些程度不等的“视差”现象给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交流带来了一些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障碍以及提高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我们应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
提及翻译策略,我们先看一些中外学者对翻译所下的定义:矛盾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正确无误地、恰如其分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去的创造性活动”;曹明伦教授则认为翻译是“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文化活动[5]”。西方学者卡特福特(Catford)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到:“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材料替换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的话语材料[6]”,而尤金·奈达(EugeneA.Nida)则说翻译即译意或曰用最自然的语言去复制源语的信息,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定义意味着:在进行文本翻译时,意义的传译应为先。目前翻译策略有两类①尽管也有归化与异化之说,很多学者认为它们是同出一辙,不过,归化与异化策略偏重于文化层面而已。:直译和意译;它们各有千秋,即直译重形式而轻流畅而意译重内容而轻形式。上文所提到的那些有着“语言视差”的语言材料,虽然与现实有着不同程度的扭曲,但与现实却存在“异质同构(lsomorphism)”现象,故在翻译带有语言视差性质的话语材料时应采用奈达的“功能对等论”,理由是该理论不仅是建立在异质同构体(1somorphism)[7]基础之上,强调客观实体间的同构性,而且能弥补直译与意译间的不足。此外,异质同构体是在符号学中象似性(iconcity)特征基础上引伸并发展起来的[8]。而上文所提到的带有“视差”的语言素材也属于符号学中的一种,因而,功能对等是翻译“视差”语言材料的最理想策略:一是它们之间有联系,二是功能对等论吸收直译与意译的精华,弥补了两者间的不足。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仅举一例。当一个中国人对英国人说,“我不教书了,已下海了”。此处的“下海”指的是“经商”,应译成“go out for business”,而不能译为“go into sea”。“下海”的表面意义“go into sea”与其实际意义“经商(go out for business)”无任何瓜葛关系,两者“视差”过大。再者,若直译成“go into sea”,西方人听了则不知所云。简言之,在跨文化交际中,为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我们应采取功能对等去翻译带有“视差”性质的话语材料。
四、结语
综上可知,由于各种原因,“视差”广泛存在于我们现存的语料中,给跨文化交流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为了消除各国之间的交际障碍,笔者以为,奈达的功能对等论是一个较理想的翻译策略,应该加以提倡及推广,因为功能对等论是基于异质同构体之上的,与“视差”具有一定的通约性。换言之,功能对等论的优点及“视差”语料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在翻译“视差”语料时应把功能对等论视为最佳翻译策略,这样,跨文化交流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1]黄宜思.简论英汉翻译中的“视差”现象[J].中国翻译,1999,(5):22-25.
[2]EugeneA Nid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6.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75.
[4]韩宝育.语言符号的局限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90-91.
[5]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129.
[6]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396.
[7]杨司桂.浅析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68-71.
[8]冒国安.同形现象与形式可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