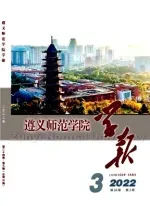萨特与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
2012-08-15刘大涛
刘大涛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萨特与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
刘大涛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在被李泽厚称之为“思想家凸显”的80年代,青年人在经历了“偶像坍塌”的短暂迷茫后,开始自我设计未来的人生之路,并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担当国家改革和建设的重任,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当他们为自己的人生规划寻求理论支持时,适逢萨特存在主义“自我选择和设计”理论的“西学东渐”,由此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萨特热”。文章探讨了萨特与八十年代知识青年之间的关系问题,并着重分析“萨特热”的起因和表现。
萨特;八十年代的青年;思想家凸显;自我选择和设计
一、青年在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迷茫
“文革”结束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随着“神”的崩溃,全国人民对文革期间压抑人性、摧残人性的行径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要求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道主义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在这人道主义思潮中,思想和学术界开始认识到文革是中国现代性启蒙中断后所酿造的恶果。为了反对愚昧,反对教条,他们提出“重返五四”的启蒙传统,这被称为新启蒙运动。受启蒙主义语境的影响,在文革中充当英雄的青年人开始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行自我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反思过去那荒谬的年代,青年人认识到自己过去所追求的崇高理想不过是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过去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英雄的壮举,反而给国家和他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于是毫不犹豫地告别了过去对偶像的盲目崇拜,“抛弃了对政治理想的盲从,对领袖个人的崇拜,对圣人道德以及虚假乌托邦的迷信”。[2]由于此时适逢社会的转型期,年青人的梦虽然醒了,可是在文革中荒废了学业,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新时代的弃儿,历史的悔恨和现实的挫折交织在一起,使不少人陷入了精神危机和价值迷茫之中。当《中国青年》杂志社在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署名为“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了全国范围内数以万计的同代人的共鸣与声援。
潘晓在信中真实地叙述了自文革以来的曲折经历:“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少年时代的潘晓在接受了雷锋、保尔无私奉献的精神教育后,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在文革中遭遇过亲情、友情、爱情等种种不幸的她,最终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潘晓这句“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话,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声音,它触发了人们对道德伦理的争论。《中国青年》杂志社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青年人围绕着“人生的价值在何处?”“怎样实现人生的价值?”“怎样看待‘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30年前的5月,当人们在不经意中翻开《中国青年》,读到潘晓的来信时,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它的痛苦、它的对此前说教式的教育的控诉、它的对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念的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覆、它的对一直被压抑的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毫无心理准备的年青人的第一反应是:“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3]
潘晓的信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的文章刊发后,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读者“问题讨论”的稿件和致潘晓的信达25,000多件,还有许多人通过电话、电报和直接来访表示支持、关心着这场讨论。对于潘晓这句颇具争议性的话,武汉大学的学生赵林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说法,“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他把“自私”看作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一种自我发现,“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4]潘晓现象热了整整一个夏天,由于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中国青年》在第12期上宣布了讨论结束。据统计: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受这场讨论思想影响的青年以千百万计。[3]
这次由潘晓的困惑所引起的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促进了广大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刚从蒙昧状态中走出来的年青一代又立即被卷入了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开始积极地思考“人为什么活着”这样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再一次充塞了他们年青的胸间。为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盲从、迷信、遵从“他人的设计”、崇拜个人权威中迷失自我,他们开始自我规划、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
此时,柳鸣九将萨特的理论作为启蒙的思想资源介绍给了广大读者。虽然许多青年人看不懂他的《存在与虚无》和他的一些文学作品,但并不会妨碍他们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一些诸如“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自我设计”等概念的理解,以及萨特对“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正是什么?个体如何达到本真的自我获得完美而丰富的存在?”[5]的思考所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精神危机条件下,原有社会理想破灭后所试图进行的自我重建,由于与新时期的年青人对自我的寻求有相通之处,并能解答他们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一接触萨特的理论,他们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并迅速在同龄人之间传播其思想,于是很快掀起了学习和实践萨特理论的热潮。
二、萨特的“自我选择与设计”理论与青年的思想相契合
在80年代的年青一代中出现的“萨特热”,究其原因,有其外部因素和内在主体因素两个方面。
从外部上讲,首先,新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萨特著作的积极译介和围绕萨特存在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展开的学术争鸣为知识青年了解萨特的“人学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从70年代末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的翻译到80年代末,萨特的大部分著作有了中译本,并在书店公开销售,介绍和研究萨特的论文有360余篇。在新时期召开的文学界、哲学界的学术研讨会上,萨特的理论成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和热点。这一时期,文学界共召开了三次年会,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每次年会中心议题的关键词,学会副会长吴富恒给它的定位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性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从文艺复兴开始就一直贯穿于西方文学中,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6]吴富恒的发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对萨特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挖掘工作,如1982年6月在无锡召开的法国文学讨论会上,就是以“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为中心议题的,这表明萨特的人道主义思想已被文学界所认可。在哲学界召开的几次外国哲学学会上,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如第二次大会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为重要议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还于1984年6月在江苏镇江召开了存在主义哲学专题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三部代表作,即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当年青人把目光转向外来书籍,寻求问题的答案时,最先进入他们视野的便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其次,谌容的书信体小说《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使知识青年更容易接受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理论。谌容的这部书信体小说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妻子”阿璋对杨月月的人生之路的介绍;一条是“丈夫”阿维对萨特的研究。阿维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有两点值得肯定:“第一,它是反对有神论的,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了自己;第二,它是反对宿命论的。人不是命运的奴隶,而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塑造自己的形象的。”[7]小说中杨月月这一人物形象和萨特的理论看似毫不相干,其实作者是在用杨月月的故事来演绎萨特的“自由选择”理论。杨月月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面临三次重要的选择:前两次都由别人替她选择,其结果是跟不上时代,失去了自我,被丈夫抛弃;第三次由自己决定,并最终在“怀梦牌洗衣机”中找到了自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青年人从杨月月的人生三部曲中认识到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也就很容易接受萨特的理论。
青年中“萨特热”的出现,除了上述外在因素,也与其自身内在主体因素有关。“文革”以后,青年一代的心理倾向和思想倾向为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理论提供了主观条件。首先,萨特对人的存在的偶然性、孤独性,世界的荒诞性、无意义性的描述,符合当时许多中国知识青年对现实和人生的体验。萨特认为,每个人的出生都是一个偶然,是被偶然地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世界又是荒诞的,毫无意义可言的。在这个“前无庇护,后无托辞”的世界里,人的存在无依无靠,陷入一种“孤独地无法辩解”的状态之中。这恰好与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青年的心理体验相吻合,当他们阅读萨特的著作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我刚接触萨特的存在主义时,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它很深刻,以哲学的语言说出了人生的真谛。”[8]
其次,萨特对传统价值观的彻底否定和提出的“自我选择和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的主张,对“偶像坍塌”后正在探索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自我问题的知识青年有很强的吸引力。萨特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除了人的存在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先验既定的价值系统。“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人的一切都是自己自由选择、自由规划、自由设计的结果,“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只讲个人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和义务,而个人的自我价值却不被认可。文革十年浩劫过后,经历了“理想主义精神”破灭后的青年从噩梦中醒来,开始了极端痛苦的反思。他们渴望求解这一灾难形成的历史原因,渴望求解人的价值、自我存在、生活意义等这些严肃的人生课题,并渴求在意识形态上有相应的、新的精神支点和理论武装自己,而这个时候,我们理论界由于仍然无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显得苍白无力,无法满足他们对新理论的呼唤。于是,当萨特的自由选择与自我设计的理论传入时,青年人开始阅读萨特,普遍接受了他的观点,并从中寻找心灵的安慰和人生的答案。“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等词汇成了青年一代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三、青年在萨特的理论中寻求人生路标的狂热
1980年萨特的逝世,可以看作是在中国青年中产生“萨特热”的标志性事件。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5万人为萨特送葬的场面时,完全被萨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住了,并由此出现了持续时间长达10年之久的“萨特热”。那么,“萨特热”在青年中的表现如何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些事例和数据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
首先,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在上海演出时,场场爆满,引发了广大青年观剧狂潮。1981年春,上海青年话剧团在上海艺术剧院舞台上演出了萨特的这部名剧。虽然这是萨特的剧作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却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导演胡伟民说:“不少观众看了演出后,热情地说:‘四十年代异国发生的斗争,对于我们是亲切的,雨果、捷西卡、贺德雷、路易、奥尔嘉等人物,都是我们生活中可以见到的,就是你、我、他。’”[9]对当年青年人抢购剧票的现象,十年后,刘翔平仍记忆犹新,在演出最后一场时,“只见前来‘截’票的人越聚越多,一双双焦急期盼的眼睛,一张张十元的大票。当演出的铃声响起时,焦急的人群终于失去了理智,随即爆发了一场数百人冲剧场的‘闹剧’。冲剧场的年轻人看上去并不野蛮,大多数戴着一副近视镜,动作笨拙,一派书生模样,他们拼命涌向剧场去寻找什么?”[10]
其次,广大青年对萨特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萨特那本通俗性的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曾在二战后的欧美刮起过一股强劲的存在主义时尚之风,当周煦良将它翻译发表在《外国文艺》1980年第5期后,在中国青年中掀起了一场阅读热潮,以致萨特被中国80年代新一辈视为自己启蒙的精神导师。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的需要,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8年以单行本出版它时,印数高达75,000册,这在当时完全是作为一本畅销书来发行的。198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鸣九编选的资料最为全面的《萨特研究》。这本书籍被青年人广泛阅读,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2年,国内“清除精神污染”时,《萨特研究》一书在全国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也因此书的缘故,“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太阳镜)、“喇叭裤”曾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11]解禁之后,《萨特研究》被准许重新再版时,1985年又加印了30,000册。对于一本纯学术性的书籍,在当时,这样的印数是相当惊人的。即使如此,仍然无法满足所有广大青年的需求。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的张柠回忆道:“1985年5月的某一天,我正在上海旅游。逛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正在排队,我也加入了队列,当然不是买减价咸鸭蛋,而是买一本畅销书,叫做《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两块多一本。”[12]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晓明也曾有过用拜伦的《唐璜》和一大堆吃的东西从朋友那里交换过一本萨特的书的经历。就连萨特的那本非常晦涩难懂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据了解,除专家学者外,也有不少青年读者坚持啃完了这本大部头著作。由此可见,青年人对萨特存在主义理论的兴趣和关注非同一般。
再次,萨特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一时成为青年们热烈谈论的话题。在高校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理论沙龙”、“研究会”、以至在“课桌文化”上、大学宿舍里,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愿意做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只有人们自己承认软弱,才是软弱的”、“他人即地狱”等格言式的观点很受青年人的欢迎,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新命题。
最后,当时大量批驳萨特人生哲学对青年的“消极影响”的文章和一些“反面教育材料”的出现,我们也能够间接地感受到萨特在青年人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青年中的“萨特热”引起了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人的警觉,为了抵制萨特对年青人的“精神污染”,他们纷纷撰文加以批判,诸如“浅析存在主义对青年人生价值观的误导”、“试论萨特人生哲学的消极影响”、“存在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对我国青年人的毒害”、“存在主义哲学的歧途”等文章将萨特对青年人的“毒害”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但是,觉醒过来的青年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愿再被那毫无现实根据的道德说教左右自己的思想。
萨特的存在主义对80年代知识青年的影响甚大,是其它西方思潮无法相比的。首先,萨特对个体主体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增强了青年人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当时我国正面临社会一系列改革的转型期,自我意识觉醒的青年人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高涨,纷纷为改革献言献策,并对社会上仍然残存的官本位观念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在这“思想凸显”的时代,他们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实现国家的民主、富强为己任,并勇于承担责任,渴望在改革中大展宏图,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其次,萨特的自由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年人的自由意识和自主意识的觉醒。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不少青年不再遵从“他人的设计”,更不想让别人来塑造自己;他们力求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奋斗”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同时,这种自由观的传入,对于那些自主性差、依赖性强、缺乏自我选择勇气的青年有激励作用,促使他们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培养开拓精神。
总之,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生价值观对自我的强调和论述,在一定条件下对青年确立“自我”为价值主体的观念有促进作用,对他们高扬“自我”的观念提供了思想资源。
[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2]刘济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34.
[3]彭波.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9-10,24.
[4]赵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J].中国青年,1980,(8).
[5]谢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41.
[6]吴富恒.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闭幕词[J].外国文学研究,1981,(1).
[7]谌容.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31.
[8]陈中亚.我告别了存在主义[J].中国青年,1982,(10).
[9]胡伟民.让·保罗·萨特的《肮脏的手》在上海舞台上[J].外国戏剧,1981,(2).
[10]刘翔平.精神流浪的轨迹——大学生“读书热”现象分析[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65.
[11]柳鸣九,钱林森.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柳鸣九、钱林森教授对话[J].文艺研究,2005,(11).
[12]张柠.“萨特热”污染了我们吗?[N].南方都市报,2008-5-5.
(责任编辑:魏登云)
Sartre and Young Intellectuals in 1980s of China
LIU Dao-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In the 1980s featured by “Thinker Salience”,the youth began to seek their own roa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fter experiencing a short period of“Idol Collapse”.And they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forming and constructing our country as public intellectuals,thus the so-called “Vangards”of that time.When they sought certain theory for their practice,Sartrean existentialism is “on the way from west to east”,resulting in ten years'“craze for Satr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rtre and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in the 1980s,and analyzes the origin and phenomenon of“the Craze for Sartre”.
Sartre;intellectuals in the 1980s;thinker salience;self-choice and design
I06.4
A
1009-3583(2012)-03-0011-04
2012-02-18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QN015)阶段性成果。
刘大涛,男,湖南麻阳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及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