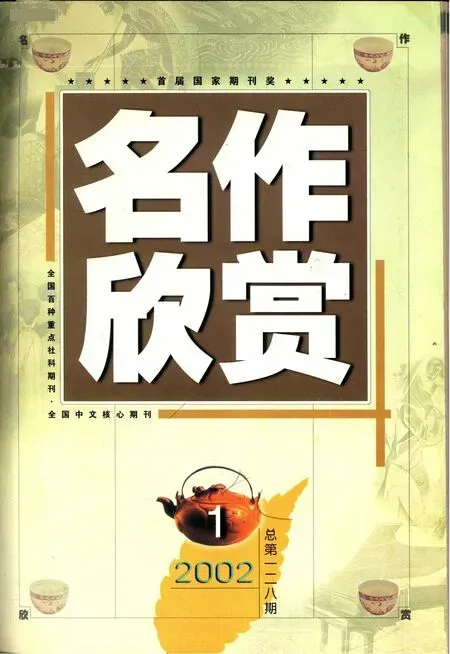真正的影响力取决于价值观
2012-08-15天津
/ 天津_朵 渔
作 者: 朵渔,诗人,《名作欣赏》杂志文化观察员,现居天津。
邮 箱:tjduoyu@sina.com
前些天在深圳参加了两个诗会,讨论的话题颇有些相似:一是“当代诗歌写作的现状与传播的可能”,另一个题为“诗神远游——建构当代中国诗歌国际传播力”。两个话题有一种共同的焦虑感,那就是汉语诗歌在当下的影响力问题。
所谓“当代诗歌传播的可能性”,话题本身即预设了一基调:当代诗歌的传播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所谓不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当代诗歌的文化边缘身份,更是基于诗歌在文化金字塔中的自身定位:诗歌只影响“无限的少数人”,它与普遍的大众无关。但每一首诗歌、每一个写诗的人,又都在苦苦寻找或等待它∕他黑暗中的读者,这种期待又成为某种可能性的动力。就是这么纠结。可能——总是可以找到一堆似是而非的办法,比如网络传播、在公众面前朗诵等等,这是可能的;但结果依然是不可能——读诗的人永远只是那少数中的少数。
诗人韩东认为,“诗歌的传播”,它在最根本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跑到大街上,揪住一个人的脖子来读你的诗——如果他对诗根本就不感兴趣。但韩东同时也强调,即使当代诗歌不能进行有效的传播,诗人们也不应拒绝各种传播的可能性。因为自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的新诗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个成果,怎么和不写诗的人,怎么和民众去分享?至少也是一部分诗人,不应该拒绝的东西。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好的东西”。诗评家姜涛将诗歌的传播或者是诗歌的公众性分为几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指你的诗歌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来读,这是一种所谓的传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诗歌提供的一种价值……现在读诗的人的确不多,但是这种阅读,恰恰是有价值感的阅读,不是简单的观看和简单的知道,这是有区别的。”
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每个诗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几个理想的读者,这些“理想读者”不可能太多,有时可能是三五知己,有时也许就是那一个“她”。我从来不会奢望马路上的每个人都喜欢我的诗。讨好所有人的写作,肯定是一种变态的写作。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一个诗人的写作,你到底为读者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不能平白无故地让别人爱上你。如果你和那些读者心灵都没有沟通,连恋爱都没有谈,再奢谈所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就是一种撒娇。
如果说探讨“诗歌传播的可能性”是一种身份焦虑的话,那么“建构当代中国诗歌国际传播力”就是一种存在感的焦虑。你写诗,但别人根本看不到你,根本无视你的存在。这种虚无感的吞噬性太强大了。很多诗人嘴硬,说“我们本来就在世界中”,但问题是,“世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要让“世界”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预设的中心。这个中心肯定不在越南或柬埔寨,而是在“第一世界”——一种强势文化。如何让强势文化认同?一个最简便的逻辑就是:你自身也要强大起来。诗人于坚就认为,目前中国诗歌的“实力”可以说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我觉得中国诗歌要走向国际这个问题,回到最根本的层面来说,从历史发展来看,有武力就有文化,如果你这个国家非常强大,如果你有武力,你的文化就成为世界标准,如果你是弱小民族,你受欺负,你就没有什么文化。”如盛唐的时候,长安城就是世界的诗歌之都,许多日本诗人跑到中国来学习。文化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跟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的经济强大,可能你的文化标准就会得到接受。
但是,这个逻辑又太过便宜。如果一国的文化影响力是由其经济、武力强弱所决定,那我们就很难理解像波兰、捷克、立陶宛等等这些东欧小国的诗歌影响力何以如此之大。波兰这样一个历遭劫难的东欧国家,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有四位。我认为,一种文化或文学的国际传播力,取决于它所提供的价值观,而非一国之经济或武力。如果你输出的价值观不能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再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可能都于事无补。
不久前召开的第八届“作代会”,其主题之一也是要解决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力”问题。作协无疑拥有巨大的体制资源,是可以做些事情的,但问题是,国际传播力的建构不取决于你占有多少经济资源,而是取决于价值观,就是说你到底向世界输出了什么东西,这是最关键的。在深圳的讨论会上,翻译家高兴举了几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他曾多次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世界各地,一些作家名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但一张口还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老话题,根本就与“世界”不在同一个轨道上。这种传播方式,其实是一种“反传播”。
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狂奔之后,“文化”这只纸老虎又被重新提高到国家叙事的层面上来。这是件好事请。无论是“大发展大繁荣”也好,还是“党管文化”也好,至少已关注到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决定性作用。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每一个文明板块的勃兴,都与其为人类的共同生活所贡献的原创性价值有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世界历史从150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在西方是以其大量特殊的个性、不朽的诗篇和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动力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创造而著名的。”而这段时期,正是我们这个日益僵化的东方帝国开始走向没落的时期。
价值的原创性基础是鼓励文化多样性,并为与社会秩序相容的个人主动性提供最大空间。很难想象在一个僵化的文化环境里,会有什么样的原创性思想出现。罗素在他的题为“权威与个人”的广播讲座里曾提到:“通过使人驯服和胆怯,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而是要通过鼓励他们勇敢大胆、敢于冒险和无所畏惧来创立一个美好世界。”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和环境,思想的原创性将很难出现,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