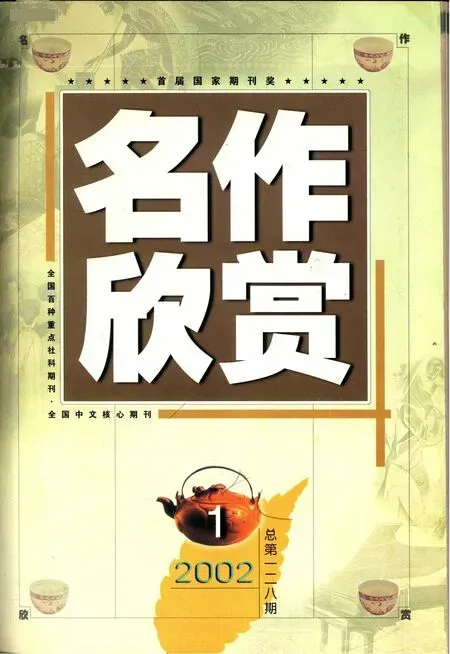为爱落款——读蔡劲松雕塑有感
2012-08-15北京杜文涓
/ 北京_杜文涓
作 者:杜文涓,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艺术学院教师。
我常想,如果人生只是现在这般的初秋正午,太阳光躺在池水的下面,一点都不出声,寂静会在这里放牧时间的羊,我们脸上的生动会淡下来,像杉本博司的书名:直到长出青苔。直到这绿褥漫上舌尖,身体就这样枯坐着,闭门谢客,而灵魂却如一阵风,吹过牧场,穿越寂静山岭,染了绿色、携了草香,消失在远方的海面上,于是话匣子打开,纵然没人倾听,也可以说到晨光,说到斜阳。所以有时候我愿意忽略蔡劲松所有物理坐标上的位置,只剩下他那一颗漫游的心,用人间诗意的乡音,道着黎明的早安,唱着浪漫的歌谣。
蔡劲松的雕塑是诗,诗也是画,画也是音乐。它们是山,是树,是天空,是泥土,它们没有坚固的名字,不会身陷言论的囹圄,有一种令人羡慕的自由。
他在用一种很模糊的形态说故事,那是一个永远以不同形态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着的故事,没有情节,周而复始,无穷无尽。于是在《怀抱》里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个故事的深切眷念。也许是陶土的纯真朴实勾起了他的乡愁。人们由尘土出生,又归于尘土,挚爱的人和我们自己终有一日都会消失的命运叫人心碎,而故乡却从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自古就是使人断肠的烟波江,是在水一方的蒹葭伊人,永远不会离我们太近。或许真的只有空虚才是最后的故乡。我们都是走着走着就回不去的人,这是残忍也是不忍。《怀抱》似乎是两个人的组合,是要挥去的一抹伤痛,是在心底呼喊着一个深爱的名字,无数的悲喜离合,都在这个雕塑里埋藏。手指在陶土上不经意的紧促和轻缓,揉捏间的稚拙是怕力过伤情伤韵,才隐忍着克制着。孟浩然说“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两人相对相望,太多的情感无从诉说,不如一醉方休。《怀抱》就是这样的一壶酒。
另一件陶土作品《黄釉时代》也是朴拙的,却另有一番情致。黄釉,汉代即有,唐宋三彩上都用了黄釉,明代的黄釉色泽更为纯正美丽。我想我的大脑必然有一种无趣的惯性,反复猜度这个“黄釉时代”的确切年份,比如像“公元638年”会给我安全感。可我一直没问,因为不想做一个煞了风景的人。对蔡劲松来说,这可能更是个无关宏旨的问题。我看着《黄釉时代》,即使它静静地摆在那里,也似乎一直在游移,一片混沌中只给出一丝微茫的暗示,仿佛远古时代转瞬即逝的、不定的、初始的一小点文明之光。
世界是相对的,不同的心灵境界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景象,有时地狱,有时天堂。境界一词从唐代开始和“心识”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美学中非常核心的概念。我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命精神,很多人质疑,说这个词在感觉上过于含糊。到底什么是生命精神?我想境界和生命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这么定义:生命精神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有关于宇宙人生的反思,所有表达出来或者体验到的人生的伤痛、欢乐、苦恼、希望、无奈、挫折等等一切感受和情感,所有人类对于个体进化和幸福、群体进化和幸福所抱有的理想和做出的努力。生命精神的主体是人,同时并非客观存在。它可以是低级生命能量的反映,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本能精神,但是境界的追求一定是生命有意识地朝向更加理性更加完善的努力。这个方向必须是一个刚健向上、充满光明的地方。
于是我们又看到《萌》《起舞》这样满是情趣和生机的作品。蔡劲松的雕塑没有重复,情随境迁,面貌自然也就变了。他用三种材料表现了“萌”,而我最爱青铜的那一件。因为柔绿色的玻璃钢减弱了生命的曲折和幽深,颜色的含义一旦约定俗成,意义就变得浅近,终难为上乘。而青铜的光泽和质地更好地渲染了生命的厚重形态,沧海桑田中生命始终在绽放,仿佛万语千言的情意,仿佛驷马难追的誓言。白昼的大脑睡着了以后,灵魂就滑落脚边,在森林的夜光里安静舒展,古老而情切的姿态。而在《起舞》中,他又以组构性现场和拟人化的隐喻方式,塑造了“鱼尾鸟”的生命艺术形态。起舞,既是对生命精神应然状态的赞美,也是对鸟、鱼和羽翼等审美意象自由畅达的综合刻画。我以为他的这件作品最为抒情,有种不动声色的张扬。
可是到了《势》,感情抒发得就“明目张胆”了。情一旦不是柔和的,抒发起来,要么是一种炫目的疯狂,要么则更像是一种冷静的思考,《势》明显属于后者。蔡劲松诚实地记录了他的心境,可他还是在抒情。这种抒情性的抽象,反而给了我们共同创造意义的很大空间。比如,我会很诙谐地想,这多像三个坏心眼的中世纪教徒在进行一场密谋啊。又或者我会想到一句诗——“从后花园到月台的安娜”,逃出樊笼的安娜要去争取自己的幸福。那么锋利的不顾一切向上突围的力量,仿佛是春草要争夺更多的阳光。强势转为脆弱,刺痛变为感伤,都不过是强弩之末的孤单和凄凉,像管风琴的钢铁和最后一首绝望的歌。势是虚的,需要我们的预计和想象。在想象中的势是很深微的,它是一片平静的落叶,却足以让我们遍知秋天。势还是一个因果,一种流转,也是一个尽头,故而我每每都觉得这雕塑的最尖端上蕴藏着无数的险恶与悲情,叫人无奈和惊心。开到荼靡花事了,可是,美丽也恰恰就在这里。
人的心很奇怪,有时候会忽然在繁杂的生活中闪现出轻松的想象,忽然想打趣点什么。比如《匍匐纪》和《双鱼座》,我想一定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产生的。我曾在电脑上反复看《匍匐纪》,我把那些照片左左右右点击了半天,然后哑然失笑,原来他是有如此情趣的人,愉快而纯真,有着不大不小的幽默感。不像我,就是做梦,也总是僵尸、魔鬼、空难、洪水、火柴人,然后我会一直战斗到醒过来。所以我很愿意把《匍匐纪》看成是一次童话般的冒险,是七座环形宫殿里的潘神,是哇哇大哭的曼德拉草根,是一只匍匐在地又拼命想要站立的怪兽。它两角朝天,鼻孔笨拙地贴着地面,沉重到它都无法提起来。它显然不是《山海经》里的神兽们,而是一只费劲的可笑又可爱的家伙。而《双鱼座》似乎是废旧零件的再创造,我惊叹蔡劲松化腐朽为神奇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同时,也为此黯然神伤。记得小的时候,我住在工厂里的外婆家,外婆有一个大抽屉,里面装满了类似的零件和铁丝,它们都曾是我的宝贝,我会编出很多的花样来把玩它们,爱不释手,孩童的乐趣真是来得简单而美好,如今想来只是徒添心酸而已。人生什么都留不住,难怪李后主会叹息:人生长恨水长东。虽然年年都春花秋月,可是“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我们赞美生生不息,可是每个个体却坚定不移地走向寂灭。很难得,蔡劲松还有如此孩子般的兴致。
说了这么多,未必一定读懂了他的雕塑他的心思,但是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对生命的一往情深,这使得他不断地捕捉着风一样拂过心间的各种感受,神往着心灵里那些若存若亡的秘密波动,他的深情如月落潮涨,如种子鼓胀,必须有个抛洒的地方。雕塑只是他抒情的一个借口一种慰藉罢了,他已在生命里越走越深。爱的烟火落在他的手上,变成了雕塑的诗,这雕塑是能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