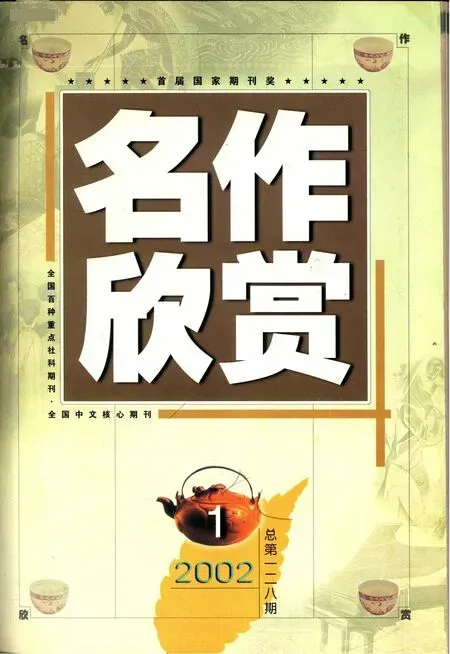我们缘何欣赏名作——以散文为例
2012-08-15江苏范培松
/ 江苏_范培松
作 者: 范培松,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散文天地》《悬念的技巧》《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散文批评史(20世纪)》和《中国散文史(20世纪)》等。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有这样一个交流机会。因为你们是《名作欣赏》杂志,所以我就把今天的演讲题目定为“我们缘何欣赏名作”。
没有名作欣赏,就没有文化
如果某个电视台给观众出个竞赛题目:现在社会最缺少什么?要让我来回答,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最缺名作欣赏。我一直是呆在书斋里面,没有离开过学校,对社会不了解。但是,就在学校里,我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浮躁。照理,学校是最安静的传授知识和学习知识的圣洁的地方,但是有人戏称,现在学校浮躁到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了,我并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现在流行的是快餐文化和快餐阅读,各类名目繁多的文摘报刊泛滥,学校也被这种快餐文化笼罩着,一切都为了名利,人人都想一夜就成为名人、明星,谁还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读名作?快餐文化和快餐阅读实在是名作欣赏的反动。我不反对快餐文化和快餐阅读,但是快餐文化和快餐阅读一旦成为文化的主流,把快餐文化作为第一精神需要,以快餐阅读作为主要阅读方式,整个社会就会在浮躁中恶性循环,长远来看,必然会影响民族的文化素质。名作欣赏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现在全国上下重视文化建设,在我看来,应该从提倡名作欣赏开始。我不是说,名作欣赏可以包打天下,主宰一切,但是它是基础工程。我看到一则材料,说秘鲁有个小城市,那里的警察性情非常暴烈,影响很坏,但市长并没有给警察任何处罚,而是用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办法,给他们放三天假,每个人还赠送了三本经典文学名著,要让他们在假期读完。结果假期回来,每个人的性情都大变了。这效果似乎是立竿见影,我对这个材料也有怀疑,但是它说明了名作欣赏的必要。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名作欣赏,就没有文化?
目前学校的浮躁,还表现在管理层面上。现在对教师的考核和奖励,就是以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多少作为依据。这样就把教师逼到这条路上,抢着到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要想评职称,没有核心刊物就不行。再有奖励,现在的评奖有多少是真正按照科研水平和质量来衡量?很多是靠关系靠权力。这也是使教师的精力不能集中到科研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名作欣赏和阅读上,底气不足,所以现在的报刊上文化垃圾非常多。
现在提出要文化强校,重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核心基础就是要大家都来读名著。去年我看了一个报道,说西班牙总统发布了一道命令,政府免费赠送西班牙公民每人一本《堂·吉诃德》,要大家来欣赏、阅读。我觉得这个总统的做法对我们很也有启发。我已年近古稀,回顾我学术研究的一生,我觉得自己最有收获的时段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读大学时的学习生活。那时学校强制我们要阅读名著和经典作品,规定每一学期要背诵一百篇古代经典散文和一百首古代经典诗歌,星期一每个人要到小组长那里去背,然后小组长向老师汇报,没有半点舞弊。还要我们认真阅读中文名著一百部,正是这三个“一百”,给我们打足了底气,为我之后漫长的散文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真不理解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不重视名作欣赏,为什么对于名作欣赏的态度是这样的拒绝和冷淡?所以,《名作欣赏》这个刊物是一种文化的坚守。我们应该向它致敬,为它鼓掌。坚守在某种情况下就有先锋的意义,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不管人们怎样批评它,其实它就是一种坚守,在当时就成了文化的先锋。
欣赏的底气何在?
当然我们现在也要看到,名作的欣赏方法、视角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名作欣赏》的编辑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你把上个世纪90年代的《名作欣赏》和现在的《名作欣赏》拿出来比较一下,你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变化。如果不认同这个变化,恐怕也不行。这说明《名作欣赏》的编辑们做到了与时俱进!我们原来学的一些文艺理论,也跟着时代在变化,因为现在已经是数字传媒化的时代了。在《文学报》三十周年纪念的会议上,一位年轻的学者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大学类型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们以前的课堂上学的文艺理论对于“类型文学”是很排斥的,是把它作为典型的对立面来看待的,总认为它是复制品,而文学典型是讲究创造的,但是现在的文化创意恰恰颠覆了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的名作欣赏也应该变化,也确实在变化。
这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名作欣赏明星化的文化现象,很多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说这是表演、娱乐,我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不能对此简单化地否定。名作欣赏的天地应该是无限宽广的,欣赏的方法也是多姿多彩的,我们要以包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文化现象,文化是多元的。不管是学者明星化,还是明星化的学者,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推动了名作欣赏,使名作欣赏大众化、普及化,这是应该肯定的。诚然也不能够自娱自乐,不能像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先生那样,他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吟诵,课堂下面的学生却在各干各的事。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些学者,写的学术文章都是云里雾里,让人看不懂,曾经热闹一时。因此,真正起作用的东西还是真学问。
文学作品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苦闷的象征”,是生命燃烧的结晶。陆文夫生前对我们的一些评论者的阅读和欣赏屡次表达不满。他认为,名作是一个有生命的鲜活的个体,像一只猪,他批评我们一些评论者的阅读和欣赏,只会把名作这只“猪”宰杀,然后告诉人们这是猪头,那是猪尾。他的批评是指我们一些评论者在文学欣赏上没有感觉。我们千万不要做屠宰工。而讲得更为传神的是钱锺书,他在《写在人生边上》说到,很多文学评论家,都是皇宫里面的太监,整天跟皇宫里面的宫女待在一起,却没有感觉。我对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也讲过,我们不要当太监,这会被人笑掉牙的。因此,阅读和欣赏有没有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名作是有丰富的内涵的,就像一个文物鉴赏家,你拿到一件文物,你就要能马上判读出它属于哪个朝代、哪个年代段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名作欣赏一定要有感觉。比如毛泽东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资治通鉴》和《鲁迅全集》,他有感觉,在《红楼梦》中看出阶级斗争的东西,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王蒙评论《红楼梦》也是一绝,我读了王蒙评论《红楼梦》的文章,感到王蒙真是个政治家,因为他在这文章里把他阅读《红楼梦》的政治感觉发挥到了极致。有感觉是名作欣赏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有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对名作有感觉,但是他的感觉有些“偏”,我们把它称为“偏见”、“偏爱”,我感到有“偏见”、“偏爱”好。郁达夫说:“对于文艺作品,不能感得偏爱者,就是没有根器的人,像这一种人是没有鉴赏文艺的资格的。”(《文艺鉴赏上之偏爱价值》,《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他把“偏爱”提到“鉴赏文艺的资格”层面上,我非常认同,尤其在当今,我感到在名作欣赏上,应该提倡“偏爱”。
名作欣赏,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套过硬的鉴别本领。为什么现在的文化垃圾满天飞,就是因为我们不会鉴别,或者有鉴别能力而故意不鉴别。鉴别要求对作品的档次作评判。我们不妨把作品分成三类:一类是经典性的作品,一类是有特色的、优秀的作品,一类是一般性的作品。我曾对我的研究生说,我可以允许你们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把一部有特色的作品说成是一般性的作品,或者是把一般性的作品当做是有特色的作品,诚然这样的错误最好不犯,即使犯也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你把经典性的作品说成是一般性的作品,或者是把一般性的作品看做经典性的作品,这样的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是笑话。遗憾的是,现在的文坛和报刊,恰恰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论,把一个一般性的作品吹成经典的伟大作品,而且吹的人还是什么什么权威。所以我提醒研究生,你们不要上当,特别当某个权威把一个作品吹成经典性的伟大作品时,千万擦亮自己的眼睛。鲁迅早在上个世纪就对瞒和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扫荡,不幸的是现在在文学的批评和欣赏上,这样的现象还在发生。
名作欣赏,还要对艺术的审美意义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和认识。以散文为例,散文创作有特定的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比如冰心在她的《寄小读者》里写到她在美国留学时又发病了,她如此写道:“我爱我的病。”怎么理解?爱自己的病,不是神经不对头了吗?请注意,这是艺术作品。冰心生的是肺病,这是她的母亲遗传给她的。如此一来,这个病就不一般了,母亲是她心中的上帝,这病是她的身体和母亲的连接,这个病上染着灼热的亲情,所以她说“我爱我的病”。我们如果依照日常的逻辑来阅读,有谁能喜欢自己的病呢?这不是很荒唐吗?恰恰荒唐里有痴情,她爱妈妈是无条件的彻底的,彻底到妈妈给她的病也爱。这就是散文的情感和艺术逻辑。它是绝唱!我读到一篇欣赏朱自清《背影》的文章,批评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越过铁路买橘子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不可取。这样的欣赏,我真的很难过。这不仅是钻牛角尖,我看是审美心理出了问题。但这种欣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尊重艺术。审美的价值、审美的意义和审美的力量,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审美是有它独特的规律的。
同样是欣赏《背影》,1992年第2期的《名作欣赏》上发表了一篇余光中的评论《论朱自清散文》。我当时读到这篇文章,就对《名作欣赏》怀有极大的敬意。余光中评论朱自清,拓展了我们的评论视野,当时流行的散文评论,还习惯于用政治和艺术的两分法,余光中的评论让我们眼睛一亮,感到从头到尾是全新的,散文欣赏竟然可以这样写!当然,余光中这篇文章有些观点还可以商榷。他提出朱自清散文有意恋倾向,我认为这是他的创见,我在拙著《中国散文史(20世纪)》中采纳了他的观点,但是他对朱自清散文的艺术人格的分析我不能接受,你欣赏像苏东坡的这种豪放人格是可以的,但你不能用苏东坡的豪放人格作为标准,来否定朱自清散文里的艺术人格。余光中是一手写散文,一手写诗歌,在散文和诗歌上都很有成就。朱自清开始时写诗,是以诗歌踏上文坛的,但是后来他感到诗情枯竭,就转向散文创作,这是成功的转型。从人格类型考察,余光中是属于诗歌的,朱自清是属于散文的。余光中在这篇论文中,总是以诗歌的经验来评判朱自清的散文,不免有的时候就有些粗暴。这里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在欣赏名作时,对不同的文体要有不同的欣赏方法,我们千万不能把欣赏小说、戏剧和诗歌的东西照搬到散文里来。余光中以诗歌中的创作手法以及艺术人格的形成来要求朱自清,这就未免显得有点僵硬和粗暴了。我认为,在名作欣赏中,应该也必须提倡对文体的尊重!
名作欣赏要绝对的“自私”
名作欣赏要绝对的“自私”。因为只有“自私”才能出个性,才能够防止欣赏的同质化。而所谓的“自私”就是在阅读作品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特的阅读品味。不要看别人的脸色,也不要看名人的脸色,更不要看书本上已经有的现成的观点的脸色,要绝对“我是我”!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来说,在名作欣赏上的独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老舍在生前讲的“戏迷公”的故事应该成为我们名作欣赏的座右铭。那位“戏迷公”痴迷戏,被强盗捉住,强盗对“戏迷公”提出一个要求,他也爱戏,现在他要唱给“戏迷公”听,只要“戏迷公”为他喝彩,他就不杀“戏迷公”。接着,他就唱开了,“戏迷公”听完后,说你还是把我杀掉吧。名作欣赏应该提倡要有“戏迷公”的骨头。我在这里也寄希望于《名作欣赏》,为社会多培养一些像“戏迷公”这样有骨头的人才。
附带在这里说一说,现在散文创作领域里,有人说现在的散文太“我”了,应该写“我们”。我认为散文写“我”是一种解放、一种进步,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这里。因为文学创作就是个人的精神活动,文学的欣赏也是。其实,创作和欣赏是相通的。我提出名作欣赏要绝对的“自私”,那么,要“自私”到怎样的地步才行呢?朱自清为我们提出一个标准:“……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乃是他们独得的秘密!”(《山野拾掇》,《朱自清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他讲的是创作,但是我们的名作欣赏最理想的境界,正是要有“独得的秘密”。“独得的秘密”最“自私”,只有最“自私”,才能获得“独得的秘密”。我们的名作欣赏也只有在“独得的秘密”上才能显示出它品位的高低来。“独得的秘密”就是名作欣赏的学术成果。我相信《名作欣赏》在审稿时肯定也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因为这样的文章才是自己的,因为它有独得的成果和秘密深藏在里面,是有厚重的学术含金量的。
名作欣赏在我看来,说到底,是一个艺术再创造的工程。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名作欣赏,名作欣赏的文字不应该是和尚念的经。许多优秀的名作欣赏文章让人倾倒。如我推崇的李健吾的《咀华集》,是欣赏巴金、曹禺、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和林徽因等人的作品,写得出神入化,文字之精美,见解之独特,堪称一绝。我实在太偏爱它了,忍不住把它作为散文来看待,列入了拙著《中国散文史(20世纪)》中,虽然有些勉强,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读者的批评。我在治学时,也以绝对的“自私”来要求自己,至于结果如何,还要请读者检验。
我们的名作欣赏也有一个要得到社会承认的问题,在我看来,选题很重要,格局千万不能太小,选题本身的审美观念和价值意义到底怎么样,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关死门,还要和社会相通,使名作欣赏充满活力。
学术研究要有学术的自信,名作欣赏要有欣赏的自信。我研究散文就是“无法无天”,当然你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只要你排除了其他因素,你就是优势,你就能出成果。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名作欣赏》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