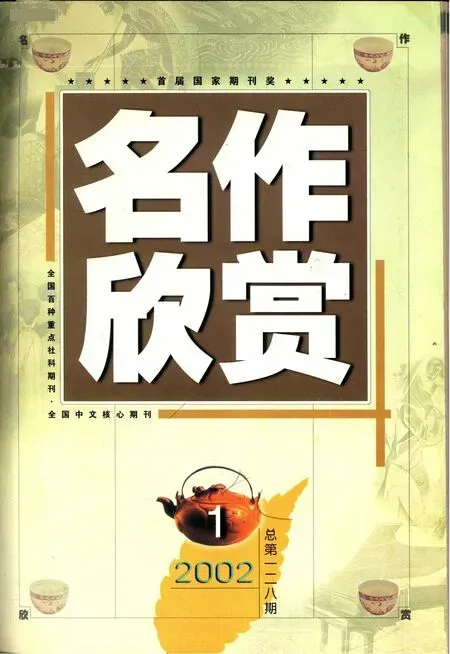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故事新编”
2012-08-15天津张谷鑫
/ 天津_张谷鑫
作 者:张谷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传统资源相结合的科幻小说成为中国科幻界新兴的文学潮流,神话、传说、志怪小说、历史小说等作为写作素材受到青睐。本文以“故事新编”这一术语对该类小说加以概括,并根据其与传统文本之间距离的远近,初步将其分为传统题材科幻小说、戏仿式科幻小说和问题式科幻小说。“故事新编”借自鲁迅的小说集,原意为“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而科幻“故事新编”则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加以“创造性转化”的科幻小说的统称。
传统题材:以古观今
20世纪90年代初是科幻“故事新编”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作品数量较多,但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有限。其中,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的作品有刘兴诗的《雾中山传奇》、姜云生的《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晶静的《女娲恋》、王志敏的《无际禅师之谜》、江渐离的《伏羲》等。从创作手法来看,早期作品多采用简单的类比方法,将神话人物换成外星人,将自动木偶换成机器人(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页)。以这种方式对传统故事和历史谜题加以改编的作品,本文称之为传统题材科幻小说。这类小说用科学理性精神反观传统文本,并试图为传统文本提供符合科学想象的全新阐释。
这类作品中,有部分佳作是侧重于科学技术与人性、社会的关系描写,为传统故事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从而达到了“陌生化”效果。比如1998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的短篇小说《偃师传说》,就叙述了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
偃师的故事最早见于《列子·汤问》,早在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饶忠华等科幻元老就已经提出了“列子是中国最早的机器人小说的撰写者”这一观点,“偃师的故事”遂成为历史科幻小说的常见题材。与其他采用相同题材所创作的历史科幻一样,潘海天的《偃师传说》也将偃师所造的“能倡者”简单置换成机器人,也同样将“偃师的故事”视为科学造就的奇迹。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偃师传说》不再多费笔墨去记载科技史,而是将重点放在机器人纡阿与宠妃盛姬之间所产生的爱情。小说中,机器人纡阿对盛姬忠贞不贰,而盛姬却为了世俗的利益背叛并出卖了纡阿,导致机器人被周穆王彻底毁坏。纡阿作为机器人而具有人性之光,懂得爱情的真谛是牺牲、奉献,而盛姬作为人类却表现出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作品由此达到了反讽的艺术效果。这篇作品凸显了科幻小说“软”的一面,它从科学故事出发,对永恒人性加以追问和探索。
应该说,传统题材科幻小说与传统文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些作品为传统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角度。经过长期实践,这类小说的创作已渐趋成熟,近年来屡有佳作问世,刊登在2010年第5期《科幻世界》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天与火》就是一篇杰作。
戏仿式:以古释今
戏仿指的是作品有意模仿某些经典的题材、主题、风格、体裁等,以达到升华或降格的目的。科幻“故事新编”中的这类作品,以现代社会为背景,糅合神话、志怪小说、传奇小说的主题、情节等,对传统文学加以戏仿。如果说传统题材科幻小说是“以今观古”,以科学思想反观传统文本和历史的话,那么,戏仿式科幻小说就偏重于“以古释今”,建立传统文本与现代故事之间的关联。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有王晋康的《南柯新梦》《百年守望》、何夕的《盘古》等。
王晋康是获得过银河奖的著名科幻作家。2003年他的《南柯新梦》发表在《科幻大王》上,该小说戏仿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小说的主人公刘马以蚁人的身份进入大怪博士计算机中模拟的“蚁人社会”,刘马发现,蚁人的文明早已跨过“后工业社会”而进入了“后农牧时代”,实现了向自然的回归。与这种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是,每一位蚁人都需要承担一定的集体义务。刘马既不愿履行雌性工蚁的劳动义务,又不愿意做雄蚁,过一妻多夫的生活,他只得匆匆逃离了蚁人社会。《南柯新梦》情节较为简单,但小说勾勒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并论证了相应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该作品的主题还与罗伯特·A·海因莱因的科幻长篇《严厉的月亮》的主题相似,在《严厉的月亮》中,严酷的月球生态环境促进了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群婚制成为新的伦理规则。
王晋康发表在《科幻世界》2010年第10期上的《百年守望》,写作技巧和思想主题都显得更加成熟。昊月公司设在月球上的氦能源采掘基地使得地球进入了全新的能源时代,该基地只有一台主电脑“广寒子”和一名蓝领工人负责基地的所有事务,但却提供了足够全人类使用的氦能源。在故事开头,这名蓝领工人武康正值三年轮换期,他即将前往地球,与分别了三年的妻子秋娥、儿子哪吒团聚。这一切却随着偷渡客——八十二岁的“吴老刚”的到来化为乌有。原来,“吴老刚”就是“武康”的化名,八十二岁的老武康是真正的自然人,月球上二十八岁的工人武康只是昊月公司用自然人武康的口腔细胞所生产的克隆人,而工人武康的妻子、儿子都是电脑中虚拟出来的场景。每一代克隆武康,在完成工作任务后就会被销毁。怀着对克隆人的内疚之情,老武康冒险偷渡到了月球,想要拯救克隆人武康的生命。广寒子告诉老武康,昊月公司正是为了保障全人类的利益和人类员工的安全,才从“人道的初衷出发,作出了一个不人道的决定”,用克隆人作为挖掘基地的员工。出于人道立场,昊月公司提出了一个补偿方案,即设法使电脑中的秋娥和哪吒在五十四年以后成为真正的人类,与克隆人武康一家团圆。克隆人武康经历了“充满希望——彻底绝望——将希望留给未来”的心路历程,最终接受了气化死亡的命运,将希望留给五十四年以后的自己。
《百年守望》的情节看似与“嫦娥奔月”无甚关联,但作者通过精心安排的细节,使现代文本与我们所熟知的神话之间产生了互文关系。比如,在克隆人武康的记忆中,他与妻子秋娥吵架后负气来到月球,这一细节与嫦娥的故事相类似。关于武康在月球上难耐孤单与寂寞的心理描写,又能使读者联想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句。小说人物的名字“秋娥”、“吴老刚”、“广寒子”都与“嫦娥奔月”的神话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武康”、“哪吒”也与神话相关。
戏仿式科幻小说多为古代故事和神话的现代演义,它们为科学的未来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设想。此类作品与传统文本之间构成互文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使现代文本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问题式:文化反思
近年来,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比如杨振宁先生就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思维与认知方式上。在这一背景下,某些科幻小说则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刘慈欣发表在《科幻世界》2003年第3期的《诗云》,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功能能否互相取代的问题。该小说虚构了一个科学技术至上的社会,甚至连物种之间的关系也由空间技术的发达程度所决定。在小说中,三维空间的人类被掌握四维空间技术的恐龙视为家禽,而恐龙又将掌握十一维空间技术的生物奉为神明。而神明则认为“技术能超越一切。技术本身才是真正的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处在生物链底层的人类伊依向神明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即如何以技术的形式超越人类的传统文化(以李白的诗歌为代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神明提出了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即将所有汉字排列组合起来,“把所有的诗都写出来”。汉字排列组合的巨大信息量形成了宇宙中最大的“诗云”,占据了整个太阳系的空间,从而导致恐龙帝国的覆灭,地球人类得到了解放。
令人深思的是,在小说中传统文化虽然成为拯救世界的契机,但归根到底,人类的获救仍然是通过科学技术力量实现的,恐龙帝国覆灭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技术上落后于更高等的生物,也即小说并没有建立“技术决定论”以外的其他规则。
同样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科幻小说还有韩松的《红色海洋》,该作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探寻现实、未来以及文化本身的意义。
科幻“故事新编”的文体实验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科幻“故事新编”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科幻小说作为幻想小说的一个分支,与神话、传说有着天然的联系,与其他幻想文学相同,科幻小说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不同之处则在于要符合科学精神和原理;另一方面,在中国科幻小说史上,早有论者提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含有丰富的“科学幻想”成分。科幻作家饶忠华主编的《中国科幻小说大全》,将“偃师造人”(《列子·汤问》)、“能飞的木鸢”(段成式:《酉阳杂俎》)、“返老还童的药”(沈括:《梦溪笔谈》)、“自沸的瓦瓶”(洪迈:《夷坚志》)等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幻想故事”。二十年后,杨鹏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幻故事》也收入了上述材料。
科幻“故事新编”的兴起或许还与台湾科幻有关,早在1982年的台湾科幻小说座谈会上,就有与会者指出“科幻小说与神话、历史之间的联系”,并提出“朝向传统文化发掘科幻素材的创作途径”。(林健群主编:《在“经典”与人类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科幻世界》杂志1991年第5期上刊登了台湾著名科幻作家吕应钟的理论文章《创造中国风格科幻小说》,文中提出中国科幻作家的使命之一是实现从“中国古典小说”到“现代科幻小说”的转变,“塑造出我国独特的科幻形态”,并列举了中国科幻的若干发展方向。《科幻世界》作为科幻界销量第一的杂志,这篇理论文章必然会对当代科幻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随后吕应钟还自出经费为大陆科幻设立了“年度科幻文艺奖”,进一步影响了科幻“故事新编”的创作潮流。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分裂由来已久。笔者认为,可以将科幻“故事新编”的出现视为弥合文明裂缝的尝试之一。这类作品再次审视了传统文化,并对其重新加以衡量,作出取舍。其结果正如列文森所言:“那些能被现代人重新肯定的中国的传统价值,将依然是符合现代人各自标准的价值。”(〔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就科幻文学而言,中国科幻“故事新编”不仅仅是一股创作潮流,它也是一次成功的“文体实验”,为中国科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当然,该类小说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部分作品中对科学原理的叙述较少,没能充分表现科幻小说的“科学性”特征,此外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也会限制了对未来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