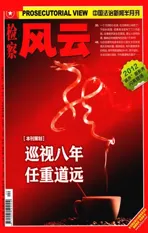曾文革:学术研究要跨出专业限制
2012-07-07卢煜林
文/卢煜林
曾文革:学术研究要跨出专业限制
文/卢煜林
“高校行政化的改革,就是要把不同的东西放到不同的位置,做行政的就是做行政的,做职员的就是做职员的,做教师的就是做教师的,各司其职。这些行业的定位要清楚,不能搞乱,不然最后什么都在做,却什么也做不好。……教学也好,学术也好,都是有规律的,我们要尊重规律,然后来探索到底怎么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学法律的人要多走走,多看看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1987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在大学四年中对哪些事物印象比较深刻呢?
曾文革(以下简称“曾”):大学四年,虽然西政的物质条件比较差,校舍也不漂亮,但我觉得西政的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上自习往往要抢座位。老师们也非常敬业,当时我们教室不多,有时就不得不在宿舍里讨论案例问题,老师们也经常来宿舍指导我们。我觉得西政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强调理论教学和实践的案例并重,这种教学方法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我收获很大。而且西政的学风是比较开放的,一直延续着兼容并蓄的传统,这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记:老师您从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一直到获得硕士学位,当中跨度有12年之久,能谈谈这段时间的经历吗?
曾:我毕业后去了重庆工学院的前身,当时的重庆工业管理学院任教。这期间还到彭水县支教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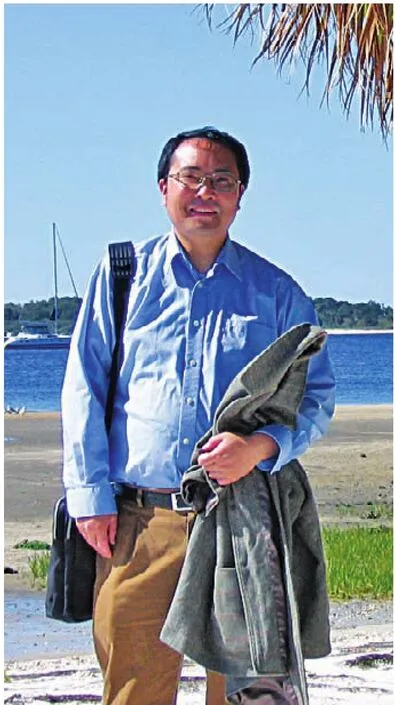
曾文革: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法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记:您为什么选择出去支教一年呢?
曾:支教一年是国家的规定,而且那个时候我刚毕业,年纪很轻,阅历不深,就想出去锻炼锻炼。这样锻炼一年,对我之后教学帮助很大,在如何控制课堂节奏、备课、组织课堂讨论等环节都有很大的提升。
记:在您的求学经历中,有哪些非常难忘的老师?
曾:印象深刻的老师实在是太多了。本科时的张孝烈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让我学会如何收集资料,如何修改论文的框架,如何提炼观点等。在硕士阶段,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昌麒老师,他是我导师,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对我影响很大。经济法实际上是非常难研究的学科,研究材料很多来自于经济学领域,要求学者运用法学的思维对其进行解读,但是我觉得李老师在这方面比较专长,很有学术天赋,他讲经济怎么跟法律结合,怎么从法律角度来研究一些经济现象,怎么研究农村问题等等,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时我考博士之后,就面临选导师的问题,昌麒老师劝我一定要换一位不同的老师,这样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非常有帮助。因为每位老师的研究思路不一样,这样对学生而言可以博采众长。
博士阶段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的导师种明钊老师,他是学经济学出身,所以强调的和李老师强调的又有些不同,他认为经济是第一位的,法律是第二位的。他常常告诫我一定要把经济的问题先弄清楚,然后再去分析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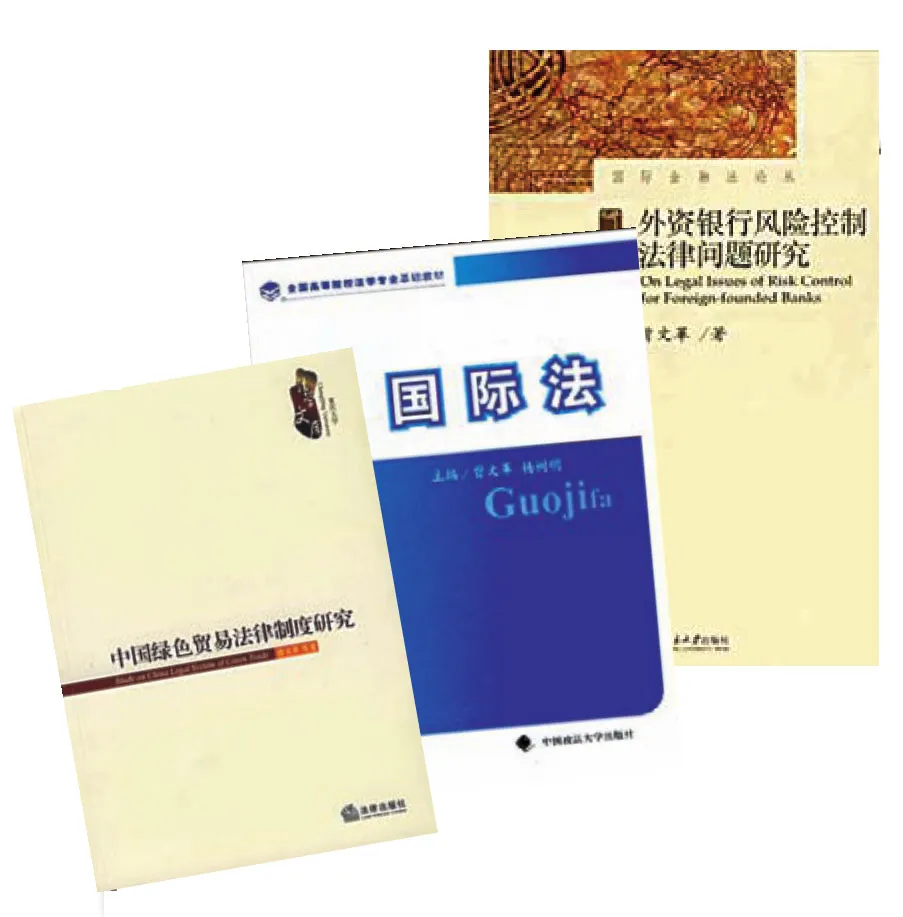
主要著作及论文:
《农业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研究》、《外资银行风险控制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绿色贸易法律制度研究》、《国际环境法新论》,《论构建我国资源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论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政策与法律措施》、《中国西部农村饮用水安全法律保障研究》等。
记:老师您博士毕业之后又是如何来到重庆大学任教的?
曾:我硕士毕业后就来重大了,原本我毕业后准备回重庆工学院,但当时发生了一件很突然的事:我太太生病了。所以我就决定要去重大,那里离我太太的单位近,可以照顾到一些。我从1999年6月份到重庆大学一直工作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时光。
记:您曾在香港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能谈谈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吗?
曾:当时有一个香港法律教育基金的项目,在全国选了五个人,我作为其中一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有金融法的一个项目,也有很多优秀的金融法老师,我在那边主要也是做一些外资银行法方面的研究。
当年下半年我去了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主要也是研究国际经济法和国际金融法。我利用那段时间把佛罗里达大学的国际法课程听了一遍。学校还开了一门很有趣的课程,是针对高年级学生的,将国际贸易、劳工和环保合并在一起教,让我开了眼界。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使我产生了双语教学的想法,回国后我就开了法律英语的课程。
记:这两段访问学者的经历,对您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曾:我觉得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作为访问学者,我不仅去听他们的课程,也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我们不一样,非常细致。比如有一次佛罗里达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到法学院开讲座,关于佛罗里达的农产品贸易,甚至具体到了WTO对于佛罗里达柑橘的出口有何影响。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对我影响很大。
在教学方面,美国非常注重案例讨论,这是他们的传统,能让学生更多地进行自主学习和讨论。我觉得他们这种讨论式的学习,对培养研究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回国之后,就经常开展读书会,一段时间推荐读一本书,读完后在一起讨论问题,在这过程中学生提高很大,对我自己来讲也是教学相长。
美国的法学注重精英教学,他们的师资配备、硬件条件也都非常好。美国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理念,比如佛罗里达大学每年从全世界招50个学生,包括欧洲、亚洲、非洲的学生,有些学生基础并不好,但也招进来,主要是为了注重学术的多样性。这个理念我认为是国内很多大学不具备的,所以现在我带研究生也趋向这样的理念。因为学生都有专长,比如以前学过金融的,学过计算机的,那么当他们经过法律的学习之后,竞争性就会很强。所以我觉得,学习法律的人还是要多走一走,这不仅是做研究的问题,也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对研究方法很有帮助。
不同的专业背景对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记:您从国外回来以后继续在重庆大学教书,和之前相比在教学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曾: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教学方法也进行了改革,比如说我教法律英语,可能和有些老师的教法不太一样。比如,一般而言法律英语都是老师讲得比较多,我增加了听力的环节,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能看懂不能听,到了国外就不能和老师交流。另外我在课程中有一个使学生压力很大的地方,就是要求学生翻译,由我来点评,这让学生提高很快。
记:您既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又从事环境资源保护法的研究,您怎么看待跨专业的研究?
曾:以前的学术基础和学术积淀,对之后的研究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以前研究合同法、民商法的领域,对研究环境侵权是很有帮助的。如何看待跨专业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要把这个背景作为一个优势而不是包袱。
记:老师您觉得自己从事的研究,对国际经济法等领域的贡献有哪些?
曾:说不上什么大的贡献,现在我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做得比较多的,一块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尤其是外资银行法这块。当时我在重庆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建立我国外资银行风险防范法律机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另外一块就是国际环境法方面,尤其是绿色贸易,我应该是做得比较早的。现在我又把它衍生到了国际法中的农产品贸易,也申请到了一些课题,我在2009年也出了本关于农产品补贴的专著。国际金融法和国际环境法方面的研究我还是有一点体会,所以这两个领域做的稍微多一些。
记:您是如何看待我国目前在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呢?
曾:从国际金融法的学术研究现状来看,应该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需要整个金融法学界、国际法学界一起来研究,这样才能做得更好。最好也有实务界的人士一起参与,这个领域中有许多新兴的东西,这些新兴领域开拓空间是非常大的。
从国际金融法的研究队伍来看,我觉得研究人员现在还不是非常多。同时,研究国内法的学者应该更多地关注一些国际背景,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新巴塞尔协议出来后,有一些新的理念,肯定要引领国际金融监管的潮流,如果这些东西不去关注,而只是研究国内的东西,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就会有局限性。
从国际环境法、绿色贸易这方面来看,我觉得整个的研究感觉就是法学界和我们理工界的学者交流还不够,因为国际环境法很多领域的研究需要一些工科背景。就是说,如果就法律谈法律,得出的结果可能会有失偏颇。
记:按老师的意思,学术研究要深入下去的话,就必须跨出自身专业的限制?
曾:对,我个人体会是这样。我读书是在法学传统深厚的西南政法大学,工作的第一所学校,是经贸和理工相结合的学校,然后又到了一所具有工科背景的学校。我的感觉是,做法学研究当然要通过一些法理学的范畴来分析解决问题,以确定具体的权利义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把相关领域的东西弄懂。不能说研究金融法的不懂金融,研究环境法的不懂生态学,这样研究就无法深入了。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其他学者的参与,可以提供很多新的思维,这个对于学术研究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学校要把学术和行政分开
记:您觉得当前我国的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资源保护法的学术环境还有什么不足?
曾:我觉得两个学科都有不同的特点,两个学科的年会我都参加,环境法这边是高度开放性,每次开会的人很多,各个学科的老师都会来。因为环境法是新兴的学科,可能是在理论的体系化、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突破。国际法这边我感觉很专业化,但相对来说,开放性还需要加强。
记:老师您对这两个学科未来的展望如何呢?
曾:人类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生存的要求,对空间质量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环境法是非常朝阳的学科,前景非常好。
研究国际法的背景在于中国的崛起,国家的经济实力上去了,政治影响扩大了,法律人才的缺口很大。而且国际法是皇冠上的明珠,是很艰深的学科,很多学生都望而生畏。但对国家而言是非常需要国际法领域的研究人才的,这是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问题,所以这应该是一门焕发青春的学科。
记:现在大学老师面临着不少学术压力,发表的论文数量往往和评教直接挂钩,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曾:考评这个制度,首先要看大的背景和学术环境,民国的时候不设置考评,是因为那时有非常好的机制,比如说教授委员会。有这样的机制,同时学界的学风也很好,环境是很公正的。比如聘请一位教授,像陈寅恪先生,虽然一本著作都没有,但公认水平很高,大家也服气。而我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呢?我觉得是处在转型期,相应的学术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纯粹地否定考评,这是不对的。我觉得还是需要考评的,但关键是如何考评,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考评的周期,每年都进行的考评,可不可以改成三年一评,否则会影响学术质量。本来一篇文章可能需要三年磨一剑,现在要求一年就要磨好,这样就不会磨出好剑。
我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学校的行政化。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要求学校或学院放弃考评,这样对成果多的老师也不公平。关键是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重庆大学现在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所以组织教授委员会,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新的问题,比如院系如何划分职权、教授们如何自律、讲诚信……这些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就这个过程而言,可能有时是非常痛苦的,各个学校也都在探索。
我是比较主张循序渐进地改革,改变行政化这样一个状况,把学术和行政分开。还有对老师而言,需要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不能光看科研,还要看教学质量,对学生怎么样。老师不是研究员,研究员可以只管研究,老师主要面对的是学生,如果你连课都不上,研究做得再好,都未必是个合格的老师。
记:之前我们采访过的一些老师认为如果使教师的生计压力和学术压力合二为一的话,会使他们为了生计而一直追求发表文章的数量,会导致学术环境的浮躁。
曾:我觉得生计问题确实要高度重视,作为一名学者,他所必需的硬件设施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成天要回家去研究,效果就会差很多。从待遇来看,作为一名教授或者是副教授,要有相应的待遇,不是说让他富,而是让他安心做学术。
佛罗里达大学有一位得过诺贝尔奖的老师,他从高中到本科到博士,到最后顺顺当当拿诺贝尔奖,所经历的环境一直很宽松,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国外大学也有考评,但是考评机制有些不同。我们的学术管理还是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总是看论文的级别,而不管它们的内容。但是国外大学聘教授很简单,你拿一篇论文过去,学校觉得行,就聘请你了。你在那三年一个聘期,学校会有基本要求,你要发多少文章,完成就行了。指标不会定很高,因为学校知道定得太高反而适得其反。教学也好,学术也好,都是有规律的,我们要尊重这个学术规律,然后来探索到底怎么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记:您对现在学习法律的学生有什么寄语和期望呢?
曾:我觉得学习法律的学生,基础和素质是关键。比如说,我常常会看到连句子主谓宾定状补都分不清楚的学生。这也是我们国家文科教育比较失败的地方,很多学生没学好语文,也不知道怎么学好语文,以致人文方面的素养很缺乏。作为学生,首要考虑的是要打好基础,要多去看一些课外书。本科四年,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是用来读书的,不是用来争分数的。学生必须要好好地打基础,基础打得不扎实,就是读到博士也不济。其次,学生要有持续学习心态,要坚持终生学习,要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学习能力,要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善于去吸收最新的东西。最后,我个人认为情商教育是最重要的,它对个人未来发展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建议学生注重个人修养,培养感恩之心,学会尊重他人和具有团队精神,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爱心和责任感的未来的社会建设者,这对于学生的成长很关键。
编辑:董晓菊 dxj5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