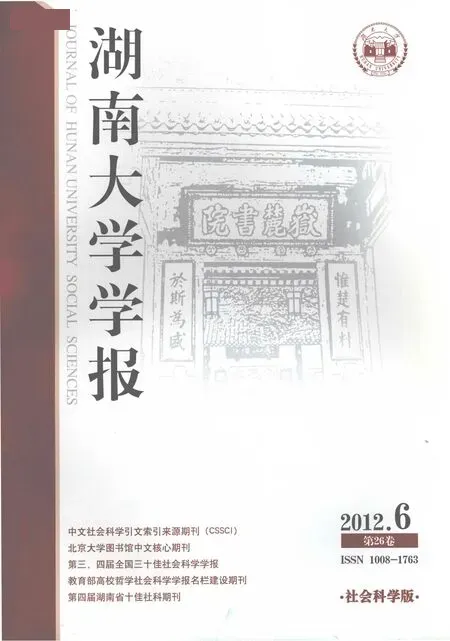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上)*
2012-07-05蔡慧清
蔡慧清
(湖南大学 留学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2)
宋代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和研究与汉学其他领域相比呈现出起步晚、局面相对冷清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欧美对传统汉学的研究集中于先秦,后逐渐延伸至秦汉。一战前后,欧洲汉学研究几乎中断,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加强,但关注的重心转向聚焦现实问题的中国学,对于既远离先秦又与现实中国有距离的宋代,极少有学者问津。二战结束后,白乐日(Etienne Balazs)在法国推出历时二十余年、延揽大批欧美、亚洲学者加盟的“宋史研究计划”,西方宋学研究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向深度转进,在中西方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包括朱子学在内的西方宋学研究逐渐繁荣,在研究内容与方法方面为国内朱子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生长点。与此相对应,国内关于海外朱子学研究的反研究也已然成为整个朱子学乃至宋代思想研究的亮点。
即或如此,近年来有关海外朱子学的研究依然存在着盲点,有些问题仍然处于混沌的状态。管见所及,以《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为中心上溯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就尚属首次。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拟以《印中搜闻》关于朱子学的译介、研究为中心,尝试呈现朱子学面向英语大众传播的历史语境、早期文本形态、主要内容及其方式方法,揭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等传教士译介朱子学的基本动因。
一 《印中搜闻》——英语世界朱子学大众传播与研究的最早文献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始于何时,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陈荣捷认为,朱子著述之翻译以《朱子全书》为中心,最早是美国汉学家裨治文(E.C.Bridgeman)1849年选择《朱子全书》中有关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的若干条论述①详见: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Heaven,Earth,Man,Beats,etc, Chinese Repository,第78卷342-347页,1849年。,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1](P273)。这种观点影响极大,后来学术界对英语世界的朱子学研究便以1849年的《中国丛报》为文献之起始。事实上,陈先生本人并没有下此论断。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陈在谈到朱子及其他理学家逐渐为传教士所注意的问题时说,“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五年J.A.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译《通鉴纲目》为法文。然此书与朱子哲学无关。......至于直接研究朱子,尚有待六七十年。”[1](P273)显然,在他看来,仅仅是文献翻译还不能算做研究,法译《通鉴纲目》不能视为“直接研究朱子”。西方世界“直接研究朱子”是此后六七十年的事情。朱子文献的英译始于《中国丛报》,但这种翻译是否就是“直接研究朱子”呢?陈先生没有明说。
关于朱子文献英译的时间,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有更早的著录。朱先生在书中提到“竺赫德(P.Duhalde)《中华帝国全志》1736年版,第二卷中有宋朱熹(Tshu Hi)所著《论文选录》,‘关于建公立学校使人民谋幸福的方法’(《劝学篇》),译者殷弘绪”。并特别注明:“朱熹《论文选录》见1736年版第二卷,页319-322。又见于Edward Cave英译本(北京大学藏)第一册,页383-384:Extract of a Treatise by Chuhi,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Doctors in China,who lived under the nineenth dynasty called Song。”[2](P199)但是据笔者考察,朱子一生并未作过《劝学篇》,具有劝学意味的《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童蒙须知》、《志学》、《自论为学功夫》、《警学》等均未见相似内容,此其一。其二,书中所谓朱熹的文章,据笔者查阅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藏Cave《中华帝国全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1734-1741)]英译本,第一卷383-384页:Extract of a Treatise Upon the Same Subject,made by Chuhi,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Doctors in China,who lived under the nineteenth dynasty called Seng。其内容要点译成汉语如下:修业是为敬德、学射而志于彀则知所学、有志则人人可以成尧舜;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告诫学子勿耽于过多允诺、玩耍、酒、放荡、淫靡的生活。全文重点在今昔对比九项内容,例数古之学者求学艰难困顿而热情执着,今之学者在教师、图书资料、场地、生活条件都很好的情况下,却耽于无聊闲混,使得一切优越的办学条件变得如同女人华丽的衣饰无益于身体和头脑一样没有意义[3]。笔者在翻译时尽量查找、采用朱熹的论学话语,发现朱先生文中所说“公立学校”应该是指“义学”。再参阅《中华帝国全志》中该篇前后文,大致可知该书是在介绍中国教育之义学、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等大框架下,选录了相关著述中的几篇文章作为例证,其中之一便是朱熹论文的选录。但是对照《朱子全书》进一步核实,其所录文字通篇是否朱熹所作难以确定,因而也就难以确定传播的信息是否完全属于朱子学内容。可以肯定的是,《中华帝国全志》的编者确实已经注意到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并对其文字加以了摘录译介。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文献的最早英译应该始于Edward Cave译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需要补充说明的有两点。其一,如果将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研究”作为历史文化现象来考察,需要有一个确切的界定。那就是朱子学已成为明确的介绍和研究对象,具有了面向英语世界公众传播的“自觉”,而不仅仅是蛛丝马迹、片言只语的提及[4](P131)。本文没有将《中华帝国全志》所录朱熹《论文选录》列为英语世界朱子学最早研究和大众传播的文本,原因除前述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之外,主要是考虑到书中所谓朱熹的《劝学篇》译自法文,且仅仅是译介而已,没有评述或研究性的文字。此外,《中华帝国全志》的其他英译本,比如R.Brookes的译本,并未见录朱熹的《论文选录》。其二,如果将“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大众传播”作为历史文化现象来考察,则需结合大众传播的理论及其载体本身的特点来界定。按照一般的定义,所谓大众传播,就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信息的全过程[5](P98)。《印中搜闻》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共同主编的一份英文季刊,按期发行并定期出版各卷合订本,撰稿者(“传播者”)包括马礼逊、米怜及其他在英华书院的英国传教士;“受传者”就是该刊的订阅者,包括亚洲、欧洲各地的传教士及其他读者。该刊内容上宗教性与世俗性并重且越来越重世俗;在面向公众的社会传播过程中对传教组织乃至社会发生影响,但又在经费、编辑内容等方面受到相关组织和社会的控制。关于这些读者可参阅吴义雄先生的论述[6],此不赘言。
笔者认为,英语世界朱子学研究和最早面向大众传播的文献应该是《印中搜闻》。该刊创办于1817年5月,至1822年4月共出版三卷20期,直接论及朱熹的文章有7篇20余处,其中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有2篇,作为重要阐释依据的有2篇,其他3篇亦多处论及或引用朱子原文,并且具备大众传播的各项基本特性。[7]略早创刊且与中国相关的英语刊物只有《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1816-1845)和《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1817-1980)[8],但通览二刊后没有发现其中有早于《印中搜闻》的关于朱子学的介绍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印中搜闻》是英语世界朱子学研究和大众传播的最早文献,这是世界朱子学研究中需要提请注意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印中搜闻》的原刊本在中国的图书馆或学术机构无收藏。海外藏有该刊的图书馆也不多,而能保存完整者更少。近年来,研究19世纪前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份刊物,但限于资料难得鲜有论及,因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印本《印中搜闻》直到2009年12月才出版发行。二是我们更习惯于从汉学专著出发开展海外汉学研究,而较少关注面向大众传播的期刊杂志。事实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期刊,因为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交流信息的途径和方式的特殊性,对文化经典的传播比其他专业的学术著作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和广泛性,值得特别加以关注。
二 从文化传播视域看朱子学西传滞后问题及《印中搜闻》译介朱子学的动因
文化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是运动、流衍着的生命机体。“一种文化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播散性,其播散力度,由该文化的能量大小和传播渠道的畅通状况,以及受容方汲纳该文化的需求与能力等因素决定”。[9](P131)按照传播学理论,文化传播的内核是人们的精神追求,以及这种精神追求引导下的思维、行动模式;文化传播的范围包括文化圈层之内和之外,而文化传播之能够实现,又依赖一些基本的因素。首先,传播者和接受者须具有文化共享性,也就是传播者和接收者对文化具有相似的理解,可能达成认同。其次,文化传播必须经由一定的传播媒介,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再次,文化传播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时空条件。[10](P14—15)以此考察朱子学的海外传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在东亚繁荣而在欧洲寂寥、滞后,并且争议颇多的原因。
朱熹作为孔子、孟子之后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传承者,集理学之大成,是宋代以后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学说自15世纪起即开始支配东亚思想。但在西方,对朱子学的介绍和研究,时间上晚于孔孟研究一二百年之久,态度上明显少了对孔孟及其儒学的尊崇而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心态。欧洲对儒学的介绍始于《利玛窦中国札记》,该书写于1583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到1610年逝世期间,因为“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之重古经而不采朱子传注”[1](P278),自然在介绍儒学时不会涉及朱熹,更谈不上对朱子学的译介。此后,龙华明、艾儒略、利类思、汤若望、卫匡国、陆安德、卫方济等人的著述论及宋儒时都只是批驳其理气、天道、太极、阴阳等观念,并不绍述其体系和内容。法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等曾论及朱子哲学且纠正了龙华民等人关于宋儒的理学观,但他们都不通汉文,也没有直接研究朱子的著述。直到1711年,“卫方济翻译《四书》兼采朱熹和张居正的注疏,朱子学才首次西传。虽然因为采用过多注疏,导致版本不够浅显易懂,但学术价值得到后世汉学家的充分肯定,雷穆沙就认为它是当时最明晰、最完全的儒家典籍的西译本”[11](P108)——拉丁文译本。
朱子学在东亚的繁荣是因为东亚各国同属于具有地理邻接性和文化趋同性的共同体——汉字文化圈,也因为朱子学始入韩国和日本之时中国强盛的国力等时空因素所赋予的强劲的文化播散力。
朱子学西传欧洲晚于上古儒学,并且争议颇多。从时空条件来看,是因为缺乏地缘优势,缺乏传入亚洲其他国家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更重要的是从传播内核的精神追求来看——缺乏文化趋同性。这可以从理学与神学的不同特质、理学家和西方传教士的不同精神内核来说明。“理学的形成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是宋代义理之学深入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的新形态”。“宋代理学家是一批要复兴儒学、敢于怀疑经典、倡导义理之学的儒家学者。但是他们注释儒经时不仅要否定汉唐注疏传统,阐发道德义理,尤着重建立一套包括宇宙论、心性论、修身工夫论等各种理论问题在内的思想体系。”[12](P60)由此可以见出理学三个迥异于西方神学的特点:一是受佛、道影响很深,而从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一直将佛、道视为异端,虽然采取“合儒”政策,将天主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但是“尊先儒,贬宋儒”,自然不会在译介中国经典时援采朱子的注释,更不可能系统介绍宋代的理学。二是体系完整。与上古儒学零散、年代久远、解释时发挥的空间较大等情况不同,宋代理学不存在三坟五典中对“上帝”、“天”、“理”、“道”等根本概念语焉不详的情况,因而也就很难为耶稣会士按照天主教的神学重新理解儒学或套用儒学传播天主教提供空间。三是重宇宙心性和世俗道德学说,轻宗教。儒学自孔子以来即“敬鬼神而远之”,对宗教采取谨慎、含糊的态度,发展到理学,虽然吸收了佛教的教理,谈论“天道”、“性理”,强调天人合一,但朱熹对宗教的态度始终模糊不清,既说“天曰神”又说“天曰理”,且与中世纪欧洲全部知识体系都是围绕神学体系建构不同,朱子理学还有一套世俗的道德学说,“天即理”的无神性与西方宗教的有神论格格不入。“把自然界的‘天’和‘道理之天’混同,把‘上帝’的地位淹没了”[13](P152)。这些都是耶稣会士们无法认同的。
那么,《印中搜闻》何以对朱子学青眼有加呢?或者说,《印中搜闻》译介、研究和传播朱子学的动因在哪里?又何以能够实现面向大众的传播呢?一般认为,西方介绍和翻译朱子学,是因“中国礼仪之争”中的重要问题“译名之争”而起。天主教传教士在翻译God为“上帝”或“天”、“天主”时发生内讧,各派观点相争不已,从而促使他们研究理学,从中寻找支撑和借鉴。陈荣捷指出,“欧洲自早即注目于朱子理气之学,然其用意,却非在哲学之研究,而在于肯定上帝之信仰。”[1](P278)除此以外,朱子学作为中国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客观上也是欧洲学界系统介绍儒学时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迟早要引起他们的重视。《印中搜闻》对于朱子学的重视,原因概而言之亦不外乎此。而面向大众传播的实现,则得益于马礼逊和米怜以刊物为阵地开展与之相关的讨论甚至争辩,得益于刊物分期、定期出版可以反复、循序、互动传递信息的特征。
据米怜自述,创办《印中搜闻》是为了交流传教信息,为在所谓异教徒国家推进传教服务。他说,“对于异教徒国家,我们首当其冲要做的就是了解其思想和道德特性,了解其各种哲学体系的真实的、文本的观点,了解其国家和各地的各种规定和制度,了解其偶像崇拜。”①英文原文为:It has therefore occurred,that,to us,who have chiefly to do with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character of the Pagan nations,just and SCRIPTURAL views of their various systems of Philosophy,--their national and local institutions---their idolatrous worship&c.[14](P11)米怜的这段话,直截鲜明地阐述了《印中搜闻》译介、讨论、研究和传播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学)、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动机与目的,为我们理解其中有关朱子学文献的译介打开了一扇窗口。
综观《印中搜闻》的办刊过程,其宗旨没有质的变化,但在栏目与内容设置等方面不断朝三个方向调整。其一,世俗性与宗教性并重且渐浓。其二,内容采集放眼东南亚,但聚焦中国。其三,时政报道兼顾典籍介绍。其中中国时政报道和典籍的介绍占据了刊物的主要板块。这从栏目设置的不断丰富和调整中可见一斑。如从第5期开始,在“随笔与传教花絮”栏目增设“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版,专门介绍中国典籍。该专版一直持续到第14期固定不变,直到第16期新设“印中文学”栏目后,始移至新栏目。从第5期至第19期,“汉学书目”专版对《明心宝鉴》、《西方公据》、《圣谕广训》、《三字经》、《御制律例渊源》、《高厚蒙求》、《论语》、《中庸》、《佩文韵府》、《大学》、《孟子》、《天然和尚同住训格》等中国典籍作过专门介绍,提及或简要介绍的汉文典籍还有《三字经训诂》、《三字经集注》、《易经》、《春秋》、《万书总目》、《功过格》、《三才图会》、《书经》等。又如第4期开始将“杂录”栏改名为“印中杂录”(Indo-Chinese Miscellanea),内容之一是介绍中国典籍。专门介绍的有《性理大全》、《朱夫子文集》等。引用或提及的典籍很多,如朱夫子的《四书章句》、《中庸集注》等。再如,从第12期开始,将原来一直置于“杂录”栏的“译文”版单列成“译文和评论”专栏,内容扩展到翻译、评点关于中国人的道德、风俗、奇闻方面的文章。随着内容的扩充,页码从二十余增加到四五十不等,最多时达到九十余页。
再进一步考察《印中搜闻》中依次出现的汉字,不难看出其译介和评述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哲学、信仰、民俗三方面。该刊第1期依次出现了佛、三十三重天、变化、神仙、地狱、清茶门教、奴才、臣、挑筋教、礼拜寺等汉字、词组或短语。第2期至第14期依次出现的汉字、词组或语句(重复者不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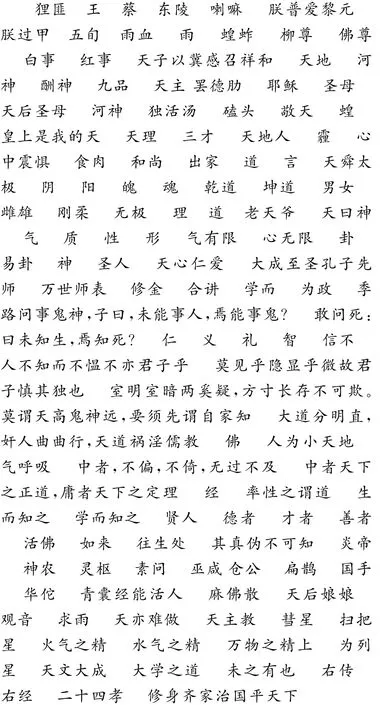
仔细分析这些汉字或语句,除地名、姓氏、中药等字词外,关于中国人的哲学和风俗信仰的字词出现得最早、最多也最频繁。
具体到对朱子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一般在“汉学书目”专项和“印中杂录”栏展开,“译文”等栏目也有少量文章涉及。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关于朱子学译介和研究的基本态度、方式和方法,有必要先概述其对于中国哲学、信仰、民俗的译介和讨论,了解这些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把握该刊研究和传播朱子学的历史语境。
三 《印中搜闻》关于中国哲学、信仰、民俗的介绍和研究
概括地说,《印中搜闻》对于中国哲学、信仰、民俗的译介和评述,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传教服务的。
1.以译介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为中心,关注中国人的哲学信仰、文化习俗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进行比照和解释。如创刊第1期摘登一封马礼逊转来的读者(实际即马礼逊本人)来信《中国教士关于基督的看法》(The Opinion of a Chinese Priest Respecting Christ)[14](P16),谈到:西方人尊崇耶稣,就像中国人尊崇佛,他阐述说,中国人认为“梵(FAN)”是佛的出生地,但他认为梵不是地球上的一个地名,而是三十六重天中的某一重。同时耐心细致地解释中国的“佛”和“神仙”,并追溯其中国本土说法的来源。通读全刊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马礼逊为何在创刊之初即如此耐心细致地解释“神仙”二字,并追溯其本源:因其一直主张用中国本土术语对译基督教术语、解释和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传教理念。这种诠释方法贯穿在《印中搜闻》译介、传播朱子学的全部内容。
2.直接讨论基督教根本概念和中文对译的问题。如第16期《中国人不知上帝》(The Chinese Know Not God)[14](P842)和《中文表达“上帝”的术语》(Chinese Terms to Express Deity)[14](P843)。前篇引述几位翻译《圣经》的学者陈述汉语中没有能够完全对译基督教最根本概念之God和Deity的情况,后一篇形式上是致编辑的信,讨论Deus、Theos或God这些基督教的根本概念用中文怎么表达的问题,谈及:有法国绅士力争用“天主”一词作为汉译God的唯一合适的概念。作者认为,“天主”是一个新词,汉语中原本没有,所以不妥;马礼逊在《圣经》中文译本中用的是“神”这一概念,作者认为“神”这一概念泛指精神存在,更适合于用来指精神的、全能的上帝或造物主(the Deity);穆斯林用的是“主”这一概念;其他译者或“神”、“主”二字分开使用,或联合使用;雷穆沙主张单独使用。作者认为凡此种种各有欠缺,而主张用“上帝”一词对译。该信的作者没有署名,但经吴义雄先生论证,就是米怜本人,他在“译名问题”上与马礼逊发生分歧,并希望能劝说马礼逊放弃“神”的概念,改用“上帝”来翻译英语中的God。
3.讨论中国人的信仰,认为中国人只尊崇儒教,崇拜孔子。如第5期《佛儒比较》(The Foe and Confucius Compared)[14](P156)是王阳明《谏迎佛疏》一文的英译。借王阳明的排佛表达自己尊儒的观念和对佛教的否定。第11期《孔子崇拜》(The Worship of Confucius)[14](P500)一文,确认中国人崇拜孔子,并列举了孔庙的数量和祭祀孔子所动用的牺牲的数量,并追问“如果中国的‘学者’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崇拜,为什么要动用数以千记的无辜生灵作为祭祀来表达对仁慈的大学者孔子的崇拜了?”[14](P501—502)意思是中国对于孔子的祭祀之礼类同于祭祀神灵。作者旨在借此寻找中国人的信仰与西方宗教信仰的相通性和相似处。
4.讨论中国哲学的性质,以及中国哲学背景下对基督教的认识。认为:中国哲学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多神主义强烈反对基督教的自然神论。如第9期《中国的形而上学》(Chinese Metaphysics)[14](P390),通过评述《性理大全》和《朱夫子文集》的重要概念和思想,介绍朱熹的哲学思想。第14期《中国的自然神论》(Chinese Deism)[14](P690),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反映“天主教在中国被视为基督教,仅仅意味着‘自然由上帝管理和指导’的自然神论”,“在鞑靼统治之下的中国人自持具有博爱观念,认为‘天下一家’。现今统治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头领们深受‘优雅’和‘宽恕’的多神主义的影响,对另外一些来自这个大家庭其他分支的人民,既不抑制也不杀头,而是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他们”[14](P690)。写信人声明,自己对这种“优雅”和“宽恕”的多神主义与基督教的诸多不一致丝毫不感到吃惊。[14](P690)
5.讨论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如第12期《评雷穆沙译〈中庸〉 》(Remarks on M.Remusat’s Translation of the中庸)[14](P583),通过评价雷穆沙对“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的解释以及作者马礼逊本人的看法,阐明中国人“中庸”的价值观。又如第13期《中国的道德格言》(Chinese Moral Maxims)[14](P617)一文,翻译和解释《太上感应篇》中关于美德、善恶的名言,也传达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标准。
6.关于中国人的宇宙观及中国文明起源的介绍、分析和讨论,结论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同源。如第20期《古代中国关于天地形状的观念》(Ancient Chinese Idea Respecting the Form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14](P1039),翻译了一段中国人关于天地形状的文字,大意是“天圆如鸟蛋,地浮于蛋壳之上,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星球……”。同期所刊《论中国的冥府》(On the Chinese Hades)[14](P1034),分 别 介 绍 “阴 间”、“天堂”、“十冥王府”、“地狱”。结论是:借助此类稀奇的神话片段,作者认为有学识的读者会从中国神话中发现与罗马、埃及、希腊和印度神话的共同之处,显示出同源的特征①英文原文为:In this curious piece of Chinese mythology,the learned reader will perceive many features in common with those of the Roman,Grecian,Egyptian,and Indian mythology;and such as seem to indicate ONE COMMON ORIGIN。[14](P1038)此外,第14期翻译栏目所刊《天后娘娘》(The Queen of Heaven)[14](P688),是关于民俗的介绍;同期《天亦难做》(None Can Please Everybody)一文,将中国人所说的“天亦难做”解释翻译为“None can please every body”,“It is a hard thing even to be a God”or“Even the part of heaven is hard to fulfil”[14](P690)。意思是人生在世,左右为难,做人难,处事难,即使为天也很难,因为每个人对于天之“好”、“恶”的判断完全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的,并没有固定的客观标准,“园丁希望上天不刮东风以免吹落满树桃花不结实”;“航行扬子江的水手渴望狂暴的东风”;“旅人希望和煦天气”,而“农夫盼望下雨”[14](P690),不同的人对于天有不同的企盼和要求。
《印中搜闻》中关于朱子学的译介、研究正是在上述历史语境下展开并传播的。
[1]陈荣捷.欧美之朱子学[A].朱学论集[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73-278.
[2]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3]http://catalogla.ue.ngov.au/Record/4854902/Offsite?url=http%3A%2F%2Ffind.galegroup.com%2Fecco%2Finf omark.do%3FcontentSet%3DECCOArticles%26docType%3DECCOArticles%26bookId%3D1729700101%26t ype%3DgetFullCitation%26tabID%3DT001%26prodId%3DECCO%26docLevel%3DTEXT_GRAPHICS%26version%3D1.0%26source%3Dlibrary%26userGroupName%3Dnla
[4]张国刚.儒学在欧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周庆山.传播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吴义雄.《印中搜闻》与十九世纪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J].中山大学学报,2010,(2):70-82.
[7]韩洪涛.简论西方社会的精神共同体思想[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4):97-101.
[8]宋丽娟,孙逊.近代英文期刊与古典小说的最早翻译[J].文学遗产,2011,(4):125-132.
[9]冯天瑜.中国原典文化十六讲[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10]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11]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2]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 一种文化学的诠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3]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 历史文献和意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米怜(William Milne)主编.印中搜闻[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