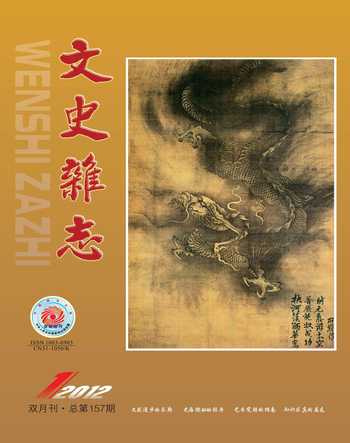“瓜娃子”考释
2012-04-29且志宇
且志宇
一、“瓜娃子”的起源
“瓜娃子”是四川人的口头禅,其意为傻瓜。检点旧籍,成书于1930年的《蜀籁》已有“瓜娃子有瓜福”、“瓜娃子头上有青天”的记载。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说:“方言俗语,皆有所据”。那么,“瓜娃子”又是怎样来的呢?
“瓜娃子”是由“瓜子”一词加上“娃”而产生的。清代孙点《历下志游》:“呼小儿日娃。”原注:“吴有馆娃宫,后官人美者皆日娃,盖爱惜之称也。”四川人称呼别人时也常常加上一个“娃”字,如男孩叫“男娃子”,女孩叫“女娃儿”;在叫自家孩子时,家里的长辈会取其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明称“某娃”。“娃”的称呼也由爱惜转而略带戏谑,如称小偷为“贼娃子”,称高大结实的人为“莽娃儿”等。
“瓜子”一指瓜类的种子,也作瓜籽,如苦瓜籽、丝瓜籽;一指由植物的种子炒制而成的食品,如南瓜子、向日葵瓜子;一指拳头,江湖以拳头为瓜子,清唐再丰《鹅幻汇编》卷十二《江湖通用切口摘要》载“打拳头、跑解马,总称日瓜子”。
愚蠢呆笨不聪慧的人也被戏称为“瓜子”。民国胡朴安先生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十一记载:“甘州人谓……不慧子日瓜子”。“瓜子”一词在《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五回里又叫“乡瓜子”。“乡瓜”也作“香瓜”,《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凡乡人初次进城,不知事理不知人情,俗谓之香瓜。”
不管是“瓜子”还是“乡瓜”,都是以“瓜”为词根的。“瓜”在四川方言作为形容词,意为傻。(参见张一舟:《从(跻春台)的校点看方言古籍整理》)通常以为“瓜”是由“傻瓜”而来,何谓傻瓜?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语》中解释道:“愚人,傻人,则大家恒呼之为傻瓜。”、但在解释傻瓜一词的来源时,他却说“‘瓜字来源未详。”其实,“瓜”表示傻,并非从“傻瓜”一词省文得来。“瓜”这一语源出于古代敦煌地区。
《宋书》记载:“瓜州,出大瓜故也,亦云出美瓜,因以为名。”瓜州即古代敦煌,《汉书·地理志》:“敦煌,古瓜州也”,敦煌因出产甜瓜,于是就把此地命名瓜州,也把此地种瓜的农民也叫做“瓜子”。种瓜人被叫做“瓜子”,这与“棒子”一词来源相同。清王葆心《虞初支志》引铁保《吉林穷棒子说》:“人,何以棒子称?吉林产参,土人称参为棒棰,称刨夫为棒子。”东北山区出产人参,当地人把人参叫着“棒棰”或“棒子”,而挖参人也被叫作“棒棰”和“棒子”。
除了以“瓜”代傻,四川方言中还有以“苕”代土的。土气、土头土脑在四川方言里叫“苕气”、“红苕气”、“苕眉苕眼”。在李劫人先生的《死水微澜》里,有这样的话:“顾天成虽是个粮户,但终于洗不脱周身的土气,也就是成都人所挖苦的红苕气。”四川先前一些城里人还把农村姑娘叫做“红苕花”,把进城的乡下人叫“红苕娃儿”,把土气还未脱尽叫做“红苕屎还没拉完”。这当然是歧视语了,是毋须赘言的。
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市镇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一文提及其家乡贝亚恩当地的农民受到嘲讽:“乡下人(branasses或branes),生长在小块土地上的禾本科植物(aubiscous),山林中的人(bouscasses),一种洋葱(escanoulhes)壁虱(laparous或lagas),这就是萨波尔的农民(payanasde Soubole)的贬义绰号,他们是粗鲁的,笨拙的,沾满泥浆的,没有教养的,穿着古怪的。”(《单身者舞会》)可见无论中外,都有那么一些自视甚高的所谓城里人会以甜瓜、棒棰、红苕、洋葱一类农植物、禾本科植物来当做农民的代名词,以表示嘲讽和轻视。旧时一些人除以职业的对象指代从业者之外,还有拿从事该职业所使用的工具来指称从业者,以表示贬低的恶习。如《戒庵老人漫笔·今古方言大略》:世俗“诟骂农吐之称日牛”;又如成都的人力三轮车师傅常被喊作“三轮”,重庆街头的持棒子的临时搬运工被叫作“棒棒”等。
二“瓜娃子”体现的文化心理
《吉林穷棒子说》载:“高丽称穷贱者为棒子,棒子而穷,故称之云尔。”穿梭于深山密林,攀援于悬崖峭壁的挖参人者是经济贫乏、地位低贱的穷人,故而把穷贱的人也叫做“棒棰”或“棒子”。“瓜子”与之道理相同。“瓜子”一词最初并无褒贬之意。但是由于产业的分工不同,有的行业人员会歧视其他行业人员。农民的勤劳本分、踏实诚恳、老实厚道的品质被曲解为愚蠢呆笨,“劳动人民总是干着最为笨重的体力活,被看着是‘砸(zhang)笨的。”(孙和平:《四川方言文化——民间符号与地方性知识》)“砸笨”也写作“奘棒”,《新场乡志·方言》:“奘棒:愚人。”(成都市大邑县新场乡志编写组:《新场乡志》手写本,1984年10月编写,藏于大邑县档案馆)此现象在扬雄的《方言》里早已体现出来:“僵,农夫之丑称也。南楚凡骂庸贱谓之田僮。”(钱绎:《方言笺疏》)同理,“瓜子”一词的蠢人、傻子之意,也是逐渐演变出来的。传统社会其实一直是瞧不起作为“卑贱者”之一的农民的。吴聪贤先生认为:“中国社会虽然重视农业而受它的影响很大,可是农民却一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中国的重农思想可以说是重视农业而没有重视农民。”(《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性格之蜕变》)长期以来,一些人在提到农民或和农民相关的事物时,多鄙夷轻贱之称,如“土包子”、“乡巴佬”、“黄泥巴脚杆”等等;过去一些四川人口头的“弯弯”、“弯脚杆”、“二哥”、“农二哥”、“栾二哥”、“工人老大哥,农民傻二哥”的说法,就是这种思想的残余。
旧时乡下人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纯生活,对都市里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自然是陌生的。再者他们安土重迁,很难进城,见识不广;即使进城也如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上城一样什么也不懂,对什么都好奇——这在元人杜善夫的套数《庄家不识勾栏》、明人冯梦龙的山歌《乡下人弗识枷里人》以及清人曹雪芹的笔下早已有反映。(《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于戏谑中折射的是广大农民的辛酸与愤懑。)由此而形成讽刺乡下人见识短浅的俗语方言:“乡下人弗识某某”,如“乡下人弗识鬁头丑”(王有光:《吴下谚联》)、“乡下人弗识秀眼”、“乡下人弗识走马灯”(《清稗类钞·方言》)等等。这样的乡下人在一些城里人眼中就成了呆傻的人。“山民朴,市民玩,处也”(汉·荀悦:《申鉴·时事》),归根结底,阶级的对立、城乡的差异乃是所谓城里人(实谓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有闲阶级)歧视乡下人的主要原因。
三“瓜”的产生时代与传播分布
“瓜娃子”以“瓜”为词根,“瓜”表示傻的义项具体产生于何时,已难考证。但从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笔记》记载来看,至少在盛唐之前已经有此说法:
甘州人谓不慧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谓。后读唐书贺知章有子请名于上,上笑曰:“可名之曰孚”,知章久乃悟上谑之,以不慧故破“孚”字为“瓜子”也。则知瓜子之呼,自唐以
前已有之。(转引自《辞海》“瓜子”条)
检索新旧《唐书》,《贺知章传》里皆无对此事的记载。笔记中的“唐书”并非二十四史中的新旧《唐书》,而当为“唐代之书”——唐人郑綮的《开天传信记》:
贺知章秘书监,又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别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耶?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为爪子耶!”(《丛书集成初编》)
《仁恕堂笔记》的资料源于《开天传信记》,但是两则材料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破“孚”为“瓜子”,一破为“爪子”。孚在《说文解字》里属爪部,“爫”即“爪”,但有时也写作“瓜”。《中文大辞典·爪部》爪哇:“元明史皆作瓜哇,系爪哇之误。”又《瓜部》“瓜哇:国名,今之爪哇。”唐并州司兵张义墓志把“弧”字的偏旁“瓜”写成了“爪”。(秦公:《碑别字新编》)可见古代书写时“爪”与“瓜”常相混。辽代释行均在其《龙龛手镜·瓜部》提出:“瓜,古花反,《尔雅》曰:‘瓜,华也。《广雅》云:‘龙蹄兽掌者,瓜也。亦州名。又瓜部与爪部相滥,爪音,侧绞反。”“瓜部与爪部相滥”正是形成以上两则材料差异的原因。在《通俗篇》中也记载了“瓜”、“爪”相混以致张冠李戴的现象:“俚俗谓补不足日找。据《集韵》,找即划之变体,而俗读若爪,盖以划音胡瓜,误认瓜为爪焉耳。俗字之可笑,类如此。”
从《开天传信记》可知,在唐朝时,“瓜子”一词已传播到大唐的都城长安和东南吴地。在宋元明清的典籍中,它一直在变化着,或以“爪子”的形式,或以其他变体流传。“瓜子”在元明戏曲中多作“爪子”,如元无名氏《村乐堂》第二折:“兀那爪子也,你不要言语,我与你这枝金钗儿。”元刊本《西蜀梦》第三折有“瓜关西”一语,瓜关西,是说关西人愚蠢。(这也可证瓜的语源在陕甘一带。)清褚人获《坚瓠二集》卷之一:“各省皆有地讳……山西日瓜”,而清西压《谈徵》:“今山西人有爪子之称。唐代宗(当为唐玄宗之误)以孚名贺知章子,盖戏其为爪子也。([日]长泽规矩也编《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第三辑。此也可证“瓜”“爪”相混同,“爪子”即“瓜子”一说。)
提到“瓜”表示傻、笨的义项的地区分布,《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中记载有三处:陕西西安、江苏扬州、四川成都。除了“瓜”义项的发源地甘肃,上段提及的山西,和《醒世姻缘传》所在的山东方言区外,这一义项的地区分布尚有吴语区、云南昭通等。吴语区从清周亮工《字触》卷之五《谐部》:“吴人谓孚乃爪下子”可证;云南昭通见于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释人》:“昭人斥人愚鲁喜用瓜字,日呆瓜,笨瓜,傻瓜,黄瓜。”
从地理位置分布来看,这“瓜”表示呆傻义项是以甘肃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的;往东经陕西西安、山西到山东,由山东向南,到江苏扬州,再到浙江吴语区;往南经四川,到云南昭通。而组成词语“傻瓜”之后,更是成为普通话的通用语,通行于汉语使用区。
四“瓜”与巴蜀文化
“瓜”是何时引进四川的,已不可考。今所见“瓜”的较早的文献记载为清朝光绪己亥年(1899年)刻本、四川方言拟话本小说集《跻春台》:“要我同你背,莫得那们瓜”。
以“瓜”为词根,重叠为“瓜瓜”。《成都通览·呼物土名》载:“瓜瓜,痴呆也。”李劫人先生对此有更详细的解释。他在《大波》第二部中自注:“瓜瓜,即普通话所谓的傻子。不过在四川人使用的这个名词涵义中,又不完全指傻子,但凡—个人不太狡猾,说话老实,做事有些傻劲,大家也呼之为瓜瓜。”此外,四川方言中尚有“瓜呆子”、“瓜宝气”、“瓜兮兮”、“瓜不兮兮的”、“瓜眉瓜眼”等词与之意思相近;甚至衍生出另—个词汇——刘全进(又讹为“刘前进”)。此语是从《西游记》第十一回刘全进瓜的故事演化而来,即“刘全进——瓜”的歇后。
“瓜”除了在四川方言语词上的表述外,在四川文化上也有深层的渗透性影响。四川民间故事中就有许多关于瓜娃子、瓜媳妇、瓜女婿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西城区卷》中有《瓜媳妇哭丧》的故事,形象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傻乎乎的媳妇形象。《东城区卷》中瓜娃子的故事,看了以后不禁让人捧腹。
“瓜”原意指的是—种智力上的缺陷,是一种歧视语,但在对四川文化的渗透中,却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一脉相通,异曲同工。如张潮《幽梦影》所说:“曰痴、曰愚、曰拙、曰狂,皆非好字面,而人每乐居之。”痴愚对应的四川方言就是“瓜”。民国初年成都中华书局经理胡浚泉先生即以此为号,自号“瓜翁”。一“瓜”字,即把他乐天知命、抱朴守拙、“吾不变吾痴”(《辛巳冬作山居杂咏八首》)的品性显现无遗。
在川剧表演艺术中,“瓜”还是一种艺术表现技法。被誉为“川剧小生泰斗”的袁玉望先生认为要演好川剧中的文小生,便离不得瓜、腻、秀、媚、宝、痴、傻、呆等情态。在《小生表演技法漫谈》一文中,他这样解释“瓜”的表演情态和表演技法:“痴与傻,是指一种生理病态而言,瓜却不同。小生的瓜,不是真瓜,也不是假瓜,更不是一味到底的瓜,而是在某种情况下,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情态——就是俗话说的‘现瓜像。”(《袁玉堃舞台艺术》)这里的“瓜”,便是一种傻乎乎的情态,但是傻里还透露出一点文气、一点娇气,傻得乖巧,傻得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