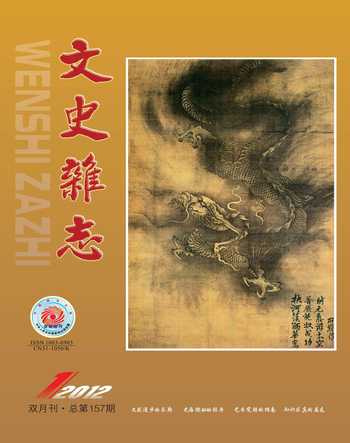“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应是假牌
2012-04-29钱玉趾
钱玉趾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关于西高穴墓发掘一年,经专家研究,基本认定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发布会公布了六大证据,其中,“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被认为是确定墓主身份的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学依据。我们认为,上述石牌应是后人伪造,以下试作辨析。
一、曹操下葬时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曹操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夏六月,曹操担任“丞相”;建安十八年(213年),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汉献帝进曹操爵为“魏王”,魏公、魏王都是诸侯王,但其地位处于其他诸侯王之上,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二十三日,曹操在洛阳去世,《三国志》载:“王(魏王)崩于洛阳……谥日武王”。其时,曹操的儿子曹丕继任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代汉称帝为“魏文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也可称为“魏武皇帝”。
曹操担任“魏王”,是汉的诸侯王,是汉的魏王。曹操去世,被汉献帝谥(加封)为“武王”(带有褒义),也是汉的武王,不是魏的武王。在这里,“魏王”与“武王”是两个不同的爵号,不能将这两个爵号糅合在一起成为“魏武王”。在曹操去世前及梢后一段时间,在文献及出土实物中,都没有发现有“魏武王”的称谓。郝本性《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说:“史书中都没有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当时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说史书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某人某物)还没有发现“很正常”,是可以的;但是,将向无记载,从未发现,突然冒出个“魏武王”石牌便当成绝对确凿,而且不容置疑,那就很不正常了。
林奎成《曹操“魏武王”谥号存疑》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谥日武王……而不是‘谥日魏武王……‘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名,‘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建兴六年冬,“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侯”与“王”是相当的爵号,诸葛亮与曹操是同时代人,都担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诸葛亮生前爵号是“武乡侯”,死后谥爵号“忠武侯”,能不能合称为“武乡忠武侯”?显然不能,史书亦不见载。“忠武侯”可简称“武侯”,后世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以曹操的谥号“武王”比照诸葛亮的称呼,或可称为“曹武王”,可惜史书上没有;但有“曹丞相”的称呼。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易孟醇《毛泽东诗词笺析》说:“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帝曹操北征位于幽燕的乌桓。凯旋时,路过碣石山,赋有《观沧海》,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实际情况是: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加封武平侯;十月,曹操将“大将军”职位让于袁绍,汉献帝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在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乌桓凯旋时,还不是“魏公”,更不是“魏王”,所以严格说,将“东临碣石”的曹操称为“魏武帝”是不合适的。不过,作为文学作品的诗词与史述是不同的,因此,《北戴河》说“魏武挥鞭”应属可行;但是,却绝不能用它来证明建安十二年的曹操就有“魏武帝”或“魏武王”的称号。
曹操去世许多年,成为历史人物后,出现了“魏武王”的称谓。《华阳国志·蜀志·刘先主志》载:“二十四年,先主定汉中……魏王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华阳国志》是常璩所著,成书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至永和十年(354年)间,距曹操去世已有132年左右。上述引文,前句说“魏王”是正确的说法,后句说“魏武王”欠妥。正确的说法应是:魏王薨,谥日武王。《水经注》载:“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以成堰。”《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527)著,晚于《华阳国志》;汉建安九年,曹操还不是魏公,更不是魏王,此说也显然不妥。《太平御览》引晋孙盛《魏氏春秋》说:“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策。”南朝宋沈约的《宋书》有“汉献帝二十三年……明年,魏武王薨。”这与《华阳国志》说法相同,亦欠妥。范子烨《“魏武王”:曹操高陵的铁证》引用多条类似上述引文后说:“出土文物上‘魏武王这三个字,恰好是西高穴村东汉大墓为曹操高陵的铁证。”此说缺乏说服力,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曹操下葬前就有“魏武王”的文献依据,所以,刻有“魏武王”名称的石牌就有伪造的嫌疑。
二、“挌虎大戟”的词语没有文献实物佐证
《三国志·魏书》等文献没有曹操打猎、“挌虎”的记载。屈原《招魂》有“君王亲发兮障青兕”,是说楚王打猎,用箭射兕(一种独角兽)。司马相如《子虚赋》写楚王赴云梦打猎,主要用弓箭。其中“使用专诸之伦,手格此兽”(译为“派遣专诸之类的勇士,格杀此野兽”)。司马相如《上林赋》写汉武帝打猎,主要还是用弓箭,其中有“格虾蛤”(格杀猛兽)。扬雄《羽猎赋》写汉成帝打猎,其中有“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从以上引文看,君王打猎,主要用弓箭,要猎杀多种禽兽,不单是虎;而且“格”兽是派勇士,不是君王自“格”。楚王有专门的打猎场所——云梦,可容“千乘”青骊驰骋。汉武帝打猎,有专门的“上林苑”,在长安之西,据说周围广300里,内有离宫70座。曹操没有专门的打猎场所。在曹操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一直忙于打仗,可以说没有时间去打猎挌虎。那柄所谓的“挌虎大戟”似乎没有用过,更说不上“常所用”了。
《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载:“曹真……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权(孙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
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石虎(298~349),在位五年(迁都邺),爱好打猎。《资治通鉴·晋纪十九·穆帝永和元年》载石虎打猎,是“命劲骑百余”奔驰射猎,是用弓箭射猎。在这里,没有“挌虎大戟”、“挌虎大刀”的影子,石虎本人更与“挌虎大戟”、“挌虎大刀”没有干系。楚王打猎用箭射,汉武帝打猎用箭射;而比曹操晚100多年的石虎打猎还是用箭射。那么,曹操如果打猎,他会不用箭射而用“挌虎大戟”与“挌虎大刀”吗?显然不会。因此,“挌虎大戟”与“挌虎大刀”应属子虚乌有。再说,又是大戟又是大刀,怎么拿呀?如果是右手拿大戟,左手拿大刀,又怎么挌虎呢?或者是头天拿大戟,第二天执大刀,换来换去会不会影响“挌虎”效果?这些都值得怀疑。
“挌”也有嫌疑。司马相如《子虚赋》写楚王赴云梦打猎,司马相如《上林赋》写汉武帝打猎,扬雄《羽猎赋》写汉成帝打猎,都是派勇士格杀,不是君王自
“格”。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有“帝纣……手格猛兽”;陈琳(?-217)是曹操同时代人,其《饮马长城窟》有“男儿宁当格斗死”;曹操的儿子曹彰,223年封为任城王,《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有“任城威王彰……手格猛兽”;《后汉书·祭遵传》有“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稍晚于曹操的左思(约250~约305)之《吴都赋》有“猩猩啼而就禽(擒),狒狒笑而被格”;《魏书·羯胡石虎传》、《晋书·载记·石季龙传》有后赵国君石虎派人造“挌虎车四十乘”、“格兽车四十乘”;《文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注则有“王肃格虎赋日”;《全汉文》还有《谏格虎赋》……
以上古籍有关挌虎、格兽,全都用“格”,未见用“挌”。有人引用《说文·手部》“挌,击也”,说“挌虎大戟”等是“曹操高陵出土”的“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古代,用“挌”表击;用于“格斗”、“格杀”,则非常罕见。《礼记·学记》有“发然后禁,则扦格而不胜”,“扦格”已传成现代汉语用语,其中用“格”未用“挌”。“挌虎大戟”等石牌,如果是从真的曹操墓中出土,其中的“掐”应刻作“格”。现在,我们有理由推测,“挌虎大戟”等石牌,可能是不大精通文字应用历史的造假者制作出来的。如果此观点能成立,说西高穴墓是“曹操墓”就缺失了最重要最直接的证据。
三、“常所用”既违史实且无先例
对“曹操墓”持肯定说的王子今《关于曹操高陵出土刻铭石牌所见“挌虎”》也说:“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曹操亲自‘挌虎的明确记载……虽然目前还没看到相关史籍资料……”这里没有史籍“记载”曹操“挌虎”,有两种可能:一是曹操没有“掐”过虎;二是曹操“挌”过虎,但“挌虎”次数不多或很少。曹操常用剑,说曹操“常”挌虎、或“常”用大戟“挌虎”,就缺乏依据,违背史实。再者,在石牌上刻“常所用”也有违史实。
1980年,安徽舒城出土“蔡侯逆戟”(春秋晚期兵器),胡上有铭文“蔡侯逆之用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三戈戟”,援胡部有铭文“曾侯乙之用戟”。1980年,安徽霍山南岳公社出土一“蔡侯戈”,从援至胡上有铭文“蔡侯口之用戈”;有学者认为其中看不清的第三字应是“蔡侯”的名字。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其靠近格处有铭文(鸟篆)“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剑”为“金”旁加“检”的右偏旁)。
以上实例的兵器铭文,显示了一个相同的格式,即:开头的词是侯或王(器主)的称谓,紧接的是侯或王的名字(或姓氏)。如“越王/勾践(鸠浅)”。依照上述格式来辨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开头四字应释作“魏武王/常”,“魏武王”是器主的称谓,“常”应是器主的名字或姓氏。但曹魏时期还没有魏武王常的人物。因此,只能解为“常所用”;但这却不合兵器铭文的常用格式。于是,刻有“常所用”的石牌就有伪造的嫌疑。何况上述兵器铭文皆铸刻于兵器器身之上,“挌虎大戟”等铭文却刻于石牌上,这是个问题;而且“挌虎大戟”、“挌虎大刀”又不见实物——如果是被盗墓者盗走,可以通过追缴获得,或者在文物市场等地出现,可是却至今不见踪影,这又是问题。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曹操墓真相》说:《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录孙权事迹,就有“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的话……《宋书》卷八十八《肖思话传》也有“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的记载……王立群还列举六例“常所用”词条以佐证。笔者认为,仅根据以上两条,或据后代其他词条,便说“常所用”是汉末或三国时期的社会常用语,大为不妥。裴松之(372~451)于429年开始注《三国志》,是曹操死后200年的事了,而陈寿(233~397)写《三国志》乃是曹操去世50年后的事。《三国志·周泰传》本身没有“常所用”;即使是社会常用语,也不是都能刻到兵器或石牌上。从古至今,除了安阳的石牌,还找不到一件刻有“常所用”的实物。西高穴墓出土的六边形石牌中,刻铭有“镜台一”、“渠枕一”、“口水碗”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数量。按发掘者的观点,“渠枕一”则应刻作“魏武王常所用渠枕”,或者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刻做“挌虎大戟一”。笔者认为,两种刻铭必有—假,而刻“魏武王”的石牌就可能是假造。
四、“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最可疑
59件刻铭石牌有8件圭形(五边形),有51件六边形。如果说“慰项石”是墓主人的常用物品,应该刻一块石牌,刻上“慰项石一”或其他文字。奇陉的是,没有石牌,却将文字刻在“慰项石”底部。如将“慰项石”正放,底部向下就看不见文字;如反放,看到文字却看不清楚是何物。“慰项石”如果是曹操常用之物,随便刻上文字会造成残损,是一种不允许的亵渎行为。
“慰项石”实际是石枕,沉重的石枕不便携带;对于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曹操来说,实际也不能常用。石质料材热传导快,散热快,在炎夏闷热容易出汗的季节,枕石枕睡眠尚可,但春秋不能用,冬天更不能用。因此,“慰项石”的常用性成了疑问。曹操有头疾,《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说:“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方技传》说,华佗为曹操治疗头疾,却没有说过要用“慰项石”。一般说,对于风寒造成的头疾,春、秋与冬季应该好好保温,而不应该把头枕在冰冷的石枕上。曹操说:“吾有头病,自先着帽帻。”他其实是在用戴帽等方式保温。
据贺云翱等说“慰项石是警方追缴而来”,这就谈不上科学发掘。张国安《颠覆曹操墓》说:“两块碑文的隶书字不能登大雅之堂,显示了初学者尚未脱俗的稚嫩……其中的‘魏字、‘慰字、‘王字斜钩都是败笔……”这样低水平的随意的刻字,也应是对墓主人的亵渎。这样的刻字当然有造假之嫌。
在51件六边形石牌中,有一块上刻“渠枕一”。“渠枕”是何物?“渠”有大的意思,又可解做“盾”,如左思《吴都赋》有“家有鹤漆,户有犀渠。”“鹤漆”指矛,“渠”即盾。因此,“渠枕”应是盾枕。夜晚睡眠,头枕盾牌,矛在腰侧手边,符合统帅、领军将士身份。“渠枕”可能把盾牌与枕头的两种功能集于一体了。这种“渠枕”,对于曹操来说,应比“慰项石”(石枕)更加“常所用”。试问,为什么“渠枕”的石牌上不刻“魏武王常所用渠枕”,却要在石枕上刻“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呢?再说,中国历史上哪个帝王用过“慰项石”?有“慰项石”出土了吗?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慰项石”的造假嫌疑最大。
五、圭形石牌的形制、字样与排列疑问多
西高穴墓多次、严重被盗挖,发掘者声称进行了“科学发掘”,挖到了石牌等铁证,便确定是曹操墓。试问,如果有座金字塔被挖得面目全非,然后进行“科学测量”,测得的外形数据能说可靠吗?西高穴墓出土石牌58件(另有1件追缴),其中有8件圭形石牌;8件中有7件是在该墓“前室一块被挑动的石质地板残块下
面”挖到的,而且石牌多数被打坏。这说明,地层关系已被破坏,已无法进行“科学发掘”。唐际根《释疑有关曹操墓的关键质疑》说:“是按程序操作的发掘。8枚石牌中,多枚出自明确的地层关系中……这样的考古地层关系,不可能造假。”不说“被扰动”的地层,而说“明确的地层”,这样的“释疑”能服人吗?
现在来看在“被扰动的石质地板残块”下挖到的包括“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7件圭形石牌以及2010年6月12日挖出的“散落”墓中的“常所用长犀盾”石牌,再加上追缴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其圭形石牌的形制是:长10.8,宽3.1,厚0.8(厘米);51件六边形石牌的形制是:长8.3,宽4.17,厚0.7(厘米)。两者形制为何不同?六边形石牌中有“胡粉二斤”石牌,宽4.75厘米,比“挌虎大戟”宽1.12倍。刻有至尊至贵的“魏武王”圣名的石牌难道比“胡粉二斤”要卑贱吗,只能用窄的石牌吗?还有,“胡粉二斤”只有4字,石牌长却有8.3厘米;“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有10字,按“胡粉”石牌布排文字应有20厘米以上。这是极不合理、极难理喻的形制。
六边形石牌的文字,字与字之间基本上都有较宽的间隔。许多墓志的文字也都有较宽的间隔。“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圭形石牌文字,竖行排列,字与字相连,基本没有间隔;尤其是“武”字的笔画,还突进了“魏”的字框之内。这样的排列,可以说对“魏武王”的极端不敬,镌刻工匠可能会被杀。因此,文字排列拥挤的圭形石牌,可能是伪造。
再比较“挌虎大戟”、“慰项石”的字样与相关铭文,笼统地以其“八分书”就断定年代、墓主,不可信。这里举几通大家熟知的汉碑为参照物以论说。乙瑛碑,又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立(在山东孔庙);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刻(原存山东孔庙);曹全碑,全称《邰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立。其中乙瑛碑有2个“魏”字,礼器碑有1个“魏”字,这3个“魏”字的“禾”与“女”不相连,“禾”与“田”基本齐平,“女”与“山”的底画基本齐平,“鬼”的末画“竖弯钩”苍劲有力,整字间架结构合理,典雅刚健;而“挌虎大戟”的“魏”与之完全不同。曹全碑有3个“武”,有2个是“止”、“戈”的合体,有1个是“山”、“戈”的合体(“山”近似“止”),还有个“止”字;“戈”的横画之下是一短撇画(或说短斜横)。它们与“挌虎大戟”的“武”也完全不同。礼器碑选有2个“王”,曹全碑选有8个“王”,隶书特征明显;而“挌虎大戟”的“王”字已经不是隶体。
《王舍人碑》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立,山东平度县出土,其上有一“挌”字。在曹操时代,“挌虎”、格斗应用“格”;而“挌虎大戟”石牌用了“挌”,可能是伪造。
“慰项石”上“魏”的“禾”与“女”相连,“武”上面是两长横画的特征与“挌虎大戟”的“魏”、“武”相同。“王”的末画波磔向上太凶,超出所有石牌文字的隶书风格。尤其是“武”字下部的部件,横画上有4个齿形笔画,这是绝对错误的刻法。甲骨文“武”是个会意字,从戈,从止(趾),会意持戈行进,显示征战或阅兵的威武;后来,“戈的一撇变体为一短横”置于长横之上。“慰项石”的“武”,违背了会意的初衷,刻成了错字,凭此可认定为造假。
再说“慰”字。《史晨碑》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立,上有1个“尉”,部件“示”下是三“点”。《曹全碑》有1个“慰”、4个“尉”,《礼器碑》有3个“尉”,其部件“示”下都是三“点”;而“慰项石”的“慰”,“示”下是‘小”字形,很不同。但是,后赵建武六年(340年)的《赵西门豹祠殿基记》刻铭拓片上的“尉”,其“示”下是“小”字形。要知道,此《赵西门豹祠殿基记》的入土比曹操下葬要晚120年。这就意味着:“慰项石”的文字可能仿刻了100多年后曹操下葬的刻铭,而不是效仿曹操下葬前的刻铭。况且,“慰项石”的文字笔画随意、纤细,与圭形石牌及六边形石牌都不同,伪造的嫌疑更大。
笔者在《认定“曹操墓”证据的辨析》一文里说,仅凭公布的“六大证据”还不能基本认定“曹操墓”。这里,笔者鉴于西高穴墓多次、严重被盗挖,“挌虎大戟”等圭形石牌在“被扰动的石板下”挖出,其形制可疑,其上文字缺乏文献、实物依据,排列拥挤,字样可能是仿刻后代铭刻,这便有充分的理由可基本认定:“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圭形石牌及“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是伪造的假货;将西高穴墓定为“曹操墓”的证据严重不足。最终的确定,应在逮住了伪造者,获得了招供,缴获了造假工具、材料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