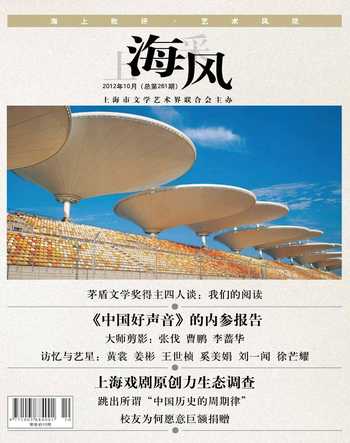姜彬:一生忧乐留民间
2012-04-29张军

壹
姜彬,笔名天鹰,著名作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他是干部型的学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年轻参加革命时,就热爱民间文艺,自学成“家”。他以革命热忱对待工作,成了党的干部,同样以革命热忱从事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著书立说,即使在他担任出版社、作协、宣传部文艺处和社科院文研所领导时,也没有忘记对民间文艺的研究。
1956年,我调进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组织通俗文艺作品和民间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我是个文艺“新兵”,一切都从头学起。那时姜彬同志已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他已经出版了《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中国古代歌谣散论》等书,社会反映很好,令人敬佩。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文艺出版社,我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编辑室主任。有次听说姜彬同志要调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当领导,我们民间文学的编辑特别高兴,后来不知为什么他被调到上海作协工作,1960年又调到市委宣传部任文艺处处长,1963年再调回作协。在这期间我们和他的工作交往就更多了,他的著作都是在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贰
1960年中央召开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姜彬同志与徐景贤、任嘉禾等作为代表出席这次盛会,我因为1959年民间文学编辑室被评为先进集体,也作为集体代表出席了这次文代会,在京加入中国民研会。姜彬同志是我们民间文艺代表的领队。这次文代会上,上海代表和中国民研会领导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记得主要是对民间文学作品和新民歌的看法不同,以后就传为北贾(芝)南姜(彬)的说法,也就是京派与海派。所谓“看法不同”,就是京派比较注重继承传统,海派注重创新。例如新民歌有很多是个人创作,没有经过口头流传,能否算是民间文学,京派有保留,海派比较肯定,因为这是劳动人民写的。《上海民间故事选》与《上海民歌选》是一起出版的。书中有些故事多是农村、工厂、文化干部或故事员写的,没有在民间流传过,算不算民间文学作品,上海认为可以在报刊上先发表,然后再流传,外地有些同志不以为然。这些问题领导知道后,周扬在给民间文艺界代表讲话时,重新肯定中国民研会过去提出的方针,对待民间文艺:要“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并强调搜集整理传统作品与创作新作品都需要,传统作品搜集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意思不要偏重某一方面。
在这次文代会期间还有些趣事。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宴请文代会代表,上海代表进入宴会厅遇到老市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大家感到非常亲切,有人介绍作协文研所陈骥德给他认识,陈老总笑着说:噢!你是个小理论家喽?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还有在宴会进行中间,因为高兴,姜彬同志要和姚文元“拼酒”,讲好各饮一杯,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姜彬同志只饮半杯,不肯喝完,姚把脸一板,气得拍桌子说:“你怎么骗人!”弄得全桌人都很尴尬。姜彬同志一直都很严肃,未见过他与别人开过玩笑,不知为什么这下和姚开了玩笑。从此,我们知道不能和姚随便开玩笑的。
在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来作过政治报告,他们都谈到自己年轻时喜爱文学。特别是陈毅同志,说年轻时写诗,也写过小说等,参加革命后忙于斗争和战争,很少有空创作,但一有空闲还是写些诗。所以后来在文人面前,他说自己是军人,在军人面前,他说自己是文人。他又说如果有人说他的作品艺术性不强可以,如果说政治思想内容有问题,对不起,那就要商讨商讨!这些坦诚、亲切与代表们零距离的讲话令代表们欢欣鼓舞,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谁也没有想到,文代会开过没有几年,代表中的姚文元、徐景贤等伙同造反派大批特批陈毅同志。用“文革”时期的语言,他们真是“罪该万死”!这里我还要再说几句:从1959年至1963年间,在姜彬同志领导下,徐景贤积极参加上海民研会活动,编辑出版上海民歌选,协助姜彬同志工作,对民间文艺事业是有贡献的。但“文革”一开始,他就鬼迷心窍,去投靠张春桥。1967年1月,他在市委“后院放火”联络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夺了市委领导的权,被称为“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影响极坏。上海市革会成立,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成为市革会领导人,群众讥讽他为“徐老三”,从此他走上了一条邪恶不归之路。“文革”结束他被判刑入狱,出来后,曾打电话给李子云(夏衍同志前秘书),要求见面谈谈,被拒绝了,李对他说有什么好谈的?的确,“四人帮"为了打倒周扬、夏衍等,对李子云批斗、隔离审查、抄家,同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相煎何太急,置人于死地!应当承认徐景贤是有才能的,徐如不投靠张春桥造反,跟随姜彬同志去作协搞文艺,那将是另一番景象,也许他会成为出色的作家,或是著名学者。但可惜世界上的事不存在“如果”,道路是他自己选择的,怪不得别人。这些当然都是题外话。
叁
三次文代会后,我们根据“全面搜集、重点整理”等调整了出书,先后出版了系列民间叙事诗,出版了青海省流传的一部格萨尔史诗,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动物故事集》《中国谚语资料》,影印《歌谣》周刊内部发行等。姜彬同志在此期间也转到市郊组织任嘉禾、王文华、皮作玖等同志搜集传统民间文艺作品,如奉贤的《白杨村山歌》《哭出嫁》等,以后又转到吴越地区,撰写《吴歌及其他》《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在对过去新民歌创作的问题上,他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认识到“民歌创作中的种种弱点”,“大跃进民歌,反映浮夸风、冒进风和共产风,在一定程度上对不良风气起了助长作用”。作为一个终生热爱民间文艺的干部和学者,有这样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后,形势发生变化。他先后两次对文艺界作出批示,主要之点就是共产党员不热心社会主义文艺,却热衷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岂非咄咄怪事;文艺界成了裴多非俱乐部,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等。听到这些话,连劳动人民创作的传统民间文艺作品,我们也不敢出版了,民间文学编辑室也撤掉了。到了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后,开展文化大革命,世界文学名著也列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出版社从三楼挂下一张批判周扬文艺黑线大字报,黑线头目周扬下面—姜彬—张军,我和姜彬分别参加作协和出版社“文革”运动,到干校劳动,接受审查批判,可以用“生死茫茫两不知”来形容,直到“文革”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我对过去参与民间文学编辑出版工作进行过反思,认识到自己过去轻视传统,重视革新;在民间文学创作与作家个人创作上,往往抬高了民间文学,贬低了作家创作。说民间文学是“源”,也是“流”,作家是“流”不是“源”,只强调作家向民间文艺学习,不强调民间艺人向作家学习;我们对待“五四”以后研究民间文艺的专家、学者不够尊重,没有主动联系出版他们的著作,甚至把他们看成封建文人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其实文化传统问题,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标准划分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离不开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鲁迅等,文化的主流在作家方面,作家的创作和劳动人民的创作这两方面文艺创作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流”而不是“源”,社会生活才是整个创作的源泉。以上这些反思,可惜未和姜彬同志深入交流,想必他也会有同感吧?
“文革”后我被调到了作协《上海文学》去当编辑,不搞民间文学了,而姜彬同志仍搞民间文艺。
肆
我在作协期间,姜彬同志是民研会负责人。“文革”结束后,1977年市里派钟望阳、姜彬同志筹备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5周年,并在此基础上恢复文联和作协的工作。钟望阳同志希望姜回到作协一起工作,并在自己办公室给姜安排了桌位,直到姜去社科院文研所前夕,还要我到姜家进行劝说,钟是真诚的。我也希望姜回作协工作,这不仅是过去认识,更主要的在我看来,作协与戏剧家协会、翻译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前称“民研会”)关系最密切,有很多跨会会员,姜来作协工作会加强与民协关系。但姜考虑后没有来作协,去了文学研究所当所长。
1990年,我离休后,曾和张世珠、峻青同志等筹建炎黄文化研究会,陈沂同志任会长,张世珠、峻青等是副会长,我是秘书长。我曾向姜彬同志建议民协与研究会加强联合,一起开展文化研究活动。姜同意并举行过一次活动,由姜彬主持,陈沂到会讲话。不久,我辞去了研究会秘书长。从岗位上下来后,我因为与民协联系很少,姜彬同志生病住院,最后去世,我都不知道,没能去医院看望他,临终送别他,这使我非常惭愧和难过。姜彬同志去世前交待夫人郑渭礼,他的文集出版后送给我一套,当我拿到五卷《姜彬文集》时,书是沉沉的,我的心情也是沉重的。和姜彬同志相识交往半个世纪,民间文艺对于他像是空气,像是生命,他的一生可以说都献给了民间文艺事业了。他的满腔心血赤裸裸的凝聚在文集里。他那浙东人的耿直、坦率、坚强,毫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热情以及他那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在文集中处处呈现出来,我敬佩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