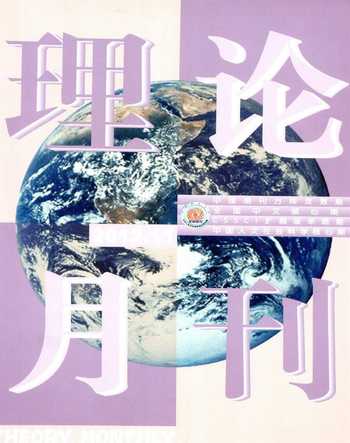引经据典与白话散文写作
2012-04-29刘弟娥
刘弟娥
摘要:引经据典是传统诗文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在新文化运动伊始,引经据典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被提出,成为当时散文写作者极力规避的修辞;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写作者以及读者对散文作品的审美要求不断提高,传统散文中的一些传统写作因素零星被写作者采用,引经据典在这种情形下被吸纳到现代散文中。新的历史时期的白话散文写作,势必使得引经据典在白话散文中的应用相应地作出一定的调整。随着白话教育的普及以及传统文学教育的退居幕后,接受白话教育的一代人对于引经据典更有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不但体现在引经据典语言与形式的改变,同样也体现了写作者面对不同的读者而采取的不同的写作策略。
关键词:引经据典:白话散文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1-0073-05
引经据典是学术写作中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段,同时也作为修辞一体应用于诗文中。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称它为“引用”,并将其列为修辞格之一。历代不断有学者论述这类修辞现象,并有过不同的称呼。所谓“引经”,当源自“文本于经”这种对儒家原典的信奉。“文本于经”指向三个方面:其一,文章的理论起点应该来源于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文以载道”;其二,文体的观念来源于五经,如赋、比、兴三体以及文论家对后代文体的溯源;哄三,文人在写作中对经典语录的引述。所谓“据典”,“典,来自旧的,所以也成为‘典故。用典,也称为‘用事或‘隶事。”王力则又将之称为“稽古”,“稽古是援引古人的事迹来证实自己的论点。”“引经与稽古的分别,主要在于:(1)稽古是叙述一些历史事实,引经则是援引古代里圣贤的言辞;(2)稽古可以有正面的,有反面的,而引经则一律是正面的言渝。”学术著作中的引经据典。主要作用是着眼其说明论证等方面的实用价值,所谓“着眼于学理——尊重对象。依赖先贤,商榷同道,此乃使用引语的三大动机。”;而文学作品中的引经据典,“只是为了使文章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使文章更具有审美性。
20世纪初,一场席卷中国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向,引经据典与“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一样,成为新文学的对立面。但是,散文在新文学中的发展,与小说,戏剧这样的新锐文体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内无继承,外少借鉴的情况下,散文短时间内空无依傍的发展结果是:当胡适等人认定“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评论的时期”的时候,不仅文化保守者提出异议,就是新文化人士也颇不认同。这种情况得以改变是在周作人提出“美文”与“晚明传统”之后,外借英美Essays,内接“晚明传统”,为散文写作借鉴传统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中国白话散文发展影响至巨当是传统的力量,“当时(五四时期)思想界有影响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者无意地回到传统中的非传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由新文化的开创者来提出传统散文文本的可继承,拓宽了散文写作者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可供描摹的蓝本。“晚明传统”的提出不但为新文化人,同样也为周作人自己继承传统提供了一种可能。这样。随着晚明传统的登坛入室,引经据典这种修辞开始在散文中出现。为集中笔墨,同时也从白话散文创作的实际出发,本论题关于白话散文中引经据典的讨论集中在对传统修辞方式的继承以及对传统经典文本材料的引用。因而,除非是行文所需,对于西方文本的引用当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一、读书记——学术与散文之间的桥
传统文人在书斋苦读之际,一般会随手将自己所读之内容与心得以读书记的形式记下来,从而有了数量颇多的读书记。以有清一代为例。
当时(乾嘉,笔者注)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当中者。
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资料性质者,有渐成粗制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
当这种“原料与粗制品”一旦“精制”则成学术,而稍加修葺,“添上了书林掌故、得书经历、读书所感”时,便具有了相应的审美性,则成为散文史上清新可读的小品文。正因为有此特点。“读书记”就显出其学术性与文艺性的两方面的性质。但是,在传统文人眼中,这种文体既不能入学术之林,亦不能进选家之眼,是颇为尴尬的文体。
写作读书记,两个基本的工作,其一就是“读书”,其二,则是“抄书”,这种抄书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引经据典”的过程。
“读书记”在现代散文中的延续,就是被目为“书话”这一体。普通的资料性质的“读书记”、“藏书题跋”因为“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的审美性而具有了散文的性质。当然,对于大多数的书话写作者来说,书话写作也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如阿英、郑振铎、唐弢等人,他们的职志也不在此。在散文写作史上,以写作书话尉为大宗的当以周作人与黄裳为代表。与唐瞍等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终其一生以散文为最主要的写作方式,学术研究很少或基本不涉及。如黄裳,尽管藏书颇丰,但是并不以研究学问为志向,先后有书话作品结集的就有《榆下说书》、《来燕榭读书记》、《清代版刻一隅》等,以这些“读书记”为起点。“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夹杂了大量世俗感情”的散文在其后的散文写作中大放异彩。
黄裳在书斋阅读之余,由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以及个人兴趣。在青年时期以及79年之后的岁月中,根据自己游历之感触写作了大量的游记,前期以游记结集就有《锦帆集》、《锦帆集外》、《金陵杂记》等,后期有《花步集》、《晚春的行旅》等,自然,这些还不包括散落于其他书中的零章杂篇。黄裳之游记,着眼点不在于风土人情与山川风物,而在于对当地的人文之胜的探秘之趣。如《贵阳杂记》与《昆明杂记》,受当时时代兴起的“南明热”之影响,黄裳对“南明”史实颇有兴趣,平常所阅也以此类为多,当接触到与“南明”与重大历史关系之人物的生养之地贵阳与昆明时,前朝往事,不由得纷至沓来,由杨龙友、马士英,昆明有吴三桂、陈圆圆这样的中心人物,带动整个文章的线索,以自己游踪所及串联起这些人物的活动。读这一类散文的时候,“时时会感受一种‘左右逢源之乐,它会诱使你翻出另外许多本书,对读、思索。”㈣只有腹笱广博者,才能面对有着历史积淀的人文风物涉笔成趣。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前期的藏书收集,没有书斋阅读的感受,没有记下或发表或未曾发表之“读书记”,是不可能成就其之后的散文写作。以自己的阅读所得,形成日后散文写作的资料,这种散文,其后也被称之为“文化散文”或者“学者散文”,而这种写作体例,在现代散文史上,是以周作人与鲁迅为起点的,而周作人对“文抄公体”之悉心经营更给后代文人以示范作用。
二、“文抄公体”昭示引经据典在现代散文写作中的文体意义
所谓“文抄公体”。指的就是周作人中后期“以阅读为契机,依靠知识的绵延和思想的碰撞,深入到文化、文明、人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而具体的写法。则是大段摘抄原著,中缀少量按语,亦即‘文抄公是也。”相对于传统散文中的“师其意而不袭其文”式引用,周作人在“文抄公体”对前人文献是采用直接引用的方法。为何要采用这种直接的引用法,周作人有着自己的认识,“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周作人“文抄公体”所着意之点在两个方面:其一,“别人”“思想”之“高明”;其二,“别人”“文章”之美妙,以“思想”与“文章”的两个标准来衡定摘抄进入自己文章的前人文本。正因为此。周作人“文抄公体”系列为保证原文“思想”之“高明”与“文章”之“美妙”能如实传达,相对于前人之“引前人成语,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抄袭”之引用,周作人对原文加以直接引用。虽然这样可以让读者悉知其引文之来源,文章成文之过程。以及原文“思想”与“文章”之“高明”与“美妙”。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增加写作者应用语言之难度。大量摘抄原文不但容易形成“殆同书抄”的第一阅读印象,同时,文本之间不同行文风格以及语言之间的冲突就会表现得很明显。许是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周作人认识到了语言之间的隔膜,继而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行文风格,从而不但弥补了自己文本与所引文本之间语言上的隔膜,同时也稍稍弥缝了文言与白话的缝隙,形成了“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这样一种观点。
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这样文白杂糅的语言,在引用原文,特别是古典文本的时候,才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从而使得文本在语言上具有一定的和谐感,周作人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平淡”(胡适语)“枯涩苍老”、“古雅遒劲”(郁达夫语),这种风格,是以周作人自己的语言以及所摘抄文本共同构筑的语言风格。“用若干穿插语,串连起一大堆先贤语录或原始资料,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学界,乃是文史学者著述的不二法门。在“文抄公体”中,本有许多属于知识与思想的介绍,如实引用原文,便于保存先贤之妙言隽语,也便于读者复核,写作者得旁征博引之乐,读者则得“按书翻检,随时触发”之趣,这本是作为一个启蒙者的带有学术性质的思想探索,语言与意境之不和谐当不成写作之时最主要考虑的问题。但是一旦以“美文”的要求来衡量文本。试图追求“余情”之时,那么,除了要面对除文、白语言之间的隔阂之外,不同文本之间意境与思想之协调也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水里的东西》一向被论者以为“奇文”,此文化虚为实。将“河水鬼”这一虚无缥缈的东西,化身为“在岸上柳树下‘顿铜钱,”“的野孩子”这种实有之物。此文分别引述柳田国男之《山岛潭集》、冈田建文之《动物灵异志》以及《幽明录》中关于“河童”之文,并非是从学理之层面的求证,而是从情感角度的印证。如果孩童似的“河水鬼”给读者以无穷的想象的话,那么其写作意图则预示着“文抄公体”及后广阔的写作天地,“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从“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角度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成为周作人弥合本文与引文之间思想差距的粘合剂,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以这种普世的“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精神,对民间荒诞不经之传说,挖掘其深层之民间心愿与人情。并予以体贴之同情。推而广之。周作人此类文章的精品,不但集中在对知识与文化的介绍,同样也体现在以文化、人情之视角来观察前人文本,从而再生出新意,这也是周作人前人从学术的角度多加诟病的“琐语”表示“可喜”的原因。从而由引经据典的学术性应用中引发出来的散文审美性。
作者对人世隐曲之痛完全融合在所摘之文中,在别人的生活体验中(哪怕是一种完全虚幻的感情经验)中融入到自己的感情,同时将读者也带入到这种个人感情体验中去(如《鬼的生长》、《无生老母的信息》)。因而,如果仅仅以“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意义与价值来估量周作人的此类散文,无疑会陷入到“知识性”与“文献性”的窠臼中去。“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不过是其表,而对“凡俗人世”深沉的感喟以及浓烈的身世之感才是文章之实,这也上接周作人对散文的“余情”之要求。文章之表层原文引用。是为了从“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忠实反映鬼物存在之信仰与认识。文章深层之感情则表现为写作者对前人的遭遇的深切之同情之理解,并由而发生之深切的身世之感,情感之恸。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周作人写作此类文章的目的乃在于表达感情之需要,而并非仅仅为了知识之传达,甚至也并不是为其引文之“以足其文气也”之功效。
正是借由这种语言的实验以及感情的驱遣,周作人“文抄公”系列的一部分文章不但具有“知识之趣”。同样也具有“知识之美”,而这种“美”与“趣”是统一在文学的审美之一体中。因为有着自身的感情体验。所以在“文抄公体”中所摘抄之文本,其情感体验已经远离原文本,成为周作人文本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是周作人在处理引文之时候,赋予了引文迥然不同的文本意义。从而构建了新的审美体验与情感经验。
三、引经据典在白话散文中的延续
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散文热,将久已沉寂的散文写作再一次推向读者的视野。关于文化散文(主要指的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体式渊源关系,有论者将其与桐城派的散文写作联系起来,认为“绝大多数“文化苦旅”散文中都包含了一个名胜、一个历史故事、历史名人、历史遗物,笔者的笔触也多落笔于对这些史实、史事的考辨,追述。”关于“桐城派”,在有清一代考据盛行之时,姚鼐旁枝斜出,认识到“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桐城派以及后之“文化散文”,采用“助文之境”的方式将前人文献剪裁成文,或略或省,或用自己的语言转述之,一切取决于行文之方便。基于此,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在引证文献之时,去“考证累其文”之弊,而扬考证“助文”之长,终使世纪末的散文大放异彩,成为一代之胜。
余秋雨的散文名篇《风雨天一阁》的题材并不新鲜:中国延时最长的私人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历来多有人论及。但多就“天一阁”书籍之流散作版本之考证,如黄宗羲之《天一阁藏书记》、赵万里之《重整万氏天一阁藏书记略》及近人黄裳之《<天一阁失劫书目>序》等,为求资料引证之详实,写作者也尽力将所得资料在文本中得以全面反映。关于《风雨天一阁》的写作,余秋雨也不否定在写作《风雨天一阁》之前所做的史料考证工作,自诩为“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但是,当《风雨天一阁》这一文本呈现于读者眼前的时候,并不见写作这类题材所习见的资料的大段摘录,一切材料的取舍都服务于写作者的情感的流动,文献成为写作者任意驱遣的材料。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文本中(以《风雨天一阁》为例),对于必须要有所取舍的浩如烟海的前人文献典籍,他采用的方法并非周作人式的直接引用,也不是传统的“换句换字”法。在他的文化散文文本中,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反语之类的修辞在此文中已经不再适用,其成文的过程,就是文献资料破译成直觉造型的过程。这种破译的过程,就是在古典文献记录之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人物及事件加以想象,以自己的语言出之。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这是余秋雨《风雨天一阁》中的藏书家范钦形象的塑造,这种造型,自然来源于文献中关于范钦生平记载以及日常行事之记载。试以黄裳关于江浙另一藏书家祁承鄴的文字相比较。
诸札中,以“藏书事宜书付二郎、四郎奉行”一札最可珍重。澹生堂抄本书于书林有重名,传世稀若星凤。赵谷林毕生求之,所得不过数种。今日公私所藏,通计之亦不过二、三十种耳。读澹翁手札,知于中州所录书共一百三、四十种,皆坊间所无,而京内藏书家所少者,意当多出朱氏万卷堂。其书于明末黄河决口尽付东流,承鄴传写更流散殆尽,是书林一巨劫也。承鄴论两浙藏书无逾我者,非不知有天一阁范氏。特于范氏所收书不甚措意而轻之。其言曰:“出发回书共八夹,内有河南全省志书二夹,不甚贵重。”其意可知。此藏书时代风气使然,不足异也。澹翁言:“十余年所抄录之书,约以二千余本。”此后虽有增益,必不甚多。以此计澹生堂写本书。当约略近之。每本工食纸张不过银二、三钱,可见当日物力之廉。澹翁慨然言曰:“只是藏书第一在好儿孙。”似预知四郎后日佞佛,藏书多为沙门赚去之事者。
作为现代藏书家,黄裳的文字更具有资料的性质,资料得之不易,公之于同好之急切,在这样的写作心态之下,详细的引证相关的资料,自是行文之需。关于范钦,在学界中并非籍籍无名之辈,其生平之资料也并非是难觅之轶品,作为余秋雨来讲,不能或不愿“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甚至也不能达到“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陈寅恪语)的高度,所以,余秋雨选择了当年姚鼐之路:与其在人才济济的考据学之路上作一个平庸的学问家,不如旁枝斜出,将学术融入到文章中,以文章的艺术性来突出自己的个性价值。不斤斤于文献之忠实记录。这在书话作者中本就有所体现。余秋雨擅长以文献记载为线索,提炼人物形象,创造事件场景,用在学术写作中极难容身之“夸饰”建构自己的文本,而舍弃了对前人文献之忠实的再现。这样,引经与据典在余秋雨的文中,即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文献记载之文字,用现代白话将诘屈聱牙之文言用白话出之,在白话教育普及的当下,自然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阅读;另一方面,典故,或者“稽古”之方法,在余秋雨文中。很好的利用来建构“直觉造型”与“意象”。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会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做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这一材料的原始来源出自谢垄《春草堂集》,原文是这样的:
鄞县钱氏女,名绣芸,范茂才邦柱室,丘铁卿太守内侄女也。性嗜书,凡闻有奇异之书,多方购之。尝闻太守言:范氏天一阍藏书甚富,内多世所罕见者,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不生蠹,草之功也。女闻而慕之,绣芸草数百本,犹不能缀,绣芸之名由此始。父母爱女甚,揣其情。不忍拂其意,遂归范。庙见后,乞茂才一见芸草,茂才以妇女禁例对。女则恍然如有所失,由是病,病且剧。泣谓茂才日:‘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
文字之改变是显然,原文作为写作材料出现在余秋雨的文中。赋予了另外不同之深意:既有对为天一阁之牺牲者之哀叹,也有为天一阁强大的向心力而惊叹。这种复杂的心态,一同构筑了《风雨天一阁》集挽歌与赞歌于一体的哲理意味。或者可以这样说,造型与意象的塑造,并不是余秋雨写作的根本之目的,相对于学术写作中的“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斩钉截铁,余秋雨在散文文本中表达的更多的是将造型再一次破译成自己所理解的“人生赞颂”与“哲理”。
“把艺术家对这些江河湖海的描写仅仅当作自然景物的描写而收入《风景描写辞典》是冤枉的,它们应该立即被读者‘破译成人生的赞颂,只不过这种人生还包含着自然本身的洪荒神貌和固执意态。”“只有哲理。才能使遥远的故事焕发出普遍的魅力。”
而这“人生赞颂”与“哲理”过程,就是将传统文化与传统文人造型化,意象化的过程,支撑这一过程形成的有力之资源就是浩如烟海之古典文献。文化散文,以自然风物的游览为感触之经。以传统文人的生命历程为记叙之纬,以文献资源为记叙之源,以“人生赞颂”与“哲理”为行文之实。这些内容,将余秋雨的散文再一次指向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与“桐城派”的“义理”接上了源头。
四、结论
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借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罔矣;以考证之体,而妄援著作之义,以自文其剥窃之私焉,谬矣!
这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学术之文的引经据典所做的要求,文学之文之引用,不管是“援引古义”还是“袭用成文”,均可不受章学诚所标举之“陋”、“罔”、“谬”的限制与约束。但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如周作人、鲁迅等,其内心强大的传统文学因子,以及刚刚建立起来的学术规范,使得他们在写作旁征博引之散文的时候,其丰厚的知识素养,熟记于心的文献与掌故,无论是以白话还是文言均可自由出入而毫无障碍,当时的理想读者在阅读之时自然有会心只体验。但是,在面对白话普及之后的青年读者的时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于平时文章的写作方式。这一点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病后杂谈》当可见出蹊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作为演说面对的是普通读者,以口语讲述之,关于文献资料,直接以间接引语,乃至于糅合夹杂平易之语言出之。而《病后杂谈》,并非为通俗易懂之演讲文,其理想读者也要宽泛得多。因而,所引之文献仍旧以直接引语加以摘抄。新一代的散文写作者,他们对传统文献的了解多由成年之后习得,并不具有与前代学人相比肩的与经典之间的体贴亲近,因而,在他们眼中,无论是文献还是典故,在行文过程中,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读者。文言传述之古典,白话传述之今文,其间隔膜显然,为求行文之统一,语言更为接近大众,白话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作为流行文化来讲,它有着自己的流行性,必然会被后起的流行因子击溃:同样是引经据典,百家讲坛以更为大众所接受的演说体取代文化散文成为新的文化宠儿,这一点,是否在鲁迅的前述写作中就已开始逗露其意?
随着文化散文的势成强弩之末。以黄裳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仍旧有着自己的需求市场。这一脉散文,以其不温不火的语言,以其扎实的传统学问功底,行文之见解不够炫耀人耳目,但以其知识性赢得了固定的读者的关注。随着这一代传统文化人的逐渐凋零,后起之写作者知识结构之不同,这一体散文写作或将成为广陵散绝了吧!
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