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陷阱
2012-04-29叶丽雅
叶丽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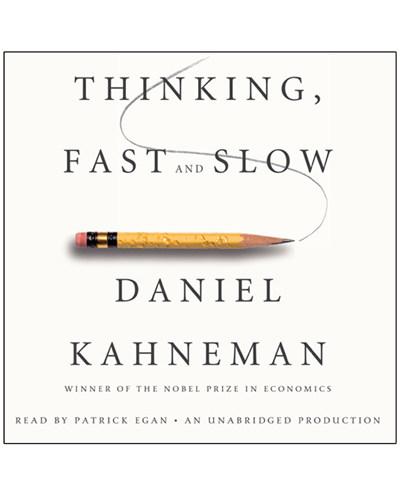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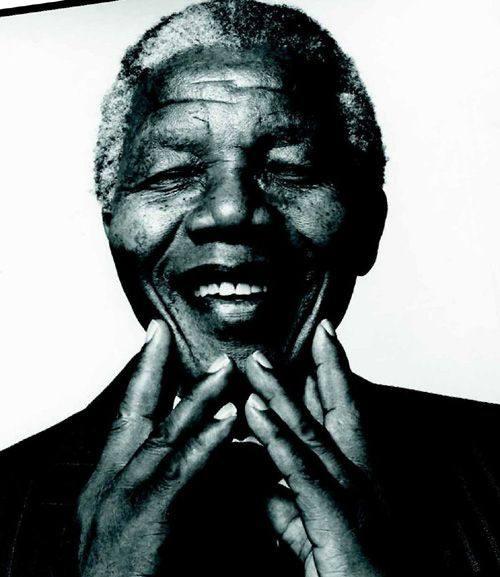
假设有人告诉你有一位名叫琳达的女孩,她年轻、单身、活泼、非常聪明,而且在读书期间即热衷于社会公益和歧视问题,那么,您觉得琳达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可能性更大些?
这里我们提供选择两个选项:(1)银行出纳;(2)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
您会选择什么?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选项(2)。
很不幸,选项(2)违背了概率原则:因为所有的热衷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都是银行出纳,而并非每一位银行出纳都热衷女权运动。就可能性大小而言,选项(1)是唯一的答案。
非理性的人
或许您会站出来辩解,“琳达问题”的题面给人太多暗示,而没有定语的选项(1)似乎也暗示了琳达不是女权运动热衷者。设计这个实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新书《思考,快与慢》(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分析道,“琳达问题”并非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即使是那些受过严格概率学训练的斯坦福商学院研究生们,也有85%给出了错误答案。
这位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与研究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大前提:人是理性的,最终提出了不同见解并因此获得诺奖。《思考,快与慢》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的基础,加上最近10年的研究,整理出来的一部有趣而又充满智慧的书籍,它被《环球邮报》称为“如果你今年只能读一本书,读它”,被《纽约时报》称为“今后100年人们都会记得它”。(可惜的是,特沃斯基于1996年即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否则他会和本书作者一起出席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
在这部书里,卡尼曼提出人脑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先说令我们引以为豪的“系统二”,在卡尼曼的定义下,这是比较缓慢,但谨慎、善于剖析、认真推理的,符合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系统。“系统一”,则是比较敏捷、机动,更依靠直觉的无意识体系。系统一帮助我们快速地辨识电话语音中的热情或者敌意,在初次见到某人时形成第一印象;而系统二让我们最终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去填写枯燥的税单,并将汽车停在某个狭小的停车位。系统一提出建议,系统二处理问题。要判断人们是在用迅速敏捷系统一思考,还是用理性审慎的系统二思考,是观察当时思考者的瞳孔大小。
乐观的观点认为,系统二是系统一的主宰,正如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不过作者数十年的研究证明,谨慎而理性的系统二通常也比较懒惰,容易疲劳,或者用一个学术上比较概念性的词,容易“自我耗尽”。经常的,系统二会自动怠工而去主动接受系统一感知的简洁但可能不太可靠的答案。
“琳达问题”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甚至本应该知道答案的进化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也在面对问题时纠结不已。这位对概率学了熟于胸的学者称:“(面对题面的时候,)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小人在上窜下跳,对我喊,‘琳达不可能只是一位银行出纳员,看对她的描述!”卡尼曼解释说,这就是古尔德的系统一。
“理性的系统二可以说是思考的主宰,是最终行为的促成者,人是理性的。” 卡尼曼在书中写道,“但不得不说,本书认为,主角只能是敏捷直观的系统一。”这或许并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再度深究,我们就会发现直观感性的系统一背后,是个人大量历史数据案例积累,然后在面对某一问题时,突然跳出来,给出可能不是很理性但很经验的结论。我们每天的对话都包含有大量未曾明确表达的背景和前提条件,语言学家称之为“暗示”。这很好地解释了人们思考过程中的某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断层。
“人们的思考过程充满了系统失误”,但是,这些失误并非由于情绪或者某些偶发因素,而是内嵌在我们认知体系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以,人不可能是理性的。
认识自己
事实上,直观感性的系统一虽然可能导致很多错误,但也是我们在大部分时间把事情做对的原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系统一面对世界。系统一帮助我们迅速辨别碎片信息,使大脑自动产生解决方案,那些有经验的医生、救火队员尤其如此。这些久经沙场的专业人士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可以完全不假思索地做出正确反应,就好像华佗口中的大哥一样,在病还没有产生影响的时候,他已经发觉其苗头,施救于未然。
本书的绝妙之处在于,在区分了人类思考的快慢两大系统之后,作者通过一系列实验指出系统一最可能犯的几类错误,让我们了解:为什么统计学数据经常与事实不符,为什么那些昂贵的理财师们挑选的股票组合和审计师做财务预测没有任何价值,为什么商人们忽而极度自负忽而又极度谨慎,以及为什么记忆会让人做出与直觉相背的决策。我们并不一定都能一一修正,但至少知道哪些地方应该警惕。毕竟,更理性的系统二大多数时候都在偷懒怠工。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一起设计了大约20个精巧的实验,最后归纳了三类最主要的思考误区,其一为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其二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其三为享乐心理(hedonic psychology)。
锚定效应指人们容易被一些偶然遇到的数据所影响。曾经有这样一个实验,在模拟审判小偷前,要求德国法官们掷骰子,做了手脚的骰子结果非“3”即“9”。结果掷到“9”的法官平均给小偷判刑8个月,掷到“3”的平均判5个月。
前景理论是卡尼曼获得诺奖的理由,它展示了在不确定情况下决策,人并非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思考者。假设选择1,你可以获得46美元,如果尝试第2种选择,则有50%的机会获得100美元。一个理性经济人通常会选择尝试第2种方式,但实验却证明更多人选择第1种方式,避免任何可能损失。有趣的是,同样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损失,高尔夫球手在最后推杆的时候往往可以表现得更好。
享乐心理则是卡尼曼在其伙伴过世后发展演绎出来的。他从问人们是否快乐开始,发现人们对快乐的体验有两种,一种是经历型,一种是记忆型。经历型的快乐体验是累积的,而记忆型往往忽视过程,只记得高峰和结尾时的感受。在一项充满争议的实验中,两组病人分别去做痛苦的结肠镜检查。A组按常规流程进行;B组同样,只是在检查结束时增加了几分钟相对温和的探视,但B组未被告知他们获得“额外”待遇。如果我们问哪组病人更痛苦?就痛苦总量而言,显然是B。但B组因为结束得相当轻柔,反而是B组的病人感觉痛苦更少一些。大部分人记忆快乐/痛苦的模式是“过程忽略型”,或者说符合“高峰-结尾规则”。
作者在书里还介绍了其他几种系统失灵,或者称直觉失误。比如片段截取(framing),如果人们被告知他们即将面临的手术成功率是90%,而另一组人被告知死亡率为10%,前者比后者更愿意接受手术。又比如沉没成本(sunk-cost),为了避免事后后悔,人们总是倾向于把钱投入已经投入大量资源,但并没有太大前景的项目上。
计划失误(planning fallacy)则是我们编订预算时常见的。人们过于乐观地忽视了一些小概率事件,而这些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人们又偏执地认为这件事会有个美好的结尾,结果预算一再扩大。1997年人们计划在英国爱丁堡建造苏格兰国会大厦的时候,预算400万英镑,2004年这座大厦最终完工的时候,耗资4.31亿英镑。“计划失误是认知失误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卡尼曼指出。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盲目乐观让我们每天最终从床上爬起来面对全新的一天。乐观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免疫系统,它让我们比现实中的自己更有生命力。而且,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乐观,让个人或者组织能够最终战胜其他所有失误可能带来的糟糕后果。
实力,还是幸运?
上述案例都只是一些实验,在一些现实生活场景中,人们并非像在书中看到的一样容易犯错。事实上,在面对一个骗子而不是一个逻辑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分析事物而非某一象征性图形的时候,在我们评估原始数据而非百分比的时候,人们都还是比较容易能够做出理性选择。
毕竟,我们人类都是自然选择的幸存者,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的任务就是在处理复杂多变的环境,以更好地适应这个环境,哪怕是心理学家精心设计的实验陷阱。事实上,人类在认知失误上的犯错率并不见得比我们在语法上犯错的概率更高,所以如果我们对理性的要求如果超过现实的需求,那便是无意义的。
作者坚持认为理性与否并非经济上成功的原因,他发现所有在商业上和体育竞技场上有卓越表现的人,最终的理性程度都接近于平均值。成功,更多的是因为幸运——这个幸运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在书里,作者提到他研究的一家绩效很好的零售商店,短期看或许是因为这家店的选址极佳。然而长期看,它的业绩未必一直如此好,因为商业也有其回归平均回报值的自我修正功能,成功终会引来竞争者。
所以,作者撰写本书并非教导大家如何克服日常生活中的误区,而是建议大家“认识到自己可能会踏进某些认知的误区,慢下来,向你的理性求援”。当然,如果你在下棋、救火或者医疗等领域受过超过1万小时的专业训练,那么或许你可以闭着眼睛,听从你的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