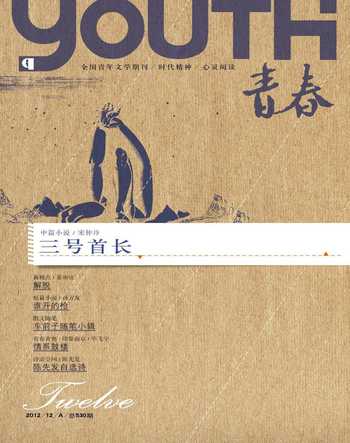车前子随笔小辑
2012-04-29车前子
称呼之难
我真不知道怎么向外人介绍自己妻子。
“这是我妻子”,听着总别扭,像炫耀一件内衣似的。
“这是我太太”,按照老理,称呼别人家的妻子才称太太;向外人介绍自己妻子的时候说“这是我太太”,就像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你好,我是车前子阁下。”
“这是我夫人”,有爵位的人才能说,在中国古代。“这是我夫人”,进士都不能向外人这么介绍,除非近视眼。
“这是我爱人”,老一辈干的事。
“这是拙荆”,太糖醋。
“这是糟糠”,太粗鲁。
“这是老婆”,太亲热。
“这是内子”,在一个宅男时代,很不符合现实。
“这是席子”,太方言。某地把自己家的老婆叫“席子”。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不知,比如知青聚餐,杀鸡一只,人多鸡少,只能炖汤,茶馆店老板的女儿嫁给洗浴中心董事长的儿子,这叫汤里来水里去,汤汤水水好对付。知青去村里借坛子借碗,他挑了一只空箩筐,毕恭毕敬地站在贫下中农门前,把落在鼻尖的眼镜推到差不多额头上去,清清嗓子,字正腔圆:“大叔,您好!我们想借你家的坛子用用,马上就回,行不行?”大叔十分客气,一回身,拿起锄头就从房里冲杀出来。
此地方言把自己家的老婆叫“席子”,自己家的女儿叫“坛子”。知青初来乍到,不知道,扔下扁担箩筐,边跑边想,这大叔也太小气,不愿意借坛子,那就借几只碗吧。他站住,喘着气说:
“大叔,大叔,坛子我不要了,借我几只碗吧。”
大叔追得更凶了。知青初来乍到,不知道,此地方言把自己家的老婆叫“席子”,自己家的大女儿叫“坛子”,“坛子”的妹妹,叫“碗”,大妹妹叫“大碗”,二妹妹叫“二碗”,三妹妹叫“三碗”,话说武松,三碗不过冈,武松偏要过,女人是老虎,武松打老虎。武松打死老虎,为以后怒杀潘金莲埋下伏笔,古人就是会写文章,十面埋伏,滴水不漏。
知青的头被打破,闹到公社。语言不通所引发的械斗与战争,并不荒唐。荒唐的是——公社书记决定——这是真事——从今往后,为了避免争端,知青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诸如“席子”“坛子”“碗”这样的敏感词,要屏蔽,为了稳定,为了和谐,一定要屏蔽,没有商量余地,“你们既然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就应该向贫下中农学习。”公社书记叼着“大前门”,给出指示。那时候乡下人抽烟,有首顺口溜不妨录下,再过几年可能会被忘记:
大队书记“四脚奔”,
公社书记“大前门”,
县委书记“戴红花”,
市委书记“屌一根”。
这说的是四种香烟牌子。“四脚奔”,飞马牌香烟;“大前门”大家知道;“戴红花”,牡丹牌香烟;“屌一根”,中华牌香烟——极其不严肃,居然把中华牌香烟壳上的华表说成“屌一根”,奇怪的是那时候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倒没把编这顺口溜的打成“现行反革命”。另外,“市委书记‘屌一根”云云,指的是十年浩劫时期的市委书记,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四人帮爪牙”,现在——改革开放的市委书记请勿对号入座。
想写写我向外人介绍自己妻子时候的称呼之难,忽然跑题,回来!我的一位朋友向外人介绍自己妻子时候,说:“这是我女朋友”。
另一位朋友向外人介绍自己妻子时候,说:“这是我后妈”。
这一位
这一位先生,我想朱季海走后,他大概是苏州最有学问的人了。
我说朱季海日子悲惨,你比朱季海的日子更悲惨。朱季海好歹顶了个章太炎弟子的名头,章太炎的学术好歹还在延续;你老师名震东南,璧沉深渊,传灯一盏,你老头地光明,该出山了。
先生说:“河也没过。”
近来又说起此事,先生冲我一笑:
“你莫害我。”
今天我想,失传一些学问也是好事,否则后人研究不过来,哪有时间创新,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哼!呸!
我的诗中,偶尔有“过河”“意象”,与这一位先生所说“河也没过”有关?五百年后,自有了断。
马
村里人养了一匹母马,母马生下一匹小公马。村里人让它们交配,小公马死活不肯。秀才想出个主意,用墨把母马涂黑,放到暗室,牵来小公马。交配时小公马差越出母马本色,悲鸣而死。秀才在一边说:“嗯,怎么会这样呢?”一则读后感。
废纸
钱牧斋的一本杂记簿,被后人当作废纸,用来练字。鲁迅的几页手稿也曾被人包油条。
一六四二年的大水
在写几首有关河流的诗。一六四二年,黄河发大水,冲垮犹太会堂,也把城外犹太人公墓毁坏。十七世纪来过中国的传教士说,开封府的犹太会堂与中国的庙宇相似。维特根斯坦说:“犹太人的头脑对他人作品的理解超过对自己作品的理解。”诗人也是如此,但却不会发现开封府的犹太会堂与中国的庙宇相似,他的眼睛里只有大水过后的恒久语言景象。
一个考证
此民族记忆力极差——所以文化源远流长。
演出结束
从技巧角度看——无论书法、绘画,还是诗与小说,最先被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错觉,或者与技巧关系不大的虚张声势的花招。我读小学的时候,邻居是市技巧队队员,他常常给我看一张照片,一群人叠在一起,他站上面。他是公安局局长的小儿子,从来不好好练功,去那里混世,所以每次表演,他只能爬到叠起的人梯上面,两手朝上张开,做出欢迎的样子,表示演出结束。
座右铭
一方面清心寡欲,一方面不断地和虚荣、谎言、庸俗与陈词滥调肉搏。
阿波利奈尔
不成体系也无意做成体系,他横溢的才华在外行看来十分草率。
不良习惯
“你的生殖器滚烫,可以煎蛋。”
这是双关语吗?
“你的生殖器坚挺,可以操蛋。”
这是双关语吗?
这是双关语吗?不是!这仅仅是不良习惯。或者,在一个特殊社会,所有的语言都是双关语——以此安慰人心。
时代英雄
肤浅是每个时代的英雄。
绝交
《昭昧詹言》论黄山谷:“黄只是求人与远。”“又贵截断,必口前截断第二句。”
“口前截断第二句”,这是韩愈的句子。
文学艺术中,有一种风格如绝交,很有意思。
浮世绘
胡适(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人生哪能日日作庄语?其日日作庄语者,非大奸,则至愚耳。
严肃
看上去不负责任,其实很严肃。十分严肃。
奇迹与大奇迹
奇迹:是猪都在飞;鲤鱼宽待黄河之水;饱学桃花一泻君子千古恨;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不阔。
这个穷世界!
谁能亡命月球,飞船叔叔和脸蛋通红的婶婶。
而大奇迹:在飞都是猪。
啊
啊,不要被束缚在现实所构造的叙事框架之中。
戏评
打情骂俏颇不容易(杨宝森《游龙戏凤》叶盛兰《得意缘》俞振飞《写状》录音听后感)。
猛龙过江
昨晚是我第一次看李小龙电影,大吃一惊:一个人居然能使自己的身体成为哲学与宗教;一招一式,具有清洁的能量。
翻译机器
“在村里的警察局度过一个北方的家”。
水土
一个想象力急速流失的民族,真的十分可怜(若干诗人与艺术家访谈读后感)。
鸡湖美术馆
艺术不是千百种怪癖,但它是一种怪癖。
文化
文化是个垃圾堆,迷恋其中的话,只有几个人能变废为宝,大部分人无非苍蝇那样嗡嗡飞在其中。
杜甫
“语不惊人死不休”。
并非要我们故作惊人之语。
而是,一个诗人必须能够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坚持他个人的文化立场和严肃的写作态度。
萧山萝卜干
访戴而归,王徽之借一晚风雪,用来熬稀饭。
大锅稀饭。
“你,也来一碗?”
剡溪枯水之上,子子孙孙早餐。
条件好的时代还能吃到萧山萝卜干。
文字
听!批判耳朵。正好批判到耳朵。
不是政治的;不是经济的;不是文化的;不是艺术的。是,声音:噪音的。是艺术的;是文化的;是经济的;是政治的。
动物只能是小动物。
没有偶然听到的;只有偶然录下的。
工具:机遇即工具。
灵魂:材料即灵魂。
先锋意味着还不够胆怯,需要做得更多。
谁能比保守更勇敢、更粗鲁、更肆无忌惮呢?在艺术上。
沉默的分贝超过噪音,在中国中?
洗手之际水发出尖叫——“左”“右”;洗耳的时候大河见底:们的脸在河床预订了松软的枕头。
一点也不独特,所以我们兴致勃勃。
听!幸亏还有噪音是兴致勃勃的。
《三元图》跋
一元——“意识形态流”与“意识控制论”以及……一些人在艺术那里是粗暴的;艺术在一些人那里是粗暴的。前因后果就说不清了。
二元——另一方面,语言仅仅作为反抗媒质而并没有自觉自证可言。
三元——真理是思维乐趣。编织四维内存的思维网,自由不是网眼,是一维与一维之间的间隙。我们(这是承认局限性的称谓)所能探索到的宇宙仅仅仿佛一首印刷在纸上的诗,它的深度感恰恰是由平面唤起的。但如果说宇宙是个平面却是错觉。宇宙是一只线轴,四维(或者八维)各得其所,它们被上升到交缠的层面,就是四维后的思维——这个层面的思维才说得上思维。《伏羲女娲图》是揭示四维被上升的过程图,这是一个平面,所以互有遮蔽,是四维(或者八维)交缠图,它缺失的部分是思维图。一开始就是缺失的。
《蛋》
这几天在编诗集,准备自己印五十本,作为明年五十岁生日的答谢礼。
普天同庆文化产业大国即将建立之际,我觉得我用“非法出版物”这个定义概括我的半世人生,是天人合一的。
一共三十二首诗,“32”,谐音“生而”,生而平等,生而低贱。
蛋(2010—2011)
三十首短诗。
亲爱的皮影先生(2009)
一首疑似小说的长诗。
荡妇(2005)
一首疑似戏剧的长诗。
诗集名《蛋》。
“鸡飞蛋打”的“蛋”。成语在我嘴中常常乱码,“飞鸡打蛋”的“蛋”。
“杀鸡取蛋”的“蛋”。
“覆巢之下无完蛋”的“蛋”。
“操蛋”的“蛋”。
“扯鸡巴蛋”的“蛋”。
“滚恁毒娘格青胖咸鸭蛋”的“蛋”。
你能把一颗鸡蛋竖起吗?有两则竖起方式:一则在哥伦布轶事里;一则在中国民间巫术中。
还有第三则。
蛋:男性生殖器的俚称。
蛋:一种易碎品。
《木末芙蓉花》序
一个诗人的读书与梦游,如“木末芙蓉花”矣。
另外,此书以《偏看见》为底本增减而成。《偏看见》十多年前出版,印数较少,一些收我图书的读者常常找不到这一本;或者找是找到,品相不好。有人鼓动我再版。但我对自己的出版物无论何种,是都不愿意再版的。必须有所增减,同时换个名字,这几乎已成毛病:我如果自恋的话恰恰表现在对自己的过去不够欣赏。
是为序。
2012年深秋车前子识于北京目木楼头
《木末芙蓉花》后记
在我这里,读书就是梦游;至于梦游,说它是读书——某种可遇不可求的状态——也未尝不可。“木末芙蓉花”,我无来由地用王维诗句作为书名,就因为这芙蓉花是“木芙蓉”,也就是“辛夷”,“辛夷”别有个名字“紫木笔”的缘故?我想文章的确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而从“紫木笔”,古人又好奇地发挥出另一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古怪,叫“书空”。我想文章的确是“书空”的事业,有时候,还“咄咄书空”。
在我这里,“木末芙蓉花”是当然的,而“山中发红萼”未必,“涧户寂无人”未必,但“纷纷开且落”即使不在我这里,也是当然的。
后记结束。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