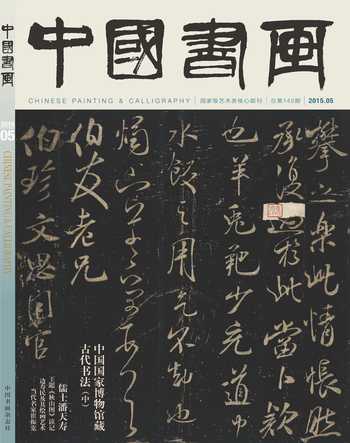象与显
2015-05-30彭峰
彭峰
德国美学家泽尔(Martin seel)近来以“美在显现”的主张赢得了美学界的关注。所谓“显现”(appearing),即是事物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活泼样态。当我们用无利害的态度来关注对象时,对象就会处于一种完全开放的活泼样态。这种活泼的状态体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泽尔称之为“Erscheinen”。为了体现它的动态性,英文译者用动名词“appearing”来翻译它,而不是用现代美学中的常用术语“semblance”(外观)来翻译它,也没有用名词“appearance”(表象)来翻译它。我把它翻译为“显现”而不是“外观”或“表象”,目的也是为了突出它的动态和过程的特征。鉴于“显现”有时候也会被理解为名词,用单字“显”来翻译它也许更为合适。
我们可以对照两个概念来说明“显”的特征:一个是“being-so”,为了突出它的不变性,我把它译为“确在”:一个是“appearance”,可以译为“表象”。事物的“确在”,就是一般人朴素地认为事物确实存在的样子。事物的“确在”,可以用概念来描述,从而形成关于事物的命题知识。事物的“显现”则不同,它不能用概念来描述,不能形成关于事物的命题知识。事物在未被我们认识的情况下可以说是“确在”,事物透过概念显现出来就成了“表象”或者知识。“显现”处于“确在”与“表象”之间,是事物在被概念固定为“表象”或知识之前的活泼状态,是事物“显现”为“表象”的途中。正因为“显现”是在途中,因此它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确在”和“表象”都可以被当作结果,但“显现”总是处于幻化生成之中。“确在”和“表象”,都可以不依赖观察者而存在,但“显现”依赖观察者的在场。一旦观察者缺席,事物的“显现”就蜕化为“确在”或者“表象”。总之,泽尔在西方一分为二的本体论区分中间划出了一个新的地带,这个地带既与对象的存在有关,也与主体的在场相连,这个地带就是“显现”。
泽尔的显现概念,对于习惯于一分为二的本体论区分的西方哲学来说,算得上新的发明。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它就有些似曾相识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区分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中国形而上学将实体划分为“道”“象”“器”。根据西方形而上学中的标准区分,我们可以勉强将“道”归结为抽象对象或心理对象,将“器”归结为具体对象或物理对象,但这种标准区分中没有“象”的位置。“象”在这里不能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被理解为形象、形式或者轮廓。“象”不是事物本身,不是我们对事物的知识或者事物在我们的理解中所显现出来的外观。“象”是事物的兀自显现、兀自在场。“象”是“看”与“被看”或者“观看”与“显现”之间的共同行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说“象即显现”。
让我借用王阳明的一段对话来对象即显现做些具体的说明。《传习录》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王阳明与他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似乎相当奇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既不会有“与汝心同归于寂”的花,也不会有“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的花。我们的认识功能自动地将概念赋予给所看到的花,给花命名,将它视为比如桃花、梨花、菊花、芙蓉花、杜鹃花等等,这些都是在王阳明和他的朋友们游玩的山上容易见到的花。
让我进一步假定王阳明和他的朋友们看见的花就是芙蓉花。现在,我们有了三种不同的芙蓉花:“与汝心同归于寂”的芙蓉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的芙蓉花,以及有了“芙蓉花”名称的芙蓉花。这里,我用有了“芙蓉花”名称的芙蓉花来指称芙蓉花的显现结果,也就是我们依据概念或名称对芙蓉花的再现或认识。我们可以将这三种芙蓉花简称为“芙蓉花本身”、“显现中的芙蓉花”和“再现中的芙蓉花”。根据中国传统美学,审美对象既不是任何芙蓉花本身,也不是任何再现中的芙蓉花,而是所有显现中的芙蓉花。
这三种不同的芙蓉花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区别?简要地说,芙蓉花本身是一种树木。比如说,它有三米高、众多的枝桠、绿色的叶子、粉红色的花瓣等等。我们可以去数它的枝桠的数目,触摸它的树干的硬度,嗅它的花的香气,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尝尝它的叶子的滋味。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是芙蓉花,我们在芙蓉花本身中都可以发现众多的诸如此类的特征。这种芙蓉花可以存在于心外,可以处于“寂”的状态。
显现中的芙蓉花是在我们知觉中的芙蓉花或者正被我们知觉到的芙蓉花,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的芙蓉花。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他想说的也许是:我们只能有在心上显现的芙蓉花,而不能有芙蓉花自身。王阳明的这个看上去相当奇怪的主张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感知某物就无法知道它是否存在。不过,这里的显现中的芙蓉花不能被理解为主观臆想的产物。“心”在这里如同“镜子”或“舞台”,借助它芙蓉花显现自身,这是我们在禅宗文献中很容易发现的隐喻。因此,在许多方面,显现中的芙蓉花都十分类似于芙蓉花本身,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是知觉中的对象,后者是物理对象或自然对象。
实际上,王阳明并没有取消芙蓉花本身,他只是将它转变成了显现中的芙蓉花。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拥有芙蓉花本身,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它、摸它、嗅它、尝它。现在的问题是,一般人的普通看法跟王阳明的深刻洞见之间有何区别?在王阳明眼里,一般人心目中的芙蓉花本身并不是真正的芙蓉花本身,而是芙蓉花的再现或幻象。我们通常将某种再现中的芙蓉花当作芙蓉花本身,比如,我们今天就容易将科学对芙蓉花的再现当作芙蓉花本身,因为科学在今天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科学对芙蓉花的再现并不是芙蓉花本身,它只是关于芙蓉花的现代植物学知识。我们还有对于芙蓉花的其他再现,还有关于芙蓉花的其他知识,比如,中国传统中草药学知识。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芙蓉花知识。享有统治地位的再现或知识,通常就会被误以为事物本身了。
显现中的芙蓉花与再现中的芙蓉花之间又有何区别?关于显现中的芙蓉花,王阳明只是说它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他并没有说他看见了不同的颜色或者不同的树。我们假定在某一时刻我们看见的颜色是一样的,比如说粉红。王阳明看见的颜色与植物学家或中草药学家看见的颜色并不是两种不同的颜色,比如前者看见了粉红后者看见了橘红,而是同一种颜色的不同样态,即在显现之中的粉红和不显现的粉红,前者是我们对粉红的感受,后者是我们对粉红的知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不显现的粉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来没有进入感知的粉红,一种是曾经进入感知而现在不在感知之中的粉红。让我们暂且撇开前一种粉红。“正在感知之中的粉红”与“曾经进入感知而现在不在感知之中的粉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活泼泼的“象”,后者已衰变为死板板的“知识”。在活泼泼的象的状态,我们的感知处于逗留之中,并不立即提交或上升或抽象为知识。我们得到的是象还是知识的关键,不在于观看的程度是否仔细,而在于观看的态度是否松弛。王阳明的观察不一定有植物学家或中草药学家那么仔细,但王阳明能够看见花的象,而植物学家或中草药学家只能得到花的知识,因为王阳明在“游”南镇,“游”让王阳明的感知摆脱了概念的束缚。
艺术的灵魂就是“象”或者“显”,就是处于途中的正在“显现”的活泼泼的“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