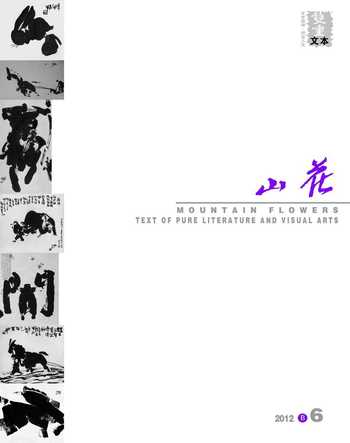唐诗中的“因”字被动式
2012-04-29张延俊
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诗歌等作品中,叙述句都是一种最为主要的句子形式。叙述句一般又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在汉语中,被动式的使用频率虽然低于英语,但是也毕竟是一种重要的句子形式。汉语的被动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标记被动式,其语义结构是“受事·及物动词”(如“碗打了”);另一种是有标记被动式,其语义结构一般是“受事·被动标记·施事·及物动词”(如“碗被他打了”)。汉语的有标记被动式类型非常丰富,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于”字被动式、“见”字被动式、“为”字被动式、“吃”字被动式、“教”字被动式、“给”字被动式等多种类型。对于这些被动式类型,许多著作和文章都有介绍和探讨,因此,人们比较熟悉,本文对此也不做讨论。本文要介绍另外一类被动式——“因”字式以及与之类似的“由”字式、“缘”字式和“以”字式。这类被动式,在过去从未有人提到过,更不要说进行研究了。认识这些被动式类型,无论是对于学习和研究唐诗,还是对于研究汉语语法历史,都具有显著的意义。
所谓“因”字被动式、“由”字被动式、“缘”字被动式和“以”字被动式,就是分别以“因”、“由”、“缘”和“以”等虚词为被动语法标记的被动式类型。例如:
林与西山重,云因北风卷。(唐·张九龄《临泛东湖》)
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唐·白居易《鹅赠鹤》)
身忝乡人荐,名因国士推。(唐·白居易《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宣歙翟》)
残色过梅看向尽,故香因洗嗅犹存。(唐·白居易《故衫》)
眼昏久被书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唐·白居易《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
狂风落尽莫惆怅,犹胜因花压折枝。(唐·元稹《妻满月日相唁》)
远被登楼识,潜因倒影窥。(唐·元稹《代九九》)
名因天下闻,传者入歌声。(唐·张籍《祭退之》)
却羡浮云与飞鸟,因风吹去又吹还。(唐·李频《春日思归》)
半夜腊因风卷去,五更春被角吹来。(唐·曹松《江外除夜》)
西施因网得,秦客被花迷。(唐·李商隐《和孙朴韦蟾孔雀咏》)
未因丞相庇,难得脱朝衣。(唐·姚合《暮春旧事》)
幸念翅因风雨困,岂教身陷稻粱肥。(唐·项斯《病鹤》)
空被秋风吹病毛,无因濯浪刷洪涛。(唐·曹唐《病马五首呈郑校书章三吴十五先辈》 )
畹兰未必因香折,湖象多应为齿焚。(唐·李咸用《依韵修睦上人山居》)
海上春耕因乱废,年来冬荐得官迟。(唐·郑谷《赠宗人前公安宰君》)
终期道向希夷得,未省心因宠辱惊。(唐·崔涂《夏日书怀寄道友》)
炉为窗明僧偶坐,松因雪折鸟惊啼。(唐·韩偓《小隐》)
半生因酒废,大国几时宁。(唐·杜荀鹤《寄窦处士》)
潜被燕惊还散乱,偶因人逐入帘帏。(唐·李建勋《蝶》)
例子中画线部分是以“因”字为被动语法标记的“因”字式,“因”相当于“被”,“云因北风卷”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云被北风卷”。再如:
二乱岂由明主用,五危终被佞臣弹。(唐·张道古《上蜀王》)
因循每被时流诮,奋发须由国士怜。(唐·韦庄《绛州过夏留献郑尚书》)
门缘御史塞,厅被校书侵。(唐·无名氏《右威卫嘲语》)
讵以天地累,宁为宠辱惊。(唐·李隆基《经河上公庙》)
这几个例子分别是以“由”、“缘”和“以”为被动语法标记的“由”字式、“缘”字式和“以”字式。“由”、“缘”和“以”都相当于“被”,“由明主用”相当于“被明主用”,“缘御史塞”相当于“被御史塞”,“以天地累”相当于“被天地累”。除了唐诗,其他文献中也有此种被动式类型,但是数量极少,而且出现的时间也很晚,如:
我三途不出,皆因贪爱所迷。(无名氏《维摩诘经讲经文》)
无名氏《维摩诘经讲经文》是敦煌变文中的一篇,据学者研究,它产生于五代时期。这些语例可能是唐诗“因”字被动式影响的结果。
“因”字式、“由”字式、“缘”字式和“以”字式这几种被动式类型,可以说都是比较特殊的。原因是:(1)它们的用例比较少;(2)历史比较短;(3)使用场合有限,只见于唐诗和敦煌变文中;(4)用来引进施事的被动标记“因”、“由”、“缘”和“以”等都来自原因连词。其中第四个特点也是其最大的特点,因为以往大家所熟悉的被动式中从来没有以原因连词为被动语法标记的,它们的语法标记一般来自动词(如“见”、“为”、“被”、“吃”、“教”、“给”)或介词(如“于”)。
尽管这类被动式有其特殊性,但又不能不将它们视为被动式。原因有二:(1)它们的主语也是“受事”,谓语也是“及物动词”,也有类似于“施事”的成分,其语义结构与一般有标记被动式的语义结构“受事·被动标记·施事·及物动词”是一致的。如在“云因北风卷”中,“卷”是及物动词,主语“云”是其受事,状语中的“北风”是其施事,因此,“因”字自然是一个被动标记,“云因北风卷”便是一个以“因”字为被动标记的有标记被动式。(2)这类被动式经常与“被”字被动式或“为”字被动式构成对仗关系。如前举诸例:
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
眼昏久被书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
远被登楼识,潜因倒影窥。
半夜腊因风卷去,五更春被角吹来。
西施因网得,秦客被花迷。
空被秋风吹病毛,无因濯浪刷洪涛。
畹兰未必因香折,湖象多应为齿焚。
潜被燕惊还散乱,偶因人逐入帘帏。
二乱岂由明主用,五危终被佞臣弹。
因循每被时流诮,奋发须由国士怜。
门缘御史塞,厅被校书侵。
讵以天地累,宁为宠辱惊。
那么,这类以来自原因连词的“因”字等为被动标记的被动式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可以从语法标记的形成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从语法标记的形成机制上说,一般有两种途径:(1)语法化,由一个词在句子中受一定组合关系变化的影响逐渐演变而成;(2)类化,由于同一聚合关系中其他成员的影响,添加了一种新的用法,从而转变而成。本文认为,“因”等被动标记的形成不是通过语法化,而是通过类化。
语法化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因”、“由”“缘”和“以”等就像一群空降兵,作为被动标记出现于被动式中是非常突然的,是缺乏语法化过程的。在汉语被动式中,被动标记所引导的名词性成分一般是动作行为的施事,也可以是动作行为的工具,如“桌子被锤子砸坏了”,甚至是动作行为的原因,如“她的短发立刻被雨水贴在脸上,花布衫被紧紧裹在身上”,“远道的客人被阴雨困住了”。现代汉语如此,古代汉语也是如此。例如: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斩于法……(战国·韩非子《韩非子·五蠹》)
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战国·韩非子《韩非子·五蠹》)
“斩于法”就是“被法律斩杀”,“法”可理解为“斩”的原因。“苦水”就是“苦于水”,就是“被水所苦”,施事“水”就可理解为“苦”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便将被动式中的施事成分称为“使因成分”。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薛凤生先生把“被”字句的语义特性定义为“由于B的关系,A变成了C所描述的状态,而不是A如何被B处置”,表明他也是把被动标记所引导的名词性成分看做动词动作的原因的。但是,动作的原因毕竟不同于动作的施事。有时原因成分确实可以理解为施事,但这种情况毕竟非常少见,无论外语还是汉语,它们只能理解为施事的扩展用法。不应把所有的施事都理解为原因成分,也不能因此认为原因成分可以自然转变为施事。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无论是汉语还是外语,一般都不会以原因连词作为被动标记,这就是一个证明。“因”字等被动标记的形成显然不同于“被”、“为”、“见”、“吃”、“教”和“给”等被动标记的形成。
因此,本文不采用“语法化”说,而采用“类化”说。具体地说就是认为“因”等原因连词,是在同一聚合关系中“为”字的类化影响下,添加了表示被动的新用法,从而转变为被动标记。
类化得以发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类化者与被类化者之间,在形式或用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为”字除了用作被动标记,它还可以用作原因连词,如《孟子·梁惠王上》“为甘肥不足于口与”,《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非为织作迟”等,这就是它与“因”、“缘”或“由”等词的相似之处。在唐诗中,“为”的这种表示原因的用法格外常见。不仅如此,在唐诗中,“为”字作为原因连词,还经常与“因”、“缘”或“由”等原因连词相对使用。例如:
为客烹林笋,因僧采石苔。(唐·刘禹锡《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茸水》)
犬因无主善,鹤为见人鸣。(唐·张籍《哭山中友人》)
家每因穷散,官多为直移。(唐·王建《送吴郎中赴忠州》)
为结区中累,因辞洞里花。(唐·元稹《天坛归》)
予因谬忝出,君为沈疾婴。(唐·韦应物《寄职方刘郎中》)
石净非因雨,松凉不为风。(唐·卢纶《宝泉寺送李益端公归渖宁幕》)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唐·杜甫《又呈吴郎》)
买山多为竹,卜宅不缘贫。(唐·李端《寄王密卿》)
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唐·裴度《中书即事》)
色鲜由树嫩,枝桠为房稠。(唐·刘禹锡《和令狐相公春日寻花有怀白侍郎阁》)
鸟飞直为惊风叶,鱼没都由怯岸人。(唐·李隆基《春日出苑游瞩》)
可见,“为”字与“因”、“缘”或“由”等字均属于同一聚合——原因连词中的成员,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为”字既有原因连词的用法,又有被动标记的用法,受其类化影响,“因”、“缘”或“由”等字在原因连词这个用法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用法——作为被动标记的用法。
从动因方面说,“因”字式等被动式类型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唐诗对仗和平仄等方面的需要。对仗要求,出句与对句所用的被动标记应该有所区别,否则对仗就不合诗律。平仄要求,出句与对句所用的被动标记在平仄上应该相对,否则就会造成“拗句”,也与诗律的基本形式不合(有的可以在相应的位置“救”)。另外还有避复等方面的考虑。多种被动式类型的存在,无疑为满足以上需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综上所述,唐代汉语中存在着“因”字式等比较特殊的被动式类型,它们的被动标记是在原因连词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被动标记不是在具体的语句中受组合关系变化的影响“语法化”而成,而是受原因连词这个聚合中另一个成员——“为”字用法的影响“类化”而成。“因”字式等一般存在于唐诗之中,它们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唐诗对仗和平仄等方面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薛凤生.“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结构意义——真的表示“处置”和“被动”?[A].戴浩一,薛凤生主编.沈家煊译.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2]张伯江.“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J].中国语文,2001,(01).
[3]张红运.论唐宋诗词的时空结构形态[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2).
[4]丁恩全.韩愈“以诗为戏”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3).
[5]张延俊.汉语有标被动式主流类型更替中的适者生存规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
[6]郝广霖.论李商隐与晚唐绮丽诗派[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
[7]张延俊.《红楼梦》“叫”字被动式来源研究[J].古汉语研究,2009,(02).
[8]张延俊.“特殊被字句”形成机制研究[J].语言科学,2010,(03).
[9]张延俊.汉语被动式历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张延俊.试论“给”字被动式的方言背景[J].方言,2010,(04).
[11]张延俊.近古汉语“教”字被动式研究的形成与发展[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12]王跃平.汉语主语成分的预设及若干相关问题探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
[13]周健.“被”字句中“被”字的词性分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
作者简介:
张延俊,江苏徐州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