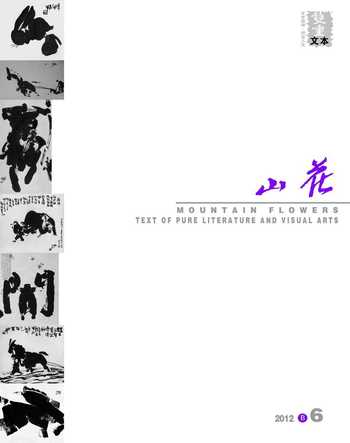从《菊花》看女性的救赎
2012-04-29李瑛
李瑛
《菊花》是斯坦贝克艺术上最成功的短篇小说,得到了评论家的广泛认可,被作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1]。故事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农妇伊莉莎一天中所经历的几件寻常事,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过度渲染的气氛,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平淡中揭示的是一个平常女人的心路历程,折射出女性对婚姻的失望、对社会期待的破灭,体现了作家对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启发读者了解女性的救赎根本上来自于自己的决断。
对婚姻的失望
由于社会生产方式、文明程度、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女性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经济与人格方面的独立与否以及对家庭中女性角色的认同等决定了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幸福的婚姻造就幸福的女人。而婚姻的幸福取决于两个层面:物质和精神。物质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基本保障,精神则是提升人格,得到满足的更高追求。故事中的伊莉莎身体健壮,与丈夫生活在南加州的萨利纳斯峡谷。丈夫经营着自己的农场,她侍弄着自己的小花园。物质上,这个三十五岁的女人衣食无忧,但她需要的不仅如此:她渴望自己的美、自己的能干、自己的价值首先能得到丈夫的认可,渴望与丈夫的心灵相通,可她最终经历的却是婚姻梦想的幻灭。
故事中,当丈夫亨利来到伊莉莎正在忙活的花园边,夸奖菊花长势很好时,伊莉莎控制不住地沾沾自喜,心里的美从话语、从面部表情中流淌出来。丈夫还夸伊莉莎干活真有一手,可话锋一转又说:“如果你能培育出那么大的苹果就好了”[2]。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让伊莉莎由起初的欣慰瞬间转变为失落:显然,丈夫觉得菊花不如苹果值钱。由此,伊莉莎心底渴望的认同并未实现。不过,此时的她并未失望。面对丈夫的评论,她还眼睛一亮,说:“也许我还真行呃……”[3]然而亨利仍然认为“种花当然没有问题了”[4]。这样的回答完全否认了伊莉莎在菊花园以外的地方所具备的能力。面对亨利的否定,伊莉莎没有继续同一话题,似乎这是永远没有结果的争论,她的梦想遭遇的打击也不过再多一次罢了,要想改变丈夫的看法很难,所以她不再纠缠于刚才的争论。后来,补锅匠来了。和补锅匠的交流让伊莉莎在遭遇丈夫的贬低后重新看到了自己被认可的希望,重新燃起了自信,重新看到了自己的非凡才能。送走补锅匠后,伊莉莎回到屋里沐浴,把自己擦洗得干干净净,并站在镜前自我欣赏。然后她穿上自己的新内衣,最精致的长袜,还有那件象征她美丽的裙子。一个35岁的女人,既有玫瑰般的迷人,又有牡丹般的大气,她的美已不同于少女的艳丽之美,多了岁月沉淀后的内涵。此时的她心中有一种渴望在涌动。 她在镜前的自我欣赏不过是想确认并增强她从补锅匠那儿获取的一点点自信,进一步证明她是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秀外惠中的女人,一个能和男人平分秋色的女人。这样的审视让她内心充满了一种快感,一种期待:她渴望丈夫能回来看到她的美、欣赏她的美并完成她的心愿,让她所有的期待都变成奔涌的热情。
不久,亨利回来并直接进了浴室。伊莉莎备好丈夫的衣物、鞋袜后来到走廊坐下。她显得有些呆滞,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连眼睛也很少眨一下。此时表面平静的伊莉莎内心定是汹涌澎湃。她期待着,却又有些困惑,她不知道丈夫能否体味她的内心,明白她的所思所想,并实现和她身心的交流。待亨利从浴室出来并“砰”的一声关上门时,伊莉莎直起身子,脸也绷紧了。她内心震荡的欲望已经从脸上表露出来。看到伊莉莎的表情,亨利丝毫未读懂这个女人的心思,却蓦地停下来吃惊地打量着她,说:“噢!噢!伊莉莎,你看起来不错嘛”。[5]然而,伊莉莎心中的渴望并非这样一句概括的话语能满足,她不禁反问道:“‘不错是什么意思?”[6] 面对伊莉莎的主动追问,亨利反倒结结巴巴:“我不知道。我是说你看起来有些不一样,强壮,快活。”[7]亨利的木讷和“执迷不悟”让伊莉莎从云端直往下跌, 剩下的只有无奈了:“强壮?这又是什么意思啊?”[8]现时,亨利已无法应对伊莉莎的“紧追不舍”了。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和经历中,伊莉莎作为女人、妻子,不该也从未如此主动、强烈地对丈夫“步步紧逼”。他显得有些迷惑不解:“你在玩什么把戏?……你显得很强壮,壮得可以在膝盖上劈死一头小牛,像吃大西瓜那样高兴地把它吃掉。”[9]闻听此言,伊莉莎如坠冰窖,刚才等待时的紧张不安没了:“亨利,别那样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10]简短的一句话语道出的是伊莉莎内心无尽的酸楚,她语气夸张:“我很强壮,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强壮。”[11]这句自嘲似的回答既包含了苦笑般的自我安慰,也融入了绝望的心碎,表面的漫不经心透出的是无以言表的痛。如果说无法在精神层面上与丈夫有共同语言尚可让伊莉莎容忍,可连自己的肉体也不能激起丈夫一点点的渴望,还有什么能让一个女人更悲哀呢?本来是以退让求生存,可最终却伤得彻彻底底。伊莉莎和亨利只能是住在同一屋檐下貌合神离的“陌生人”了。
对社会期望的破灭
西方哲学与现代美学认为存在本身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往,而非主客构造、征服客体的二分状态[12]。在人类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时,唯有通过他人的认同才能达到自我认同,并在相互认同中实现各自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婚姻中,爱的关系是交互性的主体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你—我关系,而平等的对话交流是理解信任的前提条件。在伊莉莎追寻自我的路上,她无法和丈夫达到精神上的认同,这让她异常痛苦,但她压抑着自己的感受;当补锅匠出现时,她自然地产生了移情现象,即把对丈夫的无望转移到了另一个男性身上。所以当补锅匠询问有无需要修理的物件时,她断然拒绝了请求,连她的眼神透射出的都是抵触。当那个男人装可怜想博得同情时,她甚至变得气恼:“我没什么东西好让你修。”[13]然而,这种冷漠在补锅匠提到菊花时瞬间融化;当补锅匠形容菊花像一朵彩色烟雾,并察言观色地附和说自己喜欢菊花的药味时,伊莉莎心里的阴霾散了;待补锅匠编出有位老太太想要菊花种子的故事时,伊莉莎双眼放光,炯炯有神。眨眼间,心门打开,话语流淌。她甚至一把拉下头上那顶破旧的男式帽子,让象征女性美丽的乌黑漂亮的头发散落开来。她还主动邀请补锅匠进到园子中来。
此时的伊莉莎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一路小跑着搬花盆、插花苗,迫不及待地要让补锅匠把菊花带出峡谷,送给那位喜欢菊花的女士。过程中还耐心细致地讲解如何侍弄花苗以确保其成活并茁壮成长。那份无以言表的激动让人垂怜,像一个久被冷遇的孩子突然看到一张笑脸,像一个孤独的行者突然有了伙伴、知音,可她却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出于感激补锅匠对菊花的赞赏,她甚至主动找出两个破锅让他维修。先前的冷漠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让补锅匠都无法意料的热情过度。短短时间内她经历了又一次移情现象:把对菊花的那份爱转移到了这个陌生男人身上,化作了对他的信任。在伊莉莎眼中,菊花不仅是她的劳动成果,更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如同她的孩子,又是她的化身。对菊花的爱就是对伊莉莎的爱,对菊花的赞赏则是给伊莉莎的最高奖赏。不知不觉中,补锅匠已经走进了伊莉莎的内心里。所以当补锅匠说在马车里四处流浪的生活不适合女人时,伊莉莎竟然撒娇般上唇轻轻一扬,露出牙齿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这样说?”[14]把五十美分的维修费交给补锅匠后,伊莉莎不无自豪地说:“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个对手,可能会大吃一惊……我可以让你见识一个女人能干些什么。”[15]伊莉莎想表明的不仅是自己的能干,她更想在一个她认为心灵相通的人那儿得到进一步的认同,她渴望得到赏识,她想证明女人毫不逊于男人。补锅匠却不以为然。
尽管补锅匠的回答并未给予伊莉莎她所期待的答案,伊莉莎觉得有所收获了,她知足了。当补锅匠准备离开,并承诺会按交代的去照管菊花时,伊莉莎竟显得不舍,双唇无声地动着:“再见——再见。”甚至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前面霞光万丈,一片明亮啊。”[16]就像首次送孩子出远门的母亲,伊莉莎既有不舍和担忧,又满含希望,愿这菊花能代表她去到外面的世界自由自在地生活,同时还有对离开者的留恋:可遇不可求的一个知己刚来就要离开,能不让人心底涌起无尽的思潮吗?补锅匠些许的赞同给了伊莉莎无限希望,毕竟她找到了一个能分享她对菊花感受的人,而且外面的世界还有一个和她一样热爱菊花的人,她不是孤独的,她的心灵有救了,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期待。所以准备去小镇吃晚饭前,她给了自己最精心的打扮,这是她内心最真实的体现。
然而残酷的现实彻底击碎了伊莉莎的美好期待。去往小镇的路上,她远远地就看见了被遗弃在路中央的菊花:花盆已被拿走,可花被孤零零地扔在道上——那男人甚至不愿把遗弃的菊花扔到路下边,先前的一切话语不就是最赤裸裸的欺骗吗?为了五十美分,那男人编出种种谎言,而自己却信以为真,这不是故意嘲讽伊莉莎作为女人的天真、幼稚吗?被弃的是菊花,被摧残的是女人,伊莉莎的心在滴血,这个男人代表的世界还能让她看到一点曙光吗?从身边的亲人到她以为的知音,他们展示的似乎只有人与人之间互相残忍地伤害,如同她最后提到的拳击比赛一样。她想喝酒麻醉自己,但她知道醒来时,现实仍是锥心的。无助的伊莉莎只能竖起大衣领子,躲在自己的壳里像老太太一样地轻轻啜泣。她一瞬间老了,不是她的容颜,而是她的内心,她对外面世界的渴望破灭了。
不得不做的选择:抗争或认命
伊莉莎渴望自己的才华得到认同,渴望与男人平等,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可她终究失败了。面对这样的现状,她该怎么办?是抗争还是认命?正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中王子所说:“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problem”[17](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对于伊莉莎来说,是活还是不活;是要生活还是不要生活;是要生活得丰满充实,兴致勃勃,还是活得枯燥无味;是要活得有尊严,还是活得像奴隶;是抗争实现梦想,还是认命、屈服于失败;这真是一个问题,但却是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为了女性的权利继续抗争就意味着还可能会有伤害,还可能会有失败,还可能会付出代价,甚至是巨大的代价,而且结果难料,就如同她曾经做过的抗争一样,让她输得痛彻心扉。如果她的努力成功了,她也会面临两种局面:一是女人从此可以和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拥有同样的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活;但也有另一种风险,那就是女性的强大可能让男性失去往日的强悍,变得无所适从,或者女人从此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
如果伊莉莎选择认命,屈服于失败,那她就要断了争取平等的任何梦想,心甘情愿地践行社会界定的女性的从属地位,永远卑微地活着。其实,伊莉莎的经历不仅是她作为一个个体曾经的尝试,更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早期美国“女权运动”追求政治平等、经济平等、职业平等以及精神解放的真实写照。《菊花》发表于1937年,当时美国的“女权运动”方兴未艾,美国社会也正逐渐走出经济萧条的漩涡,但妇女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女性的价值始终得不到男性的充分认可,父权统治的地位仍难于撼动。面对如此现状,作者借伊莉莎的经历揭示这场运动的艰难,呈现的是对当时背景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对女性的现实社会角色的同情,同时也暗示女性面临的两难却又是不得不做的选择:抗争还是认命?这是一个需要女性自己做出的决断,所以故事最后给予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伊莉莎躲在自己高高竖起的衣领中哭泣。这样的结局正体现了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女性的救赎根本上源自女性自己。
结语
今天,众多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为自己赢得了许多正当的权利,也取得了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充分证明了作者观点的可行性。奇妙的是这个观点在当今高度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仍然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主宰女性命运、决定女性生活的还是女性自己,外因能产生影响,但内因才是指导行为、决定结果的根本,才能帮助女性实现预期的愿望。不知不觉中,《菊花》在共时和历时性方面都超越了故事表面所承载的信息,这也正是这部短篇小说的非凡之处。
参考文献:
[1]Hayash,Tetsumaro,ed.Steinbecks Literary Dimension: A Guide to Comparative Studies[M].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1991: 154.
[2]Steinbeck,J. “The Chrysanthemums” in Extensive Reading 4 (ed. Liu Naiyin)[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8:281.Notes 3-11, 13-16 are all cited from the same book.
[12]杨时春.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厦门大学学报,2002,(01): 17-24.
[17]Shakespeare,W.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M]. Wikipedia.
作者简介:
李 瑛(1968— ),女,硕士,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