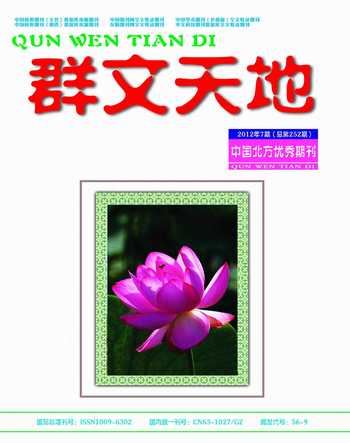对童年梦境化记忆的凭吊与对时间的哲思
2012-04-29王超
摘要:童年总会被死亡和情色的神秘吸引得欲拒还迎,那是一个迷幻的阵。《死者田园祭》是诗人导演的个人记忆的视像化,是梦游年代和理性思考的结合产物,是导演人生观的产物。成年的“我”与少年的“我”在都不同的时空对话中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经历过的更深的真相。
关键词:梦境化;凭吊;《死者田园祭》
《死者田园祭》是诗人导演的个人记忆的视像化,是梦游年代和理性思考的结合产物,是导演人生观的产物。影片以漫游的手法让观众看见了一个少年的成长路程,少年梦境和困惑的集锦、优美的俳句点缀了整部电影,使得影片充满了奇思妙想,视觉语言异常丰富。
电影的开始便显得颇为诡异,我和玩伴在墓地捉迷藏,捂着眼睛的我看不见阳光,玩伴在墓碑后藏好,而我手从眼睛上拿开后,自墓碑后走出的不是玩伴而是从墓里跳出的人。影片中,“我”是一个乖巧的男孩,和母亲相依为命,以我的视点观察村子里发生的一切。我出生在恐山下,村子里总是有着千奇百怪的事出现。母亲有些古怪,总是把家里的老钟当成圣物。母亲通过地板下的洞能够看见另一个世界的幻影,而阻隔他们侵入的方式就是地板上写满的咒语。我特别的孤单,只能将心里话对着恐山上父亲的幽魂说,而伴随我的还有一个充满诱惑的女性舞者。少年的我喜欢上了邻家的媳妇,而杂技团的来到又让我产生了走出山沟的愿望,经过一系列的时间之后,我终于弃家出走。长大成人后我成为了电影导演,在拍摄自传体影片中途创造受到阻力,于是成年的我回到了恐山和少年的我进行了穿越时空的对话。原来私奔并不顺利,我赶去与她约会时,却见她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她给他们讲了他的悲惨身世,男人让他去打酒,三人一起走。可当我回来时,只见两人双双殉情。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坐在草席上对弈,背景出现了各种属于人类的场景,葬礼,偷情,婚礼。影片的最后,我和过去母亲的见面,突然,景板倒下,我们看见两位演员坐在车水马龙的东京街头拍着这样的场景。
影片通篇都充满了奇幻和隐喻色彩,情节初看似散乱无章,实则蕴涵深意。和死者的对话反映的是导演童年的寂寞和惶恐,而少年和邻家媳妇是私奔只是表明着导演心目里一个少年告别自己长大和成熟的开始。少年时代的马戏团是孩子幻象世界的入口和长大方式,这是主观的回忆和客观的相容,这是记忆里无法抹去的少年欢乐和美好时光。在真实的世界里,导演以黑白的画面来表达一种朴素的真实感,与记忆的部分色彩的斑斓绚丽,形成鲜明对比。记忆如梦境般飘渺,绚烂的背后却有种被浓妆艳抹后的不真实感。
关于时间的哲性思考是本片中反复出现的命题,时间永恒单向的流逝着,而钟表却是记录这第四维的标尺。我一直想要一只手表,因为有了手表就有了个人身份的象征,而不在包容于他的家庭;最后被成熟女性所强暴而取得了男性身份的时候,我手腕上豁然多出了一个只手表证明了我身份的获得。时间的意象也不单单是记录个体的特异,时间交错的不同时代的本体也会在特定的时空中相逢。20年后的我与年少时候我在对弈,讨论着以时间为坐标发生的事情。以旧我和新我的对话,提出了时间不可逆的命题,是导演进行的一次思辨过程。 在这些细节意向之外,在整个影片中,导演也一再对着时间这个命题反复的提出命题,影片本身就是一个在时空中不同坐标点上的本体相会的故事,而导演更试图通过剧中的人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是否能回到过去杀死三代之前的母亲,而剧中的我也试图去这样的尝试,那些时间中所纠葛的,或许被少年时我所模糊的记忆却在成年之后的我的脑海中特别的清晰,人确实会忘记许多所谓的事实,主观的去模化改造这样的事实,而究竟客观事实又是什么,即使成年的我有了记录时间的手表,却也未必就一定是真实,毕竟手表的记录也是相对存在的。
导演寺山修司既是位出色的导演,也是诗人、摄影家、舞台剧大师。多重身份决定他的电影每个镜头都是一句诗,每个片段都是一出舞台剧,他摄影家的身份使得他电影中每个镜头都是精妙绝伦的,舞台剧大师的身份又使得电影片段节奏强劲人物表演张力十足,而诗人的身份又使他善于运用意象连贯这些意象,也所以即使如此雕琢的电影却极富整体感,贯穿一致。
(作者简介:王超,武汉大学艺术系戏剧影视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