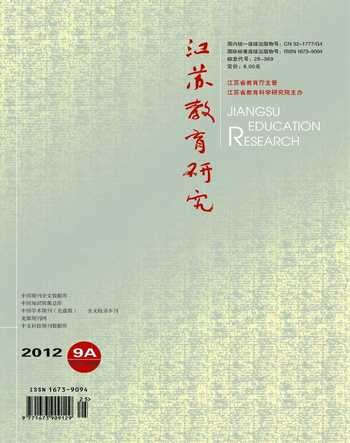教育:作为教师的专业社会服务?
2012-04-29龙宝新
摘要:在专业型教师教育中,实践智慧是赋予教师的教育服务以专业性品格的最高论据。专业社会服务产于社会分工,它是由特定人员为社会提供的一种社会必需的领域性服务。教育实践智慧具有稍纵即逝性、情景依存性,它不可能成为教师发展的目标,不可能为教育服务的专业化转变提供牢固支点。教育实践智慧寓于教师文化、发展于教师文化之中,其效能取决于教师文化系统。关注教师文化是教师面向社会构筑其专业教育服务的实践保证。
关键词:实践智慧;教师文化;专业服务
中图分类号:G4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2)09—0003—05
“专业”的实质是不可替代性,作为“专业人员”的教师,其社会立足点就在于它能够为社会提供独一无二的教育服务。因此,从专业服务角度来探讨教师工作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迄今,教师教育专业化正经历着由“教师专业(Teacher Profession)”、“教学专业(Teaching Profession)”向“教育专业(Educational Profession)”的发展过程。其中,“教学专业”是撑起专业型教师教育的顶梁柱,它体现着专业教育服务的应然状态。在专业教育观念、专业教育判断和专业自主权的合力下,教师对教育问题、教育事象形成了一种个性化的认识视角、应对方式,教育实践智慧从中赫然而现。由此,专业化的倡导者以为,实践智慧是统摄教师的一切专业性品质,是贯通教师专业化全程的一条内线。同时,教育实践智慧具有个体性、涌现性、情景性等特征,它能够赋予教师一种独特的素质构成和行动方式,从而提升教师服务的专业性水平。正是基于此,专业型教师教育认为:教师专业化的基础是教学专业化,而教学专业化的基础是教师的实践智慧。其潜在动机之一就是试图以教师的实践智慧为依托,致力于面向社会打造一种专业的教育服务。卡—桑德斯指出,所谓专业就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需要专门技术的职业,这种职业需要特殊的智力来培养和完成,其目的在于提供专门性的社会服务”。这里所言的“特殊智力”实际上指的就是教师的实践智慧。以教师的实践智慧来整合教师专业品性的所有方面和环节,并以之为支点面向社会打造专业的教育服务是教师专业化的根本旨趣所在。
一、教师专业化的潜逻辑:从实践智慧到专业服务
所谓“实践智慧”,它是指在教育情景中教师从专业教育观念出发,以教育经验为基础,以直觉思维为形式,用专业的教育眼光来对具体教育实践问题做出恰当判断,给予机智应对的能力,其实质是一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给予创造性地应对的技艺。实际上,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理性的教育判断力和教育思维力的延伸和体现,是教师的专业教育观念与真实复杂的教育生活的接合点,它是打造专业性教育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某种程度上看,实践智慧是教师专业型教育实践的最前沿,是专业型教师教育要在教师身上培植的最高智慧。钟启泉教授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发展不是基于行为主义基础之上的教师能力本位的发展,而是基于认知情境理论的‘实践智慧的发展”。换言之,正是教师教育实践智慧的境遇性、个体性、情景性、一次性等特征才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具有了专业性、独特性、不可重复性、不可还原性、难以传递性的特征,才使教师专业的社会服务有了专门性,才使教师成为了专业人员。
那么,何谓专业的教育服务呢?笔者认为,它具有五个特征:
其一,它是社会所必需的服务。所谓“必需”,是指由教师所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一种社会性的服务而非个别性的服务,这种服务的产生以社会发展的普遍需要为基础并以保证社会正常运转为目的。显然,教师向社会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就具有这种特征,这是因为教育活动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必需纽带,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实现代际“遗传”的枢纽环节。所以,社会必需性既是教育服务存在的理由,又是它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客观基础。
其二,它是基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服务。社会分工是一种专业服务产生的客观基础,社会分化的程度与行业的专业性程度呈正相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的发展是以高度分化、高度整合为特征的。在社会高度分化时,某些社会服务就会由高度专门的行业、人群、机构来提供,随之专业服务应运而生。专业教育服务的产生亦是如此,它是社会分工纵深推进和专业社会化发展的一个环节和产物,教育服务从其他社会事务中分化出来并获致专业身份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其三,它是一种领域性的服务。就专业服务而言,它是以对特定领域的垄断为后盾的。在这一领域中,不仅专业服务占居着绝对统帅地位,而且这种专业服务一旦离开了这一领域根本就无法生存,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依存性。这既是专业服务的优势,亦是其致命的弱点。专业服务在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弱点就是其难以适用于其他领域。对专业教育服务而言,之所以它“专业”,就在于这种服务是唯一而且只指向教育领域的,它具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特殊化的、专门化的社会服务。
其四,它是由具有特定知能结构的人来提供的服务。所有专业服务不仅具有服务内容项目的不可替代性,还有服务主体的不可替代性,后一“不可替代性”集中体现在专业服务提供者所独有的知能结构上。专业型教师教育认为,正是由于教师具有独特的、专业的教育观念、教育知能,故他能够针对具体教育问题,运用独特的眼光,形成独到的理解,因地制宜地给出有效的解决方式。专业的教育服务最终体现在教师的教育行为方式的独特性、专业性上,它根源于教师所具有的独特主体结构。
其五,它是一种难以程式化的服务。专业服务的不可取代性还在于当专业人员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后并不一定就能够打造出这种专业服务,他还要能够把这些专业知识、理论恰当地、灵活地在该运用的时候应用到该运用的地方,这就是实践智慧。它具有不可复制、不可模仿、不可算计、难以传递的特征。对教师而言,正是由于“实践智慧”的上述特征才使教师的教育服务最终具有了高度的专业性品格。所以,贾维斯指出,“由于每个情况都有其独特性,因此在反应过程中,专业人士会发展出新的技能。他们学习的并不是一种技能,还有支持实践背后的那些知识,他们知道为什么在特定的情况下要使用特定的技能。”就教育服务而言,那些运用专业知识、进行专业判断的教育活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初级性的专业服务,完整意义上的“专业教育服务”只有在教师娴熟、灵活地运用专业教育观念,并形成了参与教育活动的实践智慧之后才可能产生。故教育实践智慧是专业型教师教育所固守的最后堡垒,是为其专业性进行辩护的最高论据。
可见,专业教育服务决定了教育活动不可能是教师的一件普通工作,而是一项需要在高度智力活动和专业态度支持下才能打造出来的服务。工作以任务为取向,以可重复性为特征,是一般主体经过短暂训练后就可以担当的活动,而专业是以社会服务为取向,以实践创造为特征的,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担当的活动。教育活动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是教书育人。就这种服务的提供者而言,它经历了由长者到知识分子,再由知识分子到专业教师的发展演变。只有在专业教师出现后,教师服务的专门性特征才日益明显。换言之,正是由于需要专业的教育观念、教育知能、教育智慧而非一般的教育经验、学科知识,才使当代教师走出了经验型教师和知识传递型教师的囹圄,过上了一种专业生活,实现了其身份的新生。
二、对专业教育服务基础的省视
据以上分析可知,在专业化进程中人们实际上已经假定实践智慧能够赋予教师的教育服务以专业性的品质,“之所以把教师职业作为专业,是因为学校生活既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不可重复再现的,极富挑战性,要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教师就必须要具有‘教育智慧”。但是,受自身特性所限,教育实践智慧难以成为教师发展的目标,难以充任专业教育服务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实践智慧稍纵即逝,难以确保教师专业的持续发展。有学者指出,实践智慧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关教育教学整体的真理性的直觉认识,它来源于实践,通过对具体的教育情境和教学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将感性的、表面化的经验提升,使其内化为教师的实践能力”,其根本特征是“独创性”、“生成性”、“内隐性”。教师的实践智慧既非教育经验的厚重积累所致,也非教育认识的厚积薄发,而是在教育情景中将二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因此,实践智慧一般具有双重依赖性,即个体依赖性和情景依赖性,它大多不属于默会知识,具有难以显性化、符号化和不可“全传递”(鲁洁语)的特征,无法通过按部就班的方式来习得。同时,实践智慧是教师在长期实践中“悟”出来的,是其教育活动艺术化的结晶,不可积累、容易失传,难以知识化是其特殊性所在。舒尔曼指出,“教学这种职业和专业,所面对的一个困扰就是那种普遍存在于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健忘症,换句话说,实务人员的最佳表现,往往会在朋友之间失传”。显然,以实践智慧为支撑的教育服务是难以通过简单的训练、交流来完成的,教师想单单通过参与学习的方式来为社会打造一种高度个性化且持续稳定的专业服务是相当艰难的。
其次,实践智慧是一种教育艺术而非教师发展的目标。智慧总体现为一种难以言明、难以重复的实践策略,它是“被运用于生活的哲学”,是人从人性事理出发并在结合自己的直觉、经验、感悟的基础上对教育事件做出的一种情景性、机智性的应对方式。智慧的表现方式总是涌现,是绵延,是一次“创造性进化”。所以,教育实践智慧的发生总是偶然的、随机的、不确定的,它不具有可控性和预成性。范梅南指出,教育智慧“不是简单的情感或可以学会的习惯,但它可以通过更为烦杂深奥的韧性的成长、发展在教育过程得以形成”。想要将之从教育境遇中剥离出来,对之加以描述和表达绝非易事。正是基于此,佐藤·学指出,实践智慧是“依存于有限境脉”的“熟虑的知识”、“案例知识”、“不可还原为问题解决的综合性知识”、“隐性知识”、“个性化”了的知识。可见,实践智慧是不可教的,它只能在教育实践中被创生而不可能“拿”到课堂上去教授,想要在教师身上“培育”出实践智慧简直是一种奢望!
其三,将教师发展重点定位在实践智慧上极有可能将教师变为实务人员而非专业人员。如果将教师个体专业化的重心放在对实践智慧的培育上,那么,那些与之形似而神非的实务性知识可能会成为教师教育的实际内容,进而给教师专业性的提高产生不良影响。如前所言,实践智慧不可分解、不可教授,不可从实践境遇中剥离,因此如果牵强地将之列入教师的培训课程,我们势必首先会刻意地对之进行人为性的解析,使之变为碎片化的实务知识后再去讲授。其结果,它只会使教师教育蜕变为对实践智慧形似而神非的模仿活动,甚至可能导致教师专业化的进程重蹈覆辙,退回到“工作”的水平上来。正如杨慧文所言,“采取师徒制度的实用精神”、“注重教育现场的实习”和“强调发展实际的智慧”是实务型教师教育的基本特征,它并非教师教育的理想目标,而是教师专业化进程需要超越的对象。实践智慧实务化的结果只会把教育事业降格为一种更为低级、简单、机械的实务性“工作”,而非一种专业的社会服务,不可能为教师发展提供一个稳妥的支点。
三、关注文化:构筑专业教育服务的坚实基础
可见,依托教师的实践智慧来为社会打造一种专业的教育服务是专业型教师教育的预期目标,但该目标具有相当的难为性和理想性,这就构成了专业型教师教育内在的一个悖论。笔者认为,消除这一悖论的关键是要理清教育实践智慧与教师文化间的关联。与其把教育实践智慧视为教师的机智性教育行为,倒不如说它是教师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链环;与其说教师的发展是实践智慧的生成过程,倒不如说它是教师应对教育生活的认识图式和行动图式的转变过程。在文化学视野中,教师的发展将不再被理解为是教育实践智慧的显现过程,而是实在的、细微的文化转变与创生过程。对教师而言,将其发展建立在文化转变之上比建立在实践智慧涌现之上更为稳妥些。在此,笔者所言的“教师文化”不是指教师“共享的实质性的态度、价值、信念、观点和处事方式”,而是“教师的教育生活样式”,即“教师在教育生活中应对教育事件、参与教育活动的独特方式”,或教师参与教育生活的稳定图式。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告诉我们:“世界就是我们所知觉的那个东西”,而知觉的根本特征是含混性,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如感性、理性、实践等,它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一切行动都脱离出来”。因此,教师在生活中的行动依据是多样化的,其文化样式也是多样化的,教育要想成为教师为社会提供的一种专业服务就必须全面关注教师文化的创生与发展,而不能仅仅驻足于对教育实践智慧的表面性关注上。
首先,实践智慧实质上是教师文化的一个环节。毋容质疑,教师实践智慧的产生,确立了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从表面上看,教育实践智慧是教师对教育情景、教育事件的恰切、机智的应对和处理,但就其实质而言,它源自教师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种看待教育问题的独特“眼光”,处置教育事件的独特图式。这种眼光和图式是属于文化的,具有鲜明的个体色彩和文化底蕴。在教育生活中,教师在处理每个教育问题、参与每次教育活动之后都会在他身心上留下某种“印痕”,进而改变了教师审视其他教育事件的眼光,改变了教师参与未来教育生活的图式,形成了教师下一个教育行动的起点,这就是教师文化。教师文化在教师的教育生活经历中产生,在教师的教育生活经历中发展,二者之间具有高度同步性。教育智慧就位于新旧两种教师文化的转换点上,它是镶嵌在教师文化链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而教师文化就是教师所有教育智慧的载体。进而言之,教师认可的教育观念、教育理论,身置其中的教育经验、教育常识、教育惯例、教育制度,由教师身体所参演的教育仪式、教师节日等等,都是教师文化的内容和构成,都是承载教师实践智慧的媒介。所以,教师的教育实践智慧是在这些耳濡目染的文化图式中被孕育、被创生、被传载的。一旦这些文化图式被充盈,教师的教育行为就变得更为自然、自由,教育实践智慧就会不时从中涌现。故此,教师的实践智慧并不神秘,它只是教师在教育生活中创造的点滴生活智慧的凝聚与重组,是教师文化之旅中的一个“亮点”而已。正如布鲁纳所言,人类“还有一个地方存有更多的知识,这里就是‘文化”。所以,在教师教育研究中,只见“智慧”不见“文化”,只见“主题”不见“背景”是对教师教育生活的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认识,教师文化才是教师智慧的不竭之源,教师文化的新陈代谢才是教育实践智慧的真实存在形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专业教育服务的基点不应是教师的实践智慧,而是教师独特、完整的文化样式。
其次,专业服务的内核不是实践智慧而是文化智慧。在专业型教师教育中,教师向社会所提供的专业服务集中体现为教育实践智慧,即教师的专业知能、专业判断与教育情景三者相遇交合、融为一体的产物。在此,教师对教育情景的感悟力和对教育知能的驾驭能力最能体现教师的实践智慧。然而,尽管实践智慧是外显的、自由的,而其主体——教师却是扎根于教育生活之中并受制于“文化”这个无形之手左右的。因此,实践智慧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理智、完全自由的教育行为方式,而是以“文化”这个“知识库”(戴维·伯姆语)为后盾的,这就是文化智慧。文化智慧与实践智慧不同: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创造的那些具有即时性、情景性、机变性的教育策略的集合,而文化智慧则是教师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长效性、持续性的认识图式和行动图式(如观念、经验、惯例、常识、制度等);实践智慧崇尚的是教师在教育情景中产生的“格式塔”式反应,而文化智慧看重的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发生的那些细节性的教育图式的创生与转变;实践智慧关注的是教师处理教育问题的即时有效和短期变革性,而文化智慧关注的是教师的整个教育生活方式、教师文化系统发生全局性、渐进性的变革。可以说,教师的文化智慧是一种“大智慧”,是放眼于教师教育生活整体发生深刻、彻底转变的智慧,而实践智慧只是一种“小智慧”、“小聪明”,它只着眼于教师的教育行动对于解决眼下教育问题的效应。只有将教育实践智慧融入教师文化的洪流中去,它才会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才可能成为打造专业教育服务的重要推动力。
其三,实践智慧的效能标准寓于教师文化之中,实践智慧必须求助于教师文化才可能释放其效能。实际上,在教育生活中,我们所认同的那些实践智慧其实都是来自一种基于感觉、直觉的判断,故此,其是否真正有效、可行、合理,需要我们所秉持的日常智慧、文化直觉来鉴别。这里所言的“感觉”绝非心理学意义上的感觉,而是指“通过积累各种经验才能体会到的敏锐的感觉”——“机智”或理性的直觉。换言之,在一种教育常识、教育习俗、教育传统等背景之中认定为“智慧”的行为方式在另一种教育习俗、教育传统背景之中就不一定被认定为“智慧”的行为方式。所有“实践智慧”都具有多面性,在特定文化参照系内,我们之所以会认为一种教育行为方式是智慧的,更多是因为这种行为方式投合了我们的某些文化期待、文化惯例、文化经验,或者说,是二者之间产生了“共鸣”或偶合。所以,要正确理解教师的实践智慧就必须将之与其所处的文化参照系关联起来才行,否则,我们就会被一种主观的判断所迷惑,就会在实践中迷失方向。一句话,教师文化系统才是实践智慧的最后判定者。要正确地引导教育实践智慧的发展,我们就必须首先变革教师文化系统,变革教师教育生活中流行的惯例、习俗、传统、制度、生活哲学、“民间教育学”等。显然,一种教育服务只有站在这一制高点时,它才可能具有恒久的专业性。
最后,实践智慧自身处在教师文化系统之中,它也具有文化性。如果说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生活中创造的一种新颖、独特、有效、机智的教育图式,那么,它也属于教师文化的一种样态,故也具有教师文化的一切特性。只不过这种文化样态不像教师的自为文化,也不像教师的自在文化,其特殊性就在于它具有难以言表和生命短暂等特征。实际上,实践智慧就是介于教师的自为文化与自在文化之间的一种临界状态、中间状态、质变状态,是贯通上述两类教师文化间的一座桥梁。教师文化的发展是“变”与“不变”、质变与延续并存交替、相继推进的过程,在其中教师的实践智慧就是新教师文化样式生成的一个契机和起点,故它是一种特殊的教师文化样式。由此可见,教师专业的教育服务应该建基于那些常态的、稳固的文化样态之上,而非那种处于临界、质变状态的实践智慧之上。否则,教师为社会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专业性不仅难以保证,而且也难以持久。
参考文献:
[1]檀传宝.建立教师专业标准应当考虑的三个问题[J].教育科学,2004(2).
[2]陈琴等.论教师专业化[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6).
[3]钟启泉.“教师专业化”的误区及其批判[J].教育发展研究,2003(Z1).
[4]彼得.贾维斯.实用知识的学习过程[A].Lesley Kydd等编.教育管理的专业发展(陈垄等译)[C].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1.48.
[5]刘旭东.学校文化重建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6]郭东岐.教师的专业发展主要是实践智慧的积累[OL].http://www.1e.com.cn/lj/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
[7]李.S.舒尔曼.知识与教学:新改革的基础[A].学习者与教学[C].Jenny Leach,Bob Moon编(陈耀辉等译).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3.109.
[8]梁祝平.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文化素质教育[OL].www.yeshare.com/LW/10/qq—sun12989.
[9]【日】田中裕.怀特海—有机哲学(包国光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7.
[10]【加】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李树英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74.
[11]【日】佐藤学.课程与教师(钟启泉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28,370.
[12]杨慧文.变革中的教师教育范式:海峡两岸之比较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32.
[13]Hargreaves, A. Changing Teachers, Changing Times:
Teachers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Postmodern Age. London: Cassell, 1994.15—17.
[14]龙宝新.论教师文化与文化型教师教育[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165.
[15]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64.
[16]Bruner. J.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1996.55.
[17]【日】丸山高司.迦达莫尔—视野融合(刘文柱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