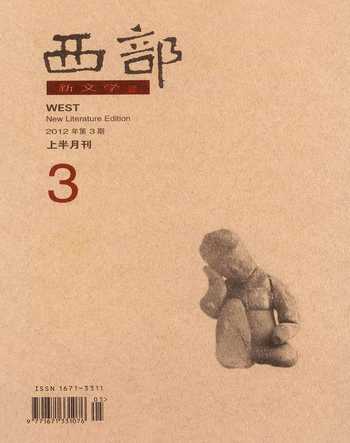酷刑
2012-04-29黄克全
众所周知,金门在抗战期间也曾经被日本占领过,当地七十岁以上的,多少也知道当时有个抗日组织,叫“金门复土救乡团”。参加者不用说,除了几个同安人外,当然大多是金门人。救乡团本部设在尚未沦陷的大陆内地。救乡团曾突击伪警所;突击沙尾街,擒杀伪区长郎寿臣;以及爆破西园盐厂等等。三番两次下来,日本人知道这类行动必定有内应,因此加紧搜捕。民国三十一年正月初八,救乡团团员许水龙潜返岛上搜集情报,在烈屿联络站青歧洪水尚家被汉奸密告,日警本部会同日本海军派遣队急往逮捕,许开枪,跳楼,不幸被伪警洪启明上前牢牢搂住,日警本部部长小森随即一个箭步欺身上前,抽出武士刀砍断许的脚后跟。许在残酷刑讯下,仍旧不肯供出同志名单,熬到隔日,终因流血过多,含恨死去。尽管这样,由于许身上原本就携带着己方情报员许顺煌的情报——前面提到的几次突袭,情报都由他提供——因此,许顺煌也紧跟着被抓。
日后表旌地区抗日志士,许顺煌列名首位,其贡献功绩及人格志节,都不可不提。他是后浦人,五岁丧父,由母亲吴粉守节抚养成人。厦门鼓浪屿新华中学毕业后,教了一阵子书,不久辞了教职,到南洋从事贸易,回到家乡时,身边多了一妻跟一对儿女。随后他罹患了半身不遂,不能如常人一般步行,因而在后浦街上开了家杂货铺以营日常生计。日本占领金门以后不久,他立刻志愿加入闽省绥靖公署节制的复土救乡团,担任谍报提供工作,直到许水龙被捕,他也跟着落入日本警察手中为止。
许顺煌死难的地方就在日警本部一间专门拷掠人犯的房间。他是先被灌水,再给高吊起来用浸了马尿的皮鞭抽。他始终双唇紧抿,只让闷哼从嘴角挤出。不到一刻钟,原来身骨就孱弱的他昏厥过去,泼水醒过来后,给架在一张有扶手的木椅上,小森和几个日警伪警轮流审讯,但许顺煌显然打定主意抵死不从。末了,小森靠过去,附了他耳朵讲了句什么,许的脸颊剧烈地抽搐,只剩下一条细缝的眼瞳迸出精光,随即又泄气般垂下头额。
不半晌,许听到熟悉脚步声,睁开眼,母亲含泪瞥探了他一眼,便调转过头去,仿佛不认识自己儿子。但在那彼此凝视的一瞥中,两人互换了母子间该有的默契。逼供者全退出去,声明十分钟后他俩必须有问必答,否则后果堪忧。
根据信史记载,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许顺煌跟母亲双双遇害,许顺煌的遗体不知所踪,据说胡乱挖个坑填了,还有说是被丢到大海里。
但在这个事件中,当时在日警本部任伪警的莫胥这个角色却少为人知,或竟不为人知。十分钟刚过,莫随着在门口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小森跨进室内。
“招?不招?”小森阴沉沉地问。
回答他的是接续先前涛浪般凶险不祥的喑然。
接下来,不用说,软的既然不行,硬的再次上场,各种酷刑又轮流派上,最后,变成只是刑讯者的怒气发泄。小森抢到皮鞭,气喘吁吁地胡乱鞭打着人犯,使得许顺煌的胸背头脸都染浸着鲜血。
“你──”跌坐在墙角椅子上的小森手指着莫胥:“去,看你的了。”
红色激发莫胥某种自动感应装置似的,不疾不徐走到许顺煌面前,手里握着夹了烧红了的木炭的铁夹子。木炭烙在早已烧得焦黑的手掌心,立刻冒出蓬蓬紫绿色的烟,肌肉像虾体般翻转爆开。
他反过身来,这次换许母,烧炭碰到手掌,汩冒的却是幽绿的烟雾。“不要连累好人哟!”自始自终,她只对儿子──仿佛也是对莫胥──交代了这句话。
许顺煌睁开那只能睁开的眼,算是拜聆了母亲的遗言。“你这不孝的──”莫胥站在许顺煌眼睑前不到半尺讲了这句话,接着把手上点燃的那支烟按在对方肩胛。
母子尸体装在麻布袋里。下弦月挂在黑漆半空。二十吨的机动船上,没风,但却出奇颠簸着。莫胥想点烟,被身旁小森粗暴喝止。最后他们来到一处落着灰白阴影的海面,细碎浪波黏滞滞鼓荡。
“就是这里。”小森无任何声调说。莫胥和另外一名日本警察,一左一右,踏前一步,将麻布袋掀落海中,船舷摆震了一下,一撮咸咸浪花跳上来,打在莫胥额角。
让莫胥灵魂震颤、险些坠海的一幕,依历史记载,发生在十二年后,也就是民国四十三年。那年,他二十九岁。这之前老天爷一直都很眷顾他。战后他没有被关被逐,大概他平日对百姓还算是较温善的,以及城里某位有势力的士绅的保护使然,又因为跟对长官,很快地就攀升到司令部的少校侦防参谋官,主管各个下属单位的情报搜集及督导。他现在的工作重点在于肃清匪谍,必须常常审讯一些罪嫌分子,以往在日本警察本部耳濡目染所学的那套,正好派上用场。这点更使他庆幸,庆幸由于昔日的经历,给他带来佐助。
他审讯起嫌疑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手段也越发狠辣。烧炭烙身那套尽管不大适用,但他却有更厉害也更管用的手法。他最擅长的一招是用五个掌爪朝对方腋下猛抓,即使最刁蛮的角色,几次下来,无不口吐白沫,气都喘不过来地连连讨饶。
五月三日,防区新司令官到任就职,这位东北虎将痛恨共产党是出了名的(上任隔日,他就到马山广播站对隔岸喊话:“我是刘某某,有种打过来。”)。统军转战大陆南北,大概吃过不少亏,因此这类人物对嫌犯毫不留情,一经审讯定案,马上就地枪决,尸体装进麻布袋往海里一丢了事。
就在那阵子,破获了一个以摇拨浪鼓挑担卖杂货的通敌集团。九三炮战前,雀山炮阵地附近不时有信号弹出现,办了几个人后,果然安稳多了。
十月深秋的一个夜晚,莫胥跨坐在司令部附近一块青石岩上,透过八倍半望远镜,俯瞰扫瞄着山下纵深景物。每值此刻,他总不可抑禁地兴起一股参与历史之流、与有荣焉的陶陶然。墨森森穹苍有星星;广袤千里的大地自己在这里,相对凝视着。而这份相对性,必然有些什么意义才是──
一枚信号弹突然自左前方山脚下,像自虚无的图画蹿出般地无声无息盈盈腾升。莫胥并非首次经历到这个情况,这次依然像往常一样跳起。“驾驶兵,驾驶兵!”他边跑边吼,朝停放吉普车的车位跑去。来不及等驾驶兵,他跳上车子。
半个钟头后,他在中南公路上拦截到一名士兵两个老百姓,阵地早关闭,宵禁时间也过了,所以仅仅这个理由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到了司令部,一听到自己惹上埋放信号弹的间谍嫌疑,那名士兵立刻朝地上扑跪,放声大喊他冤枉。莫胥先赏了他一耳光,叫人把他拖到别的房间。
“好了,”莫胥掏出佩在腰间的手枪,往桌子一拍,“你们现在可以讲了,最好讲老实话,不然,哼,后果你们也知道吧?”
两人膝盖尽哆嗦着,都不回话。蓦地,僵尸个子开始呵呵笑出声,鼻涕眼泪涂了满脸,莫胥厌恶地靠在椅背上点起一根烟。“卫兵。”他喊。卫兵踏进室内,依了长官的手势指令,利落地把两人吊起来。僵尸个子还哭个没停。
“信号弹是不是你们放的?你们属于哪个单位?对谁负责,跟谁连络?怎么连络?任务是什么?不招,别想从这里出去,我保证让你们过不了今晚。说!”
跟僵尸个子相反,矮个人怒睁着牛眼。——像是一个记忆气泡自海底汩冒腾升般的,他跳起来,迎冲向矮个子,在他眼前不及半尺处停住,随即把香烟朝犯人肩胛扎实按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人犯并没有痛极而出的哀嚎。记忆的泡沫消失了,他像刚被什么释放了般地弹跌回来。猛不防,他抄起手枪,威吓地抵住矮个子左脑门。
既亮灿又昏黄的灯光熄灭后,一辆军车在公路两旁树影的注视下,滑过陡坡,朝海岸驶去。不知过了多久,莫胥有些恍惚地来到的海湾,他清楚这里是哪里,但许是月色使然吧,他迷失了方向感。他的脚离开车子,落下来,踏在既坚强又松软的沙土上。他和士官长合力扛着装了尸体的麻布袋走了一段路,把它丢上船,引擎噗噗,切开波浪,驶离岸边。
不一会儿,莫胥想点支烟抽,他睨了身旁的士官长一眼,在朦胧月光下仍然可以看出后者正皱起眉结。莫胥忽然觉得无趣,叭叭吸了几口就给扔了。
船头激起几朵沫花,莫胥在心里估量着潮水流向。“好了,就在这里。”他默默地说。用眼神暗示士官长一起动手,抬起麻袋──瞬间,他的身子像受到电击般,晃震了一下,他立刻连带记起,用烟头去按矮个子老百姓的一刹那,自己也依稀有着那么一份异样之感。首先袭上脑海的念头是:该是时空中某种力量的覆压,使得同一件性质的事情再现着。接着他开始强烈地感觉到麻袋里根本是相同的人,自己还在做同一件事。他还有闲暇从反面回头怀疑到:果真是二人?果真是二事?果真有前后?果真是十二年后?一阵冰冷自脚底蹿上胸口及臂膀,使他几乎撑不住,差点往前栽入大海。麻袋扔了出去,迅即沉入海底没半点声响。下弦月兀自投西,船立即调转回头。
黄克全,金门人,辅大中文系毕业,专职写作。着有《蜻蜓哲学家》、《玻璃牙齿的狼》、《一天清醒的心》、《太人性的小镇》等。曾获梁实秋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