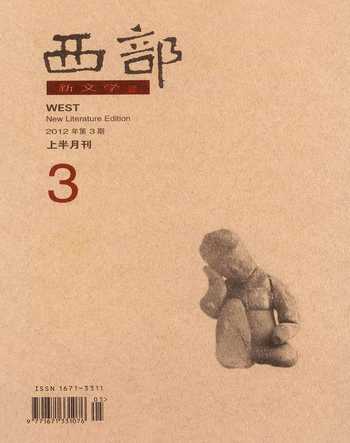昆德拉:时间外的脸与超时间的姿势
2012-04-29任洪渊
任洪渊
脸与姿势
在你们那里生活的人有脸吗?昆德拉让他的阿格尼丝羞涩地问一个遥远星球的陌生来客。
别再看着我。这是阿格尼丝的父亲弥留时对女儿的最后嘱咐。阿格尼丝知道,他去了一个没有脸的地方。
轮到了阿格尼丝自己。她也不要任何人,甚至自己的丈夫,看着她死去的脸。保罗,她丈夫的名字,早已在记忆中湮灭。她的最后意识是:对了,那边的人没有脸。
昆德拉却看到了阿格尼丝,一个没有脸的女人,并且用阿格尼丝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没有脸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平面化的,或者直接用昆德拉的话说,广告——意象形态的世界,人的脸越来越相似的世界,也许再没有比发现这个疯狂追求形象的无脸时代更有意味的事情了,至少,这比生活中承受不起的轻重些,比生活在别处近些,比为了告别的聚会缠绵些,也比玩笑更让人自娱自乐些。
阿格尼丝十七岁时,在舞厅与人对跳一种流行巴黎的多少有些放荡的舞,她的一左一右向前甩出的手臂,好像要把脸挡住,甚至要把脸抹去。当然,这不是为了遮住羞耻:恰恰是脸遮住了羞耻。抹去了脸,她才解放了自己。她一眼也不看舞伴的脸,目光只投向他身后的空旷处。就是在做爱时,她睁大的眼睛也在寻找脸后面的什么。即使她站在镜前,也从不看自己的脸,镜中无底的深处也许隐匿着真实的什么。她望着。
脸是什么?比如,法国先贤祠供奉着一种脸的系列,美国好莱坞又诱惑着另一种脸的系列,你要哪一张脸,或者你的脸要拥挤在谁与谁之间?
某一天,阿格尼丝在一本时尚画报上一眼浏览了二百二十三张脸。二百二十三张脸隐藏了脸。谁?他们是谁?一张脸后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前有一张脸。在阿格尼丝的眼里,每一个人的面相无非是人类脸谱差异很小的变形,人类样品的一个序号。于是有了一则昆德拉读法的《圣经》寓言:从所多玛城逃出的居民不能回头张望,否则就会变成盐柱。永远的盐柱!所谓瞬间化的永恒,不过是一种被时间抛出的永久的惩罚。穷其一生只为了把自己的一张脸长留在世间的人啊,脸与脸的重复就是历史,老去的,眉目不清的,彼此遮盖的历史。
于是,阿格尼丝自然要抛弃她的脸了。因为她天生是一个生活在自己脸后面的人,更确切地说,一个与自己的脸面分离的人。
同样的,虽然有那么几张斯德哥尔摩的脸给昆德拉一副诺贝尔的面孔,但是,诺贝尔的脸也好,昆德拉的脸也好,斯德哥尔摩们的脸也好,他们都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别人的脸。
脸不是人内部世界的外观,脸并不等于个性、灵魂、我。当阿格尼丝寻找脸后面的自己的时候,她也就最终放弃了“我是谁”的追问,而开始疑问:“我是什么?”有人听懂了这疑问吗?
十六岁的阿格尼丝第一次由一个男孩送回家。沿着门内的花园小径,不曾预想地,她扭过头来,朝他粲然一笑,她的右手在空中一挥,那么轻巧,飘逸。她第一次感到自己身体和身体的动作艺术杰作般的魅力。但是这个如此奇妙地首先触动了她自己的手势,却并不专属于她,也就是说,不是她首创的而是她再现的。她偷偷看到过,她父亲的女秘书也曾朝同一条花径相反的方向,向送别她背影的目光,莞尔一笑,出人意料地扬起手臂,那么轻巧,飘逸。她和她,谁在模仿谁?她们都不过是同一个迷人姿势的两个副本罢了。一个手势照亮了阿格尼丝深邃的时空:这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时刻在一瞬间的突然相遇,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女人在一个手势上的突然重合。
姿势。这是一个在告别中召唤和预约的姿势,一个转过身去眺望前面的姿势。她们挥手、触摸、抱吻、交媾、分娩、瞑目……一个姿势就是人体的一组词语。你不妨累计一下,迄今为止的世界,词语比人少,姿势比人更少,换句话说,不是我们在使用姿势,而是姿势在使用我们,正像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在使用我们一样。从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的姿势与包法利夫人服毒的姿势,娜塔莎飞月凌空的姿势与玛特儿吻别于连断头的姿势,查泰莱夫人丰乳的姿势与拉拉美臀的姿势,直到最近阿格尼丝转身挥手的姿势与她的妹妹劳拉两手从胸前一翻推向不可见的远方的姿势……姿势上演的人生。
不必考证,也无从考证,在一个姿势上,是谁复活了谁,或者是谁复制了谁。世世代代的人在同一个姿势上相遇,就如同他们在同一个词语上相逢一样。请不要再凭你的脸面而是凭你的姿势,探究你的身世、命运和归宿之谜。
姿势叠映。从阿格尼丝转身挥手的姿势里,走出了她的妹妹劳拉:
保罗好像突然老了许多。劳拉笨拙地游着爬泳,她那一次次划水都好像岁月落在保罗头上:我们看见他的脸在一点一点变老。他已经七十岁,过一会儿八十岁,他仍旧端着酒杯站在那里,仿佛要阻拦山崩一样向他袭来的岁月。他突然又衰老了十年,变成虚弱不堪的耄耋老人,一百二十岁至一百五十岁的样子。就在她走到通向更衣室的转门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她突然转过脸,朝我们轻轻地挥了挥手臂,那么优雅,流畅……奇迹出现了。岁月逐渐从他身上离去,又把他变回五十岁上下,长着蓬蓬松松一头灰发,风度翩翩的男子。
美丽女人的无年龄的姿势万岁!尽管劳拉这一次转身挥手的远眺和暗约,不是对她的丈夫保罗,而是对她的情人阿汶奈利厄斯。
两姊妹。阿格尼丝的头和劳拉的身体
这就是劳拉:充满梦幻,昂首望天,可身体下坠,她的屁股,还有那对同样沉重的乳房,都朝向地面。
劳拉的姐姐阿格尼丝。她的身体像火焰一样腾起,头却总微微低垂:一个注视着地面的怀疑论者的头。
虽然文学史上已经有那么多有名的两姊妹,昆德拉仍然忍不住要增加他自己的两姊妹阿格尼丝和劳拉。两个箭头是她们形而上的头和形而下的身体。轻视面目的昆德拉只重视头和身体。对昆德拉来说,两个箭头是否就象征头和身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相对的或者相反的箭头,的确是现代人头与身冲突与分裂的一种几何学抽象。我1988年也曾独自叙述过“头与身的战争”,十年后,读到1991年昆德拉《不朽》中文版上的这两组互相碰击的箭头,让我暗喜。
更让我惊异的是,不望她们的面貌——她们也无面貌可望,我竟从阿格尼丝和劳拉的身上,似曾相识地,看到了曹雪芹的钗与黛的侧影。劳拉沉重坠向地面的乳与臀和宝钗高过冰冷头顶的肌肤温暖的雪线,阿格尼丝体内向上腾起的火焰与黛玉泪水滴下的燃烧着的寒冷,不分古典和现代,东方和西方,都同样是生命至深的痛苦。
两姊妹,两种不可替代的美丽和诱惑,两种互相增色的仪态与魅力,两种……已经多到任何一种增加都只能是重复。于是昆德拉直接展示阿格尼丝的头和劳拉的身体。
在一个脸面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像的世界,昆德拉如此不屑于描写阿格尼丝与劳拉姊妹的肖像,以至显得那不仅是现代小说的闲笔,简直就是败笔。但是,不管她们的面容多么朦胧,她们法语文化与德语文化的头却轮廓清晰。没有头的身体是不可思议的。
两姊妹诞生在瑞士边境的德语、法语接壤地带,德语和法语是她们的两种母语。最不可知的秘密是,姐姐长大成德语的阿格尼丝,妹妹长大成法语的劳拉。
劳拉那颗“昂首向天”的头,似乎生来就为测量法语文化“加法”的高度。从革命,乌托邦,层出不穷的先锋、后先锋艺术,到随季候流行的时装与随情欲变换的脂粉,劳拉也像许许多多法国人一样,不倦地用身外可观、可量、可形、可色的什么增加自己头颅的高度,成为自我肯定的一种外在形式。天生要“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是历史的加法。加法是无限的。劳拉不知道,身外无限增加的种种属性,不一定能融为与她一体的品性,却必定要掩盖、改变甚至扭曲她的本性。
但是,劳拉的身体高过自己的头。她活在自己的身体中,那最可贵的部分是在体内。她的身体,就是性,与身俱来,先验的,终身的,不是完完全全地给予就是完完全全地占有。劳拉身体的加法是:她+他。
他是谁?她+伯纳德?+保罗?+阿汶奈利厄斯?
劳拉最常用的词语都是体内的器官和器官的功能。比如她喜欢说“吃”说“吐”。吃,是劳拉的加法,她的爱的最高形式莫过于把被爱者“吃”掉,化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劳拉“吃”掉过谁?伯纳德,不过是“一头十足的蠢驴”,一个在喜剧年头苦恼地假笑并且苦心地要别人假笑的悲剧人物。而保罗是在从韩波到布勒东的反传统之后,从斯大林到卡斯特罗的革命之后,生逢其时地在中国红卫兵与法国五月风暴的年代成年,赶上在巴黎街垒中与旧世界决裂,并且,就是这个先锋的保罗,为了再赶上一个属于他女儿的电视、摇滚乐、广告、大众文化和闹剧的时代——为了“绝对摩登”,而成为“自己掘墓人的出色帮手”。剩下的阿汶奈利厄斯,也就只好来扮演一个身怀利器却找不到战场和敌人的战士,一个过时的唐吉诃德罢了。就连保罗,少女时的劳拉初次见到他的一刹那,一个声音对她说:“要找的人就是他!”(1808年,艾福,拿破仑与歌德会见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找的人就是他!”)二十年后,同一个声音对她说:“他不是要找的人。”那么还有谁呢?于是劳拉的“吃”变成了“吐”。加法变成了减法。她吐掉了伯纳德,吐掉了保罗,也还将吐掉阿汶奈利厄斯。
当然,吐,不一定是劳拉的“真”,却常常是她的“诗”,一个隐喻和意象,类似于萨特的“恶心”。凡是那些不能与她的身体融合为一的异物,异思,异己的一切,她都一一吐尽。在身体上和词语上,劳拉都是一个女性的萨特。
劳拉坠向地面的乳、臀与那一身一百二十五磅肉体的体积和重量,就是她痛苦的体积和重量。这也同样是宝钗丰腴的痛苦。尽管劳拉和宝钗无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相距遥远,但是同一种在历史中“留下”点什么的加法,都抵偿不了她们生命中的减法,余下她们凄绝地独守自己。
而阿格尼丝那颗“注视地面”的头,却靠近德语文化的一种减法,甚至不惜一切减到零。那当然不是黑格尔那种把万万千千的悖异与偶然减为一的必然的减法。也不单是诺瓦利斯减到死亡、叔本华减到原意志、尼采减到狄奥尼索斯第一推动力的减法。阿格尼丝减掉了黑格尔,减掉了诺瓦利斯、叔本华和尼采,直减到身体零的极限:虚无。
对于阿格尼丝,她的身体几乎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她仿佛在自己的身体之外。只有性把她的肉体焚烧成一团白焰闪烁的时刻,她才在自己的身体中,那时,她沐浴在自己的光华里,像极光,或者像白夜,像烧毁了地平线、烧毁了日出和日落也就烧毁了白天和黑夜的白夜。但是阿格尼丝拥有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也就是她失去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性的减法。阿格尼丝在一次次焚尽自己。所以她才那么惶恐地,眼睁睁看着吞噬她身体的迟暮逼近。
与她的身体相反,阿格尼丝的头倒是形而下地俯向故土。她每年都要沿着阿尔卑斯山区的林中小路,重寻父亲的遗踪。“她最后一次漫步乡间,来到一条小河边。她在草地上躺下。躺着躺着,觉得河水淌进了她的身体,洗濯去她的痛苦,她的污垢,洗濯去她的自我……存在,就是化作清泉,让穹宇融融雨水般地流落泉中。”她的减法越过了零的极限,变成了加法。与万物同一。与上帝同一。她就是苍蓝的天穹,飞逝的时光,她回到了生命之前之外之上的原初的存在,家园和诗意地栖居。在头顶上和词语上,阿格尼丝都是一个女性的海德格尔。
阿格尼丝,这个从罗马巴伯里尼王宫画廊的壁画走下的哥特式少女,没有回到画上。她最后抹去了一切的痕迹,记忆,连同自己的面容,不回头地走了。这与黛玉的焚稿,同是一种无望的孤绝。
在一个她早已诀别的世界,唯有一枝蓝色的勿忘我,不为人所见地开放在她的眼前。这个直减到零的人,依然勿忘我?
存在主义数学与天宫图的时间钟面
昆德拉曾想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时间哲学变为他的存在主义时间数学。不过,他只找到初级的加法和减法,像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那样。尽管他发现了小说叙述时间的多项定律,诸如无声的巧合,诗意的巧合,推出故事的巧合以及病态的巧合,等等,我们甚至还能仿爱因斯坦的伟大公式帮他完成一个巧合的子公式:
巧合的值=时间×不可能性n
但是,也仍然不能计算巧合的时间概率。他始终也没有能够创立他的存在主义时间数学,哪怕是一个方程,因为他找不到一个时间常数,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找到时间常数。时间无常数。
生命时间不可数。
无奈,昆德拉只好把占星术的天宫图理解为一种生命的隐喻,在天穹十二宫的圆面上,看日、月、七大行星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周期位移,构成种种寓言式的星象和相位。当日月和七星的九重循环,不断由起点回到终点或者由终点追上起点,天宫图的时间钟面,便永远是圆的无限,零的无限。太阳,连同其它八星,一一司掌着你的爱情,性,性格,梦幻,血性与挑战性,活力与冒险精神,因此,你生辰注定的星座和不可重复的天象,已经是你生命先天的主题。圆的旋转,每一颗行星时针般掠过你的星空坐标时的星象,都是你生命主题的一重重变奏。
当然,昆德拉并不为你占相。他发现,似乎与天上的星象与相位对应,人体的姿势也时针般移过地面,姿势的重现、重复与重叠,也宿命地预演着人生。昆德拉的小说是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说,他把小说写成了小说学,其中,与星象的天命、也与面相的血缘同等重要的,是昆德拉找到了他的人物家族的姿势谱系。
生命之钟的指针在转动,同一个渴望不朽的姿态重叠。
文献上的贝蒂娜,每当她神往于超越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进入永久的纪念,像一句惯用语一样,她也有一个无意识的姿势:
她双手内翻,两个中指的指尖正好顶在双乳之间。接着,她的头稍稍前倾,脸上露出微笑,双手有力而优雅地往上甩去。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双臂朝外翻手掌向前摊开。
(谁第一个做出这个手势,或者,谁在她面前做出过这个手势?也许无考。也许藏在姿势后面的记忆,比藏在词语深处的记忆更久远。)
昆德拉小说里的劳拉,也突然不由自主地甩出贝蒂娜式的手势,那时,她也仿佛抵达了贝蒂娜向往的历史高度和远方:
她把头微微一偏,脸上露出淡淡的、充满忧郁的微笑,十只手指撮在胸前,接着,双手往前一摊。
(她怎么会有这个动作?她从未做过这个手势。一位不相识的人在提醒她这么做,正像曾经提醒过贝蒂娜那样。仿佛是谁的这个手势引导着她,而不是她的这个手势引导着什么。)
贝蒂娜那双从自己胸前伸向天边甚至要伸过天边的手,其实,也只能伸向歌德、贝多芬,最多再伸向裴多菲的不朽。在贝蒂娜的手势后面,歌德退走了,她因为和歌德的恋情而不朽;贝多芬退走了,她因为和他的友情而不朽。而且,不管是出于贝蒂娜的传言还是杜撰,在奥地利皇后和她的扈从们面前,一个脱帽、垂手、躬身路旁的歌德和一个帽檐低低压过蹙额和眉峰、旁若无人大步走过的贝多芬,走进了历史。最后,贝蒂娜称二十六岁早殒的裴多菲为Sonnengott(太阳神),欧洲记住了这位在1848年革命中战死在战场上的匈牙利诗人,也记住了他的崇拜者贝蒂娜。连卡尔·马克思也有一次把他的燕妮冷落在一旁,陪贝蒂娜长时间地散步。在马克思的身旁,也闪过贝蒂娜的侧影。
从贝蒂娜到劳拉,同一个渴望不朽的姿势未变。
但是历史变了。贝蒂娜的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歌德少年维特和老年浮士德的欧洲,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和肖邦葬礼进行曲的欧洲,已经变了。到了劳拉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可惜,只能是伯纳德、保罗、阿汶奈利厄斯们的欧洲,在革命之后,战争之后,种种乌托邦和先锋后先锋之后,只剩下怀旧和文化的乡愁。在一个早已没有英雄而且不再有“事件”的年代,劳拉除了孤零零站在地铁站口,手捧红色募捐盒遥望非洲,又还能为她的历史“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劳拉捧着募捐盒的孤独身影,成了二十世纪欧洲一道凄凉的晚景。五月风暴已过。在这个因为没有历史而制造历史的时期,即使她要等黛安娜王妃没有爱情的婚礼和不是国殇的国葬,等那十几年间迎她送她的行列,礼炮与钟声、花朵与烛光、赞美诗与挽词相接的长长的行列,也还有好多好多年。
生命之钟的指针在转动。同一个伸手触摸的姿势重叠。
1810年。特鲁利茨的一个傍晚。六十二岁的歌德与二十五岁的贝蒂娜在室内对坐。窗外落日的余晖与她面颊上的红晕融汇,一直蔓延到她的心窝。
“有人摸过你的乳房吗?”他把手放到她的胸口。他问。
“没有。”她回答。
(谁第一个伸手触摸,谁第一声回答“没有”,同样不可靠。因为他伸向她的手,比伸向历史、不朽、永恒的记忆的手更久远;她的第一声“没有”,也远在历史、不朽、永恒的记忆之前。)
巴黎一夕。二十七岁的鲁本斯邀十七岁的阿格尼丝在一家夜总会对跳一种流行舞。他与她相距一步,阿格尼丝与鲁本斯相差十岁的距离和贝蒂娜与歌德相差三十七岁的距离相等。
“有人碰过你的胸脯吗?”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他把手放在她的胸口,声音禁不住有些颤抖。
“没有。”她以同样颤抖的声音回答。
(是谁在暗示他伸手?她的回答,是否也同时听到那声隔世之音?)
像是一个从未停止的动作,歌德伸出他的手,触摸。鲁本斯伸出他的手,触摸。
同样的,也像是一声永远的回声,贝蒂娜回答:“没有。”阿格尼丝回答:“没有。”
伸手触摸。
没有。
生命之钟的指针同时在天上的钟面和地上的钟面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