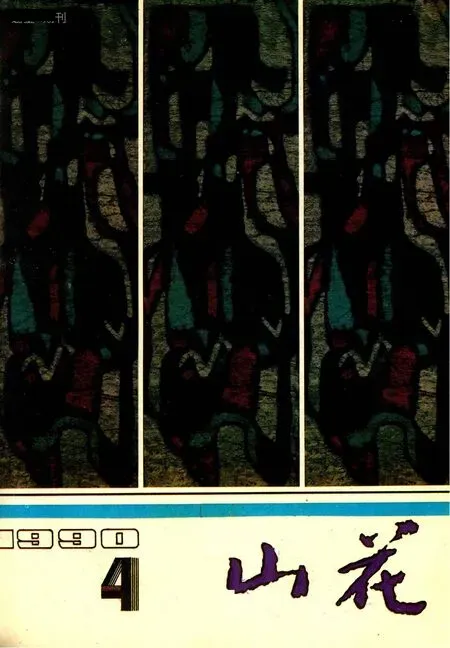探析艾米莉.狄金森的死亡诗
2012-04-29苏燕萍
苏燕萍
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被公认为“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这位与惠特曼同时代的诗人是谜一样的人。她终身未嫁,被人们称为“阿默斯特的修女”。1862年后几乎足不出户,在家务劳动和伺候老人之余埋头写诗。她生前默默无闻,仅发表过十首小诗。但她死后声名鹊起,人们甚至将其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尊她为诗界的“王后”。更有批评家指出,她是现代主义的先驱。
狄金森一生中创作的1775首诗独放异彩,诗歌主题涉及爱情、自然、死亡等,令人称奇的是她竟写了五百多首死亡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迷恋死亡呢?本文试图归纳狄金森的三类死亡诗,并分析导致她沉迷于这一主题的深层次原因。
狄金森死亡诗的四类主题
一、对死亡的厌恶与恐惧
终年不见天日的地狱、阴森可怕的凶灵、青面獠牙的恶鬼……在人们的意识中,死亡似乎更多地同肉体的疼痛与煎熬结合在一起。对于亲人和朋友的离她而去,狄金森自然表示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恐惧。
在其作品《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经结束过两次》中,她写到:
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经结束过两次
我还要等着看
永恒是否会向我展示
第三次事件
像前两次一样重大
一样,令人心灰望绝
离别,是我们对天堂体验的全部
对地狱短缺的一切
该诗表现出的对死亡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诗中提到的两次打击分别指的本杰明·牛顿和查尔斯·沃滋沃斯的辞世。前者引导她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亦师亦友,而后者是她多首爱情诗中的原型。虽然这段感情注定没有结果,但据说1862年沃滋沃斯一家迁往西海岸的旧金山后,狄金森只着白衣,更加深居简出。
二、对死亡的体验与反思
狄金森运用不同的视角详细描述了死者的心理变化、周围人的感受以及死亡的客观过程。
《我听见苍蝇的嗡嗡声》就是代表作:
我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当我死时
房间里一片沉寂
就像空气突然平静下来——
在风暴的间隙
注视我的眼睛——泪水已经流尽——我的呼吸正渐渐变紧
等待最后的时刻——上帝在房间里
现身的时刻——降临
我已经分掉了——关于我的
所有可以分掉的
东西——然后我就看见了
一只苍蝇——
蓝色的微妙起伏的嗡嗡声
在我——和光——之间
然后窗户关闭——然后
我眼前漆黑一片——
她极力渲染了一个死亡场景:人平静地躺在床上,气若游丝;在弥漫着悲痛气氛的屋内,亲朋好友的眼泪已哭干;在立遗嘱分配了自己可分配的东西后,人静候上帝来拯救她的灵魂到天堂以求永生。然而盼来的却是只令人作呕的苍蝇(fly)。fly有两层含义,将人灵魂的飞升和令人作呕的苍蝇相提并论,颇具讽刺意味。
在她的狭小天地里,许多亲友邻人由于疾病、战争或贫困相继而去。次数多了,连死神也让她觉得“彬彬有礼”。她对死亡的体验与反思有时是幽默诙谐压倒了感伤。
三、对死后世界的臆测
诗人天生的敏感和好奇心使她不断臆测死后的世界和生活,如《正是去年此时,我死去》:
正是去年此时,我死去。
我知道,我听见了玉蜀黍,
当我从农场的田野被抬过——
玉蜀黍的缨穗已经吐出——
我曾想,理查送去碾磨时——
那些子粒该有多么黄——
那时,我曾想要出去——
是什么压制了我的愿望——
我曾想,在庄稼的残梗间
拥挤的苹果该有多么红——
牛车会在田野各处弯下腰
把那些老倭瓜收捡一空——
我不知道还有谁会思念我,
而当感恩节来临时,父亲
会不会多做几样菜——
同样分给我一份——
由于我的袜子挂得太高
任何圣诞老人也难够得到——
会不会损害/圣诞节的欢快——
但是这类想法使我苦恼
于是我改变思路——
某个美好的一年,此时——
他们自己,会来相聚——
诗人想象自己躺在棺木里被人从田野抬过的情景暖人心房。对亲人的难分难舍都汇成诗人对生的恋歌。正当感伤时,诗人笔锋一转,盼望亲人在将来某个美好的日子里与自己相聚。
四、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真与美的追求
狄金森的死亡诗既让我们闻到了冷幽阴森的死亡气息,又让我们看到了灿烂诱人的希望之花。狄金森之所以迷恋“永生”,是因为她那看似冷漠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自然和生命真挚而持久的爱。
“希望”是不长羽毛的小鸟
专栖于灵魂之上
唱着没有歌词的曲调
从来不会遗忘
正是这种爱促使她在追求生命真正意义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她的《我为美而死》道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我为美而死,对坟墓
几乎还不适应——
一个殉真理的烈士
就成了我的近邻——
他轻声问我“为什么倒下”?
我回答他:“为了美”——
他说:“我为真理,真与美——
是一体,我们是兄弟”——
就这样,像亲人,黑夜相逢——
我们隔着房间谈心——
直到苍苔长上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姓名
如此美好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时刻,在人活着的时候往往因为琐事而不能拥有,却在死后实现了。诗中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真与美的渴望与追求。
狄金森迷恋写死亡诗的原因
狄金森的死亡诗竟占三分之一之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诗人如此迷恋死亡?文章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中原因。
一、充满矛盾的社会背景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南北战争不仅给国家带来了巨变,还使狄金森家乡的一些青壮年去而不返。狄金森从她二楼卧室的窗口时时看到悲伤的送葬场面。这一切死亡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内战后,美国迅速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宁静的田园生活被打破,拜金主义日益浓厚,人际关系渐渐疏远,道德水准逐日下降,这都使人感到無所适从。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狄金森也觉得生命没有安全感,她选择了离群索居来逃避。但是,狄金森的归隐并不是真正地看破红尘。她虽然不像惠特曼那样写政治题材的诗,但她一直都关注着社会。她是《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日报》和《大西洋月刊》的忠实读者。她生活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以书为伴,时刻洞察内心世界,追求真理与永恒。
二、个人信仰危机
狄金森对宗教的怀疑使她产生了信仰危机。狄金森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镇是清教主义的最后堡垒之一。她的父母、哥哥和妹妹都是虔诚的教徒。她从小熟读圣经,长期受到宗教传统和习俗的浸染,但是她一辈子拒绝加入教会。叛逆的她一再质疑《圣经》中关于死亡的解释,表示对万能的上帝夺去人们所爱之人不能接受。她向好友阿尔比·鲁特坦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世界在我的情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我去死,我也不愿为了基督而放弃一切……”
此外,狄金森深受爱默生的影响。爱默生强调人的直觉意识,认为人可以在自然中发现自身的理性光芒。爱默生使人的精神第一次完全摆脱了上帝的控制,把人从过去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带入了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他的思想渗透在狄金森的诗歌创作中。
另外,“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发表宛如一枚重型炮弹,动摇了基督徒信仰的根基,随之而来的是对上帝的怀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在美国,狄金森应算是产生危机感最早而表达又最充分的作家之一”。
但是,她虽然拒绝皈依宗教,内心却在激烈地挣扎着。她写道:“上个学期,当那个好机会到来时,我很后悔我没有屈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苦恼来自于她对上帝既信又不信的矛盾心理。超验主义以及进化论使上帝变得虚无缥缈,她感到精神上无所依靠。她的死亡诗篇道出了她的信仰危机以及她对于不朽及死亡的矛盾心理。
三、个人生活经历
狄金森的个人生活经历让她对生命的意义产生困惑,对死亡表现出迷恋。在她孤独的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亲朋是她最宝贵的财富。但是敏感而又早熟的她多次经历失去亲朋的剧痛。1844年,十三岁的她亲眼目睹了好友一步步走向死神;1853年,她的良师益友本杰明·牛顿离世;1860年,她的婶婶去世;1874年,她至爱的父亲突然辞世;1882年,母亲也离她而去;1882年,她曾一往情深的华滋华斯牧师去世;1883年,她最喜爱的小侄子吉尔伯特夭折;1883年,她的好友詹姆斯·克拉克去世;1884年,差点让狄金森走进婚姻殿堂的劳德法官不幸去世。正如她在《我的生命结束前已经结束过两次》中所写这些沉重的打击“令人心灰望绝”,如同自己的生命被剥夺。承受着亲朋离开的痛苦,狄金森只能期望死后可以得到永生,与他们重聚。
结束语
“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狄金森的死亡诗独树一帜地从人类体验的角度出发,以生动的语言来展现死亡的过程和情景以及她对死亡的理解。她对死亡主题的探索体现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领略狄金森死亡诗的精髓有助于我们将生命的意义从有限延伸到无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