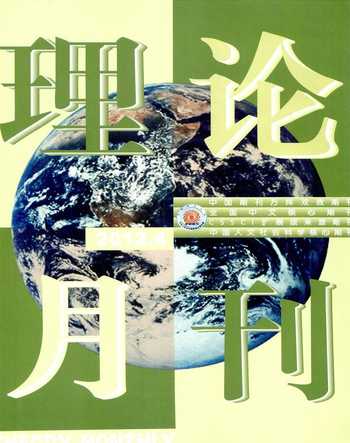言志与摹仿:中西文论观念的不同言说
2012-04-29庄桂成
庄桂成

摘要: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摹仿说被视为西方文论的基石,它们虽然都是对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但却形成了不同的文论话语体系,使之在理论内涵、逻辑起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式,而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是“主客二分”式。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物我相通、情景交融,甚至以情驭景,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情感体验;主客二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知觉认识,所以西方文论认为文学应表现的是那个客观世界。
关键词:诗言志:摹仿;哲学分野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62-04
所谓文论观念,就是文学理论批评中,对于文学的最根本的看法,例如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它往往形成于其文论萌芽发展的早期,并对一个区域或民族文论的发展,起着奠基和决定的作用。宏观地比较一下中西方传统的文学艺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抒情性文学比较发达,其抒情写意的艺术功能也发挥得比较充分。而西方的叙事性文学及其叙事理论则较为繁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中西方在文学和文论的基本观念上有着区别。中国与西方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土壤,因而有着不同的文论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诗言志”,而西方则从古希腊时起,就倡导“模仿说”。
一、诗言志:中国文论的滥觞
“诗言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命题,被视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记载有中国古代传说中“五帝”之一的舜谈论音乐的话语,原文中有以下四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它的大意是,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向的;歌的旋律悠长舒缓,徐徐吟咏,以突出诗的意义;声音的高低又配合着悠长的旋律:音律又调和着吟唱的歌声。诗言志之所以能作为中国文论的基本观念,除了它是中国文论的源起之外,还在于它在后世文论中一直得到尊崇与传承,影响着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路向。
自《尚书》始,先秦其它典籍中,也有类似表述。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荀子·儒效篇》有“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孔子和孟子虽未直言“诗言志”,但他们也在一些论述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即语言要充分表达意志,文采要充分修饰语言的意思。
汉代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意思是,诗是思想情感的体现,藏于心中称为志,形诸言称为诗。情感激动于心便会形诸语言,语言不足于表达便会咨嗟叹息,咨嗟叹息不足以表达便会引声长歌,引声长歌不足以表达便会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它指出诗是诗人之志的载体,诗人作诗,是有志在心,受到情感的激发,发言而为诗;这段话将“志”与“情”结合起来谈,进一步阐明了诗的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并涉及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许多作家或文论家为诗的言志抒情说作了各自的解说。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概念,尽管这里未言及“志”,但他并不否认“诗言志”的主张。在《文赋》中他常将“情”、“志”并举,其涵义往往相通。因此李善为《文赋》作注月:诗以言志。故日缘情。
唐宋时期,诗言志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李商隐等人便以“言志”来纠正“缘情”之不足,提出了“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观点。宋代袁燮、张戒、陆游,明代的吴宽等人都将“言志”视为“诗人之本意”。例如,宋代张戒论诗,主张诗以言志为本。他指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岁寒堂诗话》)张戒指出,因时代不同,有的诗人以诗言志,有的诗人以诗咏物,也有的诗人兼而有之,但是,言志应为作诗之本。
清代钱谦益、王土祯、袁枚、方东树、纪昀等人也有所论述,都发挥了“诗言志”说。钱谦益说:“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也。”“古之为诗者,要归于言志永言。”“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他特别强调了志“盈于情”、“志足而情生”,将“志”与“情”联系起来考察,视主观因素的“志”为内核。王士祯则借《文赋》中的话来表达诗言志说:
《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千古诗之妙谛真诠也。故知志非言不行,言非诗不彰,祖诸此矣。何谓志?“石韫玉而山以辉,水怀珠而川以媚”是也;何谓言?“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词也贵妍”是也:何谓诗?既“缘情而绮靡”,亦“体物而浏亮”,“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是也。
总体来看,“诗言志”说自其产生以来,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纲领”,其它相关理论几乎都是以其为基础而衍生。同时,“诗言志”其自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其意义在不断地延伸,从而使之免于成为一种僵化的理念,而像一条动脉贯穿于历代诗歌肌体之中。
二、摹仿说:西方文论的源流
摹仿说最早起源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年~前480年)否定了神创造世界的神话和传说中女神创造文艺的思想,提出了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的观点,这是西方“摹仿说”的源起。后来,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约公元前460-前370)继承和发展了赫拉克利特艺术摹仿自然的思想,强调摹仿是对自然事物机能的仿效,但停留在简单和机械的摹仿这一表层上。他说:“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他用人善于摹仿的事实解释了人类的许多活动,其中也包括了艺术活动。
较为系统提出“艺术是摹仿”理论的是柏拉图。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认为,文学作品如戏剧、叙事诗是摹仿的。摹仿的情况有三种:一种是从头到尾的摹仿。如悲剧与喜剧;第二种是诗人自己的叙述,如合唱队的颂诗:第三种是摹仿和叙述相结合,象荷马的史诗。但是,无论什么事物都不可能是真实的摹仿,因为真实是存在于理念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之中的,所以摹仿不可能直接来自理念,而是来自物质世界。而物质世界是理念的摹仿,那么,摹仿现实的物质世界便是对摹本的摹仿。因此,他认为文学艺术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摹仿理论,认为普遍性产生于个体,在现实世界之外不存在另一个理念世界,所以文学作品摹仿现实世界。他在美学专著《诗学》中的一开始就首先给艺术下定义:“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事实上,整个《诗学》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的,“悲剧”、“史诗”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这一概念的演绎或者说具体化。同时,他论及诗的起源有两个:“一般来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是最可鄙的动物形象。”虽然亚里士多德把文学艺术起源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摹仿和快感,但他又用摹仿的惟妙惟肖说明了快感的产生,因而根本原因在他那里其实就是摹仿。
贺拉斯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所谓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是指贺拉斯并不否定亚里土多德的对现实的摹仿,除了现实摹仿外,贺拉斯主张向艺术摹仿。他认为古希腊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学艺术,与其别出心裁地写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或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伊的诗篇改编成戏剧。从公共的产业里,你是可以得到私人的权益的,只要怀不沿着众人走俗了的道路前进,不把精力花在逐字逐句的死搬死译上,不在摹仿的时候作茧自缚。”
中世纪时普洛提诺斯在他的《九章书》的第5卷中论述到摹仿问题。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本身是摹仿,这是柏拉图的理念摹仿论,所以后人称其为新柏拉图主义者。但是,他又认为文学作品并不仅仅复制事物的外表,而且要追溯到自然的本源观念。这里的说法超出了柏拉图。柏拉图只说文学作品是摹本的摹仿,而普洛提诺斯认为,文学作品不仅复制现实世界这个摹本,并且和绝对存在有关系,因为它要追溯到自然的本源观念(the Ideas from which nature derives)。这个自然的本源观念就是绝对存在,是理念。另外,普洛提诺斯认为,文学作品是美的造型者(molder),它能弥补自然造物的不足之处,因为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摹仿现实自然的美,而且作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运用文学来弥补自然造型美的不足之处,这也是他对柏拉图理论的超越。
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又提出了“镜子说”。达·芬奇、莎士比亚都先后宣称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的镜子。达·芬奇就说:“画家的心应该象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直到18世纪末,摹仿说始终是西方文论的中心。浪漫主义兴起之后,西方虽然有了表现说,但是摹仿说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小说、戏剧等这样一些以摹仿为主的文学艺术样式,始终是西方文学艺术实践的主流和主体。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果戈里、托尔斯泰等都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中曾说,法国社会是历史家,他自己好比历史家的书记,来写这部社会风俗史。列宁称赞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把艺术视为对生活的一种模仿。俄国的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把艺术视为现实的一种复制,艺术的作用只是再现现实的美,充当它的代替物,即“美是生活”。
摹仿说是西方文论的基石。自从古希腊时创立摹仿说以来,西方艺术一直沿着摹仿自然的线路发展,后来提出的镜子说、再现说都是摹仿说的延伸和发展,摹仿说这一基本观念始终没变。甚至有学者认为,“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实与摹仿理想的区分;所谓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与摹仿表面现象的区分”。
三、诗言志与摹仿说的哲学分野
“诗言志”与“摹仿说”分别是中西文论的主导观念。它们虽然都是对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的探索和认识,但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论话语体系。不可否认的是,“诗言志”与“摹仿说”二者在理论内涵、逻辑起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有着巨大差异。
首先,从理论内涵上看,“诗言志”与摹仿说都是对文学艺术本质的解说,但“言志”说本于“心”,重写意;“摹仿”说本于“物”,重写实。“诗言志”中“志”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到了20世纪也是众说纷纭。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认为,“诗言志”就是“言情”。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一文中指出,“志”属志向,怀抱,“诗言志”就是抒发作者的志向、怀抱的。闻一多通过对古文物和古代文献的缜密考证,认为“志”有三重含义:记忆、记录和怀抱。后来有学者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概括后说,“诗言志”应该有两重含义:一是“诗歌(以及其他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承担记录社会生活的职责”。二是“诗歌乃是人类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摹仿说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时被看作对艺术本质的解说,有时被看作对艺术起源的解说。前者的意思是说,艺术最初是对现实的摹仿,现在仍然是对现实的摹仿,而后者则仅仅是强调艺术最初是对现实特别对自然的摹仿。摹仿作为艺术的共同本质,其核心问题并非如柏拉图所说是“神力凭附”的结果,而是艺术反映现实的问题,是人的本能和天性。摹仿不是传达神意,而是人求知的欲望,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现实世界的本质并非存在于理念之中,而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因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亚里土多德是摹仿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只不过历史是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是摹仿可能发生的事。
其次,从逻辑起点来看,“摹仿”说的重心在艺术的审美客体方面。亚里士多德说,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自然就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摹仿要依赖客观外物,是以再现客观事物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状态为归宿的,它要求艺术再现的真实性、精确性和客观性。亚里士多德不仅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艺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因为艺术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更带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在艺术的真善美中,他更重视“真”,强调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客观真实的反映和艺术的认识作用。中国的“诗言志”,它的逻辑起点在审美主体方面。“诗言志”的心理基础是“情动于中”,这是进入诗的状态的重要前提。虽然诗人感情的激动离不开外物的融发,但“物”已不是外在的大自然的物象,而是融注了诗人强烈的感情色彩,使之因诗人的感情与人格的投注而呈现出意象化的意味,或以心托物,或以情注物。我国古代的先贤们十分重视艺术的抒情言志作用。在他们心目中,艺术是主观的、抒情的,犹如一盏艺术家的心灵之灯,艺术家用它去映照外部世界,感染外部事物。
再次,从后世影响上来看,“诗言志”与模仿说分别影响了中西各种文体文学的发展。模仿说因为强调“再现”的
手法,所以对西方的叙事文学如史诗、叙事诗、戏剧和长篇小说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明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史诗来看,西方早在古希腊时就出现了《荷马史诗》,后来又出现了英国的《贝奥武甫》、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等英雄史诗。而中国则以抒情诗见长(以汉民族文学而论),缺少西方那种规模宏大的长篇史诗。就戏剧而论,在西方,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戏剧就已很发达,而中国到了宋元时期才有戏剧,比西方落后一千多年。实际上,中国的戏曲是由有说有唱、曲白相间,由音乐伴奏的诸宫调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还是以歌词文采和音乐曲调取得戏剧效果,它的基调主要是抒情而不是叙事的,与西方所说的戏剧是有很大不同的。西方戏剧受模仿理论影响,注重“形似”,在戏剧舞台上则极力通过物质手段给观众造成真实的幻觉,追求“活生生的”生活形象,要求戏剧人物的语言和现实中的人物语言相吻合,并制造出人物活动的真实时空。而中国古代戏曲受“诗言志”说(即表现理论)的影响,更重神似。注意把握客观对象的风骨、神韵,着意表现气韵生动的意境美。当然,中西古代文论最早的两种不同理论的区别及其对各自民族不同体裁文学的影响,这只是就主流而言,但并不绝对。在以模仿理论为主导的西方文学中也不乏有精彩的抒情之作,如古希腊萨福的抒情诗,中古时期法国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但丁的《新生》,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彼特拉克的《歌集》等。同样,在以“诗言志”说为主骨的中国诗歌中也有叙事诗甚至史诗的作品。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各自发展了“诗言志”和模仿说,文论观念具有如此差异呢?这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式,而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是“主客二分”式。中国哲学从孟子开始就主张天人合一,他认为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天道有道德意义,而人禀受天道,因此人性才是有道德意义的。老庄也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他们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根,人亦以“道”为本。孟子之以人伦道德原则为本根的“天人合一”说,至宋明道学而发展到了高峰。张载的“天人合一”说是宋代道学之开端。张载以后,逐渐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派。柏拉图开西方主客二分思想之先河,他的理念论多“从认识论角度讲理念是知识的目标。是‘真理,而不是意见的对象”。到了近代,笛卡尔明确地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式为哲学主导原则。黑格尔则是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之集大成者,他的“绝对精神”是主体与客体的最高统一。黑格尔以后,从主要方面来说,继续沿着“主客二分”式思想前进的有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哲学家,当然也有许多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则贬低以至反对“主客二分”式。总体来看,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强调物我相通、情景交融。甚至以情驭景,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情感体验,所以中国文论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不是那个外物,而是作家的主观情志和情感体验,“诗言志”观念也便籍此而在中国文论中发展绵延。主客二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使得人与外物的关系多为一种知觉认识,所以西方文论认为文学应表现的是那个客观世界,应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当然里面也不可避免地含有主观认识),所以对客观世界的逼真模仿便是文学的本质,这便是模仿说得以在西方文论中存在发展的原因。
不论古今中外,人性都是一样的,都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与是非之心,都有七情六欲,都产生爱与恨的心理,都兼有低卑的欲望和高贵的情操,也“都具有执着于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本能”,所以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世”原则的基础。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各个民族都有其各自的特性。中西方文化各自发展了这么悠久的岁月,自然会有开始时差之毫厘,而后相去千里的个别性,即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西方文论也是如此。言志与摹仿作为二者的源头,都是对文学本质的解说和阐释,却各自发展成抒情与叙事的文学传统,这其中的缘由,确实值得令人深思。

责任编辑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