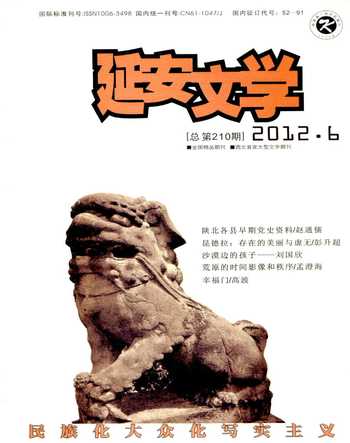绵绵不尽是亲情
2012-04-29方赫
方赫
近年来,有这样一些小说创作,作者或来自乡村,或是深入到乡村生活的事业青年。小说内容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矛盾斗争在乡村的剧烈反映,而仅仅是描写古旧的乡村在时代变革、现代化冲击下,发生的种种变化,其间涉及到人情世态、传统道德、风德习尙等等的相互交锋的碰撞,展示给我们的是落后与前进的因素相互交织渗透的乡村生活的是落后与前进的因素相互交织渗透的乡村生活的大场面,有鲜明生动的人物,有历史发展的脉络,有质朴形象的方言土语,有令人熟悉而又倍感亲切的传说旧闻。五彩缤纷,喜闻乐见。我认为这便是乡土小说创作。它应是诸多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种。
80后女作家刘国欣创作的小说《星辰闪烁》便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乡土小说。作者出生在陕北府谷,这里接近沙漠,土地贫瘠,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同样,封建礼教根深蒂固,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也代代相传,大家族的宗法制度也是自古沿袭,而且构成这个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虽然本性纯朴,但也难以摆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仍然屈服于小生产的经济活动中,满足于既定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时代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改革开放日趋深入的今天,这些封闭而有些落后的小山村,自然首先受到强烈的冲击。自古传承不断的耕作方式,哪里敌得过科学的生产经营;小私有化的静态的安居生活,在欣欣向荣的商品大潮面前,被搅乱了,被掀翻了。于是,偏僻自闭的小山村就开始变样:尽管孩子们仍然天真无邪地嬉戏,青壮年却已纷纷外出打工,奔向城市,总留下老弱妇女仍沿袭古老的耕作方式,经营残薄的土地;家庭邻里之间,亲属宗族内部,也难免分崩离析,为追逐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相互倾轧,反目成仇。市场的变化正是整个农村大变化的缩影。作者的这篇小说截取了变化中的一个横断面,以一个山村大家庭内部成员彼此关系的消长,亲情的亲疏演绎,来反映整个大时代的急剧演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是虚构情节矛盾,而是如实地直接写她自己家庭发生的变化,因此更加富于真实感和可信度。它又是以一个少女的眼光来判断和抒写这一切,所以,字里行间,描摹抒写,都感到十分细腻、绵密,亲切感人。
小说《星辰闪烁》不具备一般的小说格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惊险刺激或爱恨交织的矛盾斗争情节。它没有这些。它只是“我”(作者本人)在参加娘娘(奶奶)葬礼时的所见所闻所想。然而,这视觉和思想所驰骋的空间却十分宽阔,纵向的历史回叙,横向的亲情梳理、环境描写,都比较丰富、清晰和深入,囊括了辟野山村里这祖孙两人的大部分生活,他们之间爱中有恨,恨中有爱,难以割舍却又骨肉分离的缕缕亲情,被描写得绵绵凄楚,动人心弦。大家庭里的其他大小成员,也都有按其地位、身份所应有的命运安排。他们各自在这个家庭的兴衰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又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衬托出作者与她的奶奶的深厚的感情,是多么纯真,多么质朴,多么感人肺腑。作者为我们奏响了一支大时代下小山村瞬息嬗变的交响乐曲,展现出一幅幅山民在贫困的物质生活与充沛的感情世界间交替挤兑的生动画面。
奶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她是一个典型。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在她身上,不仅背负着千百年来封建的小农经济所固有的个性特征,作为妇女,她还要套上夫权传统的枷锁。她的身世很悲惨,母亲爬进水瓮里淹死了。她虽然出落得“个子高高,胖瘦适中,笑起来像风吹树叶抖抖,称得上是个美人!”但仍然难逃出悲惨的宿命。丈夫早死,大儿子、二儿子也相继夭亡,剩下的三儿子,却生性懦弱,窝窝囊囊,缺少男子气,而且一直未婚。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有几个孙子,其中大儿子家中的小孙女乖巧,这个“我”,是她年满七十岁时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何等的珍贵。这就注定了她们之间会发生许多故事。
如同许多中国农村里的母亲一样,“我”的奶奶不大识字,只能勉强用树枝在沙地上画下自己的名字。她最多走到过县城,自己居住的村庄便是她的一切,她的整个世界。然而,伟大的母性让奶奶深深地爱着孙女“我”以及“我”的哥哥和姐姐。她倾注全身心来抚育三兄妹,为了给孙儿女筹集学费,她叫“我”去爬树剪海红子,而后把海红果晒干,卖几十元钱,凑够开学报名的费用。又一次,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我”,把一毛毛省下来的二十五元钱,秘密地缝在棉衣袖口里,可仍然被奶奶掏了出来,用这钱,帮小哥哥小姐姐交了学费。只因贫穷,在大事面前,“我”年纪最小,就得谦让。
许是奶奶有着几千年命运传承下来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观念,许是她认为男人才能闯世界,干大事;许是她觉得“我”这个孙女儿具有潜在的男人气质,日后会有作为。所以,“我”在小时候一直被她当做男孩子养,剪男孩式头发,穿哥哥穿过的衣服。只有在“我”三岁那年,小村里刮起了打耳洞的风,奶奶才领着“我”和姐姐一道去打了耳洞。这是唯一的一次,她把“我”当做是个真实的女孩。
可是,当她的两个儿子相继死亡,剩下的一个儿子又不太成器,常常受族人和其他人欺侮时,她明白不能单靠儿子辈撑起家业增加收入了,明白从此这个家经济要衰败,日子过得很艰难了。为了不让聪明可爱的三个孙儿女不致于毁掉,减少家庭开支,她痛下决心,要把“我”送到别人家里去,做别人家的干女儿。虽仍旧是自己的人,却可以由别人来供养培养。尽管最后未能送成,但倔强的奶奶终于在艰苦的生活压力下屈服了,差点做了她并不愿做的事。
如果说,作者通过以上这一组组回忆和追述的镜头,已使一位朴实善良、和蔼可亲的山村老农妇、“我”的奶奶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那么,接下来的一些描写与剖析,则让我们进一步窥见到老奶奶深藏内心的伤痛,她的良好愿望和现实处境急剧矛盾时的心理状态。“我”对奶奶给自己无微不至关爱的眷恋以及未能朝夕伺奉她所产生的愧疚,也一一地得以呈现。
奶奶虽身居闭塞的小山村,但也多少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感觉到他们的家人也必须走出去才有发展,才有前途,但谁能够和最应当走出去呢?凭她数十年针对家人和儿孙的了解和观察,凭她把“我”从小当男孩培育积累的经验,她认定“我”是最能担当走出去这一重任的。她对“我”说:“我走了,过不了几年就死了。你要走,走到远天远地里,再也不要回来。”她另一次又对“我”说:“你这样的性格,必须到大城市里面去,住独家独户的公寓,吃自己的饭。”为了这,她甚至对她的儿媳,对她唯一活着的小儿子,都产生一些憎恨,觉得他们自己没出息,还可能连累我,使我出走不了,盼我走出去的心何等迫切!
然而,究其内心,奶奶又是不想让“我”远走的。她希望“我”留在她身边,照顾她。赚些钱,养活小哥哥,她的孙儿。她对“我”说:“你不要走了,伺候我吧!把我伺候到老死,让我天天看着你就行,你不必做什么。”她就是这样忍受着极度矛盾的心理折磨,两种想法的激烈冲突碰撞,度过难挨的一天又一天。
但同样,“我”作为她的孙女儿,她对我有养育之恩,疼我,爱我;她的东西给我吃,她的衣服给我穿,“我”长这么大,耗费了她多少心血精力。“我”理应孝顺,回报她,复侍在她左右,送老归宗。可是,“我”也顽强的追求知识,想知道外面世界的更多东西。“我”特别不愿重复奶奶曾经走过的悲惨的道路,因袭落后的农村的传统陋习:好女不外嫁。用一根无形的“礼教”习俗的绳索,把自己捆绑起来,做一个庄稼汉的附庸,循规蹈矩的媳妇而终老一生。
于是,“我”走了,去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
“我“知道,我走后,奶奶会孤单、寂寞,每日里呆呆的看着太阳升、太阳落,唯有那只肥猫陪伴她,与她对话。当“我”读大学时,曾许诺过一年回去看她一次,可有时还兑现不了。“我”哄骗她,说“我”在外面忙,其实“我”整天并没有多少事,只是喜欢陌生的空间,陌生的城市,享受从甲地到乙地赶车的乐趣。“我”感到“我”对不起奶奶,对她有深深的抱歉。她本想留“我”在她身边,却又放“我”远走。“我”辜负了她的企图,“我”有犯罪感。于是,“我”想补赏她,孝敬她。可是,“我”买什么东西给她,她都不要,还叮咛我要把钱省起来。有一次回家过年,我花三百九十八元给她买了一件睡衣,蓝底红花,配上老太太所喜欢的花纹样式去讨她高兴,可她仍不穿,依旧同往常一样,训斥我浪费钱财。后来,她索性把它当做了被盖使用。
……
作者在小说中精心描绘的这一幕幕现实生活场景,由于是作者自身经历的如实记录,她自己情感的直接表露,因而特别的真切,特别地具有撼人心魄的穿透力。奶奶与孙女之间以及围绕她的人和事之间,爱恨交织,喜怒渗透的复杂关系,被展现的淋漓尽致,是活生生的一幅幅当前形势下城乡巨变的真实图画。在当今社会这种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巨变中,多种人物所处的不同地位,所走的不同道路,所取得的不同命运结局,仿佛都能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纷争中得到印证。难道不是吗?在你的亲友中,可能就有像“我”那样远离家乡,去到城市来打工求学,来寻求发展途径的年轻男女;可能就有像“奶奶”那样孤单寂寞,留守空巢,日夜盼望亲人回来的相聚留守老人。所以,即便这篇作品不是由作者虚构加工写成,仅仅是自身经历的忠实记录,家庭变化的客观写照,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作者家乡的那些人事变换、环境的矛盾冲突、斗争和巨变,无一不是当前农村逐步城镇化表格中正在发生的事件,也可以说,就是这种大变革的形象化的缩影。
我以为,这应该是这篇小说的思想意义所在。
小说《星辰闪烁》在艺术上也是具有特色的。九十高龄的奶奶仙逝了,最疼爱她的孙女长期漂泊在外,为赶得上亲临老人床榻为老人送终,临到下葬了,才匆匆赶回来参加葬礼。面对躺在墓穴里的奶奶,她痛彻心扉,悲怆欲绝,抚今思昔。难忘的往事,都止不住在泪眼模糊中一一呈现:奶奶长长的头发往下掉,“我”捡起来缠在指尖玩,而后在炉火边烧掉,那场景多么幸福。心想,能这样过一辈子该多么好;“我”十八九岁的那几年,为讨奶奶喜欢,就帮她洗脚。她的脚是缠裹过的。洗脚时,她不是嫌水冷就是嫌我洗的慢,我知道她是故意刁难我,却常常为她这种童心式的逗趣而感到欢快;还记得,当“我”和小姐姐穿了耳洞后,奶奶为了装饰我们,从她藏有的古董中找啊找,总算找到了耳环,但仅有一只,还不太亮。奶奶又在等下用砂纸磨,而后让我和小姐姐轮流佩戴,从一个人的左耳到另一个人的右耳,再从另一个热的右耳到一个人的左耳。虽然可怜巴巴,却是永远铭记在心中的最爱。回忆,总是要在生离死别、人天两隔的关键时刻,显得才特别的清晰、具体,就如同发生在昨日,让人涕泪滂沱,肝肠寸断。所以,“我”倾泻出了“我”全部的感情,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地在奶奶的坟茔前悼念。
“我”曾经担心,怕她死掉,怕得要死。只要一想到她会死,会离我而去,我就活不过来,全身冰冷。而今,她终于死掉,埋进土里,彻底地离开“我”了。“我”倒似乎庆幸。因为,再没有这么一个人,“我”需要长久的为她担心了。
“我”知道,下面是新埋下去的棺盖。棺材里面有她。她躺在里面,还是那么面容慈祥,还是会笑,依旧说话的时候会扭动五官。她在叫着我的名字。“我”叫欣欣,她喊“我”星星,叫得如同满天星辰,而她,是月亮,挂在星辰旁边。
她也希望“我”躺下来,躺在她身边,握着她枯瘦干涸的手,希望我们总在一起,我守护着她或者她守护着她,再也没有远离和背叛……
作者就是这样反复念叨着,吟诵着。一遍遍哀嚎,一声声悲啼。如同“长歌当哭”的诗朗诵,恰似西洋乐曲中的咏叹调的直叙胸臆。读到这儿,很难不为之动容,跟作者一道同哀伤,共悲戚。
写作乡土小说时,有些作者会在故事情节的叙说和刻画人物的进程中,展现一些富有地域特征的奇异的文化风采习俗,使我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又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篇小说里写到的“我”穿耳洞的情节,就着实让我们耳目一新。原来,穿耳洞得先用小米粒在耳朵下垂边磨擦,直磨到可以看见透光的背面了,才用针扎孔;而后又像缝衣服一样穿线过去,在两边打结。尤其奇妙的是,每天还得捏着线头转一转,以免线和肉长在了一起。真难想象,传统的乡村妇女的耳洞竟然是这样针扎而成的!又如,作者写道口外常常有人杀了狐狸。因狐狸挺能下崽,一窝八九十来个,他们留几个母的做种,其余公的全都杀掉,然后用狐狸肉充当狗肉,拿到集市上去出售。真难想象,世间除了“挂羊头卖狗肉”的谚语而外,竟还真有“挂狗头卖狐狸肉”这样的事情!最后,还得唠叨一点。这篇小说是作者在墓地前祭奠奶奶的亡灵时,回想过去祖孙之间的亲密关系时,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之情如火山爆发,山洪倾泻,不可收拾。许许多多的述往的人事都骤然凸显出来,因此,在具体描述上就无所谓先后,无所谓轻重,全都随着作者的意识流动,就连意识本身也是跳跃的、断裂的、突击的,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所以,没有什么章节顺序可指,也没有什么宏言大义可供研讨,读起来会有些吃力,会有些磕绊。作为一种写作样式,本无可厚非,但细看起来,如果能把重复的字句做些适当删减,达到既不伤原意又保持清新的效果,或许会更受读者欢迎。
不知作者以为如何?
栏目责编: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