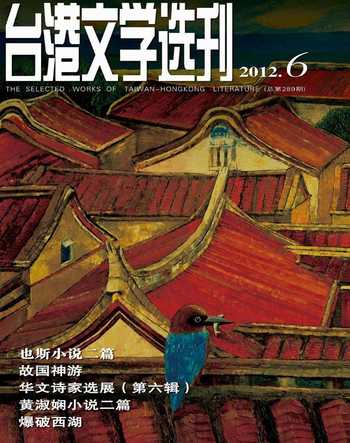站在新的地平线上
2012-04-29杨匡汉
杨匡汉
各位先进,各位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朋友:
此次国际研讨会在福建举行,朋友们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了一个文化福地。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名流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仅就和我们华文文学有关的文化名人,本土的,或客闽的,就有陈季同、严复、林琴南、辜鸿铭、林语堂、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冰心、萧乾、林徽因、庐隐等等,群星灿烂,云烟万态。更为世人瞩目的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出发,妈祖信仰和“船政文化”以此地为源。在当代,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正是以闽粤为基地,为引桥,率先打开窗口,开启“文通”,放眼世界,经过层层拓展、步步深化的长期努力,如今已发展成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一门备受关注的新兴学科。学科建设三十年,学会成立十周年,加上这届研讨会,可谓“三喜临门”。我们衷心感谢国务院侨办多年来的鼎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也要特别感谢东道主——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为本届年会所付出的辛劳与热忱。
本届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学术史视野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我看来,研讨会体现了两个“突出”:
一是突出了学术史的考量。
世界华文文学涵盖了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华人作家及华裔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它反映了炎黄子孙的精神史、心灵史,其文化背景,又是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移民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传统,渗入中华儿女的血液,化育我们的人生,也造就了华文文学的“基因”;而中华文明、中华智慧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与各种不同文化相遇、交汇,又开放出多姿多彩的既有民族性因素又有世界性因素的文学之花。一部华文文学史,也因此而成为华文作家在与异质文化交流、对话过程中,传承中华文化、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这样,从学术史的视野,去对世界华文文学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进行人文性的专题解读,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为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提供新鲜的经验;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以中华文化的丰厚内涵、滋养心灵的特殊功能和生存经验的诗意表述,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谱写着绚丽的篇章。
基于上述共识,这次研讨会,我们在华文文学的学科史问题上找到了一些内在联结点。诸如:这一新兴学科的“三十年”,实际上经历了发生期、拓展期和学科形成期,是一种可持续性的递进;华文文学史的上限,实际上并非以《埃仑诗集》和“五四”新文学为起点,可以往前移动至清末民初,故而有必要做历史逻辑和学术逻辑的修正;四十年代台湾地区的国语运动成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对接的纽带;七十年代留学生的“保钓文学”体现了“五四”启蒙精神;“百年世界华文文学”的积淀为华文文学经典化创造了条件;华文文学多元化的展开,使其复杂性、国别性、差异性的面貌更为清晰,等等。学术史的考量,让我们确认了华文文学发生的必然性和学科形成的合法性。
二是突出了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关注
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年轻的学科而言,“史”的考量也应该以20世纪的学术为基础去进行,不泥于“古”、泥于“昔”,而要和当下人们关注的疑点、难点结合起来。和以前几届华文文学研讨会一样,大家对前沿话题充满了热切关注。
这次年会,又有不少新的话题,如“台湾文学的经典化”、“女性小说欲望书写的利与弊”、“世界性的差异表述”、“两岸四地新诗文体比较”、“如何跨界互动”、“华文文学的精神意向与文化选择借镜”、“文学现场与文学记忆”、“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空间”等等。许多话题,已开始触及世界华文文学价值的谱系问题,分开来看似为“散”,合起来看,则是对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的全方位、多侧面的整体性观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信息。
我们走过了学科建设三十年、学会成立十周年的道路。当我们回首萧瑟行,穿过文学的长廊,都会感念时光的沉重,同时也看到穿越时空的力量。今天,我们业已铺设的路基,将成为走向明天的磐石。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站到了新的地平线上。
站在新的地平线上,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继往”,二是“开来”。
“继往”,就要通过回首、反思,总结一下我们获得了哪些基本的经验?
我认为,集三十年的学术经历、体验与验证,我们可以认知:
(一)中华文学版图得以调整,文学整体格局得以改变。就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长期以来受体制语境的影响,过多强调政治需要、观念规约、命名与价值同一、“主流”大于“边缘”等,学术视野比较狭窄。三十年来,由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介入,使我们得以放眼四海,看到有一个体现“万物统体一太和”的中华哲学、中华文学智慧的“大文学”——世界性的汉语语系文学的实在,其要素为“整体”、“运动”、“多样”、“平衡”。文学观念的调整促成了文学版图的变局,促成了我们对华文文学生态的思考,那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趋异共生,交流对话。
(二)“经验的旅行”的命名。萨义德将后现代理论特征命名为“理论的旅行”。而根据世界华文文学的特征,我们不妨可以命名为“经验的旅行”。其背景是:边界的移动,知识的流转,族群的迁徙,记忆的重组,家园的来去,加上网络的激荡,这一切构成了华人生存经验与文化经验的旅行。“经验的旅行”体现了跨界的特点,即跨地域、跨国界、跨族裔、跨文化、跨学科、跨语言等等。在“经验旅行”的过程中,汉字,让我们往里走,听见内心的声音;山海,让我们往外走,触摸他者的目光。这一“内”一“外”,让我们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坐标,回到作家的自我角色。同时,在“经验的旅行”中,比较诗学也自然地纳入我们视野中,通过视点融合,最终汇入到多元化的、流动性的世界诗学的潮流中。
(三)从“前学科”到“学科建设”。初期的华文文学研究有开创意义,但也存在“复述”、“感想”、“分散”、“时评”等等“前学科”现象。经多年历练,我们现在走上了学科建设之路。“学科建设”的标志是:初步形成了独立的研究对象与学术范畴;初步形成了专事此业或主攻方向的学术骨干、团队;初步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初步打造了专业性的公共学术平台、园地;初步确立了在主流大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占据应有的学科地位。
上述三条基本经验,凝聚了大家多年的心血,也得益于海外华文作家和学者们的智慧,我们十分珍惜,并且应当继续盘点和总结经验。
站在新的地平线上,我们更要做的事是“开来”。
我们仍然走在路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说到“开来”,个人想到的有以下几点,供各位参考:
其一,进一步确立“华文文学共同体”的信念。一盘散沙要不得,内斗内耗要不得。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凡是把许多灵魂团结在一起的,就是神圣的。”这种“共同体”观念对任何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求“根”、求“本”,就不难看到,华人是命运共同体(历史),华文是心灵共同体(文化),华人华文作家又拥有文字的共同体。“共同体”才有文化凝聚力,也是创作的动力源,中华文化、中华智慧为“文学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精神资源。
其二,进一步坚守文学精神。无论何类作品中,真诚是精神世界的核心,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美感是精神世界的翅膀。文学是对真性灵、真精神的守护,故而要抗拒工具理性,抗拒商业炒作,抗拒非法利诱,抗拒“现场快感”。有文学精神的作品是有思想、有温度、有气象、有愿景的。有文学精神的作品,在质疑不合理的世道时,也会质疑自己,拷打灵魂。我们渴念的是赠予读者更多的茉莉花,让它在手掌、在心里留有清香。
其三,进一步拓展新的空间。拓展文学空间,归结起来还是“问题”和“方法”。无论创作或研究,我们遇到的是:有什么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又怎么处理问题?问题意识对我们是太重要了。至于“方法”,是到达彼岸的桥。“方法”不能仅仅看作是单列的技术操作,要和对文本、文体的认知结合起来考虑,对目前流行的实用主义有所超越。多种方法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所谓的“葵花宝典”并不存在。对于华文文学来说,如果能置于众多话语系统(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学、新闻学等等)中去考察,在交叉性、互文性上面做些文章,有可能大大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和想象空间。
总之,站在新的地平线上,我们看到,春天的耕耘带来秋天的收成。我们不会满足已有。让我们一起坚持文学理想,坚持木铎传薪,坚持创辟探索,坚持交流对话,坚持团结合作,共同开拓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天地、新境界,使华文文学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张名片、一个形象代表,用更多更新的精品力作,来回应这个动荡的世纪,回应这个伟大的时代,回应四海之内兄弟姐妹们的期待!
谢谢各位。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修订,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