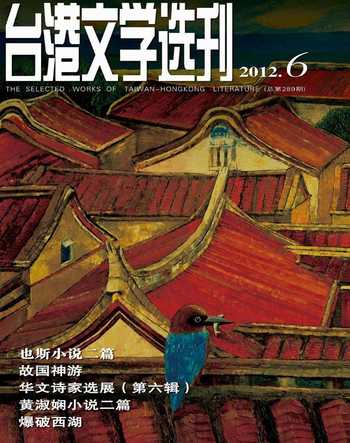蓝色的云鹤
2012-04-29陈慧瑛
陈慧瑛
2012年8月9日,菲岛友人传来云鹤猝然仙逝的噩耗,无比痛惜,特撰挽联—对,和数年前的拙作《蓝色的云鹤》一起,敬呈《台港文学选刊》刊发,以聊寄哀思于万一。
我常常怀念云鹤。
秋夜,偶步东门外,月光如梦,鹤影横塘,我不禁又想起曾经寄足此地将近三年、与我结下不了文缘的著名菲华诗人云鹤。自去年仲秋马尼拉机场一别,萧瑟秋风今又是,而故乡风景依旧,故人天涯远隔,此时此刻,他的小诗《秋潮》又一次飘上我的记忆:
“向南来,秋潮汹涌 /异乡人埋入异乡的风景里…… /一江芦花掩去一江秋水/ 掩去渡江的寒月/让我握住你彼岸的手/兰岩上鹤唳凄然……”
真是说不尽的惆怅,泱泱秋水般地弥漫心间。
真诚的人
认识云鹤,也是在秋季。
1984年底,香港知名诗人、厦门大学同窗张思鉴兄由香江之滨寄给我一篇散文《诗影交辉说云鹤》,从文中得知云鹤不仅是著名的菲华诗人,而且是一位饮誉国际影坛、荣获美国摄影学会硕士(APSA)衔以及国际影艺联盟最高荣衔(HONEFIAP)的摄影家。
次年秋天,为参加厦门特区经济建没,云鹤不远万里渡洋而来,也是由于思鉴兄的介绍。他甫抵厦即到舍下相访。这时候,我才知道,云鹤原名蓝廷骏,出生于海外,原籍却是厦门。他的一口厦门话,说得纯正而流利。
“我来厦门的目的,是设计东渡新区的西堤别墅群。” 云鹤说。
真想不到,这位以诗名著称的菲华文坛骄子,他的第一职业,竟然是建筑设计师——菲律宾远东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我深深佩服云鹤先生的多才多艺。
那一年,云鹤大约四十二三岁,但看上去他的长相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不容忽略的真诚,他的言谈里有一种毫无矫饰的天真,于是,第一次见面,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正直坦诚的君子。
那时候,云鹤既当建筑师,又任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在他驻厦期间,副刊的编务由他的太太、著名菲华作家秋笛小姐代劳。由于云鹤的督促,我偶尔给《世界日报》撰写文艺作品,后来,我担任了《世界日报》驻厦记者,于是,工作的需要,促使彼此有了更多的交往。
旅厦期间,云鹤住在中山公园西门外一幢镶贴着金黄瓷砖的美丽的洋楼,门外是一条花木扶疏的柏油小径。虽然同处一城,但大家工作都忙,相见的机会仍很有限,然而只要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曾经多次盘桓在那一条四季飘香的小路上,谈文学、谈人生、谈生活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从他的叙述中,我对于遥远的菲律宾和菲律宾的文学朋友们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从他的言谈里,我对于这位来自异邦的故乡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常常向我提起中国的晓雪、顾城、流沙河……提起新加坡的郭永秀、香港的张诗剑、王心果、陶然等等一批诗友;他常常谈及厦门大学采贝诗社的青年朋友们;他也常常思念他远在菲岛的妻儿,思念那“在热热的被窝里被妻挤到床下去”的天伦之乐。对于朋友的成果和荣誉,他怀着童稚般的喜悦,对于违法乱纪的社会现象,他有着杞人忧天的痛心疾首,那一份多情和执著,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天性中的纯真。
一年多前,《世界日报》社长陈华岳先生盛情邀请我出访菲律宾。当时,云鹤因工作之需已离厦返岷,然而,为了让我顺利成行,前后半年间,他几乎每隔三五天便从大洋彼岸寄来一信,从出国手续到所有细枝末节,都不厌其烦地叮嘱,并具体加以指导。我想,纵使同胞手足,其关切也莫过如此。因此,当我只身离开祖国,当波音机降落在菲律宾初秋金色的土地上时,我第一眼望见云鹤带着《世界日报》国际版主编侯培水先生、文娱版编辑吴惠华女士前来迎接,那一刻,对于云鹤,我感受到的便不仅仅是温暖的友谊,更多的还是温馨的亲情了。当然,对云鹤具有这种感受的远远不止我一人,凡接触过云鹤的中国作家、学者、诗人,几乎都同样领略过他不遗余力的赤诚。四川的流沙河、广东的潘亚暾、北京的刘再复,都曾经一再地向我诉说过对云鹤的赞许和眷念。
赤诚的诗
云鹤早慧。
他12岁即开始发表诗作。《忧郁的五线谱》是他的处女集——完成这部诗集,他才17岁。接着,他写出了《秋天里的春天》、《盗虹的人》、《蓝尘》三本诗集。后来,他因种种原因封笔十五载——当时,这位已经写出四部诗集的诗人,还不满25岁。到了1985年,他才又推出了脍炙人口的新著《野生植物》。
我从内心里喜欢云鹤的诗,一如我从内心里喜欢中国的李商隐、李清照、郁达夫;匈牙利的裴多菲、英国的拜伦、俄罗斯的普希金、法国的史密士、阿索林的诗一般。
云鹤的诗品如同人品,自有一种不可拒绝的赤诚。感人至深的是他的乡思、乡愁、祖国之恋。不可想象,一个衔环落草于异域的土生子,在40岁以前,从未踏上故土,完全不认识祖国容颜,对于母土的依恋却是那般强烈、那么痴迷!他的名作《野生植物》:
“有叶 /却没有茎/有茎/ 却没有根/有根 /却没有泥土/那是一种野生植物/名字叫/ 华侨”
惜墨如金、运笔如神,没有一句主观的倾诉,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眼,却石破天惊地写出了全世界华侨共同的心声!那一种飘萍野絮凄然欲绝的情怀,读来催人泪下。云鹤催人落泪的诗句还有:
“如果必须写一首诗 /就写乡愁 /且不要忘记/用羊毫大京水 /用墨,研得浓浓的……”
(《乡愁》)
“就这样站着,望归的人 /站成一棵树 /欲拥抱什么似的/向天空摊开千手”
(《乡心》)
极质朴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极深沉的情感,云鹤不愧为大手笔!这仅仅归功于他返朴归真、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是远远不够的,最为关键的还是云鹤胸中那一颗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除了少数数典忘祖的败家子,哪一个海外的中国人,读了云鹤的诗,能不感到乡思如潮,热血欲沸?云鹤在他的《虹音》中写道:
“自风尘中燃起,自海中燃起/自漂泊者骨髓中燃起了爱”
思念是一种诗化的痛苦,它因距离而神圣。这种执著的祖国之恋,融入诗人的血肉灵魂,贯穿于诗人的长行短句。于是,云鹤思念祖国、思念故土的诗篇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一种永不泯灭的灵光。这灵光,如暗夜的灯苗如寒冬的炉火,照耀着、温暖着天下炎黄子孙的情肠。
云鹤曾毕业于菲律宾中正学院,因此,他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学教育特别是古典诗歌的熏陶。在马尼拉,我拜识了云鹤的父亲蓝天民先生,这位书香世家出身、几十年间一直服务于菲华报界的爱国老人古朴而正直。我也拜会过云鹤的爱侣秋笛小姐,这位贤妻良母型的菲华作家,对祖国和对丈夫一样一往情深,她在《我的儿子哭了》一文中,充满骄傲地写道:
“我的儿子哭了,不是因为双亲的责骂而哭,而是因为中国在‘亚青篮赛输了而哭……我有一个土生土长、但却懂得为祖国流泪的儿子!”
中华文化的积累和热爱祖国的家庭氛围,潜移默化地进一步激发了云鹤的赤子情怀。在海外华侨华人诗人群中,像云鹤这样集中地抒写乡恋、祖国之恋的诗人虽不乏其人,但能够像云鹤那样把乡恋、祖国之恋写得这样贴心动情、撼人肺腑的诗人,却是凤毛麟角!
云鹤的诗有一种将“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动人心魂的力量,尤其他的爱情诗,有一份凄哀美,有一种古典韵味,有中西合璧的情调,有哲理的闪光:
“记起昨日 /你的诗是三月的云 /你的三月是我的诗/我自烟雨中醒来/眯着眼看赤绳如此系住你去秋的右足/我在烟雨中醉去/如此在我胸臆间布满棋子/如此围困我,食尽我的感伤” (《拾霞人·集云人》)
这样的诗,不能不使人想起朱淑真的《江城子):
“昨宵结得梦因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辗转衾稠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青春、苦恋、一腔碧血、九曲回肠,读罢令人不饮而醉。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人人曾经阅历的、或朦胧或明朗、或甜蜜或苦涩、或铭心刻骨或迷茫如烟的儿女之情。有时,诗人抒写的是一段岁月之河无法冲淡的永恒的相思:
“江河北去风声北去 /你的名字是不凋的鲜花 /在落月之前/在落月之前 /你是纹在我胸膛 /不凋的茉莉” (《落月》)
有时,诗人缅怀的是一次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偶遇:
“去年的夏很短/当我正在谎言里漂泊 /轻轻地 /汲水的少女踏着青苔的路走来 / 她向我的心/投下了长长的五彩绳/就这样 / 我染上了季节性的忧郁症。”(《一叶》)
有时,诗人歌咏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的偶像;
“只沉默地站着 /在晕眩中,在梦里,我 /怅然看你飚起蓝尘/ 看你的背影悄然逝去…”
(《蓝尘》)
有时,诗人追求的是一种超时空的永生不渝的美好情怀:
“你是轮,我是路,永不能相拥/惟有让时间,把这微小的接触面 /贯连成一道深深的痕”
(《痕》)
不管云鹤诗中爱的对象是确指或是泛指,但情的至诚、诗的隽美,给予读者的便远远不止是诗情的熏陶而更多的是心灵的滋养——在旧梦重温里,令人再一次感受豆蔻年华爱的悲欢!读这样的诗,人不会衰老,心不会麻木,云鹤的爱情诗一如他为人的执著。诗不如人或人不如诗者,在大干世界里比比皆是,而云鹤可以说是诗如其人的标本。
对一部分海外华文诗人的诗作,中国大陆的读者常常有或食古不化或洋味十足的遗憾,云鹤的长处恰恰在于将中西文化融于一炉,形成了天衣无缝的独特风格。如:
“宛如晨钟暮鼓 / 敲碎一山沉寂/你的笑声在我心中刻碑/四月,四月如水……”
(《云渡》)
它使人想起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想起柳永的《雨霖铃》,也想起拜伦的K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然而,那一份凄然的美、孤寂的飘逸;那一份无始无终的执著和真诚,还是属于云鹤,属于睿智而多情的云鹤。
云鹤的诗语言朴素幽默,于一如中国写意山水的淡淡的描摹中蕴含着启迪人生的深刻哲理。诸如:”好几回/试图凌空翻跃……只是/一跃再跃/总翻不出这/生活、亲情、病痛、职责、金钱/构成的五指山”(《猴想》);“是纯钢的构成,亦是/阳柔的组合”(《沙》);“每一次起飞是一次生命的预支”(《飞》):“夜是迟归的赌客/从我杯沿踏过/扇折里是去秋的低叹”(《蓝尘》)……这些诗句,形象,生动,扣人心弦,令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
忠诚的桥
云鹤像一道彩虹—— 一道横亘在中菲两国作家心上的美丽的虹桥。他不仅以他的五部诗集和散发于东南亚各国的文百篇、诗三百篇,向菲华世界,同时也向祖国表达了赤子的坚贞,为中国和菲华社会之间的文化与情感的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更可贵的是自少年时代起,云鹤这位身居异乡异土的飘零的游子,就有意识地为海外华文的昌盛和中菲文学的交融,作了大量的工作。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了推动菲华诗运,不满二十岁的云鹤第一个发起组织研究华文诗歌创作的团体“自由诗社”,接着,他在《华侨周刊》上主编《诗潮》并选编了《诗潮——第一年选》。1985年9月,应台湾“创世纪诗社”之聘,他担任了《创世纪诗刊》编委。1982年,他率先提倡并组织了“新潮文艺社”,这一支劲旅集中了一大批知名的老中青菲华作家,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华文作品,那一种海纳百川一般的阵容和那一颗颗热爱华文文学的赤子心,令我感动不已。
80年代初,云鹤主编《世界日报》文艺副刊,因为他在菲华文坛的声誉,也因为他的一片感人的热忱,他团结了许许多多中国大陆知名的作家、诗人,刊发了他们大量的诗文,从而使《世界日报》文艺版呈现出一派群星灿烂、光辉夺目的景象。无形之中,这家报纸成了中菲作家以文会友、沟通情感的虹桥。
近年来,云鹤经常往来于中菲之间,因此更加积极参与华文文学的研究和探索工作。1985年,经我介绍,他被吸收加入中国散文诗协会;1987年,他前来出席厦门大学“首届华文文学研讨会”;同时,先后应聘担任厦门鹭江出版社“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编委、广州暨南大学、花城出版社《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特约编委,应邀参加香港《文学世界》主持的“作家诗人座谈会”。
为了使华裔作家有表情达意、发表作品的阵地,1987年6月,云鹤倡导并推动创办了菲律宾第一份专门刊载华人诗人及作家作品(以英文、华文创作)的期刊《桥》(TULAY)。1987年7月,云鹤当选“菲律宾作家联盟”(UMPIL)理事——作为华人、华文作家,加入这个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群体并担任理事,云鹤是第一个。这是菲华文学界破天荒的一件大事,难怪喜讯传来,一连数日马尼拉中英文各报以及各界友好纷纷向云鹤道喜。1988年6月,鉴于云鹤文学创作的累累硕果和献身菲华文学、全心全意促进中菲文学交流的业绩,我和刘再复学兄一起,推介云鹤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获批准。能够参加“中国作协”这个国家级的最高文学团体,这样的荣誉,纵使国内作家也不易得到,对于海外华侨作家更是难能可贵。而云鹤跻身于两个国家文学界最高权威机构,这对于他本身固然是辉煌的桂冠、特殊的荣耀,对于菲华文坛,更是巨大的鼓舞、有力的促进。
云鹤是中菲文坛殷勤的青鸟、忠诚的桥,为了华文文学的繁荣,为了跨国艺术交汇,二十多年来,他无私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菲华文学史将永远记载这位才华卓绝的诗人、文学活动家的名字,祖国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位茹苦含辛、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海外儿郎。
蓝色的云鹤
云鹤最喜欢蓝色,恰好他又姓蓝。
云鹤的诗集叫《蓝尘》,云鹤的诗题叫《蓝尘》,云鹤的《短笛》里有:
“九月的气息很蓝,梦很冷”
他的《无题》里有:
“飘泊的云朵们,在蓝色的草席上/绘画薄薄的忧郁”
他的《曲》里有:
“念及蓝色的往事,念及……/我总想摘一瓣早春的桃红/装饰我贫乏的感情”
他的《战士》里有:
“九月的太阳是蓝蓝的/ 我打从蓝色里来”
他的《献》里有:
“在蓝蓝的月光下/ 我素描着爱的轮廓……”
辽阔的天空是蓝色的,浩瀚的大海是蓝色的,炽烈的火苗是蓝色的,广博如云天的胸襟是蓝色的,深沉如海洋的爱情是蓝色的,热烈如火苗的诗行是蓝色的,纯净的友谊是蓝色的,恬静的梦境是蓝色的,真诚的心和真诚的世界一样是蓝色的。
云鹤的诗歌是蓝色的,云鹤的心田是蓝色的。
云鹤是蓝色的。
呵,云鹤!永远地和天空,和大海,和伟大的相国,和忠诚的爱情,和纯洁的友谊,和美丽的心灵在一起!永远地,和蓝色在一起!
呵,蓝色的云鹤——
我从故乡,遥遥地,赠你一弯八月初三蓝蓝的月亮——但愿它是经天的飞舟,载你时时往返于湛蓝湛蓝的大洋两岸!
·责编 杨际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