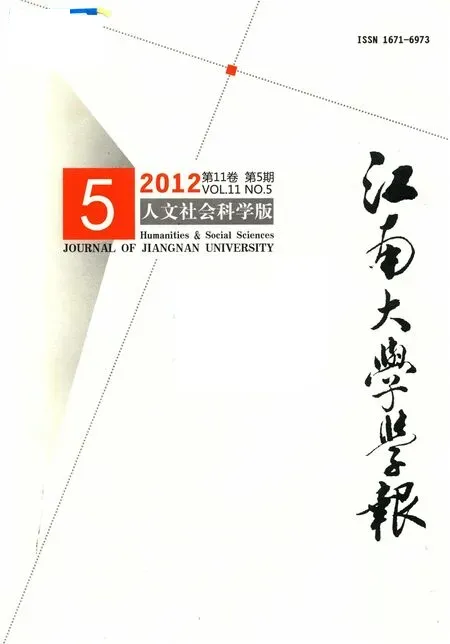父权文学传统描绘下的爱尔兰地图——浅论后殖民主义关照下的爱尔兰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
2012-04-18王斐
王 斐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361002)
一、大英帝国对爱尔兰殖民地图的绘制
制图(cartography)原来指的是地图绘制(OED)的科学或实践。在文艺复兴早期,地图绘制首先成为欧洲商人开辟与东方贸易航运线路必不可少的导航工具。直到16世纪,“科学”地图绘制(scientific cartography)才重新步入正轨。新一代绘制员根据探险家和数学知识的发展绘制了一批地图。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佛兰德斯博学家热拉尔·德·克雷·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绘制的地图。1569年,墨卡托以“墨卡托投影法”为基础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然而这仅仅是墨卡托掀起的地图绘制革命的开始。在他看来,地理不仅是确定城市和河流的位置,它还是掌握世界政治时局的途径。此后墨卡托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地图上。随着17、18八世纪欧洲航海家探险与早期殖民活动的开展,“科学”制图技术日益成熟,并为19世纪欧洲殖民强国的海外扩张铺平了道路。到了19世纪,地图的绘制(mapping)更体现了殖民主义扩张下的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在帝国主义时代,地图的绘制成为“企业牟利的推手以及主导权争夺的棋子。”[1]9换言之,“地图不仅反映了世界,但在塑造世界版图方面也起着根本性的作用。[2]
就制图的殖民话语策略,卡尔特尔提出 “空间性历史”(spatial history)概念[3]173,探讨由话语操纵绘制而成的空间地图和书写、文化再现的关系。他以“未完成的地图”(incomplete maps)来比喻空间和描述空间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仍不断被书写并覆盖在地图的想象性空间之上,因此这些地图是暂时性的。”[3]174这说明殖民的垦拓、占有空间掌握了语言行动决定空间特质的权力。换言之,没有绝对先存的单一空间,只有透过想象、权力支配、社会网络投射出的话语地图。他的论点诠释了由话语绘制而成想象的地图在语言表达权、文化再现、族裔历史、性属意识和历史脉络之间起着微妙的牵引关系。
因此,对早期的殖民拓展而言,“靠岸是一种行动,开垦空地是一种行动,但只有在那时,历史才开始发生”[3]173。殖民者对发现的异域在地图上命名并且标记边界线,实际上利用绘图机制将他们篡夺原本属于“他者”的土地的现实合理化的操作。换言之,原来用于描述地理状况的地图,在殖民主义政策的操纵下,地图即为命名,成为带有限制性、强制性和概念性的殖民话语地图。而此意识形态的地图绘制,在殖民主义的操纵下,产生修辞策略来蚕食鲸吞被殖民者的领土。葛莱姆·哈根(Graham Huggan)在他的《去殖民地图: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制图关系》一书中指出,地图绘制其实是殖民主义的修辞策略,将空间“复制改写”、“圈地”和“阶级化”,而重新打造的地图空间,呈现西方霸权版本的虚假的现实世界。[1]115
由此可见,绘图机制在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行为中扮演核心角色,因为制作地图是建构在知识与权力上,呈现绘图者利用霸权思想扩张、侵略领土进而在意识形态上剥夺原住民身份的野心。英国殖民绘制地图的意识形态,利用二元对立的修辞,刻意划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差异,造成被殖民者不仅是在实质上丧失了爱尔兰土地,而且也同时沉沦于语言、历史和文学传统上身份的迷失。地理的重新命名,事实上是通过掠夺、划定和占领语言空间的殖民过程,逐步建构西方霸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关系:中央/边缘,内部/外部,优/劣,主体/客体,自我/其他,理性/神秘。
爱尔兰著名诗人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在《位置感》(The Sense of Place)中以康诺特地区(Connacht)该地名为例,指出“地域感总是和身份观紧密相关的——在地名中往往包含着历史和传统,因此可以在地理空间的命名中找到自身的认同。”[4]该地名源自前基督时期爱尔兰神话中的国王康恩(Conn of the Hundred Battles)及其康诺塔 王 朝 (Connachta dynasty)。 康 诺 特 (Connacht)与其说是个地理名词,不如说是凯尔特爱尔兰的投射。但随着英国殖民的扩展,该地名被盎格鲁化为康努特(Connaught)。在1874年,维多利女王甚至将她三子加冕为康努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命名再次强化了大英帝国对爱尔兰控制的合法性。简言之,地名体现了双重暧昧的身份认同问题,除了反映在语言层面上,也将语言所呈现的矛盾冲击的身份认同结合上了地理上的地方名词,所被否认的凯尔特地名恰恰是受到压制和排挤的爱尔兰身份的隐喻;而所附加的盎格鲁化地名则是代表了殖民强权下的加诸于爱尔兰人的英国身份。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导致了大量爱尔兰人口的死亡与流亡海外,至1851年,爱尔兰语面临严重的衰退,已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讲爱尔兰语。[5]78语言通常代表个人的国籍身份,因此一旦丧失该国的语言,也代表失去了国家身份的认同,爱尔兰语的日趋式微标志了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在大英帝国绘制的地图中被排斥与湮灭。
二、爱尔兰民族主义与父权文学传统绘制的爱尔兰地图
与此同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对殖民地图的重新绘制和空间的重新命名则成为反抗来自英国的殖民的另一种话语策略。后殖民主义学者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们》中谈及了民族主义的觉醒,他指出,殖民地的本土居民畏惧自己被殖民者的文化彻底同化而产生某种焦虑并进而采取必要反抗。[6]176爱尔兰人在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中,逐渐出现了对“爱尔兰性的显著标志”的关注,首当其冲的便是“与宗主国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即凯尔特文化和盖尔语。[7]为了解决爱尔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医治民族心灵的创伤,一些有民族责任感的爱尔兰思想家和作家渴望从文学中找到新出路。爱尔兰民族运动领导人奥利里(John O’leary,1830-1907)曾经说过:“没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可以脱离他的民族而存在。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伟大的文学,也就无法确定它的特性”。[5]79为了摆脱英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束缚,爱尔兰作家就必须为发展爱尔兰独特的民族想象力创造条件。值得关注的是在20世纪初,爱尔兰文学界掀起了一场意图撕毁由英国殖民主义绘制而成的地图,试图重新绘制“去英国化”的爱尔兰版图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
正如霍米·巴巴所言:“记忆绝不是静态的内省或回溯行为,它是一个痛苦的组合或再次成为成员的过程,是把被肢解的过去组合起来以便理解今天的创伤。”[8]在这场基本以爱尔兰男性作家(除了格雷戈里夫人)为主要倡导者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爱尔兰作家们试图以曾经辉煌过的凯尔特文化的精华建构不同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本土文学,从而解构英国殖民者绘制的版图。在此,借用法农就殖民地人民以其璀璨的过去来对抗殖民者的文化霸权的策略对他们的尝试做出阐述,“因为他们(原住民)已经意识到他们已经面临生命的危险,进而力图重建与能够展现他们生命之源的古老过去的关联”[6]169。霍尔(Stuart Hall)也曾经指出,“由于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就像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总是‘在断裂之后’,这个过去不再是简单、事实的‘过去’。过去总是透过记忆、幻想、叙事与神话来建构的”。[9]因而对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作家而言,“美丽而辉煌的”过去似乎具有疗伤止痛、重建自尊的功能。处于“他者”地位的爱尔兰人在重新经历富于民族色彩的集体记忆之后,终于能够排除文化上的自卑,坦然抗拒法农(Frantz Fanon)所说的来自强势种族的“文化压制”(cultural imposition)。因此带有浓郁的爱尔兰凯尔特文化色彩的传说、素材等成为作家重要的话语选择方式。这种独特魅力的话语,包含了文化传统、性别、记忆和认同,从而构成某种相当牢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定位感。如叶芝主张回到古老基督教的爱尔兰,回到古代勇士传奇,寻找像库霍伦(Cuchulain)这样的英雄人物;奥格雷迪(Standish O’Grady 1846-1928)在他撰写的《爱尔兰历史:英雄时期》(1878-1880)把凯尔特和英爱传统结合起来,写就了一部爱尔兰英雄祖辈英勇斗争的历史,塑造了一系列古老的凯尔特文明和前基督教文明时期的厄尔斯特英雄人物。
在寻求爱尔兰性(Irishness)并重构爱尔兰身份的尝试中,爱尔兰民族主义(Irish Nationalism)也逐渐形成,后者在爱尔兰版图的重新绘制(remapping Ireland)以及摆脱大英帝国殖民宰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伊格尔顿曾经这样评价:“民族主义将爱尔兰(作为独立的国家)绘上了世界地图”[10],然而正如在西方历史长河中,几乎所有的作品多是男性建构的雄性史诗——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支配,实现精巧的“内部殖民”,不择手段地确保女性的依赖和驯服。因此,爱尔兰民族主义忽视爱尔兰女性在爱尔兰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贡献,只有少数参与妇女参政权运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The Irish Literary Revival)和抵制殖民的独立运动。在当时已被男性认可的知名女性,才有机会出现在历史文献和学术讨论中。女性作家也长期笼罩在同时代知名男性作家,如叶慈(W.B.Yeats)、乔 伊 斯 (James Joyce)、辛 格 (J.M.Synge)、欧凯西(Sean O’Casey)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阴影下而被淡忘。因此对爱尔兰女性作家而言,爱尔兰文学不仅是一张地图,被铭刻上英国殖民主义,并且也被划刻上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的殖民行为。就像英国殖民主义,爱尔兰文学传统,甚至具体以爱尔兰诗的传统为例,本身就是一个加诸于爱尔兰女性诗人的意识形态霸权系统,迫害并排挤女性诗人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换言之,加诸于爱尔兰女性诗人身上的双重殖民,是一种隐喻层面上制造地图的行为,因为英国的侵占爱尔兰国土来扩充地图的殖民行为,和爱尔兰文学父权传统的霸权殖民女性地位,都是不仅实质上占领一块领土,也在意识形态上僭夺身份。
事实上,爱尔兰的文学历史传统,不论自前殖民时代的凯尔特(Celtic)民族的游唱诗人,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爱国诗人,文艺复兴诗人,甚至到后殖民时代的诗人,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地位和价值,已经绘制了一幅排除女性诗人作家的文学殖民版图,他们将女性诗人的边缘化、否认和驱逐,造成女性身份认同的错置、粉碎和模糊。最经典代表爱尔兰文学的父权制度系统的作品就是在席门思迪恩(Seamus Dean)所编撰的《田野研究爱尔兰文学作品选集》(The Field Day of Anthology)。在这本文学历史评介中,清一色全都是男性作家作品,却无任何女性作家作品。换言之,女性诗人在爱尔兰文学历史地位遭到否定与轻蔑,其实就是男性诗人对女性诗人殖民的制图科学(cartography),和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扩张版图没有差异,都是建构在狭隘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上的修辞。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反映在爱尔兰的文学传统中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即女性”(nation as woman)的文化想象。“国族即女性”的意识形态不仅扼杀现实生活中女性的选择和抱负,也同时进一步加深父权社会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爱尔兰女性既然是国族的象征,她们就如同爱尔兰的疆域和土地需要时时被男性看管与保护。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的视角来看,爱尔兰男性民族主义作家将女性国家化、理想化,以及去人性化的修辞策略,皆是属于绘制殖民地图的手段。在这种爱尔兰民族主义修辞话语中,将女性当成爱尔兰民族的象征,使得现实生活中的爱尔兰女性不再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领土和民族的代名词。讽刺的是,女性看似被拔擢到崇高的理想层次,然而这种理想化却深深地宰制现实生活中女性的选择、权利和欲望。
在爱尔兰传说故事中,这个命运多舛的民族经常是由一个可怜的老妇人来象征的。如1916年复活节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在其诗作《我是爱尔兰》(Miss Eire<I Am Ireland>)中的诉说者为一位年迈老妇,她将自己比拟为爱尔兰,无尽歌颂了盖尔传统的无尽辉煌,鞭挞了英国殖民者的残暴血腥,但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却抹灭了女性人性化的一面,忽略了爱尔兰女性的现实处境,她们仅仅是男性诗人借以凭吊爱尔兰亡国之殇的冰冷客体。叶芝认为真正的爱尔兰民族精神及其文学艺术,应该充满阳刚之气:“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方法,必须经常提醒的一点是:艺术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它的造型还是声音,都应该是男子气(masculine)和智慧的。”[11]他所创作的《胡里痕的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的戏剧便反映了他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在故事中,爱尔兰化身的丑老太婆凯瑟琳将灵魂卖给了魔鬼,好让她的同胞免于饥荒,最后上了天堂。便“成功地”引发了无数爱尔兰青年的爱国热情,所有的男子刹那间都具备了库霍伦的武士气概,决心为象征爱尔兰的“凯瑟琳”牺牲,使她能从丑老太婆重生为年轻貌美的女子。在此戏剧中,“国族即女性”(nation as woman)即复制了爱尔兰民族主义中对于疆域和民族阴性化(feminization)的想象。此种阴性化的文化想象虽鼓舞无数青年上战场奋斗,却对现实生活中的爱尔兰女性造成莫大的牵制。例如,爱尔兰女性在那场1847年的爱尔兰大饥荒的真实遭遇——许多女性饿死在街道,或者遭受丧子之痛,却在男性民族爱国诗人的笔下被抹煞。
此外,柔弱无力甚至遭受蹂躏的少女也是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投射下的,饱受英国凌辱的爱尔兰的隐喻。在父权主义的内部殖民中,男性对女性驯服与支配造成女性成为性压迫的牺牲品。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所以,民族问题也可以用“性”加以表现。在后殖民语境下,“暴力”一词作为一种隐喻的修辞手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之中,来表现被压迫尤其是被父权或帝国权力压迫的主题。”[12]叶芝的代表作《丽达与天鹅》,他以性与暴力来隐喻爱尔兰殖民劫难的历史,再现殖民与被殖民的权力纠葛。诗歌中,化为天鹅的宙斯象征着残暴的英国殖民者,对柔弱少女丽达的强暴隐喻了英国殖民者对纯洁富饶的爱尔兰的侵略和残酷的剥削。诗歌最后一节“当如此被捕捉,如此听任空中兽性的血液的征服,在那一意孤行的鸟喙将她放下之前,她是否借用他的力量得到他的知识?”[13]同时也揭示了福柯所指出的权利话语系和知识的共谋关系——父权制控制知识的生产,女性仅仅是被审视的对象,她们的认知、体验由男性凝视者所决定。而她们认知的客观性却是被质疑的。换言之,在父权文学传统重新绘制的爱尔兰地图中,爱尔兰女性的真实体验是被掩盖与虚化的,处于被动、失语的状态。
值得关注的是,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影响下的诗歌创作也倾向将爱尔兰女性被物化为无生命的国家象征物体。这种“模拟”女性所塑造的国家象征是一种假象,缺乏和真实意象的相关性,却常被操作为事实,成为架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修辞手段。事实上,这种话语策略和英国操纵殖民修辞手段如出一辙——将爱尔兰呈现为边缘化且去人性化的国家。在爱尔兰民族诗中,女性意象常被理想化为不朽的女神来象征永恒的爱尔兰国家。例如,爱尔兰的拉丁名Hibernia源自爱尔兰女神海博妮娅(Hibernia)。在民族诗歌创作中,被理想化为诗人灵感的缪斯女神海博妮娅逐步成为民族男性诗人集体意识反射而形成的镜像。另外,女神海博妮娅所弹奏的竖琴,也成为民族诗中常引用的一个国家象征符号;在此,女神和竖琴意象的结合使女性被物化的修辞得以进一步加强。
赛义德认为:“处在边缘地带的我们的家园的空间被外来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占用了,因此必须找出、划出、创造或发现第三个自然,不是远古的、史前的,而是产生于当前被剥夺的一切之中。因此就产生了一些关于地理的作品。”[14]从地理环境来看,爱尔兰西部典型的地理特色便是沼泽。Bog(沼泽)更是少数几个进人英语词汇的爱尔兰词语,沼泽地本身所具有的保存历史遗迹的功用对于爱尔兰男性诗人而言,沼泽里蕴涵着爱尔兰的历史。因此沼泽地也成为爱尔兰男诗人创作所青睐的意象并成为父权文学传统将女性物化的修辞手段之一。西门思·希尼(Seamus Heaney)就曾以1781年在贝尔法斯特附近发现的沼泽地女尸为题材,写就《沼泽女王》(Bog Queen),通过沼泽女王的叙述隐喻了久经压抑的爱尔兰的民族意识犹如沉睡地底但千年不腐的沼泽女王一样终将在某天苏醒,回归人间。[15]事实上,沼泽女尸的意象实则把女性物化成无生命的符号或图腾;这种修辞策略犹如将女性的身体视为一块被侵占的领土,女性被随意的扭曲为民族精神不朽的象征符号,而真实的女性体验却是被掩盖的,沦为被动且被刻板化的物体。
对此,爱尔兰当代著名女诗人伊凡柏兰(Eavan Boland)做出了下列的评述,她认为诗应该遵守艺术伦理,也就是诗的想象力要能够反映意象的真实性,而非是通过制造幻象来获取既得利益或权力。然而,在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中,爱尔兰民族男性诗人以诗歌绘制的爱尔兰的版图,是将女性变为指涉符号(signifiers),以交换为被指涉对象 (signified),即爱尔兰国家象征。在此交换过程,真相已失去或是被扭曲,女性意象被操纵为交易的媒介或商品。[16]
三、结语
在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文化策略中,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能够逐步形成、展演、并穿透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的面向,构成独有的知识体系,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政治和文化霸权,解构英国殖民主义的殖民版图,绘制出新的爱尔兰民族文化地图。然而,在男性作家追求的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们再现复制的爱尔兰女性意象的多重版本与真实的女性内在特质和历史价值是大相径庭的,是对爱尔兰女性的过去历史的否认、抹杀和扭曲。正如琼斯所言“在爱尔兰,爱尔兰性被深刻地性别化了。”[17]随着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自我意识觉醒,争取自己的话语权,重现被掩盖抹杀的真实的“她”历史(Herstory)。如女作家奥布莱恩(Edna O’Brien 1930-)开风气之所先,着手整理爱尔兰女性写作经验,质疑被男性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爱尔兰性(Irishness),与白人男性观点所构成的西方文学典律相抗衡,写就《乡村女孩三部曲》(The Country Girls),检视女性认同的转机与危机;短篇小说家茱莉亚·奥菲朗(Julia O’Faolain 1932-)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小说《墙壁中的女人》探讨在双重殖民的情况下,爱尔兰女性的社会角色、权利和信仰以及身份认同的困境,其2006年的小说《暮色》(The Light of Evening)以母女关系为主线描写爱尔兰女性的爱情、家庭生活以及内心世界。女诗人伊凡·柏兰 (Eavan Boland,1944-)以爱尔兰女性在爱尔兰文学中的地位为主题,努力为女性赢得话语权。诺亚娜·尼·多姆奈尔(Nuala NíDhomhnaill 1952-)作为唯一一位通过盖尔语传达女权信息的诗人,以其 “女性的经历”的诗歌主题,对抗男性诗歌中“柏拉图式的”话语。女性作家将借由她们创作的作品,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在爱尔兰文学历史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后殖民语境中,爱尔兰话语版图的疆界不是僵化停滞的,事实上,爱尔兰女性的真实身份应该成为反映爱尔兰真实民族身份认同话语的“爱尔兰性”(Irishness)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而这也为研究后殖民语境下的爱尔兰身份认同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1]Graham Huggan.Territorial Disputes:Maps and Mapping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anadian and Australian Fiction.[M].Buffal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
[2]Nicholas Dunlop.Re-inscribing the Map:Cartographic Discourse in the Fiction of Peter Carey and David Malouf[M].Birmingham: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ress,2001:15.
[3]Carter P,Malouf D.Spatial History.[J]Textual Practice,1989(Volume 3,Issue 2):173-183.
[4]King P R.I Step Through Origins.Modern Critical Views:Seamus Heaney.Ed.Harold Blood.[M]New York:Chelsea House,1986:132
[5]陈恕.爱尔兰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78
[6]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7]Collins M E.History in the Making:Ireland 1868-1966.[M].Dublin:Education Company of Ireland,1993:170.
[8]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7.
[9]Stuart Hall.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Culture,Media and Identities Series)[M].UK.Sage Publications & Open U-niversity,1997:139.
[10]Terry Eagleton.The English Novel:An Introduction[M].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04:291.
[11]Yeats.The Irish Dramatic Movement,Plays And Controversies.[M]London:Macmillan.1927:127.
[12]董红缨,冯丽.从后殖民角度透视诗人叶芝民族文化身份——以叶芝诗歌《丽达与天鹅》为例分析.[J]安徽文学,2009(12):304
[13]叶芝.苇间风 [M].艾梅译,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144.
[14]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317.
[15]Seamus Heaney.Selected Poems:1966-1987 [M].New York:The Noonday Press,1994:84.
[16]Boland,Eavan.Object Lessons:The Life of the Woman and the Poet in Our Times[M].New York:Nortorn.1995:100-103.
[17]Jones,John Paul,et al.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Difference, Methodology,Representation.[M].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1997: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