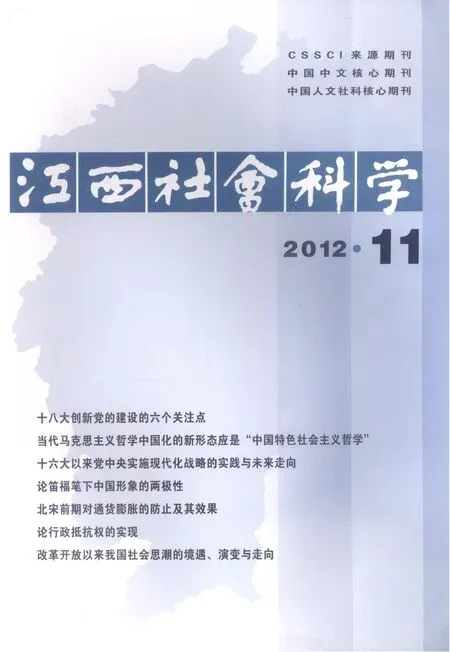传统社会家庭基础性地位的现代启示
2012-04-18顾文斌帅学农
■顾文斌 帅学农
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或共同经济为纽带结合成的亲属团体——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础组织,因担负着性爱、繁衍、经济、教育、赡养等职能而为历代社会统治者所重视。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成形于西周时期,经历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已经发展到完备形态”[1](P300)。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将儒家文化融入婚姻家庭制度,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文化,产生了以家为出发点的忠孝价值观念,并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家国一体的二元社会结构。家是把握中国伦理社会中国家政治格局和社会基层治理的枢纽,更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切入点,也是我们反思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的基点。
一、家庭利益:联姻的着眼点
古人的婚姻缔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必备条件。利益考量是家庭联姻的着眼点,也是父母以严肃态度应对缔结婚姻的内在动力。
为了在乡土社会中扩大家族势力、提高家庭地位,缔结婚姻首先考虑的便是政治利益。始于西周时期以家族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赋予了婚姻政治联姻功能。婚姻的“合二姓之好”功能将两个家族的利益链接起来,“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2](P58)。通过联姻谋取家庭在本地区政治地位的提升,成为皇亲国戚是保障家族利益的最佳途径,也是婚姻缔结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为此不惜子女进宫为妃为妾。而古人“同姓不婚”的规则既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忧虑和“防止血缘结合发生”[3](P79)的考量,更多的则是基于扩大政治联姻范围的考虑。为了抑制婚姻政治联姻的功能,以免危害皇权和地方稳定,保证行政廉洁,历朝法律皆学习《唐律疏议·户婚律》的规定,明确禁止地方官员与部曲通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4](P162)。
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男女双方家庭考虑的家庭内部利益侧重点略有不同。在男方家长看来,“上以承宗庙,下以继后嗣”为考虑首要,婚姻的缔结必须保证家庭兴旺,故而在经过表达求婚意思的“纳采”而通过“问名”程序之后,男方家长必须到自己的宗庙中就双方子女的生辰八字是否相符卜问凶吉,如果占卜结果不尽如人意,则缔结婚姻的程序就此结束而不再进行;如果属于吉兆,意味着这桩婚姻得到祖先的认同且有利于家庭兴旺,则男方家长启动表达正式订婚意思的“纳征”程序。作为被动方的女方家长,考虑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利益,即男方的彩礼能否补偿因女儿出嫁给家庭造成的损失。因为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下,妇女也是劳动力之一,当女子出嫁到男家后,女家即缺少了一个劳动力。[5](P179)如果男方提供的彩礼丰厚到足以弥补家庭损失,则女方家长一般会同意缔结婚姻,否则就可能拒绝接受男方作为订婚请求的“纳征”。
鉴于婚姻关系男女双方家庭的根本利益,各自家庭均采取了严肃而谨慎的态度。双方家长须严格遵循“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左传·僖公十七年》)的传统和“六礼”程序,他们不仅借助媒妁穿插其中,即借助媒妁调查对方家庭及其子女的各方面情况,又通过媒妁就各个阶段相关事宜进行反复磋商,寻求利益平衡并保持双方家庭乃至家族的和谐,而此后的拜堂、奉茶与庙觐程序更是将婚姻的严肃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婚姻自由已经在逐渐取代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古人婚姻缔结程序中折射出的婚姻严肃态度对今日婚姻不乏启迪。
当今社会的婚姻家庭不仅承担着抚育子女、照顾老人的家庭义务,而且关系着以婚姻家庭关系稳定为前提的社会稳定,需要我们继续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婚姻问题。但是现代婚姻,当事人意志已经取代家庭利益成为缔结婚姻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个人本位的意思自治与婚姻自由原则赋予当事人自由决定婚姻的权利,感情的融洽程度成为婚姻是否缔结的关键因素。“从一而终”观念的弱化与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导致“闪婚”与“闪离”现象不断,而婚姻道德观念的庸俗化、结婚程序的简单化与婚姻关系稳定措施的空缺严重破坏着婚姻的严肃性。现实中非婚同居现象的大量存在,“虽然同居的规制不会冲击结婚登记制度”[6](P73),但连续九年高增长的离婚率,提醒我们不能因追求结婚与离婚的便捷性而忽视婚姻的严肃问题,然而国内外没有可资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既不能采取学习西方借助宗教维护婚姻关系的经验,也不能采纳印度高价婚姻的做法,更不能回到“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国内立法不可能如《晋书·刑法志》般明确规定“崇嫁娶之要,以下聘为正;不治私约,峻礼教之防”的严格婚姻缔结程序,唯有探索适合时代需要的灵活而又不失严肃性的婚姻缔结与终止制度。而学界与立法界或许应该纠正过度追求婚姻自由的思路而应当采取自由与约束并举原则,从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来保持看似个人权利而实质关系社会稳定的婚姻关系的严肃性,以增加世人心目中的婚姻神圣性。唯有构建严肃而现代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及完善稳定的婚姻关系法律规则,才能改变目前青年一代在婚姻问题上的随意态度,确保现代婚姻既有自由性又有严肃性,进而为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存在的单亲家庭子女犯罪问题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二、同居共财:基本的家庭财产所有形态
古代家庭,呈同居共财状态,家庭内的财产属于家庭成员共有,但这种共财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共同共有(日本学者中田薰《唐宋时代的家族共产制》一文,将同居共财列为唐宋时代家族生活的常态,并将之称为中国的“家族公产制”)。家庭中,辈分最高的男性尊亲属担任家长,为一家之主,集父权与夫权于一身。家长为了家庭利益对外开展民事活动,有权管理、支配、处分家庭财产,收益则属于家庭,责任也以家庭财产承担。与此同时,家庭的其他人员在父权下没有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妻子的财产归丈夫家庭所有和支配,其以嫁妆和婚后劳动换取了享受家庭财产及其增殖利益的权利,“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为了增加家庭财产,家长甚至不惜在子女婚嫁过程中索取彩礼,计较嫁妆。在家长存续的情况下,非经家长允许,家庭成员不能拥有私人财产,无权擅自处分家庭财产,子女更无权要求“别籍异财”,否则触犯不孝之罪,常赦而不原。家庭财产从更大范围角度来说应属于家族财产,故家庭出卖不动产,“应先问亲属,后问四邻”,其亲属享有优先购买权。在这种家庭财产共有制度下,家庭财产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整个家庭,非经家长允许,任何人的离开都不能改变家庭共有状态,即使妻子因丈夫去世而改嫁也不能带走家庭财产,“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7](P179),子女经家长允许单独立户,但家庭的财产分割由家长单方决定。在家长去世时,家庭财产在分割之前依旧得以完整保全,因继承而取得家长地位的儿子因此取得家庭财产的主导权,“父债子还”便为合理的法律选择。
建立于灾害频繁自然经济时代的家,依靠内敛于“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兄弟一体”[8](P121)的共同意识,借助这种家庭共财制得以生存和延续。这种财产制度集中了家庭所有力量,既为家族的延续和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也为家庭抵御自然灾害侵害提供了稳定的物质条件,并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是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家庭在特定历史时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具有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其对于当下的家庭财产制度依旧具有启发。
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地位平等,夫妻共有为法定的家庭财产制,夫妻双方享有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家庭财产的权利,而不论其贡献大小。这种延续了历史的家庭财产制度而保持了古人的家庭共有形式并赋予了男女权利平等的现代内容,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稳定了现代家庭关系。但是最近公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关于不动产所有权的权属规定却在侵蚀着中国这一传统的家庭财产制度。依据该法解释(三)第10条的规定,意味着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且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不动产,其所有权属于首付方,另一方只享有对投资部分及其增值部分的相应债权,其本质上就意味着法律在夫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就已经强制分割了其家庭财产,从实质上违背了传统家庭财产制;特别是今日中国,广大农村依旧奉行男方准备婚房、女子准备嫁妆的习惯,如此规定则意味着女子的嫁妆婚后属于家庭共有而男子的房屋所有权属于个人,这一规定既有违现代的男女平等原则,也有悖中国传统法律家庭共财的精神,大有男尊女卑的历史痕迹,古人“有所取无所归,不去”规则所杜绝的女子离婚流落街头的悲剧可能在新的时代发生。至于该法解释 (三)第12条的规定更是剥夺了婚姻一方当事人的投资收益权,与上条犯了同样的错误。究其原因,在于立法者没有批判地继承传统婚姻制度的合理内核,犯了具有浓厚的审判实用主义和立法城市样板主义的错误。或许被废止的1993年1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关于婚前财产一定年限后属于夫妻共有的规定不仅有利于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能体现传统家庭共财传统的精神。
三、实质平等:家庭权利义务分配模式
中国式的非规范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治理以家为基础,家庭既是维护皇权的社会基础单位,又是享受国家所给予的权利、承担国家所赋予的义务名义上的主体。家长通过对国家承担纳税义务、亲属犯罪的连坐义务以及犯罪行为的举报义务而享有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权、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对子女的惩戒权及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管理权。即封建国家以家庭为公私权力的配置单位,家长集国家义务与家庭支配权于一身,属于权利与义务的综合。而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对家庭没有支配权,没有完整的的人格权,妇女依附于男子,并处于家长权的监护之下[9](P34),同时个人的刑事责任一般也由其家长承担,除特殊情况下,妇女个人无需承担对国家的“公法”义务(《明律例一二四·断狱·妇人犯罪》与《清律例三七·刑律·断狱下》。根据明清的法律,妇女犯罪除犯奸罪及死罪才收监,其余杂犯无论轻重都不收监,而责斥本夫收管)。[10](P123)妇女处于家内无民事权利、家外亦无国家义务的地位;如果纯粹站在夫妻双方民事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分析,丈夫只享有民事权利而无民事义务,妻子只承担民事义务而无民事权利,即男女民事权利的不平等。但是,如果考虑国家义务因素,则男女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属于民事权利的男女不平等而公私法综合权利义务实质上的男女平等。如果妇女履行了家庭相夫教子、侍奉老人并守孝三年,则享有了“三不去”(《大戴礼·本命》:“妇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的权利,虽然这种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夫妻安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礼义法理皆如是也”[11](P1023),却实现了妇女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了保证这种维持社会和谐与家庭稳定的权利义务分配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将严重违反家礼的行为纳入“重罪十条”,隋朝将之归入“十恶”并规定为“恶逆”、“不道”、“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常赦不原。这种以家庭和谐为目的的权利义务配置方式,促使了男耕女织、男主外而女主内的家庭治理模式的形成,满足了自然经济时代家庭生产的需要,促进了中国几千年乡土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于现代的权利义务分配同样富有启迪。
现代法律改变了以家庭为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主体的立法模式,而是将所有社会成员直接置于法律调整之下,在公法领域夫妻享有同样的诸如劳动、受教育、选举和被选举等宪法权利,承担同样的劳动、受教育、纳税、计划生育、负兵役等宪法义务,并独立承担个人的刑事责任;而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享有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相互之间拥有家事代理权和遗产继承权,享有同等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同时夫妻双方也必须承担同等的互相扶养、相互忠实、抚育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家庭义务,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男女平等原则要求。但是,在现实的婚姻家庭中,妇女除了必须履行男女同等的国家义务和家庭义务之外,还需承担着男子无法取代的生育子女义务以及更多的家务劳动;在现实的就业市场中,妇女较男子而言通常也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即法律上的平等并没有必然导致事实上的平等,男子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依旧处于优势地位,夫妻之间依旧存在事实的男女不平等。为了平衡男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救济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虽然我国《婚姻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并在该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但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并没有规定帮助的具体计算标准,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关于离婚不动产分配的规则更是丝毫没有考虑现实中妇女弱势地位的现状,将感情结合的婚姻演变成典型的财产结合的合伙,加剧了家庭妇女的婚姻危机感。现实中“男人有钱就变坏”的丑陋现象根源或许就在于我们用法律上男女平等的口号掩盖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实以及用男女平等的口号替代了具体的妇女保护法律措施。我们应当借鉴传统社会综合考虑权利义务配置的立法模式,突破部门法的局限,综合考虑妇女的公法与私法权利义务以及社会现实等因素,结合妇女对家庭的付出及其独特的生理变化,在坚持形式上男女平等的同时应当采取更为切实有效的倾斜政策来实现男女权利义务的实质平等。
总之,我们应当高度注意婚姻家庭的传统性及其历史连续性,学习古人对待婚姻的严肃态度,采取稳健而非激进的方式构建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以维护婚姻的严肃性;我们还应当学习传统社会家庭共财制的合理因素,改变隐形个人财产制度,纠正家庭财产立法中的审判实用主义,真正实现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拥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应当借鉴古人综合考虑男女公法与私法权利义务的思维方式,站在部门法之上来分配男女家庭权利与义务,并纠正婚姻立法中权利义务分配上的形式主义,以实现夫妻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实质平等,最终实现婚姻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1]张晋藩.中国民法通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王媛媛,刘元元.对我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浅析与思考[J].黑河学刊,2008,(6).
[4](日)仁升田稡.唐令拾遗[M].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
[5]于晓青.传统文化中的彩礼及其流变[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
[6]何丽新.非婚同居的规制不会冲击结婚登记制度[J].政法论丛,2011,(2).
[7]大清律例(卷八)[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金眉.论中国古代婚姻家庭继承法律的精神与意义[J].政法论坛,2009,(4).
[9]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0]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1]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