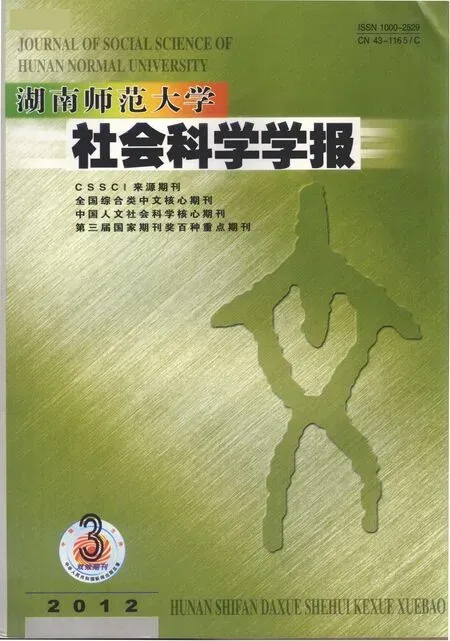人性镜像下的耻感与公共管理伦理构建
2012-04-14李宏斌
李宏斌
人性镜像下的耻感与公共管理伦理构建
李宏斌
耻感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来把握“善”的过程,是通向仁之境界的必由之路。耻感规范与公共管理伦理建构关系密切。文章从探讨我国古代圣贤的人性理论入手,以耻感分析为线索,提出了“耻感行政人”的假设,并进一步解析了公共管理伦理建构的逻辑起点及规范体系。
人性;耻感;公共管理伦理;规范构建
公共管理与国家统治不同,它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其终极目标是为公众增添福祉,促进公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因此,公共管理涉及到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基本伦理问题。伦理,是人们关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荣与辱的观念和规范的总和。公共管理伦理是职业伦理的一种类型,是人们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有约束力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公共管理伦理通过改变公务员的内在取向,促进公共管理走向善政,促使公务员真正成为民众的福音和“行政国的卫士”[1](507-508)。
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曾为公共管理伦理学绘制了一张“航行图”,他认为公共管理伦理的建构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对公共管理中伦理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研究;其次要综合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公共管理伦理问题[2]。本文尝试从探讨我国古代圣贤的人性理论出发,以“耻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分析为线索,解析公共管理伦理建构问题。
一
何为“耻”?国内外学者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耻感相关研究(如:舍勒/1913;萨特/1943;本尼迪克特/1946;皮尔斯与辛格/1953;林德/1958;爱伯华 /1964;威特金 /1971;金耀基 /1986;胡凡 /1997;陈少明/2006;高兆明/2006等)。由于研究的方向和理论基础不同,学者们对耻感下了不同的定义。
《说文解字》曰:“耻也,从耳,心声。”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广韵》曰:“耻,惭也。”《六书总要》曰:“耻,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顾炎武云:“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从上述论述中可知耻感是人们基本的心理经验之一,常伴随悔恨感、紧张感和焦虑感等情感,并会通过人的内心感受而引起人们行为的变化。
国外学者谢夫(Scheff)通过对大量文献综述后认为耻感包括困窘、羞辱、失败、羞怯、无能等,就好象一个大家庭,他们之间通过“对社会契约的威胁”关联起来[3]。波尔森(Poulson)曾指出:“羞耻经常会被人们忽视或误解,但它却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促进因素。”[4]因此,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耻感的话,可以说它是一个警告信号,人们因畏惧羞耻所造成令人痛苦的后果,从而避免那些可能发生的行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耻感也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的耻感就超越了单纯的心理学意义,开始与早期的公共管理发生联系。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谈到如何进行国家管理时指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管仲所提出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中就包括耻感;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强调“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清朝的大儒阎若琚认为:“耻乃根于心之大德也。”
在先秦儒家中,“性善论”的主要代表是孟子。它的人性论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完备形态,并且奠定了中国人性论的基调。孟子的人性立论的起点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人性论的立足点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所具有而动物所没有的属性就是人性。这种人性的内涵就是“心之同”,即心理、思想品质方面的相同点。“心之同”亦称“四心”,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德之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人生来都具有天赋的道德良知,不待特殊的教育就能趋善避恶,这种道德良知能够自然发挥出来,并形成道德的基础。耻感的人性基础是人的良知良能,而不是功利目的,正所谓“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基于“人性善”的前提,耻感逻辑起点应该是“从善”,以肯定方式获得“善”的结果。如果将“耻”与先王的“不忍人之政”联系起来,可以把它看作“不忍人之政”的先决条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则属于道德理性。道德理性是道德情感的升华,是一个由情及理而连续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耻感是通向“仁”之境界的必由之路。
总体上看,中国的人性论的主基调是“性本善”,但也有一些主张“性本恶”的,在诸儒中,荀子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就秉持“人性恶”的观点。他的人性论的著名论断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对人性的界定是:“性者,生之就也,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同上)在他看来,人性就是生来就有的不事而自然的本性,人性之中充满了情欲,使人趋向邪恶。人性本恶,然善从何来?荀子的回答是:化性起伪。善不是人的本性,而是圣人之伪。“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累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同上)荀子的性恶论及其所主张的司法教化成为日后法家的理论根据。法家承续了荀子的“性恶论”主张,认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应“信赏必罚”、“专任刑法”。他们也利用耻感来国家治理。如《商君书·算地》:“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鞍借用耻感痛苦体验会使人终止不当行为,主张用官爵来劝励功业,用刑罚来禁止奸邪。“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宋朝欧阳修),“知耻近乎勇”,“知耻而后正”,耻感首先是对“恶”的抑制,使人们“有所不为”,然后才是对“善”的激发,使人们“有所为”。因此在“人性恶”前提下,耻感的逻辑起点就是“避恶”,是以否定性方式来把握从“善”的过程。
由是观之,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和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虽然在人性的意义和善的意义上有所分歧,但在许多方面却是相同的。首先,意向和目的相同。孟子主张人性善的目的是要使人知道自己具有辨别善恶是非的德能,希望人们立德修身,扩充自己天赋的德能;荀子主张恶,目的是使人了解人的天性倾向邪恶,人不可放纵自己的情欲,应当尽心尽力,化性起伪。二者都以挽救、光大人性为目标。其次,对于心灵和情欲的看法相同。孟子认为人的心灵具有四种基本德性,即仁、义、礼、智,这种心是人的“大体”。荀子认为心是人的主体,能分辨是非善恶,有自由自主之能力,人心是善的,也是可以向善的。对于情欲,二人都认为情欲能引人向恶,都主张节欲。最后,最终的结论相同。孟子的结论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的结论是:“涂之人可以为禹”。总之,孟、荀的人性论虽然在着眼点和原理上大异其趣,但在根本精神与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他们分别抓住了人性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发挥,在表现形态上一个是主观的,能动的;一个是客观的,客体的;一个是从积极方面入手,以耻感为心理机制,采取肯定方式获得“善”的结果;一个从消极方面着眼,以耻感为心理机制,采取否定的方式来把握从“善”的过程。
二
公共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要想保持不断发展的生命力,就必须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石和完整的学科框架。李春成认为,“概论式”的行政伦理学,势必变成意识形态宣传、政治的口号,他认为,“行政伦理学就是一种行政哲学。因此,行政伦理学研究必然带有浓厚的‘哲学化’气息”[5]。
我国理论界在对公务员的人性研究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大多数学者借鉴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将行政人看作是“经济人”,其提出的对策性方案就是强化外在控制与引入市场机制。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把行政人员看作是‘公共人’而不是‘经济人’的话,就会寻求行政道德建设,就会提出‘以德行政’的要求”[6](164)。也有人提出,应当从古典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传统出发,用“德性行政人”代替“经济人”假设,“力避理论的绝望和现实的衰败”[7]。应该说,学者间的对立性的思考是有价值的,理论思考的异质性、对立性、批判性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学科逻辑起点的认识。
我们认为,这里的“经济人”、“公共人”或“德性行政人”假设,虽然借鉴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但当这些行政人假设运用到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建构中时,就必然与我国传统的人性论相衔接、相结合。
通过上文对我国先秦人性论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古代圣贤都普遍地认为完美的道德理性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性善论”者主张要通过耻感之门才能达到仁之境界,“性恶论”者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耻感的逻辑起点是“为善”还是“驱恶”,但最终都是“向善”,而不是“向恶”。“向”代表一种价值取向,“为”或“驱”则代表某种事实取向。公共管理伦理学就是在不断寻求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彼此契合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我们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绝对性思维。
我们坚持使公务员“向善”,但公务员也不可能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成为理想境界中的君子。同时,我们又力避功利主义的消极性特征,又把道德规范和道德自觉作为伦理建构的终极目标定位,把社会发展中的自然过程转化为自觉的过程。但这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只好先走迂回路线,即在坚守公务员道德的底线前提下,即先做到“不为恶”,之后,在耻感的心理机制的参与下,将道德情感进一步升华为道德理性,逐渐靠近“为善”的境界。耻感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心理机制。
耻感的心理机制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向内看——知耻改过”的过程,二是“向外看——寻找差距”的过程。从存在本体论出发,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羞耻感产生的机制在于人的存在与动物有根本的区别,人有精神的存在,这能使人意识到自身与完美的“神”有一定差距而产生羞耻感[7]。正是这种“差距”和耻感的痛苦体验,耻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向内看”的特性,不断激发人向上、向善的动力。当然,如何使耻感的补偿行为发展为“知耻改过”,而不是隐瞒逃避、嫉妒报复、权术游戏、抑郁焦虑等,还需要体制配合和管理者的教育引导。总而言之,耻感至少意味着善端,“知耻作为传统道德的基础性规范,乃是人的德性和人格的基本要求或前提”[8]。综上,我们不妨把公务员首先看作是“耻感行政人”,将培养公务员的耻感意识作为公共管理伦理建构的逻辑起点。
三
耻感的心理起点是“为善”或“驱恶”的两种不同论断,启发我们认识公共管理伦理建构的两个向度:一个是肯定性的向度,称之为“美德伦理”的建构,提倡诚信、廉洁、公正、为民等价值,促进道德理性的形成;一个是否定性的向度,称之为“规范伦理”的建构,可采取法制规范以及引导公务员知耻明耻、祛恶从善、耻不从枉等措施。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实践中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从“耻感行政人”的逻辑起点出发,公共管理伦理建构应选择由“规范伦理”到“美德伦理”的建构路线,遵循由“他控”到“自律”的逻辑思路。当然,伦理建构侧重点的确立应根据公共伦理体系发展的状况来确定。当社会伦理氛围处于稳定期或上升期时,应当提倡肯定性的建构路径,多采用顺势推舟,以道德自律为主,强调升华[9];当社会伦理氛围处于混乱期或失范期时,应以否定性的建构路径为主,强调耻感规范或制度法则的作用。
沿着这个总体思路,我们进一步探讨耻感规范在公共管理伦理建构中的应有之位。中国传统的法家一向强调将耻感作为国家治理中强有力的外部控制工具,将耻感本身视为一种规范。儒家则认为应把正心诚意、反躬自省的道德自律放在第一位,并将耻感视为“义之端也”,但是儒家也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必要性,正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西方近代历史上,从1940年的费勒-弗雷德里奇起,有关“他控”与“自律”伦理构建之争已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也都赞同由“他控”走向“自律”的路径。但是“他控”与“自律”仍存在似乎无法逾越的屏障,如何将二者有机地融合与衔接起来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公共管理伦理建构中,仅靠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制与耻感的外部控制功能。美国的先哲麦迪逊曾说:“假如人类是天使,则不需要政府。假如天使治理人类,则有关控制政府的内部、外部措施统统没有必要。”可以说,法制、耻感、道德三种规范组成的集合体,融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社会规范与自我规范于一体,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规范伦理建构的完整体系。
第一,法制规范建构。法制规范主要指通过制订和执行公正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及利益协调机制、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化和制度的伦理化等措施来制约公务员的行为。具体来说,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化包含四个方面:首先,公共政策伦理的制度化,保证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其次,公共管理制度伦理的制度化,可使保证公共管理伦理的稳定性,为创新提供可遵循的伦理路径;再次,公共管理组织伦理的制度化,设立公共管理伦理的管理机构;最后,公务员个人伦理的制度化,通过公务员奖惩制度、引咎辞职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等的建立,能够保障公务员认真履行职责。制度的伦理化是指制度的合道德性、合伦理性,使制度的实施发挥伦理价值导向和伦理规则作用。
法制规范是通过社会控制或者说是他律来使公务员“不为恶”,因此首要任务就是明晰并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这是善政之前提。
第二,道德规范建构。道德规范是公共管理规范伦理建构的高级阶段,更强调个体自律与自觉,实行的是非正式的自我控制,在对外在道德规范的确证与认同的基础上,将道德律令转化为自己内心的法则,内化为自己内心的道德需要,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遵循,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使行为合乎伦理要求。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对公务员来讲,需要通过引导、教育、重塑促进自身的反省,唤醒人性的“善”,将道德情感升华为道德理性,成为“君子像”的公共管理者,此乃善政之终极。
第三,耻感规范建构。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是介于“为善”和“为恶”之间,此时,法制的“外控”与道德的“内律”均显得势单力薄。耻感所具有的规范效果正好作用于这一空白区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缓冲区。耻感的下沿是道德的底线,其痛苦的体验使人回头是岸,弃恶从善;耻感的上沿则是通向道德理性的大门,其激发的上进力使人反躬自省,走向善政。可见耻感弥补了道德与法制的不足,在“外控”和“内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公共管理伦理建构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在非正式社会控制下要求多数公务员“有所不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为”。此乃善政之路径。
总而言之,公务员“知耻明耻”即为善端,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希望。在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建构中,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中国人耻感的个体心理过程和社会心理机制,运用好耻感规范的功能,引导公共行政走向善政。
[1]Rosenbloom,David H,Public Administration[M].New York:McGraw-Hill,1997.
[2]Dwight Waldo.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In Richard J.Stillman ⅡPublic Administration:Conceptand Case.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
[3]Scheff,T.Shame and the Social Bond:A sociological Theory.Sociological Theory,2000,18(1):84-98.
[4]Poulson,C.F.Shame and Work.In N.M.Ashkanasy,C.E.J.Hartel&W.J.Zerbe(eds)Emotions in the Workplace,2000,250-271.Westport,CT:Quorum Books.
[5]李春成.行政伦理研究的旨趣[J].南京社会科学,2002,(4):31-34.
[6]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舍 勒.论害羞与羞感[A].价值的颠覆[C].北京:三联书店,1997.
[8]刘锡钧.论“耻”[J].道德与文明.2001,(4):43-46.
[9]刘雪丰,何 静.行政伦理学有待深入研究的三个理论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3):18-20.
Shame Sense under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the Ethic Construc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 Hong-bin
The sense of shame controls the process of goodness with a negative way,which is essential to the realm of benevolence.The standard of shame sen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From the clue of analysis on shame sense,this article performs the assumption of shame sense administrators on the basis of penetrating Chinese ancient saints’theories about human nature.Also,it analyzes the logical origin and standard syste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
human nature;shame sense;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李宏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河南 郑州 450044)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