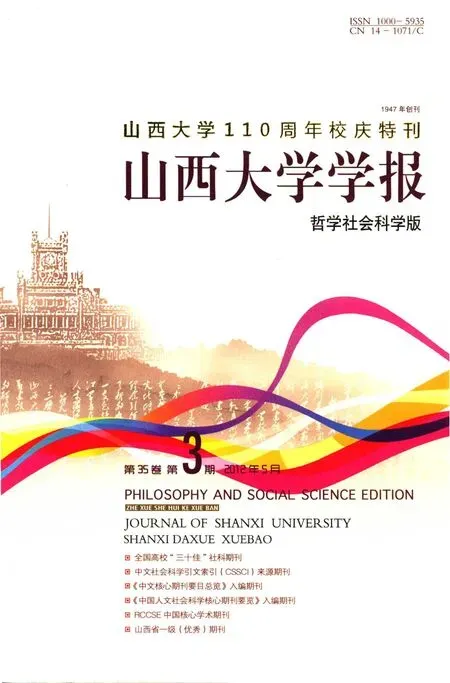晋抚胡聘之与晚清山西矿案新论
2012-04-13刘建生郭娟娟
刘建生,郭娟娟,2
(1.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胡聘之在1895-1899年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改革教育、兴办学堂、筹划实业、兴修铁路,可谓一位勤于政事、政绩显著的地方大员。但由于其为筹得开办近代矿业及修建铁路的巨额资金,1898年允准了刘鹗的晋丰公司与英国福公司签订的借款合约,为当时晋人及后来的学界所诟病,成了出卖山西矿产的历史罪人。
然而,近来随着一份记载山西保矿运动历程的珍贵史料《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①《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原件现存于山西省阳泉市西郊3公里平潭镇官沟村的银元山庄博物馆,为参与山西保矿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张士林所作,由另一位保矿运动的领导者黄守渊后人搜集。文件系麻纸手抄墨稿,共47页,加上其序文及小引在内共11 419字;记述时间从1905年2月18日至1910年2月25日共五年;详细记载了参与平定保矿运动的主要人物39人,为保矿召开的大小会议17次。该史料不仅详细记述了当时参与平定保矿运动人物的活动,而且通过这些人的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到山西保矿运动从酝酿、发起、高潮到成功的历史全过程。(平定古称石艾)的发现,引发学术界对山西矿案的再次关注。相关学者通过对《纪闻》进行史料辨析,确认其中反复提到的一位在山西保矿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幕后人物“崇儒公”即为胡聘之。②相关史料辨析见刘建生,任 强,郭娟娟“《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中‘崇儒公’的辨析”一文,刊载于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1):136-139.由上推知,胡聘之既充当了“出卖”山西矿产的罪人,又参与了为争回山西利权的保矿运动。这不仅引发笔者诸多思考:一位倾心于实业的地方大员,怎么会沦为“卖矿”的历史罪人?既然其出卖了山西矿产,为何又热衷于山西保矿运动?就此,结合相关史料对胡氏“借洋款办矿”的原因及其与福公司借款具体始末进行探讨和分析后,笔者认为,胡氏在山西矿案中自始至终都不曾有意卖矿,并为保护山西矿权与福公司进行了反复周旋。
一 胡氏“借洋款办矿”的原因分析
胡氏之所以背上“卖矿”的骂名,其原因是他在与英国福公司交涉过程中,允准了刘鹗的晋丰公司与福公司签订的借款合约。那么,胡聘之为什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借洋款”,使自己背上“卖矿”的骂名呢?
(一)胡氏“开矿”是响应清廷“招商开矿”的政策
19世纪末清政府财政匮乏,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为筹措兴办洋务所需的大量资金,对过去完全摈弃外资办矿的主张有所改变,加之维新运动兴起,光绪帝也支持和同情维新派,于是,招商开矿以扩利源在很多开明官吏中间引起共鸣。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896)奉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王、两江总督刘、闽浙总督边、江苏巡抚赵、江西巡抚德、浙江巡抚廖、山西巡抚胡、传谕护理陕西布政使张汝梅。
上谕开矿为方今最要之图,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等设法开办。兹据御史陈其璋奏:奥国博物院谓中国煤产以江西、乐平、浙江江山等处为最,而莫多于山西。
王文韶、刘坤一、边宝泉、赵舒翘、德寿、廖寿丰、胡聘之、张汝梅拣派熟悉矿务办事实心之员,按照所指各地认真履勘拟定办法,据实具奏至该御史。另片所称,官办不如商办,凡各省产矿之处,准由本地人民自行呈请开采,地方官专事弹压,其一切资本多寡,生计盈亏、官不与闻、俾商民无所疑沮等语,所走亦颇中款要,并著各该督抚酌度情形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知,王文韶、刘坤一、边宝泉、赵舒翘、德寿、廖寿丰、胡聘之并传谕张汝梅知之,钦此遵。[1]22册:40
可见,甲午战争后,通过招商开矿以解决财用匮乏的危机已成为光绪帝和很多开明官员的共识,且地方督抚大员也极为配合。对于山西来讲,其矿产之丰富早已名闻天下,胡聘之长期以来倾心实业,对此更是热心且反应敏捷。就在光绪帝上谕颁布后的第十二天,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就向光绪帝上了《晋省筹办开矿》折并很快得到批准。
(二)胡氏“办矿”的初衷是“佐国用而自强”
在拟划开矿过程中,胡氏考虑到山西矿产的运销问题,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1897年7月8日)向清廷上了《奏为晋省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一摺。他认为山西需要“借洋款修铁路办矿”的理由及建议有五:一是“晋省煤铁之利,甲于天下,潞泽平盂等处所产最旺而质亦最佳。诚宜及时开采以兴矿务而佐国用”;二是“若能采用西法购机设厂熔铁炼钢,获利必倍”;三是“以太行艰险不能远道运送,欲图畅销,非修铁路不可”;四是“现幸芦汉铁路不日动工,晋省只须赶筑支路,或由潞安至邯郸,或由平定至正定,与之相接,即可畅行无阻,且于海军衙门核覆张之洞原奏,亦属相符。诚以铁路为自强之本,必须支干相连,方能合成西北大势”;五是“惟所需经费过巨”[2]6。仔细分析胡氏修铁路办矿提出的理由,条条切中要害:要采用西法开采矿产,就必须考虑运销问题,而山西交通不便,打通交通迫在眉睫,恰遇张之洞奏请芦汉铁路动工之际,可趁热打铁,资金问题自不赘述。
客观讲,胡氏办矿开路的最初出发点是佐国用、扩利源,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以自强。这些建议可谓切中时弊,忧国忧民,且具可行性,若能正常实施,对地方经济发展必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即以胡氏批复修建,且遭时人诸多非议之山西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正太路而论,百年来为地方物资转运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为山西对外经济交流大通道。
(三)“借洋款”乃为解决资金困窘的无奈之举
采用西法大规模兴办矿业需要雄厚的资金、技术,完善的企业组织结构,高级的管理人才,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与之相配套。正如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8年1月16日)向总署的建议所说:“中国各矿,若无洋人合股代开,既无精矿学之良师,又无数百万之巨本,断不能开出佳矿”[3]。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要清政府变革政治不可能,即使撇开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讲,仅筹措巨资就是横亘在清政府办矿过程中的一个很大难题。清末,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不外乎三种方法:(1)政府从国库拨款;(2)从民间筹集资金;(3)借用外资。第一种方法不可能,甲午战后清廷国库空虚,没有财力支持地方政府发展矿业经济。第二种方法也不现实。首先,中国大多数地方风气未开;其次,华商财力有限;再次,有志于办矿但没有政治背景的华商对清政府官吏的层层需索有所顾虑,对投资办矿很不积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各省中财力最雄厚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办矿筹款至七万两,已感后继乏力。直隶总督王文韶、鹿传霖等在办矿过程中也均遇到资金难题。在这种情形下,借洋款成为很多有志于办矿之地方督抚大员的首选,就连原先反对洋人办中国矿务的张之洞,也主张利用外资开办铁路,以保持各国在华势力的均衡[4]。
山西的情况也不例外。胡聘之要解决办矿过程中的资金难题,借洋款不失为最为可行且便捷的方法。据相关史料记载:山西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曾由商务局刊发集股章程,由本省各州县并分寄各省西票,并代为劝募,日久百无一应”[5]31。可知,胡聘之办矿之初并没将借洋款作为解决资金问题的首要途径,而是先向省内地方官绅及商人筹款,但日久无人响应。在华款难以筹集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他才着手实施借洋款以兴办实业的策略。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一折中提出资金筹措问题:“惟所需经费过巨,专恃本省集股,断难有成计”,同时建议“惟有由外省殷商包办,可期迅速”[2]6。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7年7月14日)清廷上谕胡氏奏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一摺:“晋省铁路各矿,运道阻滞,必须先办铁路,方能畅销。览奏设立公司所贷之款,商借商还,余利酌提归公各条,大致尚属周妥。惟创办伊始,必须预防流弊,并借款有无实在把握,著胡聘之悉心筹办,酌定详细章程,奏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1]23册:137-138清政府对胡氏“设立公司所贷之款,商借商还,余利酌提归公各条”的建议,认为“大致尚属周妥”,同时表示担心“惟创办伊始,必须预防流弊,并借款有无实在把握”。得到清政府许可后,胡氏即委派外商刘鹗创立晋丰公司,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1897年10月25日),批准了刘鹗的晋丰公司与福公司签订了山西矿路借款合同。
如此看来,胡聘之“借洋款”主要是为解决办矿过程中资金短绌问题迫不得已做出的无奈举措,也即他“借洋款”的主要原因。
(四)胡氏“借洋款开矿”得到了清政府首肯
甲午战争后,晚清重臣张之洞、刘坤一等将开矿、修铁路置于兴办实业的重点。迫于形势,为筹集到办矿修路的巨额资金,这些洋务大员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借洋款”的方式。如张之洞为兴修卢汉铁路于1897年和比利时银行团代表签订了借款合同。刘坤一在《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中也明确主张借洋款办铁路[6]。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当时中国风气未开,无论普通民众还是很多在朝官员对于洋务派官员开矿、修铁路的做法相当排斥。洋务派官员向清廷所上的有关开矿、修铁路的奏折几乎都受到保守派官员的弹劾,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对开矿筑路并不反对,因此,虽多遭非议,但还能勉强进行。
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民风较为保守,胡氏在晋开矿、修路更是阻力重重。在他向清廷奏称筹办开采山西煤铁矿利后,声讨之声从未停止过,且一浪高过一浪,山西举人张官等联名公呈都察院,山西京官邓邦彦、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何乃莹等都先后就此事进行弹劾,但他何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其主张并付诸实施,究其原因就在于清政府最高层的首肯。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4月3日),胡氏向清廷上奏:“晋省煤铁之利,甲于天下。太原平定大同泽潞等属,所在皆有,几于取之不尽,当此财用匮乏,正宜设法攻采,以开利源。臣于去冬抵任后,即经周咨博访,筹议办法”[7]1383,清廷对此“硃批,户部知道。钦此。相应恭录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钦遵查照施行”[7]1383。得到清廷支持后,胡氏发现要将山西铁矿运销至外,必须打通山西对外交通,兴修铁路,而大规模开采山西矿产和开通铁路,资金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又上奏:“(山西矿产)欲求畅销,非修铁路不可。……与海军衙门核覆张之洞原奏,亦属相符”[2]6,他的这一请求亦得到清政府批准:“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1897年7月14日)上谕胡聘之奏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一折,晋省铁路各矿,运道阻滞,必须先办铁路,方能畅销。览奏设立公司所贷之款,商借商还,余利酌提归公各条,大致尚属周妥。”[1]23册:137而对于弹劾胡氏的诸多奏折,清廷都一一予以答复:“徐树铭原奏谓将铁轨开矿包与洋人,均属言之过甚。即山西京官两次公呈将合同章程逐层辩驳,亦多附会,无以折服洋人。何乃莹奏请停借洋款,故属正辨。惟泰西各国率皆经营路矿以驯致富强。晋省煤铁矿产之富,久为西人所羡,若深闭固拒,转恐利源旁落,何如豫为之地,尤为操纵自如。现在中国商情集股不易,仅用土法开采,实系难成”[8],明确肯定胡氏开矿、修铁路的主张。
二 胡氏对福公司本质认识不清,遭其蒙蔽
胡聘之委托刘鹗向福公司借款一事,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时人猜测纷纷,最终胡氏屡遭弹劾罢官,刘鹗也被撤退,他们因此背上“卖矿”的骂名。通过相关史料分析,笔者发现胡氏在与福公司交涉过程中极为审慎,为保护国家利权作了很大努力,其本意自始至终都不曾“卖矿”,而在“借洋款”与保护山西矿权之间反复周旋。
(一)胡氏“借款论调”迂阔但态度审慎
借洋款办矿,虽然能够解决资金短绌问题且实际可行,但稍有不慎,就会有很多流弊,导致矿权丧失。胡氏作为一名地方督抚大员,虽意识到了福公司的掠矿意图,但认识并不深刻,反而迂阔地认为如此可以预防矿权丧失。他认为:“(臣)维此事关系重大,原不敢轻议举办。第念时局艰危,强邻环伺,或代造铁路,或包办矿务,种种要挟不如其意不止,而晋省矿产之富,载在西书,久为他人所垂涎羡,我不自取,终难保人之不取。与其迁延坐误,留以异人,何如借款兴办,使之代造工程,分沾利息,或犹可泯觊觎之私而战争攘之谋。”[5]42
在与福公司交涉过程中,胡氏处理问题极为小心谨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1898年3月5日),胡氏在《覆陈现办晋省铁路矿务情形折》中,面对晋籍京官的弹劾,他首先重申“借款”的主因是“因工本过巨,专恃本省集股断难有成”;其次让方孝杰向华俄银行借款,“据该行璞科第函电并派人来晋,经臣查询俱属切实”后,仍“拟详加推勘再行”;再次,对于刘鹗与福公司的交涉,也是在其保证“声明所借之款,系两国商人自相筹借,与国家毫不干涉”,查证属实后“暂为批准”,但正式合约要等清廷“奏准后再行”。另外,在他与福公司交涉过程中,坚持在公司产权上避免洋商把持,“既系商人自借洋款,设立公司承办,必须华商毫无期饰,洋商不致把持,方可杜弊端而收实效”。在他发现福公司“第一及第十九两条有欲删改之处”后,并没有一味迁就福公司,而是“(臣)未能允许,往返商酌”。[5]42-43
(二)胡、刘二人对英人掠矿企图认识不清
由于胡聘之对福公司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又不具备近现代矿业管理体制知识,在进行具体事务交涉时被洋人蒙蔽,导致了山西矿权的丧失。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胡聘之没有认清福公司“借款”的本质。李希霍芬来晋考察山西矿产资源并发表调查报告后,山西矿产遂为西方各国垂涎。罗沙第为侵略山西矿产,早在1897年福公司成立之前,就制定了旨在掠夺中国矿产的矿业开发计划,并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福公司成立后,他将刘鹗作为中间人与晋抚胡聘之进行交涉,签订开矿借款合同,只是其进行掠夺山西矿产计划的前奏。在此情况下,尽管胡氏在奏折中多次提到“借洋款”为“商借商还”,“与国家毫无干涉”,但对于尚不具备近现代矿业管理体制知识及国际商法的清政府来讲,一旦发生矿案纠纷,其结果必然处于被动。
其二:刘鹗引进外资开矿的理论虽有见地,但在清政府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极易被侵略者利用,但热衷洋务的胡聘之接受了其主张。在刘鹗致友人罗振玉的信中,谈到他引进外资开矿的观点:“蒿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蓄养,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9]368。此后,他向胡氏呈递了《刘铁云呈晋抚禀》一书,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商办则一切须商人转禀,商禀批驳申饬,无所不可。况犹不止此,官未必皆久任,原办之人既去,后来者虽极精明,难免不受其蒙蔽。若华商业之所在,即身家之所在,慎其始,更图其终,朝夕审计,其利害奥窃知之较详,故其操纵之术,必胜官家十倍”“兵力所得者,主权在彼;商力所得者,主权在我,万国之公例也。……今日亟欲引商权入内者,正恐他日有不幸而为兵权所迫之事,必早杜其而渐之萌,为忠君爱国者当今之急务也”[9]127-130。将胡氏《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与《覆陈现办晋省铁路矿务情形折》所陈述的“商借商还”的开矿借款方法与刘鹗的引进外资理论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的主张不谋而合,因此胡氏接受了刘鹗的建议。但刘鹗“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付诸实践,导致的后果必然是“任欧人开之”,而“我严定其制”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反被洋人利用。遗憾的是,直至1903年,刘鹗在《浙江潮》上发表的《矿事启》中仍认为“借款办矿,商借商还,六十年后全矿报效国家,若有华人筹得巨款,立刻可以收回,非卖也”[9]131,依然对外国掠夺中国矿产的企图认识不清。
(三)此后签订的借款章程丧失矿权更甚
在胡氏批准了刘鹗的晋丰公司与福公司的合约后,虽胡氏屡遭弹劾并不准其再参与山西矿务交涉,刘鹗也被撤退,但福公司的侵略步伐并未停止。英国公使宝纳乐和意国公使萨尔瓦葛数次赴总署向北京方面施压,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1898年5月21日),札饬山西商务局局绅与罗沙第签押“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
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1898年3月1日)胡氏最先批准的晋丰公司和福公司借款合约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5月17日)清政府札饬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的《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相比,会发现后者较之前者所丧失的矿权更多。略举其中几条:原约是福公司向晋丰公司“借洋债无逾一千万两”,属于“商借商还”,而《章程》中则是“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等于福公司所攫取的利益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原约关于开矿范围只是“独自开办盂平泽潞诸属矿务”,开办矿务地区只限于盂平泽潞;而《章程》中将开矿范围扩大到“专办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两府属与平阳府以西煤矿以及提出煤油各矿”;关于用人方面,原约中议定“凡调度矿务与开采工程,由晋丰公司刘鹗会同洋商经理,而矿中执事则议明总以仅用华人为是”,《章程》中则规定“凡调度矿务与开采工程用人经理各事,由福公司总董经理”,山西商务局只是“会同办理”;关于国家所得利益部分,原约规定“于开矿盈余先提用本官利八厘,又公积一分后。所存余利除已提百分之二十五分报效国家外,议定再提百分之二十五分呈归宪抚拨用”,等于原约中国家获得利益可占到赢利的“百分之五十”,而《章程》规定“所余净利提百分之二十五归中国国家,余归公司自行分给”,并且“以后中国他处有用洋款开采煤铁矿者,应请一概仿照此章”[7]1404-1407,相当于国家每年只能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盈利,比原约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胡聘之作为一名致力于实业的开明地方官员,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开办山西煤铁矿业、兴修铁路,为解决实施过程中的资金难题,委托刘鹗等向“洋商”借款。他在与福公司具体交涉过程中,态度极为审慎,为维护国家利权做了积极努力,但囿于历史局限,遭洋人蒙蔽,导致山西矿权丧失,为后人诟病。正因为山西矿权最终丧失违背了他借款开矿“扩利源”“佐国用以自强”的初衷,20世纪初,当中国人民矿权意识觉醒之际,胡聘之受时代思潮所趋,投入到山西保矿运动中来。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晋人及后来的史学界将山西利权的丧失完全归罪于二人有失公允。
[1]叶志如.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2辑007[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总署电[M]//张之洞全集.第3册卷七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2116.
[4]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M].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9-13.
[5][清]步 青,柏 年.调查胡中丞聘之办理晋省铁路矿务始末详记[Z].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6]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刘坤一遗集(2)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M].北京:中华书局,1959:882.
[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资料备编(矿物档)[M].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
[8][清]朱寿朋.光绪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M].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清宣统元年(1909):3801.
[9]刘德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