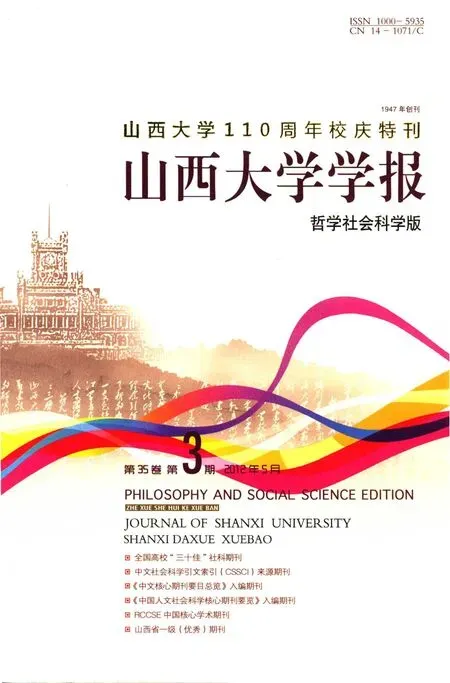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演变轨迹和研究走向
2012-04-13赵勇
赵 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就笔者目力所及,一些大众文化的基本问题还缺少细致的梳理。以下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行、演变之轨迹和研究之走向进行粗线条的勾勒与分析,既正本清源,亦回眸审视,希望能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尽绵薄之力。
一 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
大众文化的英文表达有两种说法:Popular Culture和Mass Culture,与其相近的表述还有Kitsch(媚俗艺术)和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业)等。考察这些概念所出现和使用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它们大体上经过了如下线路:Popular Culture→Kitsch→Mass Culture→Culture Industry→Popular Culture。以下为行文方便,我们暂时将Popular Culture译作通俗文化。
(一)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尽管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认为“通俗文化已经有了许多个世纪的历史,它大概与人类的文明一样古老”,[1]xvii但是,把通俗文化当作一个特殊的现象加以对待一般只是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比如,洛文塔尔思考通俗文化现象时便分析过“蒙田-帕斯卡尔之争”。伯克(Peter Burke)认为,在18世纪晚期,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有过一次发现人民和通俗文化的运动。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厌恶(美学原因),也为了配合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政治原因),知识分子发现了民众和他们的文化。而这一时期的德国作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也明确使用过“通俗文化”(Kultur des Volkes/popular culture)的概念,以和“书斋文化”(Kultur des Gelehrten/learned culture)相区分。[2]
事实上,Kultur des Volkes更应该译作Folk Culture(民间文化)而不是Popular Culture。伯克把民间文化纳入到通俗文化的思考框架中加以阐释,说明他接受了通俗文化的一种意涵:“‘Popular culture’指由普通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而这种意涵的出现恰恰与赫尔德的民间文化概念有关。[3]356只是如此一来,通俗文化便与民间文化相互纠缠,变得难解难分了。这也意味着伯克在考察欧洲近代通俗文化的起源时,更多看到的是通俗文化的民间气质。这是对通俗文化的一种理解。
对于通俗文化更通常的理解是,通俗文化并非来自于民众的文化,也不是被民众创造出来的文化。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并不是来自普通百姓的认同,而是其他人的认定。”[3]356而洛文塔尔在考察了18世纪的英国文学之后发现,当时的通俗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商品。由于阅读大众的出现和印刷出版业的兴盛,通俗小说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通俗文学作家受雇于书商和出版商,成为雇佣劳动者;文学市场主要被书商和出版商运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写作的题材,也引导着消费大众的阅读趣味。因此,以通俗文学形式出现的通俗文化实际上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1]xii如此看来,即便是在通俗文化的源头,它也无法与民间文化等量齐观。
伯克把通俗文化看作民间文化,洛文塔尔则把通俗文化看做一种商品文化,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最初的通俗文化呢?从一些学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欧洲近代的通俗文化已经拥有了现代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但是,由于它还没有完全从民间文化中分离出来,由于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初的传播媒介还不太发达,由于与工业社会相关的城市生活方式还未普及,乡村生活方式还占据着主导位置,凡此种种,都对通俗文化构成了某种制衡。因此,这时的通俗文化还不至于过分嚣张,甚至还有着一些没有完全被商业主义渗透的自然和素朴。
(二)媚俗艺术(Kitsch)
19世纪后半叶,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开始出现。为了对这种艺术进行形象的描述和说明,德国人特意发明了一个词:kitsch。根据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鉴定,媚俗艺术是与先锋艺术一起到来的,其指涉的对象主要是流行的、商业的艺术和文学,包括彩照、杂志封面、插图、广告、落套的和庸俗的小说、连环画、流行歌曲、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媚俗艺术是机械的或通过配方制作的。媚俗艺术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媚俗艺术随时尚而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媚俗艺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所有伪造物的缩影。除了消费者的钱,媚俗艺术假装对它的消费者一无所求——甚至不图求他们的时间。”[4]而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则从美学的角度对媚俗艺术做过如下解释:“可以很方便地把媚俗艺术定义为说谎的特定美学形式。……它出现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时各种形式的美就像服从供应与需求这一基本市场规律的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被社会性地传播。一旦它不再能精英主义地宣称自己具有独一无二性,一旦它的传播取决于金钱标准(或者在集权社会中是政治标准),‘美’就显得相当容易制造。”[5]246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媚俗艺术的概念被发明之时,便带上了强烈的贬义色彩。而它的内涵与其指涉的对象又与现代大众文化存在着种种重叠之处。因此,我们可以把媚俗艺术看做是大众文化概念出现之前的一个替代性的表达。当然,媚俗艺术的概念在其流变中也逐渐扩容。艾柯(Umberto Eco)指出:“媚俗也一直被用来形容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政权下那些歌功颂德,要全民欢迎的艺术。”[6]可见,媚俗艺术不仅可以指称商业主义体制下的大众文化,也可以指涉极权主义体制下的艺术形式。
(三)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的概念究竟出现于何时,本来已无从查考,但美国批评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的一个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在一次访谈中,麦克唐纳告诉访谈者:大众文化(mass-cult/mass culture)、中眉文化(mid-cult/middlebrow culture)是他本人率先使用的概念,甚至他也享有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概念的发明权。这些概念早在194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而在这一时期,加拿大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在使用通俗文化的术语。[7]考虑到麦克唐纳在1944年写有《通俗文化理论》(后改名为《大众文化理论》)一文,他的说法也许是可靠的。或者起码是在北美,麦克唐纳是最早使用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概念的理论家。
由于大众(masses)一词含“多头群众”(many headed)或“乌合之众”(mob)之意,有较强烈的贬义色彩,所以,由它组合而成的大众文化也形成了负面的价值判断。而麦克唐纳在其论述中,更是通过与民间艺术的比较,指出了大众文化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他看来,民间艺术出现于下层,是民众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艺术表达。这是一种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与高雅文化的恩泽无关。而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硬塞过来的东西。它被商人雇用的技术人员制作,其受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只是局限于买与不买的选择上。因此,民间艺术有自己的体制,它就像民众为自己开设的一个私人小花园,四周有围墙,与其主人那个盛放高雅文化的大花园隔离开来。但是大众文化却推翻了围墙,把大众整合到高雅文化的低级形式中,这样,大众文化就变成了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8]60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麦克唐纳才做出了如下清理:“大众文化有时候被叫做‘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但我认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一个更准确的概念,因为像口香糖一样,它的特殊标志只不过是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的一种商品。”[8]59
(四)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虽然麦克唐纳认为大众文化的表述更为准确,但阿多诺(Theodre W.Adorno)却不这么看待。在《文化工业述要》一文的开篇,阿多诺便如此进入问题:“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词大概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的。此书由我与霍克海默合作,194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在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后来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了这个用语,旨在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们乐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也即,它相当于某种从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文化,乃是民众艺术(Volkskunst)的当代形式。但是‘文化工业’与民众艺术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加以区分。”[9]以上的交待表明,阿多诺之所以弃用大众文化而发明和启用文化工业,表面上是担心大众文化的表述不够严谨,以免引起误解,实际上也隐含着他对美国知识界的批评。因为在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像格林伯格、麦克唐纳这种持批判立场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都深感兴趣。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在树立集体主义的目标与理想时,在重塑美国的制度和信仰时,都能直接发挥作用。[10]然而这种观点在阿多诺看来不啻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与他的同道便对文化工业展开了无情的批判。
尽管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后来遭到了许多大众文化理论家的清算,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工业之命名的精准。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已隐含着文化被工业化之后可以批量生产的意涵。而批量生产,也正是大众文化突出的特征之一。
(五)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1960年代,随着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逐渐介入到大众文化研究之中,西方学界对大众文化的性质、作用和功能等等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文化的“降调”处理。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则去挖掘和释放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文化“不但能够抵制商业性大众文化的媚俗风习,而且能够改变大众文化,使之为我所用”。[11]是在这一背景下,“通俗文化”开始取代“大众文化”,成为一种通常性的表述。显然,当众多学者用通俗文化来指称其笔下的文化现象时,他们淡化了大众文化的贬义色彩,把它还原成了一个中性词。与此同时,有人也开始重新定义通俗文化,极力开掘通俗文化的正面价值。比如,在费斯克(John Fiske)等人编撰的一部辞典中,通俗文化已成了“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12]
经过一圈概念之旅后,大众文化似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而通过以上的简要梳理,我们又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首先,表面上是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实际上却隐含着西方学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定位和价值判断。当大众文化以通俗文化之名进行表述时,它便被涂抹上种种来自民众的、革命的、可爱的、甚至带有反叛色彩的油彩,大众文化因此受到了隆重的肯定。当大众文化以媚俗艺术、文化工业之名表述时,它又成了毒害民众的鸦片,大众文化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否定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因此,“Popular Culture→Kitsch→Mass Culture→Culture Industry→Popular Culture”之旅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大众文化“肯定与否定并存→否定→否定→否定→客观面对与肯定”的过程。虽然启用新表达并非完全是抛弃旧概念的过程,但总体而言,通俗文化如今已成主流表达,这也意味着客观面对或肯定大众文化的声音已经压倒了否定和批判大众文化的声音。
其次,尽管否定与批判大众文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否定者与批判者都不同程度地拥有“精英主义”和“文化贵族主义”的审美趣味。同理,虽然肯定大众文化的原因多多,但肯定者又往往拥有“平民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因此,在否定与肯定大众文化的背后,其实是价值立场、审美趣味等等在起作用。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存在固然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审美趣味等等不断建构的过程。
第三,需要说明的是,在汉语语境中,Popular Culture有“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之译法,Mass Culture又有“大众文化”、“群众文化”、“麻思文化”(港台译法)之译法,Kitsch的译法则更多,有“媚俗”、“忌屎”、“媚美”、“奇俗”、“媚世”、“庸俗”、“刻奇”等,而Culture Industry也有“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两种译法。为统一起见,我们把Popular Culture与Mass Culture均译为“大众文化”(个别地方为了区分方便,会把Popular Culture译为“通俗文化”),Kitsch则主要采用“媚俗”和“媚俗艺术”的译法,而Culture Industry则主要以“文化工业”对译之。
二 大众文化的演变轨迹
大众文化发展到今天已有数百年历史了。虽然它的核心理念变化甚微或者基本未变,但是在其生产机制、消费规模、功能作用、传播力度、影响广度等方面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文化的变化幅度更大。下面,我们择其要者,粗线条勾勒一下大众文化的演变轨迹。
(一)从新兴文化到主导文化
威廉斯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结构中,总是存在着三种文化类型: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残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和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主导文化是指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残余文化是形成于过去但现在依然有效的文化,新兴文化则与某一阶级的兴起及其力量壮大有关。[13]在威廉斯的描述中,主导文化似乎总是处于主导地位,且不断地收编着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种文化类型理解为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去理解大众文化的演变,我们就会发现它经历了一个从新兴文化到主导文化的过程。当大众文化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出现时,它无疑是新兴文化;彼时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则是主导文化。然而,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大众文化也越来越变得兴盛起来。20世纪30-40年代,利维斯(F.R.Leavis)、阿多诺等人批判大众文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他们或许也意识到,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化将会变成主导文化,而高雅文化将会退居边缘,乃至成为残余文化。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大众文化发展事实业已表明,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位置,变成了一种主导文化。代宁(Michael Denning)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的文化都已是大众文化。”[14]我们不妨把此论断看作大众文化变成主导文化的变相说法。
大众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不仅会改变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像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娱乐道德观”代替了“行善道德观”[15]),而且也会对其他文化类型蚕食鲸吞。结果,文化越来越趋向同一,出现了一种全面抹平的效果。
(二)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区分,文化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大众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但是根据拉什(Scott Lash)与卢瑞(Celia Lury)的看法,随着文化工业过渡为全球文化工业,文化也开始发生位移:从上层建筑变成经济基础。在他们看来:“1945-1975年,文化仍基本属于上层建筑,这时,统治和反抗以意识形态、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的形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产品仍较少见,更多的是属于经济基础的物质产品(商品)。这种情形从1945年一直持续到1975年。然而,截至2005年,文化产品已经以信息、通信方式、品牌产品、金融服务、媒体产品、交通、休闲服务等形式遍布各处。文化产品不再是稀有物,而是横行天下。文化无处不在,它仿佛从上层建筑中渗透出来,又渗入并掌控了经济基础,开始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体验两者进行统治。就反抗与统治而言,文化的运作不再首先遵循上层建筑的运作模式,也不再首先以霸权的意识形态、符号、表征的形式出现。”[16]6-7
这应该是一个重要论断。也许从“二战”之后开始,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文化就开始了一个逐渐“下沉”的过程。而近30多年来,其下沉的速度则越来越快,以致最终完成了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蜕变。当文化产业变成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时,当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疯狂吸金时,文化工业已变成一种生产力。当然,大众文化产品毕竟与其他物质产品不同,即使它变成了经济基础,也依然带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色彩。像好莱坞大片,一方面它创造了票房的奇迹,另一方面又向全球输出了一种价值和观念。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工业及其产品的复杂性。
拉什等人认为,文化工业变成经济基础之后,文化被“物化”(thingified),而物则被“媒介化”(mediation),[16]7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后果。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意识到,成为经济基础之后,“文化工业”也开始变为“文化产业”,从而褪尽了阿多诺所指出的种种弊端,进而让人们的情感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之后,人们只是在经济效益的层面上重视它,而几乎不再去过问和追究它的负面价值了。这种情况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17]
(三)从中产阶级文化到青年亚文化
美国学者格罗斯(David Gross)曾经说过:“大众文化已变成中产阶级文化,反之亦然”。[18]从事过大众文化生产的中国作家王朔也思考过类似问题:“真正大众文化的主流,举凡真善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教化文明,都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体现。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小痞子都知道,所谓大众文化主流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同义词。”[19]这样的论断和思考可谓意味深长,也让我们意识到大众文化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文化存在着密切关系。然而,随着青年亚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也越来越视其为自己盟友,以至于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中产阶级文化的意味逐渐淡薄,青年亚文化色彩愈显浓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经历着从中产阶级文化到青年亚文化的转型。
如果说近代通俗文化更多与普通的下层民众发生关系,那么,现代大众文化的形成则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欣赏趣味密切相关。中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后,虽然在经济层面具有优势,但在文化层面却非常自卑。“没有哪个阶级对待艺术像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而且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在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中,把从印象派的画作一直到伪艺术家的信笔涂鸦统统算作艺术,高价收购,挂在客厅或艺术收藏室。”[20]63这里谈论的是资产阶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媚俗艺术开始出现,因为媚俗艺术迎合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的浮浅与便宜的基本特征意味着如下事实:这是一种适合于中产阶级生活节奏的、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却能够从中获取娱乐的艺术样式。而这种艺术样式又培育了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林内斯库才说:“媚俗艺术是作为中产阶级趣味及其特有的闲暇享乐主义的表现而出现的。”[5]266而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则论证了新式中产阶级的“闲暇伦理”如何取代了老式中产阶级的“工作伦理”,他们又如何在大众媒介的偶像与其他娱乐机器中找到了新的寄托。[21]
一般认为,青年亚文化浮出历史地表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富裕社会”,中产阶级的富家子弟也开始长大成人。为了反抗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他们剃光头,着异服,说脏话(四字母词),跳迪斯科,唱摇滚,甚至群居,吸毒等等,做出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举动。至19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亚文化不但发展成反文化,而且在与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的斗争中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有人指出:“‘反文化’不是别的,就是高级文化之外的一切其他文化。或者说,反文化就是把‘文化’这个概念重新消融在‘文明’之中。‘反文化’派尽管是一帮年轻人,但在策略上却显得比‘高级文化’的辩护者高明得多,难怪贝尔痛定思痛之际说他们‘少年老成’、‘狡黠’。”其具体做法是:“派出一股股小规模的袭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侵入‘高级文化’的传统地盘,模糊其一直严加守卫的等级界线,令‘高级文化’防不胜防。毛泽东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被‘反文化’派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以农村包围城市’,一方面不断在城市秘密发动起义,最终夺取城市。”[20]246正是通过这场规模浩大、影响世界的学生运动,青年亚文化借助于更激进的反文化,成功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
因此,青年亚文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青春期的叛逆色彩,而“仪式抵抗”则是其惯用手法。青年亚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但又与大众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而一旦前者挪用后者的形式或者后者收编前者,都会让大众文化的构成发生诸多变化。当大众文化以中产阶级趣味为诉求对象时,它显得中庸,保守,充满了媚俗之气。然而,当大众文化吸纳了青年亚文化之后,它则有了某种尖锐之姿,骚动之态,从而也多了几分嬉皮之气。以中国的青春文学为例,我们不可能说它是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但它显然也并非原来那种四平八稳的大众文化,而是青年亚文化与大众文化合谋之后的新产品。
三 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
虽然在19世纪就有了关于大众文化的零散论述,但成熟的大众文化理论却是在20世纪出现的。20世纪30-40年代,英国本土的“利维斯派”和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同时开始关注和研究大众文化,标志着大众文化理论的诞生。50年代,法国罗兰·巴特运用符号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大众文化,可谓独辟蹊径,也给后来者带来了许多研究灵感。从6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大众文化研究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因此,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趋势是从法兰克福学派走向伯明翰学派。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姿态:走向公允平和
无论是利维斯主义者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他们对待大众文化研究的姿态都可称之为疾言厉色。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生产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流行音乐让听众的接受水平退化到了婴幼儿状态。利维斯指出大众文化占用了受众的时间与精力,一方面使他们无暇顾及文学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心性败坏。于是,批判与谴责构成了20世纪中前期大众文化研究的主流姿态。这种姿态一直延续到麦克唐纳那里。
然而,自从伯明翰学派介入到大众文化研究之后,这种疾言厉色的批判与谴责开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心平气和,同情的理解,以及理解之后深入到大众文化内部、局部和细部中的经验主义研究。早期的霍加特、威廉斯和后来的霍尔,尽管他们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研究姿态上却大同小异。即他们大都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大众文化,进而去释放大众文化背后的复杂性。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受伯明翰学派学术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也更多开始为大众文化进行辩护。而这种辩护,既有为大众文化蒙受的不白之冤平反昭雪之意,也往往是“自体民族志”经验的一种书写。米勒(J.Hillis Miller)指出:“那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当前的互联网中泡大的第一批人。……用不着奇怪,这样的一种人应该期望研究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那些影响了他们世界观的东西,那就是电视、电影等等。”[22]这也就是说,当他们开始研究那些曾经哺育过他们的大众文化时,他们已不可能疾言厉色,而更可能是含情脉脉。
虽然大众文化研究姿态的转换背后隐含着诸多令人玩味的信息,但总体而言,走向公允平和还是值得称许的。因为缺少足够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尽管可逞一时之勇,但又往往会形成一些漏洞,从而给人留下攻击的口实。这也反证出,学术研究应把价值判断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判断基础之上,如此,它才能经得起检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理论方法:走向多元共生
成熟的大众文化研究本身就会形成一套理论。不过,当人们一开始进行大众文化研究时,往往又需要借助于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展开。20世纪中前期的大众文化研究,其理论方法比较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的效果。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方法和文学社会学方法。由于精神分析学本身还是没有经过充分验证的理论假定,所以,把它运用到大众文化研究中之后虽然也很出彩,但往往又给人无法落到实处之感。此外,因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传统是哲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也就往往被拉到哲学的思维框架中加以操练,运用艰深的哲学语言进行表述,其结果是造成了理论的晦涩难懂。
伯明翰学派开始文化研究后,进入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开始增多。巴克认为,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有三:民族志(ethnography),文本方法(textual approaches)和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23]除此之外,文化研究还拿来了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分析理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狂欢化理论,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社会理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接合理论等等,也常常是大众文化研究借用的理论方法。这些理论方法拓宽了大众文化研究的视域,也把大众文化研究带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当然,是不是这些理论方法都适用大众文化研究?借用费斯克的说法,某些理论方法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是否也只是“权且利用”(making do)?[24]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还需要深思。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5]中国的作家张承志也说过:“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26]这些论断都可以帮助我们检验这些理论方法是否合适妥帖。
(三)关联语境:走向后现代主义
美国学者胡伊森(Andreas Huyssen)认为:“就像现代主义的发端一样,现代大众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48年左右。”[27]19如果我们把媚俗艺术看作现代大众文化的先声,那么现代主义与现代大众文化确实同时出现在19世纪中叶。而两者从出现之初开始,便处在一种紧张、对立、充满敌意的关系之中。胡伊森指出:“现代主义建构自身的策略是,一种有意识的排斥,一种被他者——日益处于支配地位的席卷一切的大众文化——腐蚀的焦虑。现代主义作为敌对文化的优势和弱点都产生于这一事实。毫不奇怪,这种对腐蚀的焦虑以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姿态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运动(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新艺术运动)中,并再次出现在二战后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以及对实验写作的追捧中,还有文学、文学批评、批判理论和博物馆对‘高雅现代主义’的官方经典化中。”[27]1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确实形同水火,势不两立。而作为他者的大众文化越是嚣张,也越会刺激现代主义做出反应(甚至可能是过度反应)。凯里(John Carey)认为,知识分子把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弄得难以理解,是为了阻止大众接近它们。因此,“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可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应”。[28]这种说法应该有一定道理。
事实上,站在现代主义的维度上去维护自主艺术,进而去批判对自主艺术构成腐蚀和威胁的大众文化,也正是早期大众文化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由此,他们也就在大众文化理论中建构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一点在阿多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来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开始握手言和。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主义的巅峰时期,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业文化)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感经验范畴,今天,后现代主义把两者之间的界线彻底取消了。”[2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与美学风尚开始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有论者指出:“高雅现代主义教条已经变得陈腐,阻碍了我们对当下文化现象的把握。高雅艺术和大众文化的边界日益模糊,我们应该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一次机会。”[27]4这意味着大众文化研究走向后现代主义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回应。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于是研究者对高雅文化不再投以青眼,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开始犹疑,乃至渐趋肯定。以费斯克为例,在1983年悉尼举办的澳大利亚传播会议上,他还是“一名普通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家”,并用“绝对正统的现代主义声音”发言。然而几年之后,随着《电视文化》《理解大众文化》《解读大众文化》的问世,“一个新费斯克出现了”,而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他遭遇了后现代主义,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获得了新生。[30]而晚近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差不多都被后现代主义文化现实击中过,被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点化过,他们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就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后现代主义进入大众文化研究或大众文化研究走向后现代主义首先应该予以肯定,因为当文化现实语境发生变化后,其研究立场、研究范式等等也不可能不做出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研究的后现代主义化是直面并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造就的是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文化风格,[31]这种风格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大众文化研究中,从而让该研究变成一种认同式的、游戏化的研究,其结果是有趣好玩有余,质疑批判不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才指出:“文化研究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转变成为一场装满橡皮子弹的语言和文化斗争。与其说是炮火连天的战争,不如说是装点后现代社会和消费主义的绚烂烟花。”[32]
(四)聚焦领域:走向媒介文化
大众传播媒介本来就在催生、塑造、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由于“新媒介”(new media,一译“新媒体”)的诞生,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更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观。比如,当今的视觉文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显然与新媒介的技术革命与媒体视觉化有关。以中国为例,以往学界往往把春节联欢晚会看做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如今却有学者认为,“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个典型的‘视觉事件’,它所包孕的复杂意识形态特性和象征内容,以及显而易见的视觉性和广泛影响力,足以说明媒体视觉化的重要性。”[33]这也意味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内容恰恰是通过视觉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视觉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包装与制作除了让大众文化变得更加‘好看’之外,还降低了进入大众文化的门槛,也进一步让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轻浅之物。”[34]而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印刷媒介独领风骚的时代显然不可想象,只有在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形成某种媒体霸权的今天,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大众文化研究开始聚焦媒介文化。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甚至认为,用“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取代“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更方便于展开研究。他指出:“‘媒介文化’这一概念既可方便表示文化工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能表明它们的生产和发行模式(即媒介技术和产业)。它避开了诸如‘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类的意识形态用语,同时也让人们关注到媒介文化得以制作、流布和消费的那种生产、发行与接受的循环。此概念也消除了介于文化、媒介和传播等研究领域间的人为阻隔,使得人们注意到媒介文化体制中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打破了‘文化’与‘传播’间的具体界限。[35]60,34-35凯尔纳之所以会如此思考,是因为他意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美国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甚至“媒介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宰制力量”。[35]31,17因为媒介文化的视觉等形式已经排挤掉书籍文化的传统模式,从而制造了新的风格,时尚和趣味。于是,媒介文化这一称谓便成为后工业时代或后现代社会的一种事实指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凯尔纳才说:“‘媒介文化’一词还有一个好处,它表明: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媒介文化。”[35]61,35
以往的大众文化研究虽然也关注过大众媒介(如法兰克福学派),但往往是蜻蜓点水,其论述并不集中、系统。而它们的聚焦点或者在文化生产方面(文化工业如何制作大众文化),或者在文化消费领域(如受众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依然显得不够完善。而聚焦于媒介和媒介文化,则意味着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这样,走向媒介文化意味着大众文化研究打通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领域,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当然,这种转向也会带来一些研究隐患,比如,大众文化研究有可能会变得“见物不见人”,甚至会落入“媒介决定论”的陷阱。
四 结语
以上无论是梳理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还是分析大众文化的演变轨迹和研究走向,其实都涉及对大众文化理论的认识和理解问题。笔者以为,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至今,虽名目繁多、色彩纷呈,但追根溯源,它们差不多都可看作“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和“符号学”的变体。因此,我们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统领下的大众文化研究、罗兰·巴特借助于符号学所进行的大众文化剖析、伯明翰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究,看作三种最具原创性的大众文化理论。当然,它们不仅仅是理论,而且也是研究大众文化的思想资源,观照大众文化的基本视角,进入大众文化的主要路径。同时,它们也正好构成了大众文化理论的德国传统、法国传统和英国传统。
那么,该如何对待这三种传统呢?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西方学者的观点。早在1980年,格罗斯在比较了阿多诺、洛文塔尔和罗兰·巴特的大众文化研究方法之后就曾指出,三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均有可取之处又都有不足之点。研究大众文化最有希望的趋势也许存在于符号学与批判理论的融合之中,而这种融合的迹象已经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艾柯与波德里亚等人的研究中体现了出来。[18]140而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凯尔纳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进行比较,也在反复申明如下观点:两派拥有共同的观点又都有不足之处,所以它们亟须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对话,通过对话可以相互为对方提供一种有效的视角。[36]而新近一种更激进的观点则认为,为了使“文化研究”走出日趋低迷的困境,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因为只有法兰克福学派才能“将文化研究从目前的批判昏睡中摇醒”。[37]
以上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因为“‘理论’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它们是用以阐明特定现象的眼光,但是其中也有某些限制了其注意力的盲点和局限”。[35]42此外,我们还要意识到,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形成于既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是对当时现实问题的回应。而时过境迁之后,理论便会呈现出某些不足和缺陷。因此,不存在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理论,存在的很可能是魅力与缺憾并存的理论。而把诸种大众文化理论还原到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之中,释放其魅力,指出其缺憾,并让它们构成一种丰富的对话关系,从而相互矫正、取长补短,应该构成我们对待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态度。
[1]Löwenthal,Leo.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
[2]Burke,Peter.“The‘Discovery’of Popular Culture,”in Raphael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1:216-117.[英]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杨豫,王海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11.
[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4]Greenberg,Clement.“Avant-Garde and Kitsch,”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eds.Mass Culture: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M].New York:Free Press,1957:102.
[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意]翁贝托·艾柯.丑的历史[M].彭淮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394.
[7]Macdonald,Dwight.Interviews with Dwight.Macdonald[M].Michael Wreszin,ed.Jackson,MS: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3:98.
[8]Macdonald,Dwight.“A Theory of Mass Culture,”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eds.Mass Culture: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M].New York:Free Press,1957.
[9]Adorno,Theodor,W.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1:85.
[10]Pells,Richard,H..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思想[M].卢允中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315.
[11]陆 扬,王 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41.
[12][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12.
[13][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29-136.
[14]Denning,Michael.“The End of Mass Culture,”in James Naremore and Patrick Brantlinger,eds.Modernity and Mass culture[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258.
[1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18-119.
[16][英]斯科特·拉什,[英]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M].要新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7]赵 勇.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J].文艺争鸣,2009(11):25-31.
[18]Gross,David.“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J].Telos,no.45(1980):127.
[19]王 朔.无知者无畏[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2.
[20]程 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1][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5-188.
[22][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M].易晓明,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83.
[23]Barker,Chris.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Thousand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60.
[24][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34.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6]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长篇小说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146.
[27][美]安德烈亚斯·胡伊森.大分野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M].周 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8][英]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M].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9,1.
[29][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424.
[30][澳]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吴松江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22-224.
[31][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32]旷新年.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J].天涯,2003(1):20.
[33]周 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
[34]赵 勇.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J].文艺研究,2010(9):16.
[3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丁 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译文据原文有改动。Kellner,Douglas.Media Culture:Cultural Studies,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36]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The Missed Articulation,”in Jeffrey T.Nealon and Caren Irr eds.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31-58.
[37]Imre Szeman.“The Limits of Culture:The Frankfurt School and/for Cultural Studies,”in Jeffrey T.Nealon and Caren Irr eds.Rethinking the Frankfurt School:Alternative Legacies of Cultural Critique[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