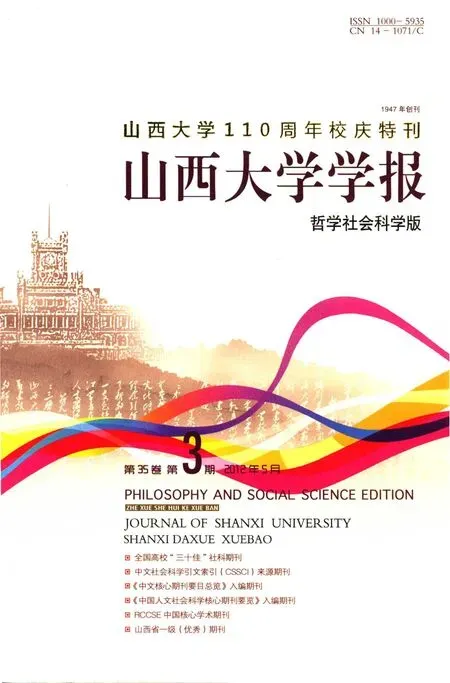民国大学体制下的学分南北
2012-04-13沈卫威
沈卫威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一 大历史与小细节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兴学之风日盛。在西方传教士所属教会办学的影响下,清政府自己所创办的大学仅有天津的北洋大学堂(1895)、上海的南洋公学(1896)、北京的京师大学堂(1898)、太原的山西大学堂(1902)等。
1905年,延续千年的封建科举考试体制消解。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新建,为现代大学的确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大学的命运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重建捆绑在一起。学术研究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尊严与地位,而“文化是每个时代固有的生命体系”,又是“时代赖以生存的生命体系”[1]82。是“现代大学”这个新兴的场域,将国家、民族、知识、知识分子、教育、公共社会联系在一起。
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5月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特别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8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学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大学理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382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潘光旦家与闻一多、吴晗、傅斯年、杨振声等几位教授谈论时局至深夜,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3]184
在讨论这一议题的开始,我引述两位著名大学校长的言论,是要确立本文基本的学术立场,同时关注历史细节。
1909年秋的某日,梅光迪在上海吴淞江上经胡绍庭介绍与胡适相识。
1916年12月26日上午9时,蔡元培到前门外的一家旅馆找到了陈独秀。
新文化、新教育和新文学从此与这四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民国时期的大学学术研究也因此形成新的格局。
据绩溪人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原名《回忆亚东图书馆》,1983年版)一书引用其叔父汪孟邹《孟邹日记》披露,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早上9时,蔡元培就到前门外的一家旅馆找到了陈独秀,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4]36。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胡适,说胡适实属可胜任文科学长一职的最上人选。随之,陈独秀立即致信在美国的胡适,说“蔡孑民先生已接任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5]6。
皖人进入北京大学,背后实际有“皖系”强大政治势力的涌动,和“皖系”间可利用的关系或可钻乘的政治空隙。陈、胡借助《新青年》搅动了中国的大政治、大文化,随后形成胡适派文人逐渐取代浙江章太炎弟子控制北京大学文科的局面。原本属于反清革命或与革命有关联的浙籍学者控制北京大学文科的局面,在1930年代因文化保守而被胡适派文人所取代。大历史背后有小细节,而所有的细节都是人为的。新文化、新北大、新文学关联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三个关键人物。民国学术的新旧、左右之分,西学中学、激进与保守之别,也与之相关联。
与此同时,另一股文化势力也正蓄势待发。
梅氏为清代名门望族,文艺家与数学家辈出,被梅光迪誉为“在中国族姓中实为最光荣之一也”[6]561。为了家族的荣耀,梅光迪和胡先骕一样,都是12岁即参加科举考试。在1905年科举废止后,他们成了真正的文化遗民。尽管后来有留学的机会,但他们要保住自己的这份文化身份和曾经的荣光。1910年和胡适已经成为朋友的梅光迪,在同胡适一起赴北京参加的留美庚款考试中落榜,次年重考赴美。1915-1917年间,他与胡适就白话文、白话新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把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受陈独秀之邀,乘新文化运动的大势归来,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大获成功。最初,这本是两个朋友之间的事,却因此改变了民国文学的历史,也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
接下来,“学衡派”阵地东南大学的人文学者与北京大学“新青年派”的对立,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梅光迪。他是1918年8月与吴宓在美国相遇,因谈话投机而相约回国后与胡适再战。据《吴宓自编年谱》所示:
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显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大战。……
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驱驰,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云。[7]177
1921年,梅光迪放弃南开大学的教职到东南大学,联合吴宓创办《学衡》,就是要纠集力量,再战胡适。
1922年1月《学衡》创刊,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势力形成。南北两所国立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学术理念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学分南北的局面。“学衡派”主要成员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所展示出的身份,是信念坚定、立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胡适派文化激进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他们拒绝写白话文,坚持自己保守的文化主见,以固有的信念和道德力量,强化自己心中的文化情结和文化托命意识,决不随新文化之波逐流。
我在评价《梅光迪文存》时,曾指出“学衡派”成员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过程中所呈现的道德力量和文化信念的忠诚感这一问题。[8]也就是说,南北对立,首先是“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并由此牵扯出大学人文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观念与治学方法上的差异。
1924年秋,群聚东南大学三年的“学衡派”的势力在南京分裂,随后梅光迪、胡先骕远走美国,吴宓先到沈阳,半年后转回清华,《学衡》杂志编辑部也落脚北京。到1925年柳翼谋(诒徵)北上,《学衡》的四大主力都离开了东南大学。
这时中国的现实生活给梅光迪、吴宓开了个很残酷的玩笑,使他们陷入自己挖坑自己陷进去的尴尬境地。梅光迪从此几乎失语,隐退文坛,实际上也淡出学术界。他在九年后的反思中自觉地承认“学衡派”的失败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6]243。此话是话中有话,因为有一个细节可昭示现实改变了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一个“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的人,到东南大学三年后,爱上了自己的女学生李今英,于是将“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给予他的包办婚姻“革命”了。抛弃安徽乡下的妻子和儿子,与李今英结婚的梅光迪,在这一条道上,比“所言所行之可痛恨”的新文化的倡导者,主张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而自己却就范包办婚姻的鲁迅、胡适走得更快、更远,和完成“家庭革命”的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成为同路人。面对新文化运动,那就只有闭上批评别人的嘴巴,远走他乡,讲授汉语。吴宓紧随梅光迪之后,更浪漫了。两个以反对卢梭以下浪漫主义著称的白璧德的门徒,西洋文学教授,却走上了中国现实的浪漫文人的路,在言行分裂,情感与理智矛盾的极度痛苦中失语(梅光迪),或靠写情诗、写日记(吴宓)来排遣。
在这个让梅光迪、吴宓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特殊时刻,“学衡派”成员郭斌龢就致信吴宓,说他因婚外情导致的离婚有损于他们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的进行[9]56,指出他的思想行为是陷入浪漫主义[9]72。陈寅恪说他“昔日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濒于破裂”[9]60。吴宓因此承认自己生性是个浪漫主义者[9]73。随后他在与女友卢葆华的交往中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里有人文主义道德与浪漫诗情的矛盾[9]441。梅光迪、吴宓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是把前引《吴宓自编年谱》中的“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这句话反讽式地改写了——“胡适、鲁迅说:‘我能倡导。’梅光迪、吴宓曰:‘我必实践。’”
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制的确立得力于胡适,1928年清华改制为大学后文科的基本师资和核心人物(校长罗家伦、秘书长冯友兰、教务长杨振声和中文系教授朱自清、俞平伯都是胡适做顾问的“新潮社”成员)来源于北大。王国维学术的最后辉煌所展示的机会是胡适给予的。
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二 文化理念
(一)反孔批儒作为文化革命的兴奋点
《新青年》因孔教会成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而奋起反孔,鼓吹思想革命。陈独秀从民族国家重建的角度来谋划中国的新生,写了《宪法与孔教》一文,呼吁:“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0]79因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0]34-35
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特别强调在伦理上进行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10]41。要在中国实施民主的共和宪政,就必须废除孔教儒经,代之西洋现代学理和政治规范。他认为当下左袒孔教者,都是心怀复辟企图之辈,他甚至不无偏激地指出,“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11]。随之,钱玄同、胡适、易白沙、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都对陈独秀的言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吴虞更是激烈地去打“孔家店”,要对儒教进行彻底的革命:“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12]
在北京大学,从《新青年》时期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及教授吴虞、胡适、鲁迅(兼课)、周作人,到“文革”后期的“四皓”(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有一条十分明显的反孔批儒的师承线索。当然,两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不同,有主动与被动之别。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思想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反孔、批孔:打孔家店是北大一部分教授的重要活动;反孔、批孔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显现行为之一。1970年代中国大地的“评法批儒”、批孔浪潮,同样是初澜于北大。特别是胡适,直到晚年,仍然拒绝担任台湾“全体大专院校校长集会”组织的“孔孟学会”的发起人。他在致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说:“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发起人之一。”[13]415他觉得“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
(二)尊孔作为文化保守的立足点
1906-1911年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的李瑞清在《诸生课卷批》中主张“奉孔子为中国宗教家,吾愿吾全国奉孔子为教主”[14]41。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制为南京高师时,校长江谦所写的校歌歌词中有“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尊孔成为这所学校的传统。
1922年1月在东南大学创刊的《学衡》杂志,第一期上所登的图片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学衡》是公开表示尊孔的,这和《新青年》是公然的对立。“学衡派”成员中的哈佛大学白璧德门徒,受导师的影响较大,因为“白璧德倡导新人文主义,对于孔子备极推崇,以孔子为人文主义极大权威”[15]11439。为《学衡》写文章的沈曾植、朱祖谋、陈三立、张尔田、孙德谦同时也是1912年10月7日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孔教会”的重要成员。其中沈曾植、朱祖谋、陈三立位列13位发起人之中。沈曾植本人也是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的积极支持者,其文化保守的性质十分明显。而张尔田、孙德谦为1913年2月创刊的《孔教会杂志》的编辑。张、孙两人为《学衡》写文章,是吴宓1923年9月3日亲自到上海约成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打孔家店高潮时,柳翼谋开始在南京高师讲中国文化史,他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16]2631932年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中央大学的教授在《国风》第3号出了“圣诞特刊”,以纪念孔子。卷前有孔子像、曲阜孔林照片各一幅。这期纪念孔子的“圣诞特刊”,也是“学衡派”对“新青年派”批孔反孔的总的反攻、总清算。当然也含有林语堂所说的提倡尊孔者“借此以报复青年者”的另一层因素。该期特刊中有柳翼谋、梅光迪、缪凤林、郭斌龢、范存忠、唐君毅的文章,从整体上为孔子重塑形象,也是从古代出发重新确立其现代价值。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第一次有意识的集体文化行为。
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翼谋到中央大学的张其昀、郭斌龢,发展到中国文化大学时期的张其昀的尊孔,“文革”时期吴宓的反对批孔,1980年代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的《孔子评传》,形成了这一学统与北京大学的尖锐对立。
三 历史观念
(一)疑古、释古史观的集中体现
“古史辨”讨论是在北京大学的师生胡适、钱玄同、顾颉刚、魏建功等与东南大学的师生柳翼谋、刘掞藜、缪凤林之间展开的。北京大学一方的怀疑与东南大学一方的信奉,形成尖锐的对立,并由此引发“整理国故”运动的深化。1921年7月31日,胡适应刘伯明主持的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17]392时,主张研究国故要有怀疑、批判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在“古史辨”论争中所产生的南北“对立”,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其中的关键“是精神上的不一致”[18]。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19]。特别是胡适“一切古书皆史也”的观点,是对元代郝经首倡,清人袁枚、章学诚系统张扬的“六经皆史”的继承。他的这一学术思想的基础是进化论。其实胡适早在1917年1月《科学》上刊发的《先秦诸子进化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荒诞神怪的万物原始论都不可算作进化论。进化论的主要性质在于用天然的、物理的理论来说明万物原始变迁一问题,一切无稽之谈,不根之说,须全行抛却。”[20]9胡适尤其不认同当时“中国学会”章程中第一条“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的说辞。他在1928年11月4日回复泾县友人胡朴安要他加入学会的信中强调:“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端。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21]606
1930年7月,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提出历史研究中要有“了解之同情”,对“古史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偏颇和局限提出了相应的修正。陈寅恪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先刊《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32期,1930年7月21日)中提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22]而“了解之同情”一语的源流来源自德国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赫尔德[23]。此术语在中国学界最早出现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胡梦华发表在1922年4月29日《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评〈学衡〉》一文。他在文中强调:“批评者第一要素是了解的同情。”①此文收入胡梦华、吴淑贞合著的《表现的鉴赏》,现代书局,1928年版。此处的引文则是用1984年的自费再版本(台湾)第145页。
从“疑古”到“释古”,学术的路向在变,“了解之同情”态度的介入,使得学术的信念也发生了变化。
(二)信古史观的集中体现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师生“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的“信古”史观,多是在传统史学中打转,这在柳翼谋、刘掞藜几乎相同的历史研究方法上有特别的昭示。这一学统的历史观念直接来自柳翼谋,并影响到他后来的一代学生。先有柳翼谋发表在1921年11月1日《史地学报》创刊号上《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对胡适历史研究的批评,继之是“古史辨”讨论中的对立,到1930年代缪凤林对傅斯年民族史观的批评,以及吴宓的“道德救国”[24]与胡适的“民族反省”①在1932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国耻一周年,胡适为《独立评论》作了《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的不同理路,都反映出两大学统史学观念的差异。
四 学分南北
关于学分南北的史实和细节,我在《“学衡派”谱系》一书中已有初步的梳理。学者桑兵、罗志田、陈平原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写有专门的文章。这里主要是依据新的材料,作进一步的学理提升。钱基博1926年12月1日在为《国学文选类纂》写的《总叙》中,对民国初期大学学分南北的局面有如下概括:
清廷既覆,革命成功,言今文者既以保皇变法,无所容其喙;势稍稍衰息矣!而章氏之学,乃以大白于天下!一时北京大学之国学教授,最著者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辈,亡虑皆章氏之徒也!于是古学乃大盛!其时胡适新游学美国归,方以誉髦后起讲学负盛名,……于是言古学,益得皮傅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而新汉学,则以疑古者考古……在欲考见“古之所以为古之典章文物”……万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横绝一世,莫与京也!独丹徒柳诒徵,不循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号曰“学衡派”。世以其人皆东南大学教授,或亦称之曰“东大派”。然而议论失据,往往有之!又因东大内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无以大相胜![25]11-12
钱基博的看法合乎历史事实,但他进一步将南北差异定位于“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义”、“数”之别,则同“学衡派”的吴宓对这两种主义的解说相差极大。
(一)新材料、新问题作为北方学人“预流”的基本要求
民国元年,取法西方大学学科与学制的一纸《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将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格局和研究范式整合进“七科”(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之一的文科,同时也将其分解在文科的文学、史学、哲学、地理学四个学科门类之中。第二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令第一号》(1913年1月12日)的《大学规程》第二章《学科与科目》,又将文学门分为国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言语学。章太炎所谓的国学(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人物、典章制度。他还将其具体分类为经学、史学、小学、诸子、文学)也被新的学科和科目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使得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如蔡元培所说的大学要成为“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2]451。这也正是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新文学等现代思想的策源地的缘由。随后,清华国学研究的四大导师,将清华的人文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王国维从早年的诗词创作、文学批评转向国学研究。早在1911年《国学丛刊·序》中他就明确表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②见《国学丛刊》第1册,又见《观堂集林·观堂别集》卷四第7页,《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二次影印本。。这实际上是要张扬一种学术独立和价值中立的学者的立场,如同胡适所说的,辨认出一个甲骨文字与发现一颗小行星同等重要。
1925年7月27日上午9-11时,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工字厅为学生消夏团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演讲的文稿被包括《学衡》(第45期)、《清华周刊》(第350期)在内的多家刊物登出,影响甚大。王国维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的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日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案,中国境外之古外族遗文。他强调今日之时代为“发见时代”。[26]49
随后,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的长文,对上古之事中的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7]2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8]266他所说的新材料主要是指殷商考古(甲骨文等)、敦煌文献和明清内阁档案。
王国维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讯导师和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住校导师,同时也是新的学术方法典范的开创者和实践者①1917年,胡适考察了上海的出版界后得出的结论是:“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到:中国现今的学术界“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三人是胡适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与胡适的门生傅斯年是德国留学时的同学(后来又是姻亲关系)。王国维进清华是胡适、顾颉刚师生两人共同推动的。据顾颉刚回忆,推荐王国维入清华的主意是他向胡适提出的[29]16。他在1924年12月4日的日记中记有:“写适之先生信,荐静安先生入清华。”[30]557查胡适的档案,果然有顾的来信[31]291。
这里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关系。
顾颉刚的日记中记有他1923年3月6日的梦后追记:“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同至蒋企巩家。……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先生果能与我携手耶?”[30]333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也,今夜又梦与静安先生同座吃饭。”[30]471
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顾颉刚于1924年4月22日致信王国维,表示:“拟俟生活稍循秩序,得为一业专攻,从此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未识先生许之否也?”[30]479所以他想让胡适举荐王国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出于真心实意。
同时,他对王国维关于“古史辨”的态度也十分重视。1926年7月30日张凤举告诉他,王国维认为“古史辨”讨论中“固有过分处,亦有中肯处”[30]773。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顾颉刚所列出的“应赠送至人”[30]799中,就有王国维。
王国维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247。这是对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更为明晰的演示和总结。同时陈寅恪又在学术研究中提出了以诗证史或史诗互证。因此,我将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归结为“四个二重证据法”。
受胡、王、陈影响的学生很多。其中顾颉刚、傅斯年将自己学术思想和方法的路向明确规定为:“历史文献考证”加“田野调查”。特别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将国学细化为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后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循着这个路子。这就是顾颉刚所总结出的: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民众中调查搜集方言、到人间社会中采风问俗。这样就可以打破偶像,摈弃成见,建设“新学问”[32],成为傅斯年所期待的真正“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1927年6月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别称道胡适对王国维的知遇之礼:“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1929年6月,为纪念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清华研究院为其立碑。陈寅恪在为王氏写的碑铭中强调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学术和学者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陈垣、李济、傅斯年、顾颉刚在北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重视新材料、新问题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燕京大学处于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
胡适与傅斯年、顾颉刚为师生关系。在王国维去世后,胡适与陈寅恪的关系呈现出彼此信任和敬重的局面。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香港,院长之空阙亟待填补。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被推举为院长候选人之一,国内学术界不少人都认为院长之位非胡适莫属。对此,“素不管事之人”的陈寅恪,“却也热心”:在1941年3月,他专程从昆明到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选举会议,目的只是为了投胡适一票。此事傅斯年在信中告诉胡适(“如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并说:“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由]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33]475胡、陈彼此的信任,使得他们在1948年12月15日能够同机离开北平(实际是胡适让秘书邓广铭找到陈寅恪,把陈寅恪带出北平)。
五四高潮过后,国文系的吴梅、黄侃,历史系的陈伯弢(汉章)、朱希祖都相继离开了北京大学,最后融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吴是1922年秋,黄、陈是1928年春,朱是1934年春)。
就朱希祖而言,因浙人蔡元培执掌教育部,何燏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2年12月-1913年11月),1913年4月随大批章太炎弟子入北京大学为师,在1931年1月被迫辞职之前,长达10年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1931年10月,陈受颐任系主任,学术权力逐渐为胡适派势力(傅斯年、姚从吾等)所把握。
自胡适1931年出任文学院院长到1934年4月兼任国文系主任,章门弟子把持文史两系系主任位置的局面宣告结束。其中马裕藻(幼渔)任国文系系主任长达14年。而马的下台,傅斯年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给校长蒋梦麟的信中说“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罪魁马幼渔也”[34]531。
至于哲学系的师资和系主任的聘任,也多受胡适的较大影响。汤用彤是1930年经胡适推荐入北京大学的,1935年以后长期出任系主任。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也是胡适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所以,1936年8月接替陈受颐出任史学系主任的姚从吾,在1937年3月19日给傅斯年的信中有如此亲切和实在的表达:“弟在母校教书以外,只想在适之先生与兄的指导下,从事私人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史学系,比较已走上轨道,兄既不在北平,适之先生多事,……我的希望是在适之先生与兄的领导之下,循序发展……”[35]114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胡适及其学生故旧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实际影响力,以及他们掌握了学术话语权后所呈现出的霸权性。
概言之,北方大学人文学术的基本品格明显昭示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品行;学无古今、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无左右之分的学术视野和学人胸襟;新材料、新问题作为“预流”的学术标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注重四个二重证据的治学方法。
(二)旧学的继承与坚守作为“东南学风”的立足点
王伯沆、柳翼谋及东南大学师生所彰显的反对北京大学主导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精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的“东南学风”[36]119。柳翼谋在《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中说:“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37]1926年胡先骕在《东南大学与政党》一文中特别强调说:“东南大学与政党素不发生关系。言论思想至为自由。教职员中亦无党派地域之别。”东南大学“为不受政治影响专事研究学术之机关”[38]。这话的另一层含义是批评北京大学与北洋政府及国共两党的关系过于密切。
当时(1923-1926)的东南大学学生,后为近代史学家的郭廷以,在口述自传中的说辞是,江谦(易园)是理学家,学问修养都好,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朴实风气。“当时学监陈容(主素)和稍晚一点的王伯沆、柳诒徵等都是讲理学的先生,循规蹈矩的,无形中养成了南高朴实的学风”[39]83。同时他将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精神方面,东大先承江易园先生等之理学熏陶,后继以刘伯明先生主讲哲学之启发,学生均循规蹈矩,一切都不走极端,既接受西洋文化,亦不排斥我国固有文化,因此学生虽鲜出类拔萃人物,但太差的也没有,这与北大恰好相反。”[39]91
现代人文学术和传统人文学术的重要区别在于科学、民主观念的彰显,代表传统学术向现代新学术转变并为之确立学术范式的王国维、陈寅恪本是吴宓拉进《学衡》杂志的“学衡派”的成员,但他们的学术工作却和北方现代新学术的重要人物胡适有思想、方法上的共性。王国维的学术工作在章太炎、黄侃看来就是新学。尽管王国维不主张将学术分出个新旧、中西、有用无用来,但在章黄学派看来仍然是胡适的同类。章太炎不相信甲骨文,黄侃也曾嘲笑王国维求新[40]302。
王伯沆以讲授“四书”著名,同时又以评点学见长,不作长文或专门著作。柳翼谋以史学见长,他的学术精神基本上是传统的继承,在方法上仅吸收了由欧洲传入日本的宏观写史之法,他的《历代史略》就是“根据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增删而成”[41],[42]93。胡适在肯定他的《中国文化史》是“开山之作”[43]151、承认他所开的“文化史”体例的同时,也指出其中的新材料不够。柳翼谋的史学观和学术方法(胡适将其总结为“勤奋而太信古”)的影响主要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时期,他的学生缪凤林、刘掞藜继承了他的学统。缪凤林喜好写通史通论。刘掞藜的《史法通论》[44]与柳翼谋的《国史要义》[45],颇多相同之处。
顾颉刚就曾对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柳翼谋的弟子表示过不满。他在1938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张其昀所著《中国民族志》,此君平日颇能留心搜集材料,惟不能融化,又不能自己提出新问题,发见新事实,故其著作直是编讲义而已。……张君与陈叔谅对我颇致嫉妒,待数百年后人评定之可耳。”[46]53
掌握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是学术增长的重要条件。相对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术研究,中央大学研究精神上的“略有欠缺”和研究“风气不盛”,还另有原因。那就是1927年首都南迁后,中央大学的教授“近官”。1930年代关于“京派”与“海派”之争时所谓的“京派”近官,“海派”近商之说,是有特指的时段。南京成为国民党政府首都之后,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的地位和优势正好颠倒过来,真正“近官”的则是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东南大学毕业生,随后为中央大学教授的郭廷以在口述自传中承认:“战前四五年间,全国的教育、学术进步很快,这应归功于教育部长朱家骅。待遇提高,中大教员都是规规矩矩的教书,但论研究精神则略有欠缺,这是因为课多而且接近政府的缘故,许多教员混资格‘做官’去了,所以赶不上清华,清华安定、条件好。周炳琳就说过‘中大是不错,但好像是缺少甚么,研究风气不盛。’”[39]145
在新旧文学之争中,南北的差异性表现更为明显。“学衡派”和章门弟子把持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校园,不允许新文学进课堂。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的国文系都开始有专门讲授新文学的课程,中央大学直到1949年改制,始终没有让“新文学研究”这门课进入课堂。中央大学毕业生钱谷融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特别指出:“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47]144。
学风的差异,与师资有很大的关系。经过短暂的浙江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长之后,蒋梦麟于1930年至1937年7月,第二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对文科师资的聘任,多是听胡适、傅斯年师徒两人的意见。余姚人蒋梦麟曾在绍兴求学,与蔡元培有乡谊之情,他接替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最长。他与胡适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1934年,胡适在准备聘任兼通中西文学的朱光潜、梁实秋之前,先行解聘了多年无学术成果的中国文学教授林损、许之衡。蒋梦麟在《忆孟真》一文中写道:“当我在民国十九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48]332
传统国学中的“经学”和“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一直是“章黄学派”的强项,并在中央大学文科形成势力。当然,中央大学的保守势力也非铁板一块,而是同中有异,或同而不和。除了胡小石重视甲骨文外,中央大学文史专业的其他教授都不染指。这是“小学”与甲骨文这门“新学”之间的学术屏障。胡小石有过1920—1922年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特殊经历。这段北京生活,对新发现的被王国维称之为“新学问”的甲骨文的接触和重视,改变了他治学的方向。1925年9月回到南京任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开始讲授甲骨文,后成《甲骨文例》一书。1927年8月改任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学(次年改为中央大学)教授后,他一直坚持这一研究,并延伸到金文,作《金文释例》。在日后黄侃与吴梅的矛盾冲突中,他是站在吴梅一边。这样在中央大学的文史教授中实际上形成章黄弟子与吴、胡的两派势力冲突。双方矛盾、冲突的焦点是治“经学”、“小学”的黄侃对吴梅词曲之学的鄙视(“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49]8,[50]490)和对胡小石研究甲骨文(“新学”)的排斥。
早年还写作白话文的章太炎,晚年趋向保守,不近新学,尤其排斥甲骨文。据黄侃日记和杨树达回忆录[51]126所示,黄侃晚年对甲骨文的看法有所转变,他购买了多种有关甲骨文的书,但多没有来得及读。杨树达敬重黄侃在传统的“经学”、“小学”研究中的见识,曾特别让其侄子杨伯峻到黄侃那里拜师求学。但他对黄侃嘲弄王国维学问求新这一点,则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在1944年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读王静安《尔雅草本虫鱼释例》,穿穴全卷,左右逢源,千百黄侃不能到也。”[51]208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文化保守的势力,主要是章太炎弟子、原南京高师文史地专业柳翼谋师徒和“学衡派”成员梅光迪、吴宓三股力量的聚合,其中梅、吴所在的时间较短。而柳翼谋师徒本有自己的刊物《史地学报》作为学术阵地,在《学衡》创刊后也加盟“学衡派”。“学衡派”势力1924年在东南大学分裂后,柳翼谋师徒则延续“学衡派”的实际影响力,在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分别以《国风》、《思想与时代》、《史地杂志》群聚人气,将“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
[1]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梅贻琦日记(1941-1946)[M].黄延复,王小宁,整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4]汪原放.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梅铁山,梅 杰.梅光迪文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吴 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
[8]沈卫威.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命运[J].中国图书评论,2011(6).
[9]吴 宓.吴宓日记:第Ⅴ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1]陈独秀.复钱玄同[J].新青年,第3卷第4号.
[12]吴 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J].新青年,第3卷第4号.
[13]胡 适.胡适全集:第26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4]李瑞清.清道人遗集:卷二[M].上海:中华书局,1939.
[15]张其昀.《梅光迪先生家书集》序[M]//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
[1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7]胡 适.胡适全集:第29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8]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M]//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
[19]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M]//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
[20]胡 适.胡适全集:第7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1]胡 适.致胡朴安[M]//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2]陈寅恪.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J].学衡,第74期,1931年4月.
[23]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20-32.
[24]吴 宓.道德救国论[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14期,1932年2月.
[25]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M].傅宏星,编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6]吴 宓.吴宓日记:第Ⅲ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7]姚淦铭,王 燕.王国维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9]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0]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
[31]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4.
[32]顾颉刚.发刊词[J].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号,1927年11月1日.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5]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册[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
[37]柳诒徵.送吴雨僧之奉天序[J].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
[38]胡先骕.东南大学与政党[J].东南论衡,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27日.
[39]郭廷以口述自传[M].张朋园,等整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40]黄 侃.黄侃日记[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1]区志坚.历史教科书与民族国家形象的营造:柳诒徵《历代史略》去取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内容[M]//冬青书屋同学会,编.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42]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中国史的建立[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
[43]胡 适.胡适全集:第1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4]刘掞藜.史法通论[J].史地学报,第2卷第5、6期.
[45]柳诒徵.国史要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四卷[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
[47]钱谷融.闲斋忆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8]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
[49]学林漫录:第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0]吴 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