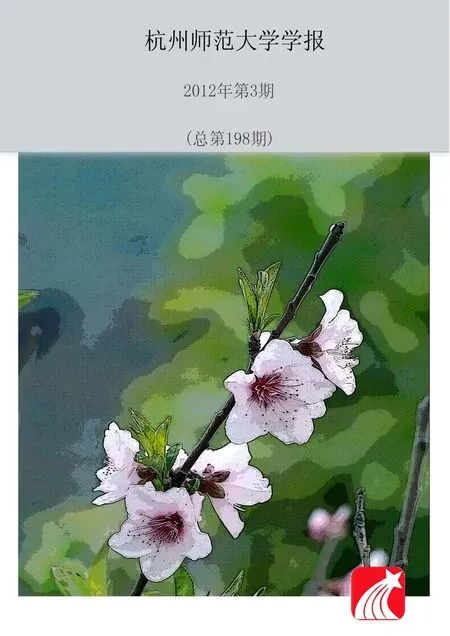从培养“贤妻良母”到造就“社会人”
——近、现代小说里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变革
2012-04-13陈桃兰
陈桃兰
(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教育与教学研究
从培养“贤妻良母”到造就“社会人”
——近、现代小说里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变革
陈桃兰
(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女子教育一直是近、现代小说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近、现代小说不仅蕴含有丰富的女子教育思想,还记录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变革过程,其变革路径在小说中清晰可见。清末民初,小说家配合教育救国的时代呼唤,主张兴女学,积极为女子争取教育权利,强调培养“贤妻良母”的重要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五四”个性解放,小说家把重点逐渐从提倡女子教育转移到男女教育平权的实现方面。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子开始走向社会,培养“社会人”成为新的教育目标。
女子教育;社会人;小说;男女平权
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基本上是一部女性失声的历史,“女子无才便是德”堂而皇之地成为限制女性受教育并防止她们觉醒与反抗的道德训条,延续了1300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更是无情地剥夺了女子走仕途的权利。随着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开展和深入,那些深受传统礼教束缚的妇女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解放妇女成为近现代民主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女子教育也开始备受人们关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强调妇女觉醒、女子教育对于国民崛起、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小说家们不仅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还积极倡导女学,记录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从培养“贤妻良母”到造就“社会人”的发展变革过程。
一 倡办女学,为女子争取教育权利
近代对女子教育的倡导与妇女解放的诉求是同时起步、共同发展的,女子教育权利的争取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只能遵从“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道德准则,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男权文化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主体意识一直被压制。妇女不仅被完全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且仅有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男尊女卑社会定位的不断维护和强化方式。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的坚船利炮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国人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反省。晚清走出国门的部分士人和留学生,发现西方女子颇受尊重。王韬1867—1869年在英、法游历时,发现英国的教育“女子与男子同”,婚姻家庭方面“女贵于男。婚嫁皆有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1](P.107)1876年李圭参加美国世界博览会发现,“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2](P.180)一些女性如单士厘等外交人员的眷属,在西方男女平等的社会中,其自我意识受到触动。受东西方妇女观念的不断影响,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中国传统的妇女地位问题。他们逐渐认识到:妇女不能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从事各类社会活动,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之一。于是,他们开始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批判歧视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摧残妇女身心的缠足陋习,倡办女学。随着广大妇女日益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中国的妇女观念开始逐渐出现了背离传统的倾向,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及缠足等陋习受到舆论的质疑与挑战。《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以女性为读者的报刊先后问世,它们竭力鼓动女子放足、上学、自立;《大公报》《苏报》《湘报》等也积极倡导女学、敦促妇女解放。小说家也加入了妇女解放的洪流,在各类报刊上积极发表各类小说作品,倡导女子教育,呼唤全社会重视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
近代对女子教育问题的认识是与救亡和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强调女子作为“国民之母”应尽的义务。因而,关注女子的才学问题及对教育权利的呼唤,成为清末民初妇女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些小说在急需重塑国民人格的现实下,大力呼吁普及女子教育。女子在晚清民主启蒙语境中,被提升到了“女国民”、“国民之母”的地位。众多小说喊出了男女教育平权的呼声,塑造了许多理想的女国民形象。如《东欧女豪杰》(岭南羽衣女士)为女子鸣不平:“你看那古今东西历史上,英雄的招牌,都被他们男子汉占尽……开口便道甚么大丈夫,甚么真男儿。难道不是丈夫、不是男儿,就在世界上、人类上分不得一个位置吗?这真算我们最不平的事了。”[3](P.33)小说中的女留学生学识、豪情并具,抱负丝毫不逊于男子。《中国新女豪》(思绮斋藕隐)讲述了曲阜辅圣女学堂的学生黄英娘受教育及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她学习优异,被官派到日本留学,入早稻田高等女学深造。在日本求学期间,黄英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任留日女学生组织“恢复女权会”的顾问员。回国后,她又任“妇女自治会”会长,为女子积极争取权利。黄英娘认为:恢复女权应从兴女学、尚自治入手。最后,在黄英娘的努力及皇后的帮助下,中国妇女自由择业、婚姻自主,更定新律,废除了以往所有男女不平等之法律。除政治军役两项女子不得干预外,女子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在小说中实现了男女平等的乌托邦。与黄英娘相似的还有《女子权》(思绮斋著)里的贞娘,她甚至为女子争得了参政权。故事发生在假想的1940年,小说力主开放女权,盼望中国妇女摆脱男子羁绊而发奋自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黄绣球》(颐琐)中的黄绣球则是一位蜕旧变新、积极争取妇女解放的女性。她本来从夫姓黄,丈夫懂得新学、思想开明。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日突然猛醒:女人也应像男人一样走出家庭、做更多的事情。于是她自己放了脚,与儿子一起听丈夫讲世界知识,在家开讲坛,劝说村里的妇女解放自我,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绣球”,决心做一番大事,使地球锦绣一新。黄绣球和丈夫一起办学校,宣传放足,组织义勇队、女军,实现一县自治,在社会上打出一片天下,“替黄种生色”。小说表现了以自由、平等、开智为思路的女性解放思想,女子接受教育则是开智、获得自由、平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小说中塑造的这些新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也不再是卑贱的弱者,而是有着崇高理想和独立自主意识的女中豪杰。她们强调女国民与男国民的平等地位,因而都接受了与男子同样的教育,表现出男性化的气质。她们不仅有聪明的才智和非凡的学识,而且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在社会上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些小说表明,晚清时代的女性理想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妇女解放的脚步,千百年来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然而,女子教育从无到有需要经历一个慢慢被人们接受的过程,况且,教育成效也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当小说家在描述这些成功女性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女子教育才刚刚起步,鲜有知识女性作为小说人物的模板。因此他们大多凭借憧憬与想象来描写女子教育或女知识分子形象,且在描写过程中多用夸张手法:这些女性往往突然如醍醐灌顶般顿悟,然后很快就学贯中西,脱胎换骨,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女子教育权利的争取、女学的兴办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这些具有幻想风格的小说在当时起到了号召、宣传与鼓动的作用。女子教育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在中国蹒跚起步,并逐渐在教育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二 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培养“贤妻良母”教育目标的提出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经由进步人士的呐喊与极力推崇,得到了初步发展。部分女子开始走入学堂,甚至走出国门,接受各类教育。但是,由于传统妇女观念根深蒂固,女子教育发展缓慢。“维新”运动之前,除了一些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女子学堂之外,尚无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教育机构。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有识之士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梁启超率先为办女学造舆论,筹经费。他把办女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要“保国、保种、保教”,“非提倡女学讲求胎教不可”。[4]1898年,梁启超在上海开办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宣布其办学宗旨是:“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贤妇之始基。”[5]梁启超明确提出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6](P.19)的教育要求,主要从承认其家庭地位的角度,强调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士人,在把女子教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又把女子培养目标定位在为对丈夫和孩子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样一个传统的框架中,特别强调其家庭教育的责任,明确提出了“贤妻良母”的培养目标。清末民初的小说对女子教育的描写,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社会对女知识分子的素质期望,基本上都反映了这一教育主旨。
20世纪初,在不少大城市及某些县城兴起了一些女塾和女子学校。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记述了醒秋小时候在家塾读书的状况:她们一开始读的书是《三字经》《千字文》,后来读《女四书》《幼学琼林》。但是塾师才学浅陋,且经常请假。醒秋姊妹在这种一曝十寒的教育环境下,“读了将近两年的书,夹生带熟,认识了千把字,书中意义则半点不能了解”,“那时私塾读书是不作兴讲的,在新学风气扇扬下,父亲要求那位伯祖教书时也带点讲解”。[7](P.22)可见,私塾教育非常有限,无非就是教人识几个字。清末女子接受私塾教育者尚在少数,能走入新式学校者更是凤毛麟角。在1907年以前,清政府学制中根本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才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但是无论女子小学堂还是女子师范都非常重视“女德”,强调要“合乎中国礼俗”,“以养成女子德操”为宗旨,女子师范明确规定以《烈女传》《女训》《女孝经》等为修身教材。《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甚至还规定:“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黄绣球》中两个官员评价黄绣球办学很成功,其中一位官员是这样说的:这个“女学堂办得很好”,“大约不过教女孩子们认认字,学学针线”,没有出现妨碍社会秩序和风化的过激言行,“安安顿顿”。[8](P.220)这就是政府官员对理想的女子教育的期望。这所被小说夸赞为中西兼学的女校,细看教学内容也就是识识字、学学女红。在女学刚刚起步,男子绝对掌握话语权的时代,或许只有这样的女校才会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女学才能得以生存。《闺中剑》中的晋夫人“读书甚多,深明大义,又善算术”,[9](P.4)她的成功也主要表现在对孩子实施了科学和人文的现代教育。可见,无论是小说还是教育现实都表明,清末女子教育以识字为基本内容,重视女德的培养,以“贤妻良母”为旨归,女子所接受的是不同于男子的特殊教育。
民国初年,有识之士在晚清倡导兴办女子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女子的家庭地位出发,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叶圣陶在《儿童观念之养成》中指出:“夫于家庭之中,长与儿童共者惟母。故欲使家庭教育之得宜,舍母无所属焉”,因此,“妇女教育,今日何可缓哉”?[10](P.4)不少小说家也通过故事说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女子教育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主张兴女学,培养“贤妻良母”。《苦教员》中黄世廉之妻秦素贞是当时受过教育的理想女性的形象代表。秦素贞是开敏女学的高才生,结婚五年,生了一子一女,主要在家相夫教子。在娘家时,她穿绸着绢,呼奴使婢,安闲自在,婚后料理一日三餐,生活极为简朴,但从未闹过意见。儿子取出一本幼稚识字教科书,请母亲讲解。素贞一面讲书给孩子听,一面逗女儿玩笑。黄世廉不禁感叹:“受过教育的女子,见识毕竟高出寻常女子一等呢!”[11](P.347)秦素贞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不仅能勤俭持家,还拥有知识,能教育儿女。当时社会舆论认可的女子教育即在于培养出像秦素贞一样的女性。女子教育的目标指向不是女性本身,而是下一代及国家未来的前途。
20世纪初,受时代风潮鼓益,部分女子开始走出国门留学。虽然她们人数极少,但非常引人注目。这些女留学生大都学习刻苦、立志高远、生活俭朴。她们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如《六月霜》(静观子)中的秋瑾,冲破种种困难,在日本艰苦求学,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和社会改革事业。《女学生》(尗夏)中的女主人公黄慧贞,父母先后谢世,但她自强不息,得房东妻洪氏资助进女校,后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兴办学堂,颇有成效。小说结尾号召:“但望天下有志女子,看到慧贞的行止,兴起点热心,破除些锢习,那中国女界就不患不出些人才,中国国家也不患不渐致富强了。”[12](PP.27-28)随着留日高潮的兴起,“江浙离日本近,父兄去日者甚多,女妹亦有随之而去者”。[13](P.129)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留学生中有秋瑾一类上进刚强的革命女性,但大多数留学日本的女性所接受的还只是一些基本的语言及家政常识教育。她们回国后除了回归家庭,顶多在学校里当当教员。《东京梦》(履冰)中贾里孝为排谴寂寞,把自己的小妾接到了日本,并送其到学堂学习,认为学点音乐技艺或家政,将来可以回国当女学堂的教习。这类女性在当时不在少数。无论是现实还是小说都表明,当时的女子留日教育水平不高,教育目标也只是培养良妻贤母,还没有提出造就和男子一样的政治、经济、科技人才这种社会人才的目标。
可见,清末民初,无论是国内学校还是留学教育,相比于男子,女子教育不仅程度浅,受教育人数也极少。此时,小说涉及关于女子培养目标问题的探讨,带有“现实主义”的小说大多注重“女性”这一特殊身份,即在家庭中处于妻、母的地位,希望通过教育来提升女子素质,以胜任贤妻良母的角色。可以说“贤妻良母”式的教育贯穿了整个近代。这一培养目标不仅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许多知识分子女性也对其积极意义给予了肯定。在文学家中,冰心具有代表性。1919年冰心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的文章。她为女学生在服饰、言行、社会活动、知识修养等各方面列出了一个“标准”,把“改良家庭”、“家庭卫生”、“人生常识”、“妇女职业”、“普及教育”等看作是解决妇女问题的积极而有实效的“治本办法”。这种“女学生”形象与传统的“贤妻良母”相比,在外形和内涵上更多了一些现代的特征,因此被称为“新贤妻良母”。她在小说中详细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如在《两个家庭》中,她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认为她们游手好闲,不事家政,影响丈夫的事业,摧残丈夫的身心;她肯定了受过新教育、治家教子有方的亚茜。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亚茜这个女性形象就会发现,她只不过是一个镀了一点点西方文明“金铂”的贤妻良母。正如茅盾所说:冰心在小说中“一方面针砭着‘女子解放’的误解”,一方面却暗示了‘贤妻良母主义’——我们说它是‘新’贤妻良母主义罢——之必要”。[14](P.192)冰心作为“贤妻良母”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具有反对封建礼教的积极倾向,“但在她的观念形态中,依然有封建意识的残余”,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青年中普遍的情形。在旧的理解完全被否定,新的认识又还未能确立的过渡期中,青年对于许多问题是彷徨无定的,是烦闷着的”。[15](P.121)冰心妇女题材小说的作品内涵虽有局限性,但肯定了女子教育在改造旧家庭、建立新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对妇女解放及女子教育思想的表述,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和一定的现实性。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贤妻良母”目标的提出,作为实现男女教育平权的过渡性理念,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
三 批判“贤妻良母”主义,提倡培养“社会人”
“五四”前后大学陆续开放女禁,女子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教育权,留学教育也进一步扩大。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女性逐渐完成了从“女奴”到“女人”再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与转化,女子教育也从培养“贤妻良母”转向培养男女平等意义上的“社会人”这个高阶目标。作家开始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个性解放的角度出发,重新阐释女子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纷纷从社会、家庭的矛盾纠葛角度来探讨女子教育问题,对她们的逐渐觉醒和反抗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对她们在现实社会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贤妻良母”主张的提出,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然而,这种“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基于这一目标培养出来的女性只不过比传统女性多了一道知识的光环。本质上它仍旧以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为依据,依然把家庭作为女子生活的主要天地,缺乏对女子社会作用的认可,因此未能脱离相夫教子的狭隘范围。因此,“贤妻良母主义”不断遭到后人的质疑与批判。早在晚清,就有先进分子呼吁女学“要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要和男子一样地投入社会。[16]《学界镜》(赝叟)中方真指出:要改变中国女子的低下地位,首先要改变过去依附男子的地位。而女子要取得独立地位,只有进学堂,受教育。“五四”以后,这种批判越来越强烈。现代小说也对培养“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进行批判,如《初秋之夜》(蹇先艾,1926)中作者对修身课采用曹大家等的《女四书》,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教育宗旨的女中校长进行了讥讽。《涓涓》(萧军,1933)描写了弥漫着封建气氛的女校教育:督军的训词是要她们好好学习,将来能做个七房、八房姨太太;校长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明确做太太的责任和权利,而女子的责任和权利即是做贤妻良母;刺绣教员也意味深长地说:“什么是我们女人的责任哪?就是嫁了丈夫,应该怎样赚得他们喜欢;有了孩子就得会做娘。”[17](P.10)涓涓对这样的教育感到无比痛恨和厌恶。作者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对“贤妻良母”式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憩园》(1944)中,巴金描写了一个善良、厚道、温柔、美丽的女主人公姚太太。她的娘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哥哥是大学教授,自己是学生出身,被人们看成“新派人物”。实际上,她的生活天地不过是“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她从书本中接触到了一个更广阔复杂的世界。她渴望呼吸新鲜空气,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她爱丈夫,爱周围的一切人,但她更希望能给人间增添一点温暖,擦干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但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也难以逃脱悲剧命运。她在教育姚小虎问题上无能为力;丈夫喜爱新女性,却把她封闭在浸淫旧道德的家庭里;她没有娜拉那样出走的勇气,只有闷在笼子里。巴金通过姚太太这一人物形象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新问题:新女性不仅要有新知识,更要有新的精神风貌。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批判了“贤妻良母”式的培养目标,希望学校教育培养出的不是“贤妻良母”,而是“人”,跟男性一样具有自我意识、健全人格及独立价值的“社会人”。
如何使“女人”成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人”?许多作家开出了“经济独立的处方”。他们认为经济问题是导致女性受压迫、受束缚的根本原因。“五四”时代,《玩偶家庭》曾经激荡起个性解放尤其是妇女解放的热潮,“娜拉”唤醒了许多女性的迷梦。但不久,一些作家便提出“娜位走后怎样”的问题。《伤逝》(鲁迅)对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给予了强调:经济独立是女性在家庭中取得平等地位的标志,是得到幸福婚姻的基础。当涓生失业,使他们的“爱”无所附丽,子君只好又回到了坟墓般的封建家庭。小说给出走的“娜拉”们提出了警示:女性只有先争取到了经济的独立,其他的独立和权益包括婚姻的幸福才有可能实现。但如何才能经济独立呢?《倪焕之》(叶圣陶)里的金佩璋说:“女子吃亏在求知识的机会不能与男子平等,故而不容易独立,自由。”[18](P.113)《客宴琐谭》(叶圣陶)中葆灵向妇女传授职业知识与技能,希望女子能自立。受教育显然是女性取得经济独立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接受教育可以增进知识、掌握技术,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把自己从“奴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现代小说用无数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道理。显然作家们不再专注于女性作为“妻母”的家庭地位,开始关注妇女的社会处境问题,强调发展其社会能力。除了主张女性“经济独立”,一些小说家还探讨了知识女性的“社会化”问题。他们认为,女性要走出家庭、真正成为“社会人”,除了接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以具备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之外,还必须有突破传统家庭观念、积极参与社会事业的热情和自觉意识。《倪焕之》(叶圣陶)描写了在师范学校读书的金佩璋曾经抱有毕业后改革教育的雄心,与倪焕之组成家庭后满足于家庭生活,忘记了当初的理想。直到倪焕之病死,她才燃起了接替丈夫事业的新希望。作者希望通过小说告诉读者,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如果没有理性的社会自觉意识,依旧很容易重蹈旧女性的道路。
作家们认识到,社会环境是推动知识女性成为“社会人”的关键。实现男女同校后,在教育内容与教育目标上不再有男女之别,但是社会就业成为横亘在女子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静媛(《蔻拉梭》,张资平)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找到相应的工作,因为小学校席都被师范毕业的男生抢去了。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一开始也满怀信心地与生活抗争,但是最后迫于传统势力的强大、顽固而屈服。如《月牙儿》(老舍)中的“我”,起初力争“自由恋爱”、“自力更生”。然而这个物质条件贫乏、思想观念落后的男权社会并没有为她提供正常、健康的生存空间,而是处处为她布下陷阱。她追求理想的热情反而成全了恶人的歹念,残酷的现实终于一步步使她“逼良为娼”、她不得不走母亲(出卖肉体)的老路。这些小说告诉我们:办几所女校、让一些女子接受一点教育,根本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女学生们盲目地趋从时尚、急于求成,可能会酿成更大的悲剧。老舍在《二马》中通过李子龙的口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今日的中国,男子都找不到事做,女子就该安心地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胜利以后》(庐隐)中沁芝在信中也说,现在我国的女子教育是大失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并无社会事业可做,一旦身入家庭,又不善管理家庭琐事,简直成了高等游民,由此产生了“还不如安安静静在家里把家庭的事务料理清楚,因此受些男子供给的报酬”的想法。[19](PP.289-290)这些小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沉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界在女子教育问题上曾泛起一股主张培养“贤妻良母”的思想回潮。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在《现代女子教育问题》中对男女教育平等提出异议:男女因其禀赋不同,其所尽天职亦异,宜分工合作,以求进步。“摇动摇篮之手可治天下”,母教问题之重要,实为任何问题所不及。妇女成为贤妻良母,较之使其成为政治家或科学家,重要得多。[20]这些思想的重新泛起并得以明确提倡,一方面是出于挥之不去的“贤妻良母”情结,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当时女子毕业后就业困难的状况提出来的。但这毕竟不是思想主流,男女教育平权、把女子培养为“社会人”是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向,势不可挡。
女子在封建社会长期被困守于家庭之中。要改变传统的妇女观,让女子获得觉醒,并像男子一样接受学校教育、从事社会工作,的确任重而道远。当时的文人以小说为工具,从强调女子成为“妻母”的重要地位入手倡导女子教育,提出了“贤妻良母”的培养目标,积极为女子争取教育权利。当女子在制度上获得平等教育权以后,他们又开始重新审视、批判“贤妻良母”教育目标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提出培养“社会人”的教育要求。他们还从女性自我精神塑造和社会就业等方面,探讨了女性“社会化”过程中的问题。在这一系列努力之中,作家们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时代沟通或契合的双重价值特点,使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在不断扬弃中获得新生。这种方式显然符合妇女解放的进程,符合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从“特殊教育”到男女平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也是与历史现实相符合的。事实上,无论是妇女解放还是女子教育问题,都不是靠换几套新装、喊几句口号,抹杀性别差异、在官府中留几个职位等就可以解决的。男女教育平权的真正实现有赖于男女两性的共同认可和努力,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有赖于男女平等就业机会的提供,有赖于民主、自由生存空间的营造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小说所讲述的众多妇女教育题材的故事为我们提供的有益启示。
[1]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J].新小说,1902,1(1).
[4]梁启超.论女学[N].时务报,1897-04-12.
[5]女学会·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J].女学报,1898,10(9).
[6]梁启超.倡女学堂启[M]//饮冰室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
[7]苏雪林.棘心[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8]颐琐.黄绣球[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9]亚东破佛.闺中剑[M].上海:小说林,1906.
[10]叶圣陶.儿童观念之养成[M]//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1]企翁.苦教员[G]//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社会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12]尗夏.女学生[M].上海:改良小说社,1908.
[13]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14]茅盾.冰心论[M]//茅盾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5]阿英.谢冰心[M]//阿英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6]苏英.在苏苏女校开学典礼会上的演说词[J].女子世界,1905,(12).
[17]萧军.涓涓[M]//萧军全集:第6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8]叶圣陶.倪焕之[M]//叶圣陶小说精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19]庐隐.胜利以后[M]//庐隐选集: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20]李登辉.现代女子教育问题[N].新闻报,1941-10-03.
FromCultivating“aGoodWifeandLovingMother”to“aSocialPerson”——TheChangesoftheFemale’sEducationalConceptinModernChinaReflectedinModernNovels
CHEN Tao-la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The female’s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modern novels. These novels not only contained a wealth of the female’s education thoughts, but also recorde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female’s educational concept in moder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writers advocated setting up schools for the female, and positively strived for the female’s rights of education inspired by the ideal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To draw the people’s attention, novelist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female’s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role of wife and mother. They advocated cultivating “a good wife and loving mother”.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topic of novels gradually transferred from advocating the female's education to achieving education equality, driven by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individual emancipation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women began to enter society, and cultivating women into “a social person” became a new educational goal.
women education; a social person; novel;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2011-09-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儿童教育的现代变革——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儿童教育叙事研究”(11YJCSS0009)的研究成果。
陈桃兰(1978-),女,浙江磐安人,教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
G776
A
1674-2338(2012)03-0118-07
(责任编辑: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