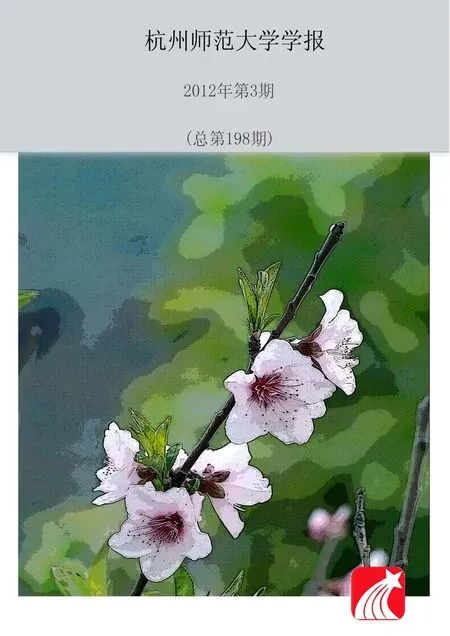重返“八十年代”的另一种可能
——《乡场上》与“按劳分配”原则的生机与危机
2012-04-13林凌
林 凌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文学研究
重返“八十年代”的另一种可能
——《乡场上》与“按劳分配”原则的生机与危机
林 凌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小说《乡场上》为我们重新勾勒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所设想的新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象提供了可能。围绕小说主人公冯幺爸独具的财产权观念的辨析,以及由此带出的“按劳分配”问题的复活,可以考察80年代初期改革的动力及其自我理解的真实情况。这种理解有别于关于80年代的主流叙述,使我们有机会重探80年代的历史复杂性。
按劳分配;八十年代;《乡场上》;财产权;改革
在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个人主义话语兴起的研究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1980年5月发表于《中国青年》上的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下文简称《潘晓来信》)。有关《潘晓来信》的研究,目前有两类意见:一种认为,身处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从《潘晓来信》中攫取理想主义的资源,潘晓是恰巧处于那个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缠绕的场域中可被救赎的对象,“……顺承、转化此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为此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稳定的支点的同时,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义的挫折所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能量和冲力”。[1]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潘晓的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本就是一体两面,这种理想主义恰恰匹配了20世纪80年代以潘晓为起点的个人主义:“今天,距离‘潘晓来信’已经过去三十年之际,倘若有人想从‘潘晓’的叙事中挖掘(比方说)革命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张力的丰富性甚或替代性方案,或者试图转化‘潘晓’那里据说仍然留存的革命理想主义,是不是低估了这个形象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新人’的力量?”[2]这两种说法哪种更有道理,笔者在此暂且不论。
可以说,王钦的论述不仅揭示了潘晓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并且进一步讲述了潘晓如何为自己理性经济人的面目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的过程。然而,上述说法(潘晓身上有个人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张力,或者潘晓是个人主义的肇始)未将潘晓这一人物形象放入历史脉络之中,从而无法历史性地回答潘晓的个人主义是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及这一形象的变化在整个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因此,这样的解读更像是一种理论空降、后见之明。而且,它仍然内在于关于80年代的主流叙述之中,这一叙述自身与革命中国截然对立,将80年代改革的动力解释为中国逐步地加入到一种普世性的规则中。换句话说,虽然前文所提到的种种解读已经足够充分,但是当我们回顾和描述具体历史的时候,能否将从天而降的潘晓作为整个80年代历史进程的单一起源,从而形成一条单一线索作为贯穿80年代的历史叙事,则颇有疑问。
如果我们将潘晓看做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种新人,她截然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三十年所塑造起来的种种新人形象,同样也不同于“前三年”*“前三年”是由蔡翔教授在《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三十年”三人谈》中提出的概念,以强调革命中国结束初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复杂性。那种带着伤痕却满怀理想、充满无畏和大公无私精神的新人。笔者想说的是,就在潘晓出现的同一年,何士光创作的小说《乡场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潘晓更为内涵丰富的新人形象。对冯幺爸的重新探索以及指出其身后的形象谱系和理论资源,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返回历史现场,深入考察进入80年代这一关键历史时刻的真实状况:它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诠释“按劳分配”,以及它以其全部热情所期待的新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
一
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乡场上》,给小说作者何士光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在一个短小的篇幅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梨花屯乡场上发生了一场不大的风波,两个身份悬殊的妇女在穷人家的儿子是否打了对方的事故中产生了纠纷,事实的真相是背后有曹支书撑腰的罗二娘仗势欺人,但是唯一的见证人冯幺爸在是否为任老大家孩子作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如果得罪了罗二娘,就“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胆的不敬,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是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如果你得罪了罗二娘的话,你就会发觉商店的老陈也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光亮,也不知道该用些什么来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回销粮,使你难度春荒……”在几经盘算之后,冯幺爸终于说出了真相:“任家的娃儿不仅没有动手,连骂也没有还一句!”并且还“扯南山盖北海”了一番,狠狠地数落了罗二娘与曹支书两人。
也许正因为这一番“盘算”,冯幺爸似乎可以被纳入“潘晓”的那个脉络中去,整篇小说的主旨在今天也很容易被解读为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个人尊严、自由的必然前提。确实,冯幺爸在无法确保私有产权的时候,“在乡场上不过像一条狗”,他对财产权的盘算在全文中非常显眼。而且,冯幺爸还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的财富在一个充分敞开的市场环境中的价值。如此看来,冯幺爸反而比潘晓更适合来讲一个“现代”的故事。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是作为主体的现代个人的安身立命之保障,两者是不可分裂地互相扭结的:财产权的充分保障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激发了商品市场的活跃,并且连同这个“市场”作为对计划分配的一种替代,彻底否定了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在此笔者想说这种形式主义经济学叙述已经多次被证明完全缺乏理论与历史洞见,无论它在整个后三十年如何位居主流话语地位,这种叙述的唯一正确之处仅仅在于它感知到了前后三十年的巨大不同,但如何叙述这种不同,具体到如何阐述《乡场上》以及冯幺爸这个人物,我们还需要更细致入微地重返历史。笔者认为,小说《乡场上》本身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个故事既包含了不同于改革主流叙事的内容,同时在讲述的过程中又极容易无意识地滑向主流叙事。
如果我们将“潘晓”看作80年代现代个人话语兴起的典型,那么何士光在创作“冯幺爸”这个人物时,头脑中并没有如此一个现代个体的形象。发表于1981年《作品与争鸣》上的一篇批评文章,提出了一个颇为犀利的问题:“《乡场上》的冯幺爸,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糊里糊涂的汉子,而是一个颇有心计的角色。作为一个颇有心计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可以低三下四地‘像一条狗’似的活着,为什么会在事不关己的事情上一反常态,竟会那样威风凛凛地怒斥老支书、罗二娘呢?从他‘确实是不敢说’到‘吼得那么响’,他为什么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内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呢?这真实可信吗?……灵魂也觉醒了,人的尊严也恢复了。然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会问,颇有心计的冯幺爸考虑了这,考虑了那,为什么没有盘算上:他若是得罪了老支书、罗二娘,他们不会用手中的权力、借其他的办法整治他冯幺爸,把暗苦给他吃么?很显然,这并不是冯幺爸的失算,而是作者有意回避的。”[3]
如果我们把“冯幺爸”理解为一个理性经济人,那么这个批评显然是成立的,因为“冯幺爸”太会算计了。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冯幺爸”本人对财产权的理解,他对财产的盘算是否意味着冯幺爸就是一个现代的理性经济人?彼得·甘西区分了“作为法权的财产”和“作为人权的财产”,他认为:“罗马人具有作为多种个人权利之一的财产权利概念;这不同于把它们归结为现代的主体权利概念。现代权利话语中所运用的主体权利术语的一个中心成分是,这一权利专属于人类主体。它不是源自于某个社会的立场或地位,而是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关。它与作为人的本质的、内在的方面相关,它可以概括为思考、推理和做决定的能力”;与作为人权的财产权不同,“能够归功于罗马法学家的,是客观权利概念,它取自于希腊哲学,取自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也就是说,罗马的法学家认为,存在着一种正义的客观标准,一种何谓权利的客观标准,每一个被分配给适合于他的东西”。[4]甘西在书中的这一表达和区分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对于财产权的关注本身并不必然与现代主体扭结在一起。同样,在《乡场上》的冯幺爸固然为自己打算良多,但他对财产权的盘算更应当被解释为对公正、正义的关注,而不是对权利的关注。在冯幺爸的言词中,居于首位的恰恰是对于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的诉求,倘若这种正义社会是可欲的,那么财产权自然可以得到保障。正因为此,在冯幺爸的说辞中,比起改革开放中农村政策的解说(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小说创作难以避免的一点)更为核心的,也更为大快人心的是对罗二娘和曹支书的斥责。这种斥责体现了他对公正的诉求:“这回就不光包给你食品站一家,敞开的,就多这么一角几分钱,要肥要瘦随你选!……跟你说清楚,比不得前几年罗,哪个再要这也不卖,那也不卖,这也藏在柜台下,那也藏在门后头,我看他那营业任务还完不成呢”;“不要跟我来这一手!你那些鬼名堂哟,收拾起走远点!——送我进管训班?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不行罗”。而这一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证词中:“莫非罗家的娃儿才算得是人养的?捡了任老大家娃儿的东西,不但说不还,别人问他一句,他还一凶二恶的,来不来就开口骂!哪个打他啦?任家的娃儿不仅没有动手,连骂也没有还一句!”
换句话说,这里确实出现了私有财产权,无论这种私有以个人为单位、还是以家庭为单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财产权并不是绝对的现代主体意义上的,它更关注正义和平等而不是权利。但是,仅仅指出这种区分是不够的。在此笔者想追问的是,当中国进入80年代的历史时刻,当何士光在《乡场上》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讲出了一条未来中国发展之道路并且还安排了身处其中的人的境况时,冯幺爸的权利观到底具有什么内容?这种正义、平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在潘晓那里,我们也能感觉出一种对于公正的要求,那么同样可以追问,为什么冯幺爸在过了那么多年似鬼似狗的压抑生活后,一下子就能找到自己的正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追查一下这种正当性来自何处?冯幺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为何与这种正义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关系?
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前三十年的中国来梳理冯幺爸人物形象的脉络,观察社会主义新人。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新人,那么与广义的现代性主体的自我设想不同,社会主义新人从来都不是建立在一个所谓抽象的动物性的自然状态中。换言之,要成为社会主义新人,首先在人格上必须具有某些品质,有时候不仅是内在的品质,甚至是外貌的要求。如果说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社会主义新人,那么,有待成为新人的人依然存在缺陷,他无法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承担在身。只有通过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知识,热情地与广大劳苦群众一起投身于革命生活实践,以及往往还需要一个革命导师的指引,他才能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具有民间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天性善良,有待塑造的青年主体。而笔者认为这个“伦理”的内在核心最清楚地叙述还是体现在土改小说中,体现在蔡翔关于赵树理小说《地板》的解读中,强调了“法令”需要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上,而劳动的神圣性则在小说中被设置为自然情理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是这个世界早已存在着的自然真实,只是被各种其他的道理(比如王老四的‘理’)所遮蔽,因此,革命所要从事的工作只是把这一被遮蔽的‘情理’重新解放出来,并进一步使它制度化(‘法令’)。”[5]
这一叙事原则的进一步要求是,青年必须通过革命的锻炼,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实现土改的理想。因为,土改中的“按劳分配”原则,如果仅仅是将发财致富的梦想分配给每个穷人,那么因为劳动能力的差别而富有起来的农民一旦重新做起地主的梦,不劳而获的情况就又会再度出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恰恰针对的就是“按劳分配”。如果没有革命的保证,如果没有大公无私、“劳动本身作为美德”等激进要求,“按劳分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青年也会因为他的“自然”正义得不到伸张以及道德沦丧、社会黑暗,从而表现出或愤世嫉俗或无所适从乃至沉沦颓废的情感形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这个有待成为新人的人,到了80年代则摇身一变,直接成为新时代的新人。这意味着,与此相对应,冯幺爸并不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作为80年代初的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既是历史记忆的,也是现实的),其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劳动、“按劳分配”,以及如何将“按劳分配”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中解放出来。冯幺爸自认为可以限制绝对的私有产权的正义,就是“按劳分配”,每个劳动者获得且仅获得他们的劳动产品,“按资分配”则被认为是不劳而获而不具有合法性。在80年代早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这样的“新人”屡见不鲜,作为其中的典型,《乡场上》实际上提出一条新的改革之路,鉴于某种关于人和财产权的想象的复归,我们暂且称80年代初为“重返土改”。这种重返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的意义,而是象征着这种平等、公正的“自然情理”和理想(按劳分配,每个人获得其劳动的全部,没有剥削和压迫以及隐含着的劳动带来尊严,劳动即是美德)在人身上的复活。这在80年代紧紧地与劳动积极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回应上述那篇批评文章,为何冯幺爸会抛开理性算计的原则于不顾,顶撞罗二娘和曹支书。
二
要言之,到目前为止,笔者只说出了两点:首先,冯幺爸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有限度的、顾虑“正义”的产权意识;其次,这样的产权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建立在某种新人的背景和基础之上。冯幺爸身上所体现的有限度的财产权,其不同于现代世界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即在于它更关注正义;这一正义的核心即是每个人应当获得其劳动所得,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合法来源。冯幺爸完全接续了社会主义中国在此刻遗留下来的“按劳分配”的问题,包括与之相关的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方面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在工业方面则是“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它与革命中国的历史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所传达的公正、平等诉求以及劳动与尊严的关系,使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分配问题,而是一个总体性问题。这意味着,在80年代早期的经济改革历程中,身处其间的人们恰恰是透过总体性的政治设想来看待经济问题,实现总体性目标仍然存在着可能性。
然而重要的是,笔者在此谈论这种总体性并没有赞美或者怀旧的意思,恰恰相反,笔者试图论证这种总体性失败的原因。当然,它在此既通过小说语言表达了出来,随后也将通过理论语言得到阐释。在历史上,“按劳分配”的理想依赖于激进革命为其提供哲学上的可能,一旦革命消退,“按劳分配”本身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对“前三年”改革题材(尤其是农村题材)的小说与80年代初期相同题材小说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如何获取更多财富的问题上,两者存在着不同的本质,前者以贾大山的《取经》为典型,后者的典型则是《乡场上》。在笔者看来,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小说是否传达了不同的激活生产力的方式:后者属于在包产单干、承包责任制确立后的政策宣传,而前者主要围绕着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前三年”小说中诞生的新人,如果回到前三十年,那么他依然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内在的危机,而以《乡场上》的冯幺爸为典型的这群“新人”的出现,则是出于克服“前三年”新人内在困境的价值动机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细究小说情节,就会发现《乡场上》的叙事仍然充满了逻辑漏洞,即“前三年”(仍在农业集体化条件下思考发展道路)的小说体现的那种自信难道仅仅是盲目乐观?正如前文批判形式主义经济学时所述,如果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确实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那么这种叙事是否有外在的前提,这个前提在小说内部是否阐释清楚了?比如,如果新时期中国真的像冯幺爸所设想的那样来改革,那么如何防止新的罗二娘和曹支书(他们可不是多劳多得的代表,而是欺压和剥削的恶人形象)出现呢?一方面是新的不平等可能威胁到冯幺爸的“自然”正义,另一方面,对于提高生产力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又如何处理呢?“私”的出现仿佛又召唤着失去的“公”。重要的是,中国在新时期展开的是一轮更宏大的工业化、现代化计划,倘若没有一个外部条件,为什么分田单干所提高的农业产量不会被新一轮的工业化建设所征用?如此一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未必就能激发所谓的生产积极性。
在笔者看来,小说中的人物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冯幺爸多次提到“国家”的重要性,“做活路——国家这回是准的”、“只要国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去”。之所以说这种意识是模糊的,因为小说叙事省略了外部环境的描写,切断了外部与内部叙事的联系,国家在此处的重要性就从具体的转变为抽象的。正如前文所说,《乡场上》所设想的改革路径(既发展生产、又维护公平正义、“自然”伦理)实际上依赖于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自我定位。简而言之,《乡场上》使改革中国的设计成为可能的审美表达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调整了建设发展的总体思路和规划,批判了过去一以贯之的“先生产、后生活”的经济发展思路,国家对农业的调整养息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之所以它们不影响改革的工业化进程,则与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登场有莫大的关系。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将吸引西方外资作为发展现代化、工业化的一条捷径。正是因为这个指向外部的国家行为的调整,使得《乡场上》的内部叙事逻辑成为可能。改革的动力恰恰来自于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而所谓的抽象,则是指由于《乡场上》的内部叙事过分突出,忽略了具体的外部条件,从而形成了一套前文所指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叙述,国家很容易变成这一套叙述所诉诸的抽象需要,于是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理论叙述,国家变成了仅仅为小说内部叙事提供服务的管理者。相应地,冯幺爸的公正和正义也就从具体的伦理道德,抽象化为市场原则要求的公正和平等:多劳多得、能力主义、能人政治就此不可遏止地登上了20世纪80年代的舞台。倘若以这种抽象的方式去设想国家,排除实际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冯幺爸的理想还能实现吗?
三
在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叙述中,冯幺爸的逻辑集中表现在《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6]一文中。该文从多个方面反驳了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这样一种激进的理论,诸如“按劳分配”不会带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存在的差别是富裕程度的差别。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不存在剥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剥削无从产生,劳动力不会成为商品,等等。它旨在说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不同于资本主义“按劳分配”,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存在真正的“按劳分配”。于是,一方面要求人们必须从激进的革命理论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要使之保持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正因此,想象这样一种“按劳分配”及其背后的产权观念,就是中国进入80年代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它的基础当然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每个人获得其劳动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要防止“按劳分配”的错位、滑入资本主义“按劳分配”的泥沼:绝对的私有产权可能导致“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致“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
先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在小说《蚕豆早熟》中,珍珠农场种蚕豆本来是“为了养地,做肥料用的”,但是在蚕豆意外早熟之后,大家决定“动员家属中的老头子、老奶奶、小孩子去摘,农场职工用非工作时间去摘”,“一律给报酬,摘一斤豆子给一分钱”。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小说人物袁光的辩解,当党委副书记赵克谦提出疑问:“现代报纸上讲的都是突出政治。这发钱的事,报上没见过。”袁光说:“要把豆子拿上来,就一定要这样做。一斤青蚕豆给商业部门,就算值一角钱。农场拿九分钱,这是国家的。十分之一给劳动者。没有人劳动,天老爷送来了豆子也拿不下来。要人家劳动,就得给些报酬。其实,那十分之九也是群众的,是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十分之一是当前利益。你们放心,十分之一拿出来是鼓励劳动,不是鼓励懒汉。就是两位大胡子老祖宗活到现在也会同意的。”[7]
很明显的是,小说实际上赋予个人利益很多的限制,不仅在工作之外才能摘,而且只有1/10才归自己所有。表面上看,这确实实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理想,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通过“个人利益”激励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因为个人只分得1/10,所以绝不会出现贫富差距过大,以致一个人可以购买另一个的劳动力或者说剥削的情况。一切看上去似乎很完善,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存在一种有限度的财产权,首先需要考虑公正的问题。公正的要义乃是社会主义式“按劳分配”,每个人获得其劳动的全部,同时劳动成为德行本身。但问题在于,一旦存在这1分钱和9分钱之分,一旦劳动所产生的产品被理解为价值而全部归劳动者本人所有(无论是长远利益还是短期利益),一旦劳动需要以商品价值去衡量(因为小说中蚕豆最终是要卖到城市的,蚕豆是商品,在此处劳动报酬就绝不能以使用价值去模糊地看待,劳动换取的就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那么,首先摘1斤蚕豆到底要给几分钱报酬,才能激发人们在业余时间劳动的积极性呢?其次,摘蚕豆本身的价值如何来计算呢,既然劳动不能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去衡量。
回到《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该文反复强调“按劳分配”滑落到“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中所体现的平等权利”,这种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并不存在;然而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剩余价值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不会随着一个实体的剥削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剩余价值的问题总会结构性地被生产出来,被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区别、工业劳动/农业劳动的差别重新召唤回来,因此它不会因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而得到解决。更直白地说,只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不存在贫富差距,只有在以“使用价值”来理解劳动产品,亦即农业或者小生产者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劳动产品就只能以“价值”来衡量,而多劳多得在商品条件下,从来就不是肯定的。因此社会主义激进革命的思想是,“土改模式”、有限财产权的理想或者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是劳动成为美德和劳动成果全部归劳动者所有的统一,亦即劳动本身获得完全的自我实现。对这一前提的否认,就意味着剥削的问题始终会被结构性地生产出来,劳动力必须以商品形式出现。这也意味着,劳动的产品一旦出现就是以“价值”的形式出现,所谓的共同富裕(只是“富裕程度的差别”)是无法实现的,是以“使用价值”模糊了“价值”来认识劳动产品的结果。由此,“富裕程度的差别”最终很难不以“贫富差距”的面目出现。
换句话说,“按劳分配”作为土改理想必须获得革命支持。也就是说,“按劳分配”的要义不能仅从公正分配的意义来理解,或者说仅从我拿到我全部的劳动所得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这理解本身就置身于商品价值形式的条件下,因而并无可能实现;其本质乃在于使劳动本身成为美德。而劳动实现其全部的意义(或者说劳动获得彻底的解放),也必须在劳动摆脱了商品形式的束缚之后才有可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念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一旦我们停留在商品交换的意义上,以价值的形式去理解,那么它注定无法实现。因此,“按劳分配”理念要么上升为革命理想的实践(劳动是美德)才能获得理性可能性,要么变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我获取我劳动的全部,与劳动的解放、劳动本身作为尊严和美德只有在革命理想中才是可能统一的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否则,劳动本身不仅无法解放劳动者,而且以价值去衡量劳动产品,指望劳动者获得劳动的全部也绝无可能,“侵占劳动成果”的现象并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所谓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区别,所谓劳动者获得劳动的全部与劳动本身获得解放的区别,是一种只能消失在统一性中的差异。“(重返)土改”似乎能让这种理想成真,乃在于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农村改革以及农产品或多或少可以以“使用价值”来衡量。有限的财产权在小生产者的背景下,出现在“(重返)土改”时期,就容易理解了。因为此时改革更多地在农村展开,农产品的生产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上相对比较模糊,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此时存在可能性。当商品经济或城市化进程一旦展开,倘若革命理想本身(彻底取消财产权,劳动者彻底解放)无法实现,那么最终回归现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和财产权概念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因此,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在哲学上的困境,使得冯幺爸的理想最终在进城的陈奂生那里——在付出一天的时间卖油绳所赚的钱却住不起一夜的旅店的时候——失败了。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冯幺爸的理想毕竟确实获得过现实的实存,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哲学(或者在20世纪90年代更多地被称为经济学原理),而是政治,是具体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问题在于,一旦它在历史中现实地存在过,人们就容易仅仅看到这种现实,而忽视这种现实的真理及其得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
如果这里存在的真理是政治,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倘若从1984年的城市改革到1987年的商品经济大潮标志着中国改革逻辑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乃是中国作为政治主体的主动选择。反思80年代,改革的动力毋宁说是寻求真正的社会主义,寻求一个总体性世界、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其间的核心问题是:“按劳分配”只能激发劳动力的积极性、却无法激活资本的积极性;从“按劳分配”到利润优先,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使用价值”到“价值”,什么是我们的理想?是小国寡民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还是大工业、高科技、军事化、金融业的兴起等需要高度资本积累的活动?改革逻辑变化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某种决策范式。
[1]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J].开放时代,2010,(7).
[2]王钦.“潘晓来信”的叙事与修辞[J].现代中文学刊,2010,(5).
[3]金实秋.试论《乡场上》之不足——兼评《乡场上》评论中的某些溢美之辞[J].作品与争鸣,1981,(10).
[4][英]彼得·甘西.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蔡翔.革命/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严实之.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J].新华月报,1978,(2).
[7]季冠武.蚕豆早熟[J].人民文学,1979,(1).
ThePossibilityofReturningto“the1980s”——XiangChangshangandtheVitalityandCrisisofthePrincipleofDistributionaccordingtoWork
LIN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figure of “New Man” conceived by Chinese Reform in the early 1980s by focusing on Feng Yaoba,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XiangChangshang(TheMarketintheCountryside). In analyzing Feng’s unique idea of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he resuscitation of the related issu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the author tries to show the dynamics of the reform in the early 1980s and the truth of its self-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restate the historical complexity of the 1980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dominant narrative about the 1980s.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1980s;XiangChangshang(TheMarketintheCountryside); property ownership; reform
2011-09-12
林 凌(1983-),男,浙江瑞安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I206.7
A
1674-2338(2012)03-0046-07
(责任编辑: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