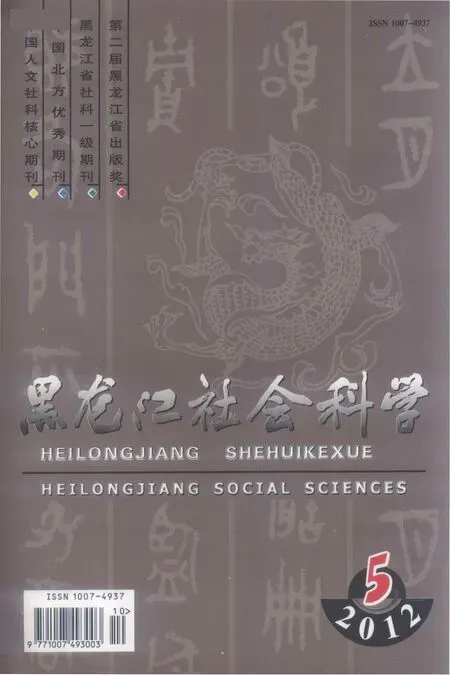清代移民与三江区域的开发
2012-04-13刘敏
刘 敏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经所构成的三江区域与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相比,具有地处边疆、人口较少、开发滞后等弱点。更由于明末清初战争等原因,三江区域满族、赫哲族等土著居民大量南迁和入关,致使清初三江区域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乃至有“荒徼”、“绝域”之称。为加强东北边疆防御能力,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移民政策的实施,不仅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人口结构,并对其开发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清代对三江区域的移民政策
清代三江区域移民是东北地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移民政策下进行的。
1.放遣罪犯。清朝前期,为抵御沙俄蚕食我国东北边疆,亟须补充人力以增强防御力量,即在东北地区实施遣戍制度,将大批反抗清朝统治及触犯刑律人员遣戍到该地区。被发遣的“犯人”,史称“流人”。他们多被“赏披甲人为奴”,用于官庄和旗地从事农业生产,以保证军粮供应。三江区域的军事重镇——三姓,就是“流人”的重要发遣地之一。
三姓,原名依兰哈拉(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康熙五十三年(1714),设立三姓协领衙门;雍正十年(1732),升级为三姓副都统衙门,管理范围大致包括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直至库页岛和海中诸岛及南北鄂霍次克海海域。康熙五十二年(1713)上谕:“此后发遣人犯,俱发在三姓地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四四)据雍正二年(1724)七月十三日《吉林将军哈达等奏报发往三姓犯人多不好管制折》中称:“今查三姓送来犯人册,自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二年六月,发配官差上行走之人一百三十九名,欲赏给穷披甲为奴之人八百七十八名,发配永戴铁索之犯人三名,共计一千二十名。”[1]雍正十二年(1734)起,正式建立官庄,“招徕耕种,以备仓储”;精心挑选从内地缘罪“发遣来三姓的会耕地之民人及发遣为奴已赎身之中年壮又有妇孺者,每庄招徕十人”,令其教民垦殖耕种[2]。雍正十三年(1735)重申:“嗣后发遣人犯有应发宁古塔者,皆改发三姓地方,给予八姓一千兵丁为奴,计一千足数再行请旨。”(《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二〇四)
2.招徕流民。清朝初年,为了尽快恢复“龙兴之地”的农业生产,使留居在东北地区的满洲同族在生计上有所保障,清政府曾一度对东北地区采取开禁政策。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六年(1667)的23年中,清政府曾鼓励向东北移民,多次晓谕地方官吏,令其“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地,永久为业”(《大清会典》卷一六六)。顺治十年又颁布了《辽东流民开垦例》,规定“免交三年粮钱,缺乏牛种者,由官府借贷。”(《盛京通志》卷二三)清政府较为优厚的开禁政策曾吸引大批山东、直隶等地以破产农民为主的“流民”进入东北,其中一部分定居在三江区域。康熙初年,“乌拉、宁古塔一带人参挖掘已尽,官私走山者非东行数千里到赫哲族居住的森林地带和乌苏里江外,否则是采掘不到的。有些采参、淘金人入山既远,一去不返。年代久了,乌苏里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汉族人民以耕种为生的村落和淘金人口集中的居住点。”(《中国近代史稿》)
3.封禁逐流。清朝奖励向东北地区移民政策实施了23年后,因其日见大量汉人移居东北,与旗民杂处,在政治上使旗人“耳濡目染,习成汉俗,不复知有骑射本艺”(《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二);在经济上“流民”“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清仁宗实录》卷一三三)。于是对该地区实施了封禁。康熙七年(1668)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五一)
为了严禁汉族移民出关,清政府采取控制东北交通要道的措施,设置官卡,并于康熙九年至二十年(1670—1681)在清初修筑的“柳条边”(即“老边”)基础上,续修从开原东北的威远堡至吉林以北的法特哈的“新边”,严防汉民逾越。
4.开禁放垦。鸦片战争后,沙俄不断入侵黑龙江边境。为抵御沙俄侵略,清政府改变了从康熙七年(1668)开始实施的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于咸丰十一年(1861)逐渐地在部分地区开始招民放垦,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全部开禁放垦。
光绪四年(1878),“吉林将军铭安,设立垦务局,拍卖荒地,允许汉民开垦,汉民北进的障碍得以解除,并向三江区域移民”[3]526。光绪七年(1881)三姓副都统衙门右司张贴招垦三姓荒地告示中称:为遵旨开放荒地以实边储而裕课赋事。照得三姓属界倭肯河东南百余里至巴湖里河,又南至奇胡力河及嘎什哈岭以南并大小雕翎甸等处,均有可垦荒地……三姓荒地既经奉旨开放[4]206-207。三姓地方从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十四年(1888)先后共放出生荒地22万垧左右[5]。三姓在全面开禁时期大量官荒得以放垦。
三江区域的开禁放垦主要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黑龙江地区全部开禁放垦后进行的,尤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该区域各地纷纷开禁放垦,移民的数量也达到了清代历史高峰。
二、清代三江区域移民的主要类型
1.流人,是指触犯清朝刑律及反抗清朝统治失败或受牵连,被清朝政府流放到环境艰苦的边疆地区的罪犯及其家属。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京师和内地的汉族人。流人到流放地后,主要是“赏给穷披甲为奴”,即给三姓地方新满洲为奴,在旗地和官庄中服役种地、充当苦差。
雍正末年,三姓地区已开垦旗地12 926垧(《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一)。乾隆元年和二年设置官庄之时,有官庄10个,庄丁100人,耕地120垧,“将从京城移来籍没入官之人及从宁古塔、伯都纳移来安插之人犯、赏奴与本地赏奴等,一并俱令入官庄……令其种田,四十五年又将本地无主之五十包衣入官庄,添设五个官庄……令其种田。”[4]353至此,三姓共有官庄 15 个,庄丁 150 人,耕地1 700垧。据《三姓副都统衙门档》不完全统计,三姓地方,由乾隆元年至嘉庆十二年的七十二年间累计发遣赏奴2 628名[2]。
2.流民,主要是指未经清朝政府允许,偷渡出关进入东北的汉民。他们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以采参、淘金等业谋生的。清朝初年,大批山东、直隶等地破产农民进入东北,其中就有一部分流民定居在三江区域。虽然康熙七年(1668)下令:“辽东招民受官永著停止。”严禁汉族移民出关后,关内北方各省众多的破产农民仍然采取种种办法冲破封紧,流入三江区域。根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编审户籍的统计,三姓有流民60户、198人(《盛京通志》卷三七)。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姓有流民69户、228人。“乾隆五十四年在三姓地区查出流民二百四十九户,一千二百四十五口,只逐出王顺等六十一户,三百零三人。其余焦万良等一百八十八户,九百四十二口则因无力出走,最后被允许留住。”[7]
由此可见,清朝政府虽然屡下禁令,严禁汉民进入东北地区,但未能阻挡住“流民入垦”之潮流。流民的日益增多,促使旗地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出现了“招民佃耕”现象。光绪初年,因“三姓官兵办公苦累,请拨随缺地亩,招佃耕种”,共划出随缺地29 080垧(《依兰地方志》卷一二)。大批汉族流民从被“招来代耕”,变为佃耕旗地,已经成为旗地上较为稳定的主要劳动者。
3.垦民(1861—1911),主要是指开禁放垦时期进入东北的关内移民。这类移民在清代三江区域移民中占主导地位,与清初、中期以流人、流民形式的移民相比,呈现出有官方组织、人数较多、分布地域较广、所从事的职业多样化等特点。
汤旺河招垦局自光绪三十年(1904)设立,至宣统三年(1911)已迁入移民18 803人,年平均移民近 2 000 人[6]374。
汉民移入桦川,始于同治元年(1862)。宣统二年(1910)前后,移民络绎不绝,或乘船、或乘车、或手推、或肩挑,“一年就增加七八千人,有时达万人以上。沿松花江一带沃野,连年被开垦。从音达木河畔,到北面松花江岸,耕地连片”[3]526。随着松花江的开航,三江资源的开发,移民数量猛增。“1910年,汉族已达3 500多户。1913年,总户数增至5 081户,即每年移民平均达1 000户。绝大部分来自山东,以黄县居多,其余来自辽宁和吉林南部。他们从事农业、商业、采金、捕鱼、林业及运输业等。”[3]526
绥远州(今黑龙江省抚远县)在宣统元年(1909)设治之初,有人口1 207人。其中:土著民族赫哲族87户395人;本省(当时为吉林省)迁入定居户14户102人;流民共161处窝棚,男692名;商共3户,男18名。直、鲁两省流入的贫民和极少数商民居本县人口数之多数,且一般多为男性[8]。
流入此地的汉人多以农耕为业,垦民成为清代三江区域农业开发的主力军。
三、移民对三江区域开发的贡献及影响
1.移民为三江区域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资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主要依靠体力劳动。一个区域只有拥有为数众多的劳动人口,才能保障土地的广泛开垦;而商业和手工业发展既需要来自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又必须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口(特别是城镇人口)相应地出现。因此,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是实现区域开发的必要条件。清代移民,为“人烟稀少”的三江区域送来了大批流人、流民和垦民,为当地的经济开发提供了来自于中原、江南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文人和官吏,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三江区域的农业开发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
2.移民促进了三江区域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兴起与发展。清初移民之前,三江区域基本处于崇山未辟、荒野未开的状态。当地居民多以渔猎为业。随着清初在三江区域移民政策的实施,农业开始兴起,并获得了持续的发展。雍正末年该区域已开垦旗地12 926垧(《八旗通志初志》卷二一);嘉庆十二(1807),“八旗官兵闲散人等现有耕地二千六百五十二块,共一万七千四百六十四垧,十五个官庄人等现有耕地一千九百二十五块,共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五垧”[4]56-57。总计垦地31 439垧。
清末开禁放垦,大量关内汉民涌入三江区域开荒种田,对该地农业经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三姓既有报官领地者,复经历任地方官,出放荒段转行售诸外来汉人。原有山林洼塘,日渐化为沃壤……各自筑屋于其所耕之田,以致形成沟端山麓,农屋星布之局。”[9]同年《永宁社佐领魁凌等为造报民人开垦生熟荒地数目册事呈三姓副都统衙门右司》一文中载:“窃查职等所属丁民人等占居开垦并价买各项地亩,现经查明共开垦熟地七千二百五十四垧七亩三分,荒地一万零一百二十五垧九亩二分。”[4]237-238
清朝末叶,汤旺河平原还是榛莽一片,林木遍地,仅有少数索伦人游猎。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关内移民及南流徙汉族丁户日渐移入并少量自由占有土地,垦荒耕植自是开始。”[6]374
有清一代,汉人大量移入三江流域,使松花江中下游一带的平原沃野,广为开垦,耕地连片,为三江区域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3.移民带动了三江区域手工业的初步发展。一般说来,农业粗放的地方,手工业、商业比较落后。三江区域在清初移民之前,除原住居民的鱼皮兽皮加工、缝制和桦树皮器物制作之外,几乎未有其他手工业技术可言。大批移民的到来,为三江区域提供了掌握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人力资源。
桦川私营手工业产生于清光绪年间。设治前有工业8家,为山东省移民,在悦来、佳木斯两镇制造豆油、靰鞡和金银首饰等。设治后手工业作坊开始发展,到清宣统三年(1911)悦、佳两镇已有工业14家,涉及酿酒业、制油业、餜点业、靰鞡业、木作业、磨坊业、染纺业和砖瓦业等多个行业[3]222,4。
光绪二十年(1894),同江(当时叫拉哈苏苏)出现了自给自足的粮油加工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面粉、榨油等行业由自给性逐渐变成了商品性生产[10]133。
4.移民引发了三江区域商业的兴起。清初,三江区域由于农业、手工业很不发达,当地人除将人参、貂皮等土特产品作为贡品和自用外,几乎并不懂得经商贸易。随着三江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活动逐渐兴起。三江区域商业的逐渐兴起,是与清代移民的到来联系在一起的。
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曾有山西太原府徐沟县商人龙吉川、永平府林榆县商人王吉忠等六人不惜冒各种风险“闯关东”,“从三姓城经营赫哲等皮张的铺子里买得黄貂皮16 567张,请求由鄂尔衮路带到吉林交过税银后转运到盛京、张家口等地出售”。道光二十年前后三姓城有商铺19家,咸丰元年(1851)增至26家,到同治四年(1865年)猛增至82家[11]。三姓城的商业活动以经营本地区盛产的人参、貂皮和东珠等珍贵土特产为主。由外地向三姓地方销售的商品主要有粮食、布匹、食盐、生猪、烟、酒、豆饼等农产品、粮食加工品和手工业产品,其数量相当可观。三姓城已经成为三江区域的商业中心,带动了周边城镇商业的发展。
汤原自1906年建县以后,随着移民的迁入,农业开发、金矿开采和私营商业日渐发展。民国3年(1914)全县有杂货铺14家、药铺5家、当铺2家、粮米铺14家、酱醋坊2家、染房2家。这些私营商业店铺大多为三姓(今依兰县)资本家开设的支店[6]623。
光绪三十年(1904)间,拉哈苏苏(今黑龙江省同江市)始有汉人开设的几家商铺,与俄国人进行贸易活动,也兼收赫哲人的渔猎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拉哈苏苏的面粉、榨油等行业,由自给性逐渐变成了商品性生产。光绪三十二年(1906),临江境内有十余家商店,皆为小本经营。尤其是旅店业较为兴旺。由于临江州幅员较广,桦川、富锦、宝清、饶河、绥远等地,均来州办事。因此拉哈苏苏已成为当时该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宣统二年(1910)七月,成立商务会,统一管理全州商务。同年,拉哈苏苏海关成立,开始对俄贸易[10]215,133,201。
区域间商贸活动的兴盛,促进了三江区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5.移民奠定了三江区域城镇的基本格局。人口是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共同发展是城镇兴起的经济基础。清代关内移民不断迁居三江流域,或因军镇设置、或因开荒垦田而聚居,促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区域商品市场得以建立,城镇也随之兴起。
三江区域的城镇,如依兰、汤原、桦川、同江、抚远以及饶河等,它们的兴起多以军镇设置为基础,以大量移民为必要条件,农业开垦为可持续发展动力,并奠定了今天三江区域城镇的基本格局。
6.移民推动并促进了三江区域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改变。生活方式和习俗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这是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传承等原因造成的。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异族和区域外文化的渗入等因素又会促使之逐渐发生演变。清代移民后,大量汉民生息在三江区域,同当地的原住居民——赫哲族杂居相处,对其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哲族早期居住比较原始而又十分简陋的“安口”(桦皮为之,捕牲住)、“搓罗”(草盖用棚,捕鱼住)、“地窨子”(半地下式住房)等,部分赫哲人由于经营农业而定居下来,并向汉人学习盖泥墙草顶的正房,居住方式和住房条件均有很大改变。赫哲族的主食也由原以鱼肉、兽肉为主,转变到把小米与鹿肉合煮成肉粥,用黄米煮成粘饭,拌入鹿油或野猪油,粮食开始作为主食原料。赫哲人还学会了种植白菜、萝卜、豆角、茄子、葱、蒜、辣椒、马铃薯、菠菜、香菜、大头菜等,告别了过去只靠采食野菜为蔬菜来源的历史。赫哲族原用渔猎产品——鱼皮和兽皮制作衣服和被褥,故有“鱼皮部”、“狍皮部”之称。至清代布匹传入三江区域后,越来越多的赫哲人也依照汉人穿起布制衣服;到清末,鱼皮衣、狍皮衣逐渐被布衣所代替。
清代移民促进了三江区域人口的激增,垦田面积和范围的扩大。以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和军事驻地为中心,形成了与内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相似的农业村落和城镇。诸多稳定的农业区和城镇的出现,使三江区域开始由以传统的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向以农业为主多业并举的生产方式转变,从而促使三江区域的经济由比较单一的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贸易和渔猎经济并存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多元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移民是引发三江区域生产方式改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因和动力之一,为三江区域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人力资源,为三江区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经济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必要而有利的条件。在广大移民和原住居民——满族、赫哲族的共同劳作下,三江区域得到了初步的开发,并为进一步全面开发奠定了基础。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G].合肥:黄山书社,1998:86.
[2] 佟永功、关嘉录.清朝发遣三姓等地赏奴述略[J].社会科学辑刊,1983,(6).
[3] 桦川县志编纂委员会.桦川县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4] 辽宁省档案馆.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G].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
[5] 辛培林,张凤鸣,高晓燕.黑龙江开发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686.
[6] 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25.
[7] 汤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汤原县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8] 抚远县志编纂委员会.抚远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8:632,676.
[9] 薛增福.依兰县开发略纪[G]//.依兰史志资料汇编:第1辑.依兰县史志办,1983:29.
[10] 同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同江县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11] 王佩环.清代三姓城的勃兴及经济特点[J].社会科学战线,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