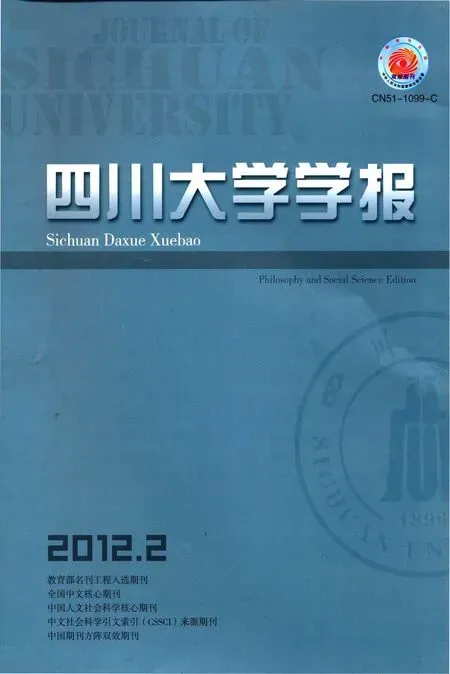建立解释主体: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建构
2012-04-12唐小林
唐小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奠基,如果从索绪尔、皮尔斯算起近百年。符号学科的建立,才半个世纪。但随着高度符号化社会的到来,符号学已成显学。不过热闹之下,潜伏危机。危机之一,是主体符号学在整体上的缺席。换言之,关于主体符号学的建立,还得从头开始。在笔者看来,只有建立了主体符号学,符号学学科的奠基性事业才算完成。麻烦的是,主体狂热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主体破碎的反讽文化局面。这种局面下,如何建立主体符号学?建立何种主体符号学?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拟深入这个时代知识的内在逻辑和主体符号学建构的某些尝试,作一粗略探讨。
一、反讽时代及其符号主体
谈论主体符号学,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关于“主体”的辨析。主体一词,意义含混,中西理解殊异。西方更强调心灵主体,华夏一脉则偏重认知与实践合一主体。在中国,主体是“主宰”的、主动的;在西方,主体既可以是主动的,又可以是被动的,还可以是“屈从”的。①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页。在人类思想史上,主体之义太过丰富与复杂。从亚里士多德将主体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②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867页。经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到拉康、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主体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进入当代,当批判和文化理论逐渐从“自我”这个词偏离出来,用“主体”取而代之的时候,主体早已不是所有知识的起源和形成知识的“本源的、先验的条件”的那个主体,也不仅是拉康、阿尔都塞们被“语言”、被“意识形态”等建构的那个主体,它似乎漫漶成一条没有边际、漫无目的且不断流逝的大河,任何关于其独立、自足、统一的想法,都可能被置于可耻的谎言之下。显然,要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体辨析清楚,委实不易。不过,在我看来,可以给出一个最简最宽的定义:主体即人。个体、自我、身份、人格等等,均可视为主体同一家族的词汇,在特定语境中可以相互替用。
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③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4页。主体符号学即是关于人与符号关系的学问。我认为,它大致有两个论述方向:一是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考察人是如何作用于符号意指的,是怎样将意义植入符号,使符号成其所是的。二是符号学关照下的人是怎样的。亦即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在前一个论域里,人是作为符号主体被检查,可称之为“符号的主体学”;而后一个论域,则是关于人这个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可名之为“主体的符号学”。因此,主体符号学,既是关于“符号的主体学”,又是关于“主体的符号学”。完整的主体符号学,应当在这两个维度上建立。如果按照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即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①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114页。那么,第一个论述方向,讨论人在符号内部结构中的位置及运动方式,更偏重“符义学”;第二个论述方向,则更多落入“符用学”的范围,重心在解析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的人。当然,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仅有第一个论域,即“符号的主体学”才有资格成为“主体符号学”,这与“主体性哲学”类似,它始终把人作为符号学的出发点和中心。而“符号的主体学”,不过是符号学理论在“主体”研究上的应用,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由于符号学界将后者视为主体符号学已成惯例,比如对巴黎学派“激情符号学”的定位。本文遵从惯例,将此作为主体符号学的另一维度。
建构主体符号学,是一项“先驱者的事业”。对此,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等有所警告:必须尽量避免“先驱者的病毒”,“即那种不了解一个时代知识之内在逻辑关系的先入为主的偏见”。②安娜·埃诺:《符号学简史》,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对于建构主体符号学而言,就是要事先了解其身处的时代位置及其符号特征,此处之所谓“时代”,与“知识之内在逻辑”相关,非政治的、经济的时代,而是文化意涵上的。这个时代关涉到人类意义的建构方式。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意义建构的历史。意义历史如何演进,有不同的猜想。这些猜想,不乏落入符号修辞理论的。或者说,符号修辞理论对这些猜想完全解释得通。符号修辞的四个主型之间层层否定的递进关系,即意义的“四体演进”逻辑:隐喻(异之同)→提喻(分之合)→转喻(同之异)→反讽(合之分)③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有意无意地成为某些思想家用来把握历史演进的方法。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恐怕是最早涉及人类历史的“四体演进”的。他在写于公元1世纪的《变形记》中,寓言人类历史为黄金、白银、黄铜和黑铁“四大时代”。④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18世纪的维柯,也许受到奥维德“历史退化”观的启发,他将人类历史描述为从神祗时期向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的依次递降过程。这一过程体现的,是从以比喻为主,向以转喻、提喻、反讽为主“四体演进”的历史符号修辞。⑤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18页。从叙述学角度,将“四体演进”推演到极端的,是20世纪中叶加拿大批评家弗莱,他认为罗曼史、悲剧、喜剧、反讽构成人类艺术叙述的四大循环,并断言今天已进入反讽时代。⑥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5-299页。
认为反讽已构成今天这个时代特征的,有来自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和学者,诸如皮亚杰、汤普森、海登·怀特、德曼、罗蒂等。即便用另外的词,比如“后现代”来描述当今的文化形态,其底里依然是反讽。林达·赫琴就明确宣称:“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反讽处于支配地位。”⑦Linda Hutchen,Irony’s Edg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London:Routlegde,1995,p.67.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17页。于是,在符号学家看来,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进入反讽社会,“反讽在当代已经扩展为人性与社会的根本存在方式,成为文化符号学的本质特征”。⑧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09页。
但在何为反讽上,看法并不一致。 “首倡、引进反讽的是苏格拉底”,⑨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底线》,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可苏格拉底对此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这就给人类思想史以极大的“反讽”想象空间。从被称为“混乱之母”的浪漫反讽到后现代的反讽解释,反讽被不断赋义到近乎反讽的程度。黑格尔视苏格拉底的反讽为“人对人的特殊交往方式”,是“主观形式的辩证法”,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9页。是以自己的故作无知去引导对方认识自己的无知,是绝对理念的显现手段。克尔凯郭尔则将反讽置于整个人类的存在来考察,认为“反讽本身便是存在的本质,须于无处不在的反讽之下认识事物”。肯尼思·伯克从语言与行为的关系以及修辞批评的角度入思,对反讽的诠释,不仅是语言符号学的,而且触及到这个时代符号反讽的实质。伯克试图“通过提示隐喻、换喻、反讽、提喻这四个比喻,尤以反讽为中心,去消解二元论”,在伯克看来,反讽相当于有着多元视角之视角的总形式;反讽展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可能,它所强调的不是线性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时间性”,而是作为“没有终结的会话”的历史过程的“空间性”;语言存在于多元多层的关系中,其本身就是一种反讽性的存在,“对立双方中有一项起着语境作用,它赋予另一方意义”。推演开去,所谓事物的定义,总是以“否定性地言及”事物为前提,并作为语境存在于前提中。正是这种悖论赋予事物以关系性,成为意义的重要因素。所谓语言,乃否定性前提本身的产物,如果词语是显在层面的话,那么对立方的词则是超越性层面、潜在层面。同样,保罗·德曼也从语言的修辞性角度去思考反讽。德曼推崇施莱格尔,认为人们对理解力与语言关系的过于乐观是可疑的。在德曼那里,反讽是“无限的绝对性否定”力量,是“对实体自我化、意义、起源或者作为终极的阐释性真理等的拒绝”,是文本自我审察之令人弦目的过程。
伯克和德曼都将语言的修辞性,作为入思反讽的前提,启发我们对反讽时代表意规律和符号特征的探究。那么,反讽时代,符号及其表意究竟有什么特征呢?笔者用“否定”、“距离”和“断裂”这三个关键词来描述。伯克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对立项之间是以“否定”性的关系存在。如前所述,所谓语言,不过是否定性前提本身的产物,语言的两个对立项互为语境,意义则为语境所决定。这样词语总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它必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显在层面,一个是潜在层面。如果此词语是显在层面的“yes”的话,那么处于潜在层面或超越性层面的就是“no”。这两个层面既相互否定,又相互赋义。其对立项共同拥有的中间部分,即是被排斥的第三项,对双方起着限制作用,并构成运动不已的中间地带。伯克反讽原理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揭示了语言符号自身存在的悖论性或反讽性特性,而且将这一特性分解为对立项和中项,呈现出语言符号的构成性特点,并对符号“标出性”的研究具有某种启示性。
德曼从浪漫派反讽那里得到灵感。他在语言与理解的不可能关系上发现了符号、符号行为之间的“距离”,德曼质疑,“批评家们误认为可以复制或‘感性重现’作家灵感闪现的瞬间状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存在于文本与评论之间’以及‘时间形式的批评家理解行为内’的某种‘存在论距离和间隙’”。从此点检查,反讽是一种艺术手法,一种美学,其符号特征即在于,言说者“即使与被言说之物发生关联,它也保持距离,一个嬉戏的距离,以美学技艺为手段去言说。”难怪,人们常常把反讽时代称作“审美化”或“泛艺术化”时代。德曼将这种“距离”或“分离”性归于语言中无所不在的修辞性结构。而语言符号及非语言符号的这种“修辞性”在反讽时代正被不断夸大和强调。
本雅明“历史等于翻译”的反讽解释被德曼引用和发挥,并由此引出符号及符号文本内部的“断裂”性。在德曼看来,“施勒格尔反讽色彩的批评,作为新的规范性决定力量,与破坏原有文本稳定性的翻译行为相类:摧毁原有秩序,摆脱既有的规范,使文本流动起来”,导致“原作与翻译之间的断裂性,语言与意义之间的断裂性,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断裂性”。②以上关于克尔凯郭尔、伯克、德曼等的反讽理论表述,参见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93-100页。
关于反讽时代符号及其表意特征的论述,显然比我上面的叙述还要复杂。“否定”、“距离”、“断裂”也不全都在符号和符号文本的某个相同层面来谈论。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通性。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比较直截了当,反讽的一贯之规是:“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在我说话之时,思想、意思是本质,而词语是现象。”③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底线》,第212页。今天的符号学家对此表述得更加简明:反讽就是符号的“呈现义/表现义”,或者“表面义/实际义”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互相否定。①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211-215页。这意味着,作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的符号,“感知”与“意义”、 “能指”与“所指”不是“合”的关系,而是“分”的关系,不是“同”的关系,而是“异”的关系。单从“感知”或“能指”无法直接洞察“意义”或“能指”。换种说法也对:感知/意义、能指/所指之间不仅不透明,有时简直模糊得像黑洞。这个特点,既是语言符号的,也是非语言符号的,覆盖反讽时代的人类表意系统——文化全域。
符号的此一特点,决定了文本的表意方式。文本是一个被组织的符号链,这个符号链在接收者看来具有时间向度和意义向度。反讽时代的文本,因符号表面义与实际义的悖谬,“真实”意义,或者说意义的“真相”移出文本之外。不是说文本没有意义,而是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发送者要表达的意义。也不是说发送者没有诚信,恰恰相反,而是说文本不可信:文本不直接呈现实际意义,或者“不再指向意义,只留下意义的痕迹,或者说似乎有意义的逗弄”。②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反讽时代符号文本的这个特点,早在浪漫反讽派那里就被察觉,施勒格尔根据其评论《断想集》的结论认为,“所谓的文本语言是逸脱于意图的”,文本自律性,使发送者的意图被“误读”或“误解”成为常态,没有终结。③施勒格尔:《浪漫派风格》,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页。
意义移出符号、移出文本。意义发送者的真实意图,被隐藏在符号和文本之外。或者其意义发送的目的本身就是反意义的,比如某些先锋艺术。“误读”或“误解”成为常态。面对符号及其表意的如此特征,真正的符号主体在哪里?或者主体符号学如何可能?
困难是明摆着的。克尔凯郭尔《反讽概念》开篇就指出:“作为无限、绝对的否定性,反讽是主体最飘浮不定、最虚弱无力的显示。”那么,“最飘浮不定”的主体,如何把捉得住?更进一步,他认为反讽只有现实因素存在,不复有主体性,因为主体性已经被赋予世界之中。④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底线》,第1、226页。德曼通过凸显动机、语言形式、内容之间的隔阂,实际上消解了传统的认识论主体。显然,在反讽时代,真正的符号主体已经不可能是传统的认识论的。建立主体符号学,必须另辟蹊径。
从符号化过程来看,主体行为可以发生在三个环节上:发送、文本、接收。诚如前述,在反讽时代,发送主体和文本主体已隐而不彰,或者躲藏在符号、文本的烟幕之后。发送主体和文本主体的隐退,唯一让一个可以把握的主体留下并在场,那就是接收主体,亦即文本的接收者。这个接受主体,实质上是一个解释主体:符号和文本的意义靠接受者来解释、来赋予。面对符号和文本,解释即意义。或者说,解释建构意义。显然,让解释主体来担当符号主体,是反讽时代符号表意的特征所决定。因此,建立解释主体,就成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内在要求。
二、解释如何成为符号主体
符号学与“解释”的关系与生俱来,已有近百年历史,但成为符号主体是最近的事。符号学哲学学派的创始人皮尔斯,在对符号进行逻辑三分时,就将“解释”与“符号”、“对象”并列,组成符号的三元组合模式,并充分注意到解释项在符号化过程中的作用:“我所说的符号化过程 (semiosis),意思是指一种行为,一种影响,它相当于或包含三项主体的合作,诸如符号、客体和解释因素”。⑤参引自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18页。他还据此提出“无限衍义”与“试推法”等关键理论,奠定了当代符号学的基础。后继者莫里斯发展了皮尔斯的解释理论,不仅认同符号过程具有三种成分:“指号媒介物 (sign vehicle)、所指谓 (designatum)和解释 (intepretant)”,而且认为“解释者 (interpreter)也可以包括进来作为第四种因素”。⑥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80页。这里的“指号”是“符号”的另一种译法。艾柯在深入阐发皮尔斯、莫里斯符号解释理论的基础上,又从“各种各样的解释成分”、“无限符号化过程”和“代码理论中的解释成分”等方面,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系统和深化。①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78-83页。
不过,虽然皮尔斯、莫里斯和艾柯一个比一个更加重视“解释”在符号表意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还没有谁将它提升到符号主体的位置。或者说,由于历史语境和时代知识内在逻辑的制约,使他们都还未将解释作为符号主体。在上面的引文中,皮尔斯在谈到“解释”的时候提到了“主体”,他认为符号化过程是符号、客体和解释因素这“三项主体的合作”。可诚如艾柯所指出,此处的“‘主体’并非人类主体,而是三种抽象的符号学实体”。②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17页。诺伯特·威利也作如是观:“不管符号、客体还是解释项,对皮尔斯而言,都不是作为主体的人。”③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文一茗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页。其实,在皮尔斯那里,解释只是符号引起的观念。我们从皮尔斯关于符号的定义可以看出:“符号代表相对于其产生或调节之观念的东西……它所代表的东西被称做对象:它所传达的即其意义;它所引起的观念,即其解释成分。”艾柯的理解是正确的,皮尔斯之所谓解释,只是保证符号有效性的因素,“是指涉同一‘客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诠解第一符号的另一种符号”,而另一符号还将被另一符号所解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走向“无限符号化过程”。④参见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78页。另一方面,解释的作用在皮尔斯符号理论体系中是有限的。皮尔斯把符号分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三类,在他看来,解释只在规约符号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规约符号“如果没有解释者”,就“会失去那种使它成为符号的特性”,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则不会。⑤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82-283页。莫里斯从行为主义理论出发,将“解释”定义为“作为一个指号所引起的反应倾向”,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只蜜蜂找到了花蜜,在回到蜂窝去时,以“跳舞”的方式指引其他蜜蜂飞向蜜源,这之中,跳舞是符号,感受到跳舞的其他蜜蜂是解释者,而这些蜜蜂因为跳舞而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就是解释。⑥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137、183页。
当然,无论是皮尔斯、莫里斯,还是艾柯,都为解释成为符号主体从不同角度开出了巨大的空间。皮尔斯认为,由解释引出的无限符号化过程,最终会触及那个最大的符号—— “绝对客体”。⑦参见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79页。莫里斯在一处把解释对符号的意义强调到极致:“某个事物是一个指号,只是因为它被某个解释者解释为某个事物的一个指号。”⑧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80页。艾柯也曾断言:“符号出现与否的关键就在它是否得到解释。”⑨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第103页。但他们都没有将此观点全面阐述,并贯彻到自己的全部符号学体系中去。
就笔者目力所及,当今世界真正承续皮尔斯、艾柯传统,因应反讽时代的符号特征及要求,将解释作为符号主体,建构起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体系的,是赵毅衡的新作《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下称赵著)。⑩下面评述此著的相关引文均出本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不再单独注明。为了查明解释是如何成为符号主体的,有必要对赵著做一粗略分析。
如果说,皮尔斯、莫里斯、艾柯还是在与“符号”、“对象”的关系中谈论“解释”的话,那么赵著则是在“解释”中谈论其与“符号”、“对象”的关系。正是这种“翻转”或者“颠倒”,使赵著最终确立了解释这个符号主体。
人类因追寻意义而存在,因表达意义而符号,并因此成为符号的动物。处理人类、意义、符号的关系,应是所有符号学的工作。赵著在此一问题上,首先承认意义决定符号。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是符号必定携带意义。没有无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无符号的意义。哪怕是“空符号”,也迫于语境压力而逼出意义。因此,意义从哪里来,谁决定意义,才是决定符号主体的关键。赵著认为,是解释决定意义。为了确立解释的符号主体地位,赵著遵循了五条符号学原则。第一,意义决定人的存在和符号的存在;第二,解释决定意义;进而引出第三条:解释决定符号和文本。是否符号、文本,是怎样的符号、文本,解释说了算。解释为符号和文本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由于符号必有意义。为捍卫解释提供意义的唯一性,或者说坚守解释必定能提供意义的绝对性,赵著又引出第四、第五条原则,即“任何解释都是解释”、“断无不可解之理”。第四原则,确立了任何解释的正当性,为符号、文本表意,释放出无限空间。第五原则,从解释角度,论成任一符号和文本必是意义之物。
这五条原则,彻底颠覆了以往将“发送者”作为符号主体的历史。发送者成为符号主体的论述逻辑是:“发送者→符号 (文本)→接收者(解释)”这个符号化过程,是层层决定的关系:发送者决定符号(文本)的意义,符号(文本)决定接受者如何解释意义。接收者解释的合法性,来源于发送者。发送者君临一切、主宰一切。接收者则处于被动之被动的地位,毫无主体性可言。 “言不尽意”体现了发送主体的“特权”。所谓“言不尽意”,不仅指符号、文本之“言”,也指接收者解释之“言”。所有这些“言”都无法穷尽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意图意义控制、判断文本意义和接收意义,高居于符号化过程的其他环节。
发送者高于一切的符号化过程,对于确立发送者的主体地位看似无疑,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发送主体往往落空,是个“虚幻主体”。一方面,符号、文本的发送者,一部分根本不是人,谈不上主体,如自然符号。但悖论是,没有人的介入,没有意义的赋予,任何自然物事,又不可能自动成为符号。“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因为解释的介入,而具有符号意义。另一方面,符号、文本的发送者可能缺失,或者无法确定。除自然符号外,再比如大局面历史文本: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历史阶段,如何找到其发送者?再一方面,即便曾经有一个作为主体的发送者,由于符号传送的时空距离、表意距离,也很难追溯,比如甲骨文、三星堆文字的符号发送者是谁,很难确定。最紧要的方面,是发送者的意图意义,依然要靠另一符号、文本来获取,而其中的“真/伪”将卷入更为复杂的问题。进入反讽时代,意义更是移出符号、移出文本,有意制造意义“烟幕弹”。总之,如此众多的因素,使发送者这一符号主体成为最靠不住的虚幻主体。“言不尽意”也因此在符号学论域中成为一个伪命题,由于发送主体的不可靠,我们无法确定“意”所包含的真实内容,就根本谈不上“言”尽不尽意的问题。
解释作为符号主体,才真正有效地将“主体”锚定在人身上,也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把这个“主体”贯穿到一切符号表意过程始终。解释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是人类通过符号、文本达到理解、进行对话的行为。而在狄尔泰看来,“理解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的主观体验性,它也属于读者,而非仅仅属于作者”,职此之故,“一个文本,甚至于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其作者所生活时代及环境的文本,都是能够阅读和被理解的;而且任何人都不需要完全以作者式的阅读来理解文本”。①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4页。钱锺书先生对此也颇有会心,所谓“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误解或具有创见而引人入胜”,②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20、1073页。以及“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③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10页。等等都力图表达解释在符号化、文本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以为,只有解释作为符号主体,这些现象也才解释得通。因为,诚如伽达默尔所言,从根本上说,我们永远是从我们自己的意义视域出发来看待文本的,解释理解实际上是个自我理解的行为:理解我们自身历史的真实以及它和过去连绵不断的联系。④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页。如果“人文学科的目标是理解,而自然学科的目标是说明”这个命题真而不伪的话,⑤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董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99页。那么,也只有解释作为符号主体的那种符号学,才能兼具自身的双重职责:“既是诸科学中的一门科学,又是诸科学的工具。”⑥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第78页。说到底,“人类历史就是一系列的解释”。⑦福柯语,转引自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77页。
解释符号主体的确立,使赵著将发送主体的符号化过程:“发送者→符号(文本)→接收者(解释)”颠倒和重建为:“发送者←符号 (文本)←接收者(解释)→……”。这一颠倒和重建,使赵著所建构的主体符号学,具有了朝向过去、此刻和未来全面开放的品格:符号向意义开放,意义向解释开放,解释向接收者开放,接收者向人开放。这种全面开放的符号学,真正具备了应对、考察和分析当今这个反讽时代符号和文本的能力。因为当意义移出符号、文本之后,唯一可靠的主体是解释主体。
三、解释怎样进入主体的符号学
主体符号学建构的另一维度,是关于主体的符号学。如前所述,主体的符号学,即是对人这个主体进行符号学研究。在这方面,巴黎符号学派的“激情符号学”被视为先驱。但以笔者的视野范围来看,除科凯的部分论述,其他符号学家的研究还是一种“非主体的主体符号学”,当今世界对主体的符号学有所建树、有明显推进的是诺伯特·威利的《符号自我》,①下面评述此著的相关引文均出本书 (文一茗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不再单独注明。以及前面提到的赵著。
《符号自我》从“自我”切入“主体”,建立“主体的符号学”。它以皮尔斯的“符号即自我”为逻辑起点,着重解决自我的内部构成、对话方式及其与他者的关系。它整合皮尔斯和米德的思想,提出自我由“客我-主我-你 (me-I-you)”三维构成。主我、客我、你分别代表现在、过去和未来时段的我,符号自我即是这三者间的不断对话、相互运动。“主我”与“客我”间的对话表现出间接性、自反性特征;“主我”与“你”的对话则是直接的和线性的。这种对话虽然在符号自我内部进行,但不是封闭的、自循环的,而是经由“客我”通达广义他者:外部环境、文化规约、意识形态等,亦即文化全域,实现符号自我与符号社会的“符号互动”。广义他者积淀为客我的主观经验,以符号形式参与当下主我的生成,部分体现为“身份”。身份作为自我的符号集合,一方面确证了自我的社会性与互动性;另一方面又制约自我对文化符号的接受方式和传达渠道。当代社会身份的繁杂和冗余,极有可能导致自我本体失落的危机。这种危机还来自自我面对经验世界时,迫于超我理想或本我欲望的压力,所作出的上、下还原:或者还原为某种文化共同体,或者还原为某种本能机器。无论哪种还原,本体自我都存在被“吞噬”的风险。对此,符号自我内部具备调节机制:从其对话性、自反性中获取反还原的张力、倾向和平衡。威利的《符号自我》,虽然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意欲通过对符号自我的分析,从实用主义的立场,为美国立宪寻求新的平等、自由根据,并自信“为民主提供了人性的基础”,②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第19页。但其对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具有明显的推进。
应该说,赵著是接着威利的话往前说的。在赵著看来,入思的“自我”,只能是过往的和未展开的自我,此刻的“自我”正在“思”,无法把握,只有经由“思”对过去和将来的自我进行把握,才能得到符号自我。赵著也同样认为,符号自我是由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身份”构成。自我落入世界,落入情景,就因时因地展开并呈现为若干“身份”。说人活在自我中,实际上是说人活在“身份”中。 “身份”是人和“自我”的在世形象。在这个意义上,身份的合集就是“自我”或“主体”的元语言。显然,这正是威利主体符号学的进路。赵著的独特贡献在于,提出每一个“身份”都是“自我”的一个“符号”、一个“文本”。既然是“符号”、是“文本”,其符号主体就依然是“解释”。也就是说,这些作为自我的符号、自我的文本,同样符合赵著的最高原则,解释使之成其所是:这些符号和文本在解释中获得意义、获得本质,而这个本质就是“自我”的本质,也是“主体”的本质。这样,赵著关于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就又回到对符号的主体研究上。主体的符号分析到此成为真正的符号学问题。主体符号学的两个维度在此处达成媾合和体系化。
除了查明一般主体、发送主体的构成外,建立解释这个符号主体的赵著,对威利《符号自我》的另一突破,是从“解释主体”的角度,切入主体的符号学,并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赵毅衡将“言不尽意”翻转为“意不尽言”。这个“言”不仅是符号、文本之“言”,也是解释之“言”。所有这些“言”绝不是发送符号主体的“意图”意义所能涵盖,理论上讲,无法穷尽。这样,在“经验/表述”的关系上,在回答人的经验在表述上如何可能,以及经验怎样得到表述和如何表述等一系列主体符号学的问题上,赵著走着另一条思想路线:既不是经验决定表述,也不是表述反映或决定经验,而是解释决定表述和经验。这就触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解释的符号主体”究竟是一个什么主体,如此神通广大?换个问法:谁决定符号、文本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如何可能?解释主体是如何获取自身而“站立起来”的?
诚然,在赵毅衡那里,面对符号、文本,任何解释都是解释,似乎解释拥有无边的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自由是有前提的。因为任何符号解释活动,都是解码活动。意义植入“感知”,成为符号,能够被接受、被解释,是有规则的。任一解释和意义重建,都会受到这一规则的“控制”。这个规则就是符码。而符码的集合,就是元语言。解释主体的解释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元语言的“限制”,解释的可能性、合法性来源于元语言。“控制”、“限制”、“合法性诉求”等即是“规训”,解释主体正是在元语言这种不断的“规训”中成长,并成其为自身。这样,元语言成为解释主体建构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在赵毅衡那里,作为文化的元语言,又是被元元语言所决定的。这个元元语言,就是“意识形态”,“它的主要任务是文化意义活动的评价体系。每个社会性评价活动,也就是意识形态支持的一个解释努力。”不难看出,赵著从解释主体这条路,同样实现了符号自我与符号社会的“符号互动”,并不期然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相遇: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对文化的决定和建构作用,虽然有别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却与广义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精神相通。这样,引入“解释主体”的赵著,就从另一个方向,将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这已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论。
结语
建立解释主体,在笔者看来,不仅是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建构的有益尝试,其突出的意义更在于,它引导着符号学研究范式的某种转型:从单纯的方法论,转向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固执地认为,这个“主体”多元含混:兼具“非同一性”、“行为主义”、“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既延续了皮尔斯、艾柯一脉的传统,又汲取了当今人文学术最具活力的诸种思想。它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应对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反讽时代,能够有效处理当代文化运演中的某些复杂问题。但与之相伴的疑虑则是:如此发展下去的符号学,在有背其某些初衷的前提下,如何才能在开出的新路上,“人文的”、“有效的”继续前行,而不会给符号学本身一个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