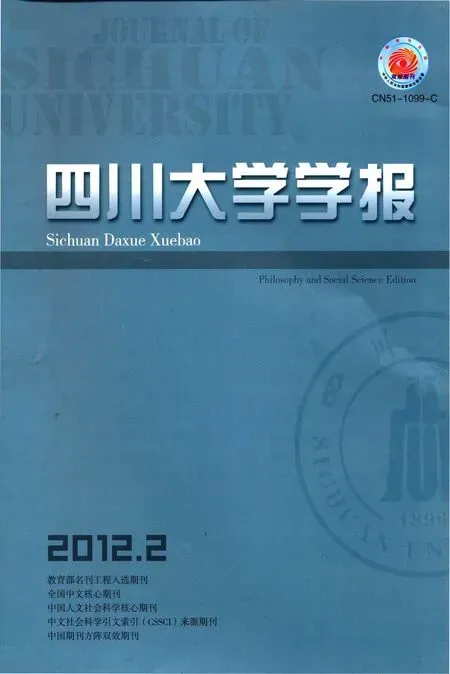俗世理想,从来如此——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民国花轿研究
2012-04-12陈长虹
陈长虹
(四川大学 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64)
四川大学博物馆民俗展厅陈列着一顶木雕花轿,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个画着阴阳太极图的牌示,四个绘有“黻”形图案的执事牌,四根顶部雕刻成凤凰头的灯杆,四件抬箱,四顶轿夫戴的彩绘竹编尖顶帽。花轿为木质穿斗式,轿厢两侧固定着两根约4米长的抬杆,另配有四根辅扛。轿身正方形,长1.01米,宽1.05米,高2.02米,采用木刻、彩扎、玻璃画、朱漆贴金、银绘、髹涂等多种民间工艺,重彩装饰。四角攒尖顶,中心为木刻镂孔髹金宝珠,往下四翼为木雕髹金飞龙,翼角为上昂的龙头。轿顶镂刻密密麻麻的花草图案,依序排列了76束火焰状木刻,分别用两寸长的弹簧加以固定,火焰中心镶嵌小圆镜,轿身晃动则熠熠生光。轿顶里面罩纱窗布,这也是几乎密闭的花轿上唯一作用于透气的设计。轿身正面开敞,上下搭挂两幅蜀绣软缎轿帘以供新娘出入,画面内容均如戏曲场景,上幅题记“状元及第”,下幅题记“全家福”。三面轿窗玻璃完全封闭,玻璃内用彩扎工艺装饰成戏台,左侧场景为“王母寿”,背面为“玉祖寿”,其下是“状元打马游街”,右侧是一“祝寿场景”。左右侧轿身拦腰处为覆瓦状玻璃画,双层,12幅画面。上层6幅所绘内容均取材自戏曲故事,经考证左侧依次为《牛郎织女》、《三难新娘》、《长生殿》里的《乞巧》一折,右侧依次为《断机教子》、 《拜新月》、《红绡姻缘》。①谭红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清代花轿》(《文博》1989年第4期)中,对这顶花轿进行了描述性的介绍。下层6幅为装饰性花鸟图案。花轿底部是若干戏台,里面是成双成对的彩扎人物。花轿基座呈栏干造型,正面留进口,有木雕彩绘小狮子分列左右。花轿的绘画手法、雕刻和彩扎工艺在细节处显得粗率,但是面面俱到,完整的画面之间都用浅浮雕或镂雕的方式布局为人物和花鸟图案,没有丝毫空白间隙,可以想像当时的工匠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制作着这样一件婚嫁用品。不论从哪个角度观看,整顶花轿都像一座正在上演着多幕戏曲的勾栏戏院。②厦门博物馆展出的潮洲布袋戏的舞台,与这顶花轿的外观惊人的一致。在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戏梦人生》里,演出布袋戏的舞台同样如此。资料显示,国内各大民俗博物馆一般都有花轿入藏,时代都大致模糊地定为清末民初。而轿身纯用木头雕刻,工艺繁琐,尤其是包含了层次相当丰富的画面内容和可资考证的故事场景,并且保存基本完好的,川大博物馆的这一件实属少见。
一、时代与功能的分析
一件文物,首先来确定它的时代。就品相来说,九成新,保存良好,只有一些小配件的脱落。根据最原始的卡片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知道这顶花轿及其附属物品全部收购于成都一家专营红白喜事的民间轿行,时间为1956年,具体制作年代不祥。四件抬箱上可以看到用毛笔书写的“上草市街鸿发号萧记”字样。草市街是成都市的一条商业老街,至今犹存。至于鸿发号、萧记,笔者至今没有在本地区清末到解放初这一大致时段的文献资料上找到任何相关记载。专理婚丧喜寿诸事,出租相应物品的花轿行作为一种行业在成都出现得比较晚。由清末傅崇矩编写,成都通俗报社刊印于1910年的《成都通览》,全面详实地记载了当时成都社会的各行各业。书中有对轿班、轿子匠、制轿和踩轿者的详细记录,描述了草市街的各种店铺,但是并没有提到花轿行。①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308-311、507页。由此可以推测直到清末,成都地区还没有花轿行出现。到民国后期,全国各地花轿行的生意逐渐凋落衰败。建国以后,城市里的花轿行更被官方严格取缔,只有部分乡村还零星保留着新娘结婚坐花轿的习俗。②欧阳平:《旧时的轿子、滑竿、花轿》,《红岩春秋》1996年第2期。我们很难想像在成都这样一座省会城市,招募各种行业的工匠费时费力制作一顶复杂的花轿,准备出一套完整的出行仪仗是1949年以后的事。因之,虽然这批文物的入藏时间是1956年,基本上还是可以断定,它的制作时间是在民国时期。
其次,我们来谈谈它的功能 (用途)。中国传统的婚姻仪式,自《周礼》确定的六礼以来,两千年基本保持不变,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过程。六礼过程中,亲迎是最后一个阶段,也是婚礼在长时间的准备后臻至最高潮的阶段。迎,需要工具。早在北宋,民间就开始用花轿迎娶新娘。③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笺注》(下),伊永文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79页载:“至迎娶日,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迎至女家门,女家管待迎客,与之彩段,作乐催妆上车檐,从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谓之‘起檐子’。”此处花檐子,即花轿。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首段绘轿夫抬着遍插时令鲜花的轿子,笔者在《清明上河图里的轿子与花》一文中,考证此为花轿的早期图像。在讲究礼制的古代社会,民间轿子受到官府的诸多限制,但是花轿从来不在此例。清代民间花轿在轿顶上可以装饰金属宝珠,轿檐子可以是双层,四角可以挂小宫灯,轿帷子可以镶嵌珠宝,并用金丝银线刺绣出“龙凤呈祥”、“鸾凤和鸣”等图案,新郎也跟着沾光,被称为“小登科”,这在封建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时代显得非常特殊。究其原因,史书无从考证,但是这种“格外开恩”也正从侧面说明,花轿迎亲对于中国人,“兹事体大”,重要性不容小觑。
“嫁”者,“女归家”也。中国古代女子结婚素称“于归”、“出阁”。花轿作为“归”的工具,一个女人一生只坐一次,就像女人一生 (应该)只嫁一次一样 (妇女再醮只能于黄昏乘一顶小轿偷偷进门),在中国女性的生命中,具有相当深刻的“时典”意义,是一个女子从娘家闺房走向夫家厅堂的中介桥梁。从这里进去再出来以后,一个姑娘就完成了理论意义上的蜕变,成长为一个妇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一般家庭是不大可能置办只用一次的花轿的。因此在城市,只有贳器店 (清代以后即发展为花轿行)会制作准备,用于出租。财大气粗的富贵人家有委托贳器店定制并言明支付高额租金得以首次使用的。在乡村,通常由宗族祠堂醵资置办,首先用于满足本族人的子女婚嫁之用,得空也用于出租。④宁波市志编委会:《宁波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828页。花轿这种物品自从出现以来,就不是属于某一个家庭或某一个女性的私人用品,是被反复使用和观看的,昭示于世人的公共物品。
虽然从清末开始,主流社会阶层就大力倡导婚恋自由,文明结婚、集体结婚等新名词频繁见诸于报章杂志,西式婚礼在中国很多大城市时有出现,然而察之民众实际生活层面,整个民国时期,大多数家庭嫁女仍然行旧式传统,采取花轿迎亲的仪式,嫁妆甚至比清代更为侈丽。⑤周全德:《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爱情观的发展》,《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1999年第1期。从刊刻于民国时期的各地县志上,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描述:“女曰于归,曰嫁。嫁媵以奁,俗名‘陪嫁’。奁之属,木器则床榻柜椟,……靡不精备,历陆离娄,藻以金漆;服饰则钗簪环约,……填笥溢厨,随用不缺;什物玩好之类,……纷杂琐繁,不可殚述。……所有者,分盛于棜架而荷之,谓之抬盒。盒之数,以百计,以十计,视贫富为隆杀。经过街市,必纡道以炫之。”⑥《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1年,第226页。我们可以想象,即令一派“西风美雨”兜头浇沐,民国时期的中国街头,频繁上演的,仍然是这样一幕传统婚姻场景:前面开道的,打执事的,敲锣打鼓的,后面抬嫁妆的,簇拥着中间一顶花轿,“纡道以炫之”,“观者如堵”,是一起大肆张扬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蒙着盖头的新娘一旦走进花轿,人们就不再看到这场沸沸扬扬惹得街市喧哗的婚姻事件的主角了,在围观者的视野中清晰凸现出来,成为被看的主体的,是花轿这件附属工具。无数的人跟从围观,看到的无非是花轿和嫁妆;无数的姑娘向往憧憬,憧憬的无非也是花轿和嫁妆。此时,花轿固有的功能意义相对消隐,而潜在的仪式性意义、宣传教化的意义,正被空前清晰地彰显出来。
除用于抬新娘外,近代很多地区还流行一种“晾轿”习俗,即由男方在迎娶前一日抬着空轿到街上预演一番迎娶过程。清代缪润绂曾在《沈阳百咏》中描述当时的晾轿盛况:“马蹄得意试轻埃,晾轿人争羡八抬。灯彩辉煌铙吹沸,前锣听响十三开。”并按称:“俗例于婚娶前一日预请娶亲男客数人,衣冠骑马前导,后列鼓吹灯笼,极后抬大红官轿一乘,诸事俱比照迎娶体例,名之曰晾轿。宗室娶妇,及娶宗室女,用八人裒舆,余概用四人,锣响十三开则达官显宦家矣。”类似的还见于黑龙江地区的汉人婚礼,“男家于期日,新郎率彩舆游街,鼓吹列仗,谓之‘演轿’,并至女家行谢嫁妆礼”。①转引自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2期。在所谓“晾轿”、“演轿”的过程中,花轿不承担抬新娘功能,而直接成为一件供众人围睹观看的物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需要重点从这样一些角度来审视一顶花轿:1.花轿是放在轿行中用于出租的,是一件商品。出资制作花轿的是轿行的老板,制作者是一批无名工匠,需要满足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心理,因此不代表某一个体 (制作者、出资或赞助者,或者使用者)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爱好,其暗示性、符号的象征意义都不具备个别性,具有群体性;2.花轿不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而是婚嫁礼仪过程的产物,是一件礼仪用具。除了抬新娘这一实际功用外,其潜在作用是在仪式中被集体观看,具有唤起集体体验的仪式意义;3.花轿是游离于官方政治和文化之外,发生、制作和使用于民间的一件物品。花轿上的各种图像与装饰所表述的并不代表社会主流文化层所倡导的道德节律和规范,而是一种朴素的民风情怀和民俗文化心理;4.花轿是一件民间工艺品,反映民俗艺术的一件艺术品。上面的木刻、彩扎、玻璃画等不可避免地饱含民间工匠的独特匠心,体现着一个特定时段民间艺术家潜在而共通的视觉表达方式和审美情趣。
稍微涉足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学者都知道,中国古代典籍虽然浩如烟海,但是相关工艺美术方面的资料却相当匮乏。历代工匠大多不具备著述立说的文化素养,而记载历史,掌握着所谓“话语权”的文人又往往对工艺美术不够重视,甚至目为“奇巧淫技”加以贬斥。从现存风俗志、风俗词典、民俗专著上,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对婚姻习俗的名称以及现象的罗列,但对处于婚姻仪式至关重要地位的古代花轿却找不到任何详细的介绍说明。
在近代民间工艺品研究领域,学术界普遍的倾向是重视工艺品群类的材质、工艺技巧、民俗内涵,单件物品则往往停留在浅层次的外观描述,即“是什么”,而少有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比如,“为什么”。似乎一件制作于近代的文物和古代文物完全不同,没有就其细部详加阐释的必要,更不具备任何值得深掘的价值。造成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就在于时代太近。对于清末民国近百年的历史,我们有大量文献史料可供翻阅,还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理所当然的认识。比如,近代中国社会,缺失爱的观念,极端重视贞操,妇女的地位普遍低下,等等,都是近乎颠扑不破的真知。然而,正如杨联芬所说:“作为一段离今日最近,影响今日最剧的历史,晚清却成为中国历史叙述中真相被遮蔽最多,最语焉不详的糊涂史。……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无名状态的女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面目,就更加模糊不清。晚清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处境,新教育,不缠足运动影响晚清女性生活的细节,晚清政治文化运动对女性心理,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具体影响,初期女权运动发生发展的详情,却空疏几至空白。”②杨联芬:《回到现场,重构历史》,《读书》2005年6期。此种状况往后到民国也是一样。“知道得太熟了,所以也逐渐失去了对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 (defamiliarized),才能对这一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③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我认为,这样一顶民国花轿,广泛采用到一个时代各种流行的民间工艺,被反复使用于中国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场人生仪式,在在关涉到当时人的婚姻、爱情、男女、家庭观诸多范畴,先天具备详加审视的必要。而对它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两类人:作为制作者的民间工匠,和作为使用者的普通女性。可是,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女性群体也如民间手工艺人阶层一样,处于一种相对的失语状态。④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期。那么,我们如何抛开和古代知识分子一样的傲慢态度去寻找这顶花轿的真实呢?它确实有值得开挖的别样真实吗?让我们回到文物本身。
二、“图说”花轿
20世纪曾盛极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崇尚对文学作品的“细读”,主张审慎、认真、反复、仔细地阅读作品,从词组、段落及其关系中把握和理解作品的主旨与深义,摒弃将先验的意识和理论导入作品。我认为,对这样一件以图像呈现一切的实用工艺品,我们大可尝试着采用这样的阅读方式,“就图论事”,“就文论文”,对画面内容进行分析,从文献材料中爬梳相关故事大致的来龙去脉,探讨其意旨,解释这些题材使用在婚嫁礼仪用具上的含义,进而结合图案布局、细部装饰,讨论从单个图像到整体组合之间的联系。最后,尝试推测花轿所讲述的,即其背后所隐藏的,关于当时社会的婚姻、爱情、男女关系,与家庭观念的一些隐约情状。
关注重点将会放在六幅玻璃画、三个戏台、两幅轿帘上,他们是构成花轿这个封闭空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于其他细节装饰,如用于辟邪的镜子、意味吉祥的龙凤和狮子,以及花轿附属物品上的图案,如象征阴阳和谐的双鱼、太极图等,由于它们在婚姻方面的象征含义大体不言自明,且在这顶花轿上只起着零星的点缀作用,考虑到文章篇幅,本文就不再特别提出讨论。
(一)三个川剧彩扎戏台。三个使用彩扎工艺制作的戏台处于花轿上部,外面罩透明玻璃,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今天时尚用品店的陈列橱窗。彩扎人物的面部采用泥塑,多数绘成川剧脸谱。人物衣饰用铜金纸和绫缎搭配而成。左侧:王母寿。画面布局为一列列仙山楼阁中的乐舞群仙,根据人物的排列组合,以及周围的装饰物如蟠桃、团寿字样等,确认为众仙赴西天瑶池向西王母祝寿的场景。西王母故事最早出自《山海经》,金元杂剧中出现了相关祝寿题材的名目,近世京剧、秦腔、川剧有《王母寿》、《瑶池宴》等剧目,盛演王母娘娘在瑶池设蟠桃会庆寿,众仙祝寿的故事,为吉庆日子各地舞台上常演的大贺戏。背面:玉祖寿。布局与王母寿大致无二,确定为玉祖寿。民间传说农历四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寿辰,其时,不论天上人间地狱的各路仙佛、凡俗鬼怪的代表,都要上朝天庭,向其祝寿。玉祖寿也是四川戏曲中的大贺戏。玉祖寿下面另有一个小戏台,为状元打马游街的场景。右侧:祝寿场景。布局与前面两幅相似,同样为几列仙山楼阁中的乐舞群仙,有蟠桃、祥云、团“寿”字样等,推测仍然是表现祝寿的画面。由于缺乏明确的中心人物,主题暂时存疑。
(二)两幅戏曲画面的蜀绣轿帘:图一:全家福。画面为楼阁曲栏内数人分列左右,侧身向画面中心一对老年夫妇拱手行礼。有“全家福”三字题榜;图二:状元及第。画面为头戴乌纱帽的状元和凤冠霞帔的诰命夫人相互见礼的场景。
(三)六幅戏曲故事场景的玻璃画。六幅玻璃画位于花轿中段固定轿杠处最醒目的位置,顺势成覆瓦状突起,左右侧各三幅,每幅高20厘米,宽30厘米。画面风格、题记、排列都和传统版画相似。
场景一:天河配。画面表现为郊野小丘,植深黑色灌丛。纵深蔓延成浅水陂陀,低空有两、三只大雁飞掠。左边一女子踏云而降,红衣青裙,低髻,眉心点梅花妆。右一背笠男子侧身相迎,身旁一头牛扬蹄欲行。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周代,《诗·小雅·大东》里最早出现了牵牛和织女两颗星的名字。汉魏时期,人们在诗歌里为这两颗星附会出了颇具浪漫色调的鹊桥相会。同时在河南、山东等地区的汉代画像石里面,我们发现了最早的以此为题材的图像。①参看《中国画像石全集》第3卷,《山东汉画像石》,《河南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到梁代,殷芸在《小说》里勾画出了这个故事的大致轮廓。唐宋以后,和如今流传的牛郎织女相一致的比较完整的故事基本定形,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作为中国古代最经典的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故事的情节相当简单,说到底还是套着一对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传统礼教,自由相恋的经典模式。相较于此类题材通常具有的大团圆结局,一年一会的尾声多少显得有些调子凄凉。然而,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也正表明普通民众对执著与忠贞爱情的赞美与肯定。另外,就主人公的身份而言,牛郎和织女的结合,就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恰好构成了一个最合理想的小农家庭。这也许才是该故事成为中国这个传统农业社会最具典型性、最深入民心的民间故事的根本原因。
场景二:三难新郎。左边一状元装束的青年男子立于书案后,左手执笺,右手举毛笔。右边石栏外有一口井,一朝服打扮的中年人左手高举石头对井欲投,脸侧向青年,眼神微有示意。二人之间为一奉茶女子,斜襟褂子,下着裤,露三寸金莲。图中有类似对联的题榜:“用 (笔者注:此字误,应为“伸”)手推开窗前月,投石击破水中天。”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最早见于明代冯梦龙的《醒世恒言》。明代以后,清人著作中常见相关记载,如禇人获《坚瓠集》三中的《东坡戏妹》,葛煦存所编《诗词趣话》中的“苏黄论诗”一节,都致力于表现苏小妹这个女子聪明智慧,诗才敏捷甚至超过了苏东坡、黄庭坚、秦观等一干须眉才子。这个家喻户晓的才女经后人考证是杜撰出来的,嫁秦少游为妻更是子虚乌有。《三难新郎》在古典戏曲中是个用于逗乐的喜剧短章。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郎的秦少游在新婚之夜为之抓耳挠腮的上联看起来似乎难度不大,而苏东坡的暗中相助也形同作弊,不是堂堂大丈夫所为。为了成全苏小妹的智慧,男人们在这个故事里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嘲弄。花轿上对该故事的图绘不同于传统版画布局,省却了中心人物苏小妹,只简单地勾描了两个呆头呆脑的男子,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婢女。
场景三:乞巧。画面表现为一座简易庙堂,香案前一对锦衣华服的男女前后站立,合十对天欲拜。男子束幞头,圆领衫,腰系革带。女子凤冠霞佩。二人服色皆为深红。相比另外五幅图,这是画面内容不够明朗的一幅。就人物服饰与行动来看,此图应出自川剧折子戏《乞巧》,为《长生殿》中一折。大约自南北朝开始,中国历代的妇女都要在农历七月初七这天,摆上各种瓜果祭拜牛郎织女,并向织女乞巧枣,以得劳动技艺和婚姻匹配的巧。七夕作为古代中国最为浪漫的一个节令,附缀了各种民间习俗,难以计数的神话传说、文人的风流雅事和以此为题材的诗文作品。其中,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故事算得上是最经典的七夕故事。自晚唐白居易《长恨歌》里写出“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一句后,陈鸿在《长恨歌传》里更虚构出这样的情节,“昔天宝十载,辇驾避暑于郦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生生世世为夫妇”。此后,李商隐的《马嵬》、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昇的《长生殿》,都反复以七夕盟誓入题。唐明皇与杨贵妃这段爱情故事经过数代文人的铺排演绎,以七夕聚散为顶点,超越了生死,被抹上了格外纯粹、唯美、坚贞的色调。到近代,川剧舞台上搬演长生殿故事,《乞巧》一折总是演出最为频繁的剧目。
场景四:红绡姻缘。画面右侧为垂着红色帐幔的房屋,屋内一桌,桌上一套茶盏、一匣书、一枝红烛。女子靠坐在桌边,左手挽鬓,俏脸微扬似有所待。屋外二人踏云而至。前一人短打,豹眼圆睁,后一人书生模样,蓝袍,右手搭在武士肩上。屋门上书四字题榜:红宵(笔者注:此字误,应为“绡”)姻缘。红绡来自晚唐裴鉶所著传奇小说《昆仑奴》。整个故事很简单:郭子仪的歌姬红绡,与前来郭府拜访的书生崔芸互相爱慕。崔芸之仆昆仑奴磨勒成人之美,晚上背崔芸入郭府与红绡相见,并盗出红绡。花轿上的图像再现的正是这一段:“是夜三更,(磨勒)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矩,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釭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①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豪侠二,中华国粹经典文库丛书,北京:崇文书局,2007年。《昆仑奴》本来是侠义故事,中心人物是磨勒。没有他,崔生猜不出红绡的哑谜,逾不了十余重高墙见佳人,更谈不上携之私逃。红绡私奔,磨勒为她负出“囊橐妆奁”,一连来回三次,十足一个贪财女子。崔生这个“容貌如玉”的俊俏后生,数年后事发被郭子仪召问,把罪责都推到了磨勒身上,任其发兵捉拿,不加回护,也不像个有义气的人。很显然,这“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全然只是为了成全昆仑奴光彩耀眼的侠客形象。近代京剧、川剧舞台上的《盗红绡》通常都是以老生应工。在花轿的图像里,题名“红绡姻缘”,显然着意于爱情主题。图中红绡着袄裤,童花头,一如《三难新娘》里的丫头。左腿曲支在椅子的桁架上,坐姿也不够雅驯。
场景五:断机教子。画面左边为房屋,屋内一台织布机,一女子背向观者坐在织机前操作。屋后一棵硕大的芭蕉树。一幼童背对房屋行走,身子微佝。《断机教子》本事见汉代刘向《列女传》,言战国孟轲少时,废学归家,其母方绩,乃引刀断其机织,责子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珂因发愤向学。元代无名氏《守贞节孟母三迁》杂剧中即有断机情节。近代京剧有《孟母三迁》,秦腔有《三迁教子》,皆含孟母断机事。而在民间传说中,“断机教子”就成了贤母的普遍事迹。明代沈受先《商辂三元记》,一名《断机记》,讲秦雪梅断绩而督子向学。清代陈二白著《双官诰》传奇,演婢女碧莲,完节教子,父子俱仕,获双官诰。此戏后来演变为《三娘教子》,成为断机情节中最流行的戏。
场景六:拜新月。画面为低矮山墙围成的庭院,一房屋,数小丘,间植青黑色的树,树杪一弯上弦月。正中有圆几,几上两件类似香炉的器皿。一红衣女子站立一旁,挽袖,左手纤指正伸向香炉。与七夕乞拜相关而又有区别的拜新月习俗,在唐代颇为盛行,一般在五月或七月进行,通常是妇女所为,以乞求青春常驻、乞巧、乞婚姻、乞遂人事。川剧里包含有拜月情节的如《妙常拜月》、《貂禅拜月》、《双拜月》等,多在中元前后演出,却不一定是拜新月。其中只有来自元南戏经典《拜月亭记》的《双拜月》,确有新月之指。剧中王瑞兰在花园烧夜香祈福祷告,一曲“香罗带”曲文为:“拜新月,宝鼎中明香满热。刚才间一拜拜将下去,把花枝错当成妹妹到,还须要一步一步拜新月。”《拜月亭记》演书生蒋世隆与大家闺秀王瑞兰在战乱中相遇并订下终身之约,后遭王父反对,将二人拆散。瑞兰不忘旧情,夜间拜月诉说心事。后蒋考中状元,被王家招赘,夫妻团圆。故事从一见钟情讲到私订终身,从几经波折磨难到最后金榜题名,合家团圆,是一出典型的才子佳人戏。
就花轿总体结构而言,表现祝寿和状元打马游街场景的四个彩扎戏台,画面为全家福和状元及第的两幅轿帘处于中心区域,占据了花轿近二分之一的面积,吸引着观者主要的视线。这些图案所提示的“百善孝为先”,和“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个核心理念,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普通民众也了然于心的。观看者的目光只要扫过这些图像,勿需仔细分辨上面的内容,就已经可以获得极大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欣悦与满足。这些图像组合在一起,在花轿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空间,讲述的似乎正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理想中的团圆美满的大家庭。这个家庭人丁兴旺,老人长寿,男人功成名就。这些图像在花轿上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同时也说明,这顶制作于民国时期的花轿作为传统旧式婚姻的标志性物件,表征的确实是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正统观念。
那么女性呢?作为这场仪式的主角,花轿的直接使用者,她在这个目前对她而言几乎是全然陌生的家庭中即将出演什么角色?花轿上的图像是否涉及到对她的角色期待?和贞节牌坊一样,花轿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专门为女性设计的物事,具有明确的礼仪性功能,那么也同样具备规训女子道德的功能吗?我们的视线下移到紧接彩扎戏台的六幅玻璃画上。如前所述,这六幅画来源自六个戏曲故事,而这六个故事都是民国时期成都地区的戏曲舞台上时常上演的经典剧目。①参见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四川省川剧学校、四川省川剧院合编:《川剧剧目词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由于花轿特定的空间,无法表现出故事发展的完整顺序,一个故事是由一个特定的富有戏剧性或典型性的瞬间场景来完成的,整个故事本身需要由观者来复原,这种对故事情景的复原又将进而引导观者去领会该图像在花轿上的含义。②当然,就这一点有人可能会提出置疑,即观看者能否,或者有多大程度的复原故事的能力。况且,在人头攒动的街道,观看者要看清花轿的细部也绝非易事。同样的,民居建筑构件上常见的精雕细琢的戏剧故事画面,若按百分比来算,究竟有多少老百姓有耐心去琢磨每一个故事的含义,从而对其心领神会?然而,这是另一个关于接受者层面的问题,由于对本文探讨的主题没有影响,此处不拟讨论。有趣的是,这六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恰好都是女性。情节较单纯的“断机教子”和“三难新郎”,前者旨在赞美女性的德行,后者旨在夸耀女性的才华,并且这种才华还是通过一定程度上对男性的贬低得以张目的。所谓“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规训,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另外四个是爱情故事,其中“拜新月”、“牛郎织女”、“红绡姻缘”都讲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红绡姻缘”更是一场“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戏,近乎于朱熹指斥的“淫奔”;“乞巧”的故事本自历史真实,男女主角身份特殊,然而他们的爱情追根溯源是乱伦的。这四个故事强调自由恋爱,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关,更与贞操节烈扯不上关系。更进一步讲,是旗帜鲜明地对抗“父母”、“媒妁”所代表的封建礼教纲常的。
那么,在花轿这种标志传统旧式婚姻的礼仪用品上,出现这样一组中心人物为女性,主题为婚恋自由、妇女解放等观念的戏曲故事图像,就有了进一步深究的必要。
三、俗世理想,从来如此
对于古代中国人的婚恋与家庭观,研究者一般持有这样的共识,即古代中国,由于人们普遍缺乏个人主体性,作为一般范畴的爱情意识并不存在,个人的爱情都通过婚姻同化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罗素甚至认为:“在中国爱的情感是罕见的。从历史上看,这只是那些邪恶的婢妾和误入歧途的昏君的特点。”③转引自《爱情读物》,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7年,第65页。同时,由于儒家将夫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确定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始终处于屈从与卑下的地位。宋代程朱理学的确立,使得明清两朝更大肆倡导夫死守节。妇女地位的卑下,在高举传统文化祭旗的五四精英笔下被描绘得非常清晰。胡适就曾指出:“他 (她)丈夫喜欢什么,他(她)也该喜欢什么,他 (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他(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喜欢。他(她)自己不用有思想,他(她)丈夫会替他思想。他(她)自己不过是他 (她)丈夫的玩意儿。”④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得更彻底:“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⑤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据1937年版复印出版),第314页。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观念抨击最猛烈的,就是所谓“吃人的礼教”。而此礼教制度,尤以束缚女性的贞操观和婚姻制度、压抑子女的孝顺观和家庭制度,及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为中心。随着五四思潮的冲击,发端于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家族意识与礼教信条藩篱的被冲破,爱情理念才开始在广大青年争取婚姻自由,追求爱情完美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然而,“生在过渡时代的中国人,一方面憧憬着新的家庭生活,一方面又不能忘怀旧的伦理思想”。⑥王政:《家庭新论》,上海,中国文化复印社印行,1946年。转引自余华林:《恋爱自由与双重婚姻标准——民国时期关于爱情定则的历史透视》,《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3月。传统婚制作为深入民间的习俗,在整个民国时期仍然支配着绝大多数国人的行动和思维。传统的强大势力造成的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使得即使是处于主流文化层的先进人士,婚姻仍然为旧式婚姻,或者新瓶装旧酒,成为中心合壁的大杂烩。因此,“民国时期的爱情观念,绝不仅仅是爱伦凯式的西方婚姻恋爱学说在中国的简单复制,而恰恰是近代新思想和传统旧观念在民国社会矛盾中共存的产物”。⑦余华林:《恋爱自由与双重爱情标准——民国时期关于爱情定则的历史透视》。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顶制作于民国时期成都闹市区的花轿,正是近代新思想和传统旧观念在民国社会矛盾中共存的产物。我们只要将祝寿、状元游街、全家福等具有明显吉祥象征意味的画面视为传统的程式化的旧调,而将那六幅似乎有些唱反调的戏曲玻璃画归为呼应近代新思潮而谱出的新腔,就可以轻松地解决问题。况且,就工艺而言,平板玻璃是晚到康乾时期才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和木刻、彩扎等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手工艺不同,玻璃画在清代晚期才得以在民间普遍流行,在旧中国算得上是一种时髦手艺。⑧朱庆征:《故宫藏建筑装修用玻璃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4期。那么,从事新手艺的工匠们,比从事传统手艺的工匠更容易摆脱程式的窠臼,而有意识将一些符合时代潮流的内容描绘出来,似乎也显得顺理成章。
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真的可以断定,这些表达自由恋爱主题的场景,一定是清末以后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观念的解放和西潮的入侵,花轿上才可能出现的题材?而此前历朝历代的花轿,必然少有甚至根本没有这样的题材,而更多地可能是表现诸如贞女、烈妇一类题材的故事画面?如果缺乏更早时段的花轿实物做比对,又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提供哪怕片段信息,以上结论就值得怀疑。
所幸我们还有同时段的实物可供参考。如前所述,国内博物馆目前保存下来的花轿,时代都模糊地确定为清末民初。这些花轿大多数都属于木构框架,四周覆以红绸的“软衣式”花轿,图案和装饰相当简单。江浙地区的宁式花轿通体采用木雕,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收藏于浙江宁波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的一顶,号称全世界最复杂的花轿,其图像主要为福禄寿三星、凤凰、梅花、牡丹等吉祥装饰图案;南京民俗博物馆藏品,图案包括魁星点斗、榴开百子、喜鹊闹梅等装饰性画面,和“三英战吕布”、“刘备招亲”、“马超捉曹”等取自三国故事的戏曲场景。浙江省博的木雕花轿上镶嵌有玻璃画,其图像包括天官赐福、麒麟送子、魁星点状元、八仙过海、渔樵耕读、金龙彩凤、榴开百子、喜上眉梢等吉祥图样,以及《荆钗记》、《拾玉镯》、《西厢记》等戏曲场景。①以上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对博物馆的实地考察,部分来自网络。这些材料透露给我们至少两点讯息:其一,花轿上普遍出现了祝寿、祈子、中状元等吉祥图样;其二,花轿较多地采用到戏曲场景,表达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才子佳人故事是常见的主题,川大博物馆所藏花轿的图像绝非特例。
众所周知,戏曲图像的运用在中国是较早的事。远在宋代,人们已经开始在墓葬壁画和建筑构件上图绘戏曲场景。明清两朝,戏曲图像更为普遍地出现在民居祠堂建筑构件、家具、工艺品、家居陈设、乃至一切日常生活用具上,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②参考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中国人对戏曲非同寻常的爱好,使他们不但乐于在舞台上搬演,在台下观看,在劳作时讲述,更要将其定格,图绘、形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惟其如此,往往那些大字不识的贩夫走卒,二门不出的民妇村姑,都能头头是道地讲述前朝故事,评说历史忠奸,为英雄叫好,为才子佳人的聚散抹泪。古代中国社会,其实始终是被不动声色地置放在时而忠肝义胆,时而柔情缱绻的戏曲氛围中。
由此回到花轿这种婚姻礼仪用具。我认为,由于其制作者,使用者都是社会的中下层民众,而上层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无论是传统的似乎铁板一块的封建教条,还是清末以后的新思潮新风尚,在他们的思想、语言乃至行为中并不能得到一一对应。这顶花轿上的图像,不论是彰扬孝道的“八仙上寿”,指望功名利禄的“状元游街”,还是体现“邪恶”婢妾的“淫奔”之爱, “无耻”昏君的“乱伦”之爱……各种画面,仍然表现为历史的传承性、延续性。她呈现给观者的,其实是一整套未经割裂的传统文化图像。这些图像素有渊源,在生活中俯拾可见。其画面结构简单,物象单纯,故事情节一目了然;绘画技法极为粗糙,并不具备多少艺术美感;画上题字歪歪扭扭,不时还有错字、误字。可以想像制作者的艺术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不高。也就是这些走街串巷干着普通营生的工匠们,将他们目识心记的戏曲故事和饱满浸淫其中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撮要整理,图绘于这顶外观恰似舞台的婚嫁用具上。姑娘走进了花轿,就是正式登上了她的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男人功成名就,女人才德兼备,他们之间存在着美好的爱情。此外还有长寿的老人,绵绵不绝的子息——一个梦幻般完美的理想空间。与其说这只是近代转型期民众新旧观念杂糅下的社会理想,我却更愿意相信,俗世理想,从来如此。
美国学者伊沛霞在《内闱》一书中曾经颇为高明地指出,“为了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社会行为的联系获得更满意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跨越并包容两种表达的思想框架。一种是言之凿凿,清晰明确,道德化理性化的思想,而另一种是必须表达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模棱两可的想法。”③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或许我们可以想像,古代中国,无论是忠孝牌坊上雕刻“西厢记”、“牡丹亭”,婚礼花轿上画“红绡姻缘”、 “拜月亭”,房梁床架上描绘“还魂记”、“活捉王魁”……这些供人们终日凝视、观看、揣摩和想像的图案,貌似不经意,其实都与广大平民百姓的心理脉络,乃至现实生活若合符节。④中国俗语有“世上有的,戏上有。戏上有的,画上有”之说,反之亦然。其实,早在戏曲尚未完全成熟的南宋,就已经发生过戏剧活动冲击封建婚姻制度的事例。据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六载,“(演绎男女爱情的)《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一仓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方面的史料记载相当有限,而目前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相关研究也还有待展开。本文也不能在这一话题上走得更远。它们所代表的理想,由于有违中国社会理性化、道德化的观念,故而只能通过娱乐或日常言谈的方式,用片断的场景表达出来;同时,由于他们只是零散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从来没有被综合成一个统辖一切的系统,因此基本上也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他们与俨然的礼教共存。也正是这些画面的存在,让我们得以略微感知,在主流文化层刻板守旧的礼教论述下,红尘俗世自在荡漾的暗地春情。
近年来已经有比较多的学者,尤其是致力于女性史研究的部分学者,对长期公认的礼教对中国社会的威权效应提出了较多质疑。他们察觉到,过去的研究可能始终高估了思想和道德的压制性,而轻估了时代和社会的复杂和殊异性。通过细察历代妇女生活细节,他们开始怀疑中国妇女是否真的被置于“三从四德”的国度。较具代表性的如美国华裔学者高彦颐,她在《闺塾师》一书中指出,妇女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形象,部分是源于分析上的混乱,它用价值规范化的描述代替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其实未能从妇女自身角度去了解他们的世界。这种似乎不可动摇的“奴隶”形象,不但模糊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驱动力,也模糊了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转的。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社会构架可以如此机械化、明了化地堆砌起来,即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中国社会支持这一性别架构如此之久且运转良好的驱动力何在?①叶娃:《五四传统的反思与近代妇女史研究》,《读书》1996年8月。
花轿上的图像给我们提供了视觉上的证据,提醒我们在官方的政治秩序和儒家的价值规范外,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很多我们过去所忽略了的因素。除了主流思想之外,历史上还存在大量的潜流、反主流的各种文献、实物和图像资料。而在占人口百分之一都还不到的知识分子阶层之外,还有大量礼教所不及的愚夫愚妇。如果我们拨开主流文化层论述的屏障,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到普通男女群众的生活细节,包括他们的娱乐、家居用度、建筑装饰、日常阅读、服饰言谈等等,我们也许就能看到,在所谓“礼学”、“节妇”等论述所营造的严苛森冷的社会表层之下,始终汹涌着一股强大的人世温情柔软的暗潮。就是这股暗潮,挟裹着下层民众总能自行其事,自得其乐,自我安慰,自我调侃,这才是真正令人身心安顿的因素。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就是在这股暗潮中,蕴涵了普通男女温情相爱,琴瑟和谐的人生理想。
结语
我并非想把花轿上的艺术呈现,简单地转化成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更不是意图通过这样一顶花轿,琢磨出全体民众的思想,简易推导出民众的集体心态。毕竟,历史是纷繁复杂的,历史中的群体,群体中的个人,更有着极其多样的心态。但是我想,就像现代社会,爱不是形容男女关系的唯一要素一样,在礼法森严的古代社会,“服从”也远远不是形容男女关系的唯一要素。普通群众虽然并无意识改写“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古训,亦无意识改变与生俱存的性别架构和社会秩序,但他们却有能力为自身创建既与现实社会并行不悖,又真正让自己身心安顿的空间。如果精英阶层是采用文字来描述生活现实,表达社会理想,那么普通民众就是利用他们自己创作的粗率的图像,他们的娱乐方式与日常言谈,来表达他们的生活与观念。这两种表述与历史真实都同样存在着偏差。而我们在研究中,如果能同时注意到这两种表达,也许就能更切实地逼近历史真相。
婚姻仪式的整个过程,原本都充满了象征性,很奇怪所有研究婚姻的学者从来没有注意到花轿的问题,本文算是一次尝试,有很多话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如果能够借此引起更多学者对花轿这类承载婚姻的物事的关注,也算是达到了文章写作的一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