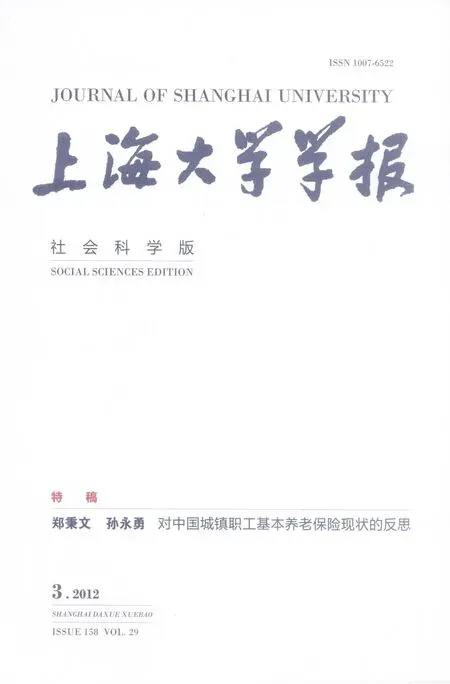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2012-04-12金文凯
金文凯
(三明学院 中文系,福建 三明 365004)
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
——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金文凯
(三明学院 中文系,福建 三明 365004)
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一门红妆闺秀也是一个活跃的诗歌群体。其创作题材突破传统闺阁之音,延伸到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取得新的超越,表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厚重思想内涵。其艺术风格既沿袭柔婉纤美传统,又不失清雅韶秀特质,还不时发出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创作,为研究清代女性诗歌的特点和女性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重要的文本,其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海昌查氏诗钞》
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六百多年来人才辈出,文脉不绝。在诗文、书画、藏书等方面均有创获,其中又以诗歌成就最大。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海宁查氏家族不仅有以查慎行为中心的成就斐然的男性诗人群体,而且一门红妆闺秀,也以其对诗歌的笃好与实践,形成了一个活跃的诗歌群体。笔者访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所藏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以下简称《诗钞》),①《海昌查氏诗钞》有校本及钞本两种,由海宁查氏第十七世查有钰(式庵)编纂,查辉(熙伯)校正。从同治戊辰(1868)到甲戌(1874),历经六年收集整理。所辑查氏家族诗作,起于明成化年间,迄于清同治末年,共存诗244家3539首。详见拙作《论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其中存有大量闺阁诗人诗作。它们以独特的艺术风貌,真切记录了闺阁诗人们的喜怒悲欢,是她们心灵史和生活史的真实呈现和原生态描画。从中亦可以窥见清代女性的生存本相和精神面貌,并为研究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特点和在社会生活、文化领域中的地位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重要的文本,其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容忽视。
一、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诗歌的创作题材
《诗钞》“录其贞静淑顺诸章,尊诗教、重壶范也”,①引自《诗钞》前集上册《凡例》第七款。以下凡引自《诗钞》诗文,为避烦琐,不再出注。共辑录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诗歌35家258首。闺秀们个个才思俊赡,且多有诗集。
查崧继室、查慎行母钟韫有《长绣楼集》一卷,《梅花园存稿》二卷;查继佐簉室蒋宜有《明心录》二卷,《蕊阁偶咏》一卷;查学继室陈素有《花角楼吟钞》两卷,《诗余》一卷;查揆室吴慎有《琴媵轩近稿》二卷;查世桢室李明有《挹翠阁吟草》一卷;查世璜室张常熹有《静宜楼吟稿》;查惜有《南楼吟香集》六卷;查蕙芳有《枕涛庄焚余草》;查映玉有《梅花书屋诗草》一卷;查若筠有《佩芬阁焚余诗草》二卷,词一卷;查昌鹓有《名媛词选》二卷,《学绣楼吟稿》一卷及辑录名媛诗作640家2674首的《学绣楼名媛诗选》十六卷。另有部分闺阁诗人的诗歌则附录或收编于其他诗集中,如查淑顺《揽秀轩稿》,见《杭郡诗续辑》;查女诗见《杭郡诗续辑》;查安人诗见《硖川诗钞》;查莱诗见《车酋轩录》;查有新室吴惇诗见葑湖《蛱蝶唱和词》;查端杼《如是斋吟草》附《篔谷集》;查余谷簉室周幼苕诗附《还读斋诗钞》;查世燮室邵佩鸾诗附《待月居吟草》;查人和室沈氏诗附《借绿阴斋诗钞》。
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创作题材十分丰富。
王鹏远《小檀奕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序》云:“女子善怀,其缠绵悱恻,如不胜情之致,于感人为易入。”[1]尤其对于文化素养较高、女性意识开始萌醒,而又心思敏感细腻的海宁查氏闺阁诗人而言,春花秋月,春归秋暮,极易触发她们的情思与感叹,因此,伤春悲秋成为她们抒发生命况味的首选题材。试看如下诗歌:
怨莺啼懒寂无声,几处飞花又暮春。破牖一灯昏夜雨,伤心如送远行人。(吴慎《雨中送春》)
惆怅春归促,凭阑百感生。乱红铺曲径,小雨弄新晴。园笋多成竹,杨花尽作萍。韶华还一瞬,愁思倩谁平。(陈素《春归》)
春草粘天春水长,春帘斜卷燕归梁。却愁好景凭谁共,花影满窗已夕阳。(查映玉《春日偶成》)
三首诗或伤悼春去花落,或痛惜韶华空逝,或感叹情何以寄。春事阑珊给闺阁诗人带来的悲怨忧惧之情充溢流贯每一首诗。
海宁士子为经商游学,功名科举,常须抛妻别子,漂泊异乡。囿于妇德闺训的约束,闺阁诗人们只能幽闭于重门深院,独自咀嚼孤独的苦涩,在落寞中虚耗青春,她们往往借伤春、惜春表达芳华流逝的哀婉和思夫怀远的浓愁。试看陈素《暮春忆外》:
小庭昨夜东风恶,满架蔷薇尽吹落。残红片片逐春归,空有浓云如翠幄。春来已是惹人愁,春去重叫恨未休。柳外高楼空望眼,花间携手记前游。前游顿觉成轻别,易水燕山渺天末。水绕山围几万重,梦中有路应难识。衡阳归燕几时来,拟把征衫着意裁。肥瘦不知近何似,欲持刀尺转徘徊。
花红柳绿,草长莺飞,只能勾起独守空闺、茕茕影只的女诗人深深的春愁;而东风无情,吹落残红,更让诗人愁情满怀,春恨绵绵。昔日花间携手漫游的夫君,如今山重水隔,远在天涯,那种欲裁征衫而不得的惆怅失落令人心碎。
吴慎《春夜》异曲同工,尾联尤催人伤感:“沉吟欲寄秦嘉去,绛蜡将销句未工。”诗人自比徐淑,于寂寥春夜欲寄相思,分明有万语千言,沉吟再三,却难以表达,愁情穿透纸背。
春色尚且撩人愁思,万木枯索、衰飒凄凉的秋景更激起女诗人的万端愁绪。试看陈素《立秋后七日作》:
夜静更阑露气侵,秋闺寂寂拥寒衾。千声蟋蟀鸣方急,一点残灯影欲沉。飒飒金风摇翠幕,丁丁玉漏搅疏砧。梦回又见前窗月,一片清光似水深。
夜静更阑,寒衾独眠,已是寂寞难耐;而蛩鸣促促、玉漏丁丁伴和着击砧声声,更敲击着女主人公孤寂的心扉,使得难眠的秋夜愈加漫长。梦醒时分,窗前寒月清光似水,凄清的景象与形影相吊的女主人公的愁绪交织在一起,令人不忍卒读。
查若筠《秋兴用杜少陵韵》则以冷枫江笛、蒹葭白露、灞桥衰柳、陶径寒花等一系列凄冷意象,营造出秋夜独特的幽寂寒凉之境,于哀伤凄惶中寄托孤寂怊怅的乡关情愁。朱淑仪《秋夜》、查映玉《秋阴》等亦充分调动视觉与听觉,对萧瑟颓败的秋色与物象细细描摹,把无边的冷落与空虚、无尽的迷惘与哀伤渗透其间,写尽了闺闱空虚中的女诗人冷寂、压抑的生命感受和心灵难以寄托的孤苦,充分显示了封建社会女性身为男性附属的角色悲凉。
清代况周颐云:“闺秀词,心思致密,往往赋物擅长。”[2]4607海宁查氏家族的闺阁诗人们也常借身边风物寄托情怀。
查端杼《盆鱼》即把“鳞潜不羡云如藻”和“有人湖海叹沉浮”作对比表达自己如同盆鱼般“且安勺水当清流”的心曲。
更多的闺阁诗人则借助咏物抒写自己不胜凄凉的身世之感。蒋宜《落叶十首》其一云:“消瘦寒林意自栖,可怜零落任东西。妒风何苦相凌逼,眷恋枝头不忍离。”蒋宜为查继佐簉室,深得宠爱,尽享荣华。及中年,继佐逝去,顿失所依,乃遁入空门。青灯孤影,甚为凄凉。诗人将自身痛苦体验映射于所咏之物,虽写落叶的惨淡悲凉,却映照出自己愁惨的生活际遇,如泣如诉。陈素《芦花和夫子》、查映玉《芦花四首和稻荪弟原韵》等也绘形摹神,刻画入微,借芦花把世上红颜的凄苦命运敞露无遗。
还有部分闺阁诗人咏物而不黏着于物,物象之外流动着她们对自己性别角色的不满和对社会角色的向往,如下面两诗:
零紫残红渐欲稀,海棠庭院晚风微。际天碧草双弓地,任尔芳原自在飞。(吴惇《蛱蝶词十绝》)
四月村村药草香,罗浮旧径月昏黄。爱他颇有须眉气,不逐东风上下狂。(朱淑均《蝴蝶花》)
前诗艳羡蛱蝶的“芳原自在飞”,后诗赞叹蝴蝶花“不逐东风”的“须眉气”,写出了查氏才女对挣脱束缚、自由展现才情个性的渴盼。
生活范围的局限,束缚了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的创作视野,其咏物诗多以封闭庭院的常见物象为主体,尤以咏梅居多。蒋宜即有《咏梅》三十首,将自我化身为清癯寒梅,写尽了梅之风神气韵,以抒自己孤傲幽独的情怀。其他如陈素《桂花》、张常熹《凌波仙子》、查若筠《新柳》、查惜《琴台》、查端杼《寒鸦》、李明《蟋蟀》等,皆以所咏之物为精神自画,抒写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悟。
还有不少作品取材于日常生活及身边琐事,如蒋宜《月下煮茗》,查蕙芳《翦秋纱》、钟韫《木奴被冰雪冻死》,李明《对镜》,朱淑仪《纳凉》、吴慎《浇花》等。由于题材本源于自己的生活,女诗人们娓娓道来,十分真切自然。试看如下两诗:
小妹安排乞巧盘,娇痴也爱说团乐。拈将双眼针穿就,帘底偷缝扇合欢。(周幼苕《闺中七夕词》)
胡蜨寻芳草,鸳鸯隐玉纱。儿家都不绣,只绣女贞花。(查纨《刺绣吟》)
前诗借七夕乞巧习俗,捕捉人物言行,把情窦初开的小妹塑造得娇俏可人。后诗先着意勾勒两幅习见而美丽的刺绣图,再点出自己刺绣题材的迥然不同。“只绣女贞花”的特立独行,恰是丈夫早逝,守贞以终的查纨守节心迹的充分体现,令人叹惋。两诗语言皆朴实无华,自然天成,极富表现力。
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还创作了大量关涉家庭、亲情的诗作。有对父母的思念,如查惜《忆母》;有对家人的牵挂,如吴慎《有怀夫子》;有姐弟重逢的欣喜,如查映玉《喜稻荪弟至》;有亲人别离的不舍,如祝氏《病中别母》;还有对逝去亲朋的伤悼,如查淑顺《梦后哭父》、朱淑均《哭归佩珊女史》,都写得情深语挚。尤其查端杼五古《雪中感怀示二弟》,缘景入情,情景相生,既真切表达了对父母养育辛劳的感恩之情,更倾吐了自己身为女子而不能纵横驰骋、回报父母的苦闷,荡人心肠。
清代女子出行较有明之际略微自由。海宁查氏家族的闺阁诗人们或偶于闲暇薄游山水,或随同父兄、丈夫宦游远行,或因贫困、灾难等被迫飘零异地,由此相对拓展了她们的生活空间与视野,给予了她们更丰富的情感体验,创作题材也因之更为丰富。
朱淑均《寒食》:“垂杨窣地与帘齐,冷节重逢诗且题。春八九分香径北,雨三四点画栏西。一双紫燕同巢宿,两个黄鹂各树啼。锦野秀林看未足,又邀女伴步花畦。”细腻勾画了一幅生机勃勃、清新明丽的寒食踏青画卷。诗人与久别重逢的女伴,徜徉于春色蓊郁、莺莺燕燕的锦野秀林,长吟短唱,乐而忘返。
吴慎《丙子三月侍家姑赴宣城道中记事偶成八绝》:“煜煜疏星映碧空,一钩新月挂船篷。鸥波几曲空流水,指点苕溪东复东。”(其一)“隔溪村落隐烟霞,竹外夭桃三两家。最好一间茅屋住,山童门外扫闲花。”(其三)诗中,步出深闺的女诗人,已然忘却了旅途的颠簸和劳顿,用新奇的目光欣赏着山光水色,打量着村落农家,颇有“坐看云起时”的闲适和“天地一沙鸥”的恬淡。
而当出行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迁播流徙的时候,羁旅之途也就深深烙上了女诗人们愁苦哀伤的印记。试看查若筠《秋暮舟行》:
枫影凝丹落叶村,几重残蓼映柴门。青拖冷意归山骨,白敛寒光入水痕。芦荻风中惊遣客,雁鸿声里断吟魂。一灯渔唱投蓑后,猿啸空林月又昏。
身为遣客,内心的凄苦可以想见。偏值秋暮泛舟,眼见的是落叶残蓼、冷山寒水,耳闻的是雁鸣断魂、猿啸空林,其凄惶苦痛又添十分。再看查蕙缀《题驿壁》:
薄命飞花水上浮,翠蛾双锁对沙鸥。塞垣草没三韩路,野戍风凄六月秋。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伤心漫谱琵琶怨,罗袖香消土满头。
蕙缀是查慎行弟查嗣庭女,幼遭家难,①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试题案发,波及兄弟四家数百口。后嗣庭庾死狱中,遭戮尸枭示;仲兄嗣瑮流放陕西,客死他乡;子弟多被遣戍千里,子妇多人自戮。随徙边塞,写下这首哀婉之作。诗歌把家逢变故的愁苦,遣戍途中的磨难,对亲人、故乡的无尽思念及生命如同飘萍杨花、无可主宰的惶恐惊惧,倾泻笔下,真真是以“血泪丝丝,沁为词华”,[3]5古代蒙难女性的悲惨境遇和痛苦心境可见一斑。
偶尔走出闭锁的深闺,接触到纷繁的生活,亦使一些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的创作开始突破“小我”的局促内蕴,超越“草草深闺度岁华,生平不解问桑麻”(林以宁《谷雨》)[4]的闺阁框囿,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稷苍生。
查惜的七古长篇《江南水》用赋的铺陈直白及满含悲悯的笔触,以一老翁自述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为缩影,记录了江南水患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发出了“但愿太平无一事,穷山海壤尽春风”的热切呼唤,已然没有闺阁诗篇常见的纤弱幽闭,显得苍凉老劲,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其《口占》:“芙蓉涨绿水,浦上一鱼竿。莫说渔家乐,渔租亦到官。”前两句以娇艳的芙蓉、初涨的绿水、悠悠垂钓的浦上鱼竿,勾勒一幅美丽宁静的渔家乐图。后两句却语锋扭转,痛揭渔民们不堪负荷的租税之苦。诗歌畅直于前,曲折幽微于后,将愤怒的诗笔直指朝廷的“苛政”,颇有尺幅千里之势。
李明的《蚕词十绝》就是十幅风情浓郁的江南蚕事图,既生动描摹了清明后村妇们髻插蚕花,进山烧香,祷祝丰年的习俗,更细细写尽了蚕农的勤劳艰辛。当他们含辛茹苦,终于迎来“茧满山头采满筐”的“大熟”年时,“有司不管民心苦,胥吏前村日日遇”,繁重的捐税也在虎视着蚕农,而姑娘们“要娘添制嫁衣裳”的企盼也迅疾成为了泡影。诗人以平实的语言,连环组图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贫富不均,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丑恶现实。
历代男性诗人常“借古人往事,抒自己怀抱”。[5]467其实咏古不独是男性诗人所长,女性诗人亦有擅笔。她们往往从女性视角出发审视历史,抒发她们的独到见解和对社会政治的思考。如查惜的《咏史四首》:
人死名须留,豹死皮可鬻。卓哉王彦章,千古同一哭。梁主虽非贤,国士为我畜。此心不可移,此身肯再辱。佩刀引自裁,天地皆怒触。至今存铁枪,余威振殊俗。(其一)
宋家王气弱,满目尽烽烟。文山文丞相,大义垂卓然。向为贤郡守,笙歌列绮筵。拜读勤王诏,繁华顿弃捐。戎马婴辛苦,流离不记年。谁知运百六,帝死臣囚燕。异哉王炎午,生祭文一篇。(其二)
前者开篇即引五代时后梁名将王彦章的常用俚语“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入诗,对其在主庸臣愚之际,忠贞有节、骁勇善战、以身殉国的高节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后者则开篇直批宋室的羸弱不堪,盛赞文天祥的高义大节,并对奋笔疾书《生祭文丞相文》、激励其死节的王炎午也作了积极的肯定。
查惜咏史诗清雄劲健,多注目于历史长河中的英雄豪杰,其诗《题家仲安画松图》道出了个中缘由:“我欲比德百折不回之孤忠,万古不灭之英雄。”袒露了她不甘雌伏、建功立业的渴盼。
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的创作,不拘泥于伤春悲秋、离别相思等传统闺阁之音,题画咏物、怀古思乡、山水行旅、伤时感事也是她们诗篇的题材。诗人的视阈与思想已经突破了狭小闺房的局限,延伸到了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并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取得了新的超越,而在表现女性意识觉醒和关注民生疾苦方面,更有厚重的思想内涵。
二、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诗歌的艺术风貌
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诗歌在总体上呈现出纤婉清雅的艺术风貌。
如同所有封建社会男权统治下的女性一样,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必须恪守“妇德尚柔”(《女史篇》)、“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等贞顺婉驯闺范和“男外女内”的角色规定,多“跬步不逾帏薄,无登涉旷观以为激发”,[6]过的是“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朱淑真《自责二首》)[7]的幽闭生活。她们丧失了参与建构外部世界的权利,创作的胸襟和视野被限制,文学主题呈现出较强的内敛性与封闭性,常注目于闺中风物清景,沉浸于自身离合悲欢,加之天性细腻敏感,折射于诗篇中的则是无尽的缠绵缱绻、哀怨忧戚,呈现出纤婉的特质。
试看吴慎《寄远》:“花事渐阑珊,关心坐漏残。帆随孤梦冷,人伴一灯寒。道远无消息,书迟少羽翰。故乡今夜月,何事又团。”花事阑珊,漏残灯寒,诗人在惆怅孤寂中思远之情油然而生,可是牵挂之人却山重水隔,音信渺渺,只能徒然望着天上圆月忧戚感叹,黯然神伤。诗歌情致楚楚,婉约温雅,而依依盼归之情、绵绵思念之意已跃然纸上。
再看查端杼《简寄沈夫人周撷华女史》:“自与伊人别,相思水一方。幽兰忆标格,明月想容光。蔼蔼暮云合,萋萋春草芳。何当同剪烛,相对话离肠。”清代知识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生活圈子相对宽泛,女性间交往亦增多,往往由此结成精神同盟,相知相契,甚或彼此成为弥补生存苦闷和爱情缺失的精神慰藉与支柱。一旦分离,其惆怅心绪堪比思夫念远。诗人情不自禁以描写男女相思怨别的意境与口吻,抒写知心闺友久别的思念与浓情,于情思绵远中充分显示姐妹情谊在闭处深闺的女诗人心中的厚重分量。
离别、寂寞能勾起女诗人的怨叹感伤,特别的季节与风物也常使她们多愁善感。试看如下诗歌:
浓阴深锁抱柴门,懒步回廊对酒樽。久雨厌听今夜漏,短桥犹记去年痕。平溪倚阁怜新水,隔岸行舟渡晚村。云影风声浑不辨,烟波况是月黄昏。(吴慎《新涨》)
夜深人静雨潇潇,只有书檠伴寂寥。自是多愁眠未得,翻嫌点滴到芭蕉。(李明《夜雨》)
蕉窗秋似水,小坐夜眠迟。曲院花双影,新凉月一眉。画余聊涤砚,绣罢偶吟诗。此夕愁多少,阶前落叶知。(朱淑均《此夕》)
东风吹雨过芳洲,送尽残红懒倚楼。欲问帘前新燕子,借他双剪破春愁。(蒋宜《春晚》)
池水新涨、夜雨潇潇、秋凉似水、春暮红残,大自然的细微律动,无不使敏锐的诗人心有所触。静谧的意象与幽怨的思致相融合,柔美中不乏绵婉情致,余韵悠长,充分体现女性诗人哀而不伤、纤婉中和的诗歌风貌。
海宁查氏家族是文化世家,闺阁诗人们多自幼接受正统诗书教育和儒礼熏陶,往往诗文书画兼擅,极具儒雅的文化内涵,加之远离尘世的生存特点和清代文坛推崇雅化的风气影响,典雅灵秀成为她们审美境界的自觉追求,在诗歌创作上则呈现出清雅的风貌。试看钟韫《西溪山庄同胡少君方眉士积石引泉》:
曲坞藏茅屋,层峦啼杜鹃。云木亘交蔽,日午窥中天。山家饶生计,梅竹当田园。荷锄恣游宴,投足生流连。经冬长蔓草,绕舍鸣寒泉。涧应石磊磊,藻上鱼蹁蹁。同时得幽兴,引源及阶轩。凿石初照月,开径夜生烟。共传山中叟,能说羲皇前。历世经长毓,草木密繁嫣。生无樵采患,安知耕凿年。
诗歌捕光捉影,描形绘声,把西溪山庄的恬静清幽尽显笔端,如同一幅精致优美的工笔小画。笔致清疏自然,超逸和雅,不失陶渊明诗的冲淡,又有王维诗的明净。尤为难得的是,诗歌不只驻笔于写山庄的美景和积石引泉的乐趣,还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怜惜,显示出不凡识见。
再看查蕙芳《暗水流花径》:“日落烟波暝,纡回几亩花。空蒙沈树色,潋滟挹香葩。疏影摇空碧,幽香落浅沙。名园春正好,领取在诗家。”诗人除却脂粉,以几组清新流动的意象,尽情展示花径的美好,用语秀雅,意境优美。
此外如蒋宜《漫兴》借雨后山青水流,禽鸟适意的秋景,抒写参透世情的安然淡寂心境;吴慎《舟中即景》以新月、芰荷、溪水、群山、闲鸥、白云及飘忽的暗浮残香,勾勒一幅意境超脱、淡冶秀逸的水墨画,均呈现出女性特有的体物入微、明净流丽的清绮之美。
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在纤婉清雅的诗风之外,还不时发出沉郁遒劲之音。
纵观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由许穆夫人悲壮沉雄的《载驰》,到李清照豪迈神骏的《渔家傲》,再到闺秀云集的清诗坛,雄浑豪放之作时有呈现。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习经史,通古今,识见与胸襟得以开阔,部分诗人也常以其不逊男子的阳刚气息,拓宽柔婉的诗境,绽放出遒劲旷放的气质。
查惜《行路难》逆常人之思,认为“行路难,不在羊肠之屈曲,蜀道之巑岏”,“不在三峡之逆流,十八之长滩”,“康庄途生荆棘,顺水舟多狂澜”,“平与安”才是人生“至险”,韬光养晦应是处世之道。语锋劲爽,耐人寻味。再看其《悲狂风》:
今我不知苍天何所怒,走石扬沙卷白茅。八姨声动逐雷电,飞廉噫气满西郊。蟠龙潜蛰无宁窟,黄鹄惊飞失故巢。幽人缩项南楼最高处,正如沧海崩泻山动摇。吁嗟世路多逼仄,何独狂飙任怒号。翻手作云覆手雨,一颦一笑皆波涛。仲安岂是长贫贱,放后无须作广骚。君不见渔翁放棹凌江上,偏向中流把竹篙。
前八句着意写景,把狂风大作时天昏地暗、雷电交加、飞沙走石、鸟兽惊慌的骇人场景描写得大气磅礴,撼人心魄。紧承两联将肆虐的狂风与逼仄的世路对比,凸显人生险象。并劝导丈夫无须怨天尤人,长守贫贱,应学渔翁中流把篙,放棹凌江,昂首直面风浪,表现出非同凡响的识见与勇气,较前诗更显贞刚劲健。
查惜《呈家仲安》更突破夫妻往来诗歌中离愁别绪、儿女情长的习见内容,以“周鼎浮洛水,龙剑出丰城”为类比,鼓励丈夫“乘骐骥”,“驾长鲸”;“励素志”,“请长缨”;既修“内美”,又“宏家声”,充满雄健豪放之气。而充满苦痛的经历际遇,“以理节情”、“以道制欲”的礼法古训和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又常使闺阁诗人们的诗歌幽咽回旋、凄恻悲凉,表现出沉郁悲慨诗风。
如浦氏《绝命词》:
罔极深恩未少酬,空贻罪孽重亲忧。伤心唯恨无言别,留取松筠话不休。
浦氏为查嗣庭子查克上室。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发,“克上因父获罪同死,浦氏同姑史氏约自尽,史氏先缢。浦氏赋《绝命词》四章,遂吞金死”。大难降临,平日闭锁深闺的女子,更如飘萍杨花,无可依傍。为保人格与贞操,自尽是她们唯一的武器,绝命诗则是她们对悲剧命运的自我祭奠。诗中充溢着生之哀痛,死之决绝,沉郁悲怆中不失清刚之气,令人叹息。
再如查端杼《岁暮杂感》:“同云如墨压檐端,风雪惊心岁又阑。消我年光凭涕泪,离人骨月是饥寒。愁同猬集驱还至。衣似鹑悬补独难。却比杜陵贫更甚,囊空并少一钱看。”在阴云如墨、风雪惊心的岁暮,一贫如洗的诗人愁同猬集、衣似鹑悬,只能在饥寒中以泪洗面。诗歌缘景入情,更兼对比,穷愁之苦充溢全诗,沉郁至极。
以查慎行为中心的海宁查氏家族男性诗人多长于写动景、奇景,尤长白描,受家族熏染的闺阁诗人们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时常呈现出同样的特点。
李明《偶占》:“天忽遮窗黑,风声卷地来。移时云四散,叶落一庭堆。”把刹那间天昏地暗,风声卷地,而片刻间又云开雾散,落叶满庭的瞬息之变写得淋漓尽致。蒋宜《朝雾》:“青青忽被染空原,野景依稀日色昏。缥缈微探云裹树,回头失却旧林园。”则把晨雾逐渐弥漫吞没旷野林园的整个过程写得清新活泼,灵动有趣,颇得家族男性诗人描写动景的真传。
海宁查氏家族的闺阁诗人们亦是白描好手。查若筠《雪》:“云冻凝成雪,斜飘小院傍。无声花满地,不夜月生光。枯柳轻拈絮,疏梅暗惹香。灞桥诗思冷,犹忆孟襄阳。”以简练轻淡之笔,把雪花飘舞之际,天地万物的素雅美景勾勒得形神兼备。尾联用孟襄阳灞桥踏雪寻梅典故亦如盐融水,真切自然,不落痕迹。李明《喜晴》:“正苦连朝雨,山头晚放晴。云开千树霁,日照一窗明。满槛花争放,沿街草蔓生。林禽先有信,干鹊两三声。”诗人师宗自然,不着色敷彩,把久雨放晴后草木林禽生机勃发的场景及自己的欣喜之情写得生动有致,极具感染力。此外如查若筠《鸳湖棹歌》、吴慎《舟中即景》、李明《夏日远眺》、查映玉《秋阴》等都不乏白描之笔,以真实自然、简洁朴素的语言,达到了“语淡而味终不薄”[8]的艺术效果。
总之,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的诗歌既沿袭了前代的创作传统,以柔婉纤美的风格为主,又因自身素养的提高而时时显现清雅韶秀的特质,加之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从而呈现出不拘一格的多彩风姿。而家族的熏染和天性的细腻敏感,又使她们在创作手法上与家族男性诗人一脉相承,表现出长于白描、擅写动景的特性,富有独特的魅力。
三、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形成原因
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形成源于多方面原因。
第一,与江南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唐宋以来,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江、浙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之地。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盛,江、浙遂成为有清一代文学重镇,亦成为女性诗学渊薮。由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可知,清代江苏女诗人最多,浙江次之,两省女诗人竟占全国女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海宁在历史沿革中多隶属吴郡或余杭郡,明、清朝曾属杭州府,夙称风雅之地。浓郁的文化氛围,为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与清代以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与开明之士的新妇女观密不可分。宋明理学的影响在清代达到极致,对女教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但出于阃教的目的,却并不完全排斥女性读书识字,这在吕坤《闺范》等女教书中有所体现。李晚芳《女学言行纂》即云:“有志女子自当从经史子传取益,几见哲后、圣母、贤妻、淑媛有一不从经史子传中来者乎?”[9]5这些见解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女子接受教育的作用。而对风行已久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此期也有了异响。王相之母刘氏在《女范捷录·才德篇》中即云:“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非。”[10]46叶绍袁在《午梦堂全集》序中亦提出女性立身传世之三“不朽”,即“德也,才与色也”。[11]他们都摒弃单纯以色相评价女子的封建观念,提倡才德并置。这些观点亦促使有清一代女子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丁绍仪《清闺秀词》即云:“吴越女子多读书识字,女工余暇,不乏篇章。近则到处皆然,故闺秀之盛度越千古。”[12]8
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人士也开始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明末思想家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即云:“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3]批判“妇人见短”的世俗偏见。戴鉴《国朝闺秀香咳集》序中亦云:“世多云女子不宜为诗,即偶有吟咏,亦不当示人以流传之。噫!何其所见之浅也!”[14]对“内言不出”的封建观念予以了猛烈抨击。
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女性文学的繁荣创造了良机,海宁查氏家族的闺阁诗人们也得益于此,尽展才华。
第三,与海宁查氏家族的文化熏染及对女子闺中教育的重视关系密切。袁枚云:“闺秀能文,终究出于大家。”[5]85《闺秀诗评》亦称:“女子能诗者,故家世族为最多。”[15]35名门巨族往往以科举维系家世,崇文重教,族中女性也因此具有受教育的良好条件。海宁查氏家族的闺阁诗人们生长于奕世甲科、人才济济的文化世家,受到以父兄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和文学氛围的熏染,文学素养亦得以提高。如查昌鹓“幼从族兄岐昌受小学、女训、毛诗、四子书,通晓大义”;查慎行女孙查安人则得其亲自调教,“脱口如宿构”。此外,母教的启蒙也十分重要。查惜《南楼吟香集》自序即云:“余年六岁,母氏授唐绝数章,《花间词》数阕。”查世燮室邵佩鸾亦称,“所学,得之母教”。母辈的诗教为查氏闺阁才女叩开了诗学之门,也为她们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第四,与查氏闺秀们读书的嗜好和无功利的创作态度紧密相关。
闺阁诗人们无缘科举应试,出仕为官,一展抱负,而天性的聪慧敏感和对文学的笃好,又使她们能摒除杂念,以文学为自觉追求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伴侣。钟韫“熟精文选”,蒋宜“性嗜书史”,查惜“纵观唐宋以来诗文”,查淑顺“读书识大义”,张常熹“喜吟咏,工丹青”,祝氏“端操明礼,兼娴吟咏”,查蕙芳“自幼工诗词,长篇短章时时闲作”,陈素“慧质天成,复好经史,于风雅源流,探之有素,得其指归”,更有查若筠“生禀异资,经史百家咸过目成诵。尤耽吟唐人诗,故拈韵得句,吐属天成”。海宁查氏闺阁诗人读书创作的热情勤勉并不亚于男性诗人。她们通过阅读,推开了一扇通向外界的心灵之门,既提高了素养和识见,又找到了精神寄托与慰藉,诗艺也日渐提高。
第五,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的唱和交游也极大地激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她们诗艺的精进。
查氏家族不仅男性成员间常相酬唱,父女兄妹间,尤其女性成员间的唱和更是频繁。查慎行母钟韫“有女兄字山容,女弟字眉士,针纴余闲,互相唱和”;查惜“暇遇花朝月夕,与从姊蕙、侄妇婉思、侄女珵二三人时相唱和”;查有炳室朱淑仪与查冬荣室朱淑均“以姊妹为妯娌,翰墨怡情,一门酬唱,刊有《分绣联吟合稿》一卷”,查若筠亦在其诗《上元有感》小序中忆及自己“在先伯映山公听雨楼,同大姊两嫂及琼侄女辈联句”。她们还突破庭内吟咏、夫妇分韵、兄妹唱答等局限,扩大了诗文交往的圈子,与家族外志趣相投的女性诗简唱酬。如查玲《仿唐子畏花月连珠体和小桐溪女史吴守白景原韵》,“原唱凡十二首,和者守白大女云涛、吴婉容、吴蕊、项本诗、马钿、陈珩、祝德筠及查玲凡八人”。诗歌的往来酬唱、联吟切磋,不仅使闺阁诗人们彼此情谊深厚,成为惺惺相惜的精神同调,对她们才思的拓展、视野胸襟的开阔以及诗歌技艺的提高也大有裨益。
总体而言,在封建社会,文化话语权主要掌握于男性之手,女性多处于失语缺席状态,本真的生命体验被忽略。原该由女性“以我心写我口”的心声之作,往往由须眉男子捉刀代庖,造成创作主体与抒情主体的错位,“男子而作闺音”成为普遍现象。这种错位必然造成生命体验的隔膜,女性真实的情感体验与心境终被男性的想像所取代而难以触及。
可喜的是,历朝历代都有才华卓绝的女性冲破重重压抑和阻碍,创作出优美动人的诗篇。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即收汉魏女诗人33家,唐代21家,宋辽元62家。明中期后,个性解放思潮兴盛,有民主倾向的男性文人如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纷纷开始关注妇女问题,主张男女平等,也因此明清之际女性诗人更加具有话语意识。明代女性文学渐趋繁荣,女诗人增至245家;清代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巅峰,女诗人近四千家。而在文化氛围浓厚的江南一带,一门联吟,拜师结社更成为文学风尚。
得益于有清一代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海宁查氏家族的闺阁诗人们亦能在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里抒写性灵,袒露悲欢。她们的诗作,定格了这一时期闺阁才媛们生活和创作的现场,为研究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的文本,并为观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和诗坛风尚提供了良好的视角。而她们在创作题材、视阈眼界上的拓展,在情感表达的广度与深度上的超越,以及与家族男性诗人一脉相承的创作手法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她们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创作风格上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更使她们的诗歌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留下了瑰丽的色彩。
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虽没有像李清照这样的大家,却涌现了钟韫、蒋宜、查惜、查若筠等堪与徐灿、吴藻、顾春、席佩兰这些清时女诗人翘楚相媲美的优秀诗人。她们与家族男性诗人群体交相辉映,给以男性为主的家族创作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促进了查氏文化家族的绵延发展和地域文化的繁荣,亦为男性霸主的清诗坛增添了几分绮丽与妩媚。
因此,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虽不如康熙年间“蕉园七子”、乾隆年间“吴中十子”及随园女弟子声名远扬,也不如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女诗人群体名声显赫,但她们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同样不容忽视。
[1]王鹏远.小檀奕室汇刻百家闺秀词序[C]//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872.
[2]况周颐.玉栖述雅[C]//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3]雷缙.闺秀诗话:卷 5[M].上海:扫叶山房,1925.
[4]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84[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5]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林西仲.墨庄诗钞序[C]//汪启淑.撷芳集:卷39.清乾隆五十年(1785)古歙汪氏飞堂刊本.
[7]傅璇琮,倪其心,孙钦善.全宋诗28册,159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7928.
[8]沈德潜.唐诗别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16.
[9]李晚芳.女学言行纂:卷上[M].民国二十六年(1937)周氏师古堂影印本.
[10]刘氏.女范捷录:卷下[M]//王相笺注.女四书.清光绪六年(1880)江南城李光明庄刻本.
[11]叶绍袁.午梦堂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1.
[12]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19[M].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
[13]李贽.焚书 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9.
[14]戴鉴.国朝闺秀香咳集[C]//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17.
[15]淮山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M].上海:上海申报馆,清光绪三年(1877)印本.
(责任编辑:梁临川)
Research on the Zha Family's Poetesses of Haining in Qing Dynasty——Data from the Rare Manuscript Collected Poems of the Zha Family in Haichang
JIN Wen-k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 365004,Fujian,China)
The Zha Family of Haining city,Zhejiang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is a well-known literary family,whose female members are also active and successful in poetry writing.Their poetic themes are not restricted to traditional women matters but cover the wider areas of nature and society,achieve new advancement in the depth and broadnes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as well as show the awakening of feminine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ir concern about masses'sufferings.Their writing styles are delicate and graceful,frequently attached with vigorous tone-variations.Like the male poets in the family who are represented by Zha Shenxing,their poems are characteristic with succinct description and expressive depiction of dynamic scenes.The poems of the Zha Family's Poetesses are rich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in the sense that they supply abundant materials and important manuscripts for studies on the creative features,social functions and cultural roles of female poetry writing in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the Zha Family's Poetesses of Haining;Collected Poems of the Zha Family in Haichang
I206
A
1007-6522(2012)03-0073-11
10.3969/j.issn 1007-6522.2012.03.007
2011-09-12
福建省教育厅A类人文社科研究项目(JA11261S)
金文凯(1968-),女,福建建宁人。三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