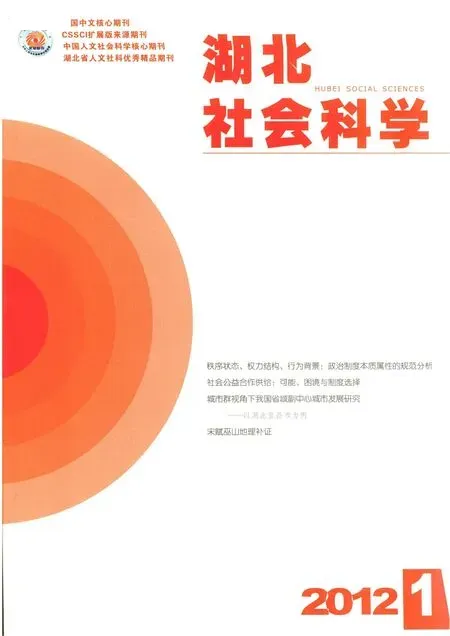追源溯流法的非正常运用
——论钟嵘主观意图对批评客观性的负面影响
2012-04-12陶春林
陶春林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追源溯流法的非正常运用
——论钟嵘主观意图对批评客观性的负面影响
陶春林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钟嵘撰写《诗品》的现实原因是借此扭转“永明体”追随者片面推尊鲍照、谢朓而出现“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创作倾向,批判武器是确立以曹植诗歌为代表的审美典范,主要批评方法之一便是“追源溯流法”。现实原因促使钟嵘贬低“永明体”相关作家,忽略他们与曹植的联系,为他们寻找一个成就一般的源头。这种主观意图破坏了方法论的彻底性,也放大了“追源溯流法”的理论缺陷,导致后人广泛的质疑。
钟嵘;追源溯流法;主观意图;负面影响
一、钟嵘对鲍谢与曹刘的承继关系的忽视
批判“永明体”,钟嵘主要使用了“追源溯流法”,但其运用耐人寻味,那就是变多源为单源,略上品源强调中品源。
钟嵘认为,“源”决定了“流”的品第,《国风》、《小雅》、《楚辞》是总源,其衣钵传人古诗、曹植、阮籍、李陵均为上品。除阮籍外,其余三者又成为新的源,其学习者除曹丕外,其余左思、陆机、谢灵运、班姬、王粲均为上品。但第三代继承者除了潘岳、张协外,其余均为中品。第四代、第五代均为中、下品。所以,钟嵘赞赏的对象,都与宗、祖、上品有紧密的传承关系,批评的对象,其源最多只能是中品。
所以,《诗品》中“永明体”代表诗人的源均没有上品。沈约源于中品的鲍照(鲍照源于上品的张协、中品的张华),谢朓源于中品的谢混,王融没有源头。
在具体的批评中,钟嵘承认他们有多个源头。如鲍照,钟嵘认为他学习了张协“諔诡”,张华“靡嫚”,谢混“骨节”,颜延年“驱迈”,并且在“骨节”和“驱迈”上,超过了谢混和颜延年。又如谢朓,钟嵘认为其出于谢混,但其“奇章秀句”可以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自然鲍照与谢朓也属承继关系。
这源是否合理,是否全面呢?我们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就可发现,鲍照、谢朓跟钟嵘的审美典范曹植、刘桢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曹植诗歌,《白马篇》属于“骨气奇高”的作品,鲍照有模拟之作《代陈思王白马篇》:
白马骍角弓,鸣鞭乘北风。要途问边急,杂虏入云中。闭壁自往复,清野径还冬。侨装多阙绝,旅服少裁缝。埋身守汉境,沈命对胡封。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含悲望两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弃别中国爱,要冀胡马功。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1](p172)
此诗俊逸稍逊曹植,而沧桑感过之,故王闿运评价其“殊有昂藏之气。顿挫慷慨,所谓‘幽燕老将,气韵沉雄’”。[2](p2267)又如《代结客少年场行》亦学习曹植,而诗中时间跨度更长,充满人生的沧桑感和众人皆获其位而己无枝可依的失落感。相比之下,曹植《白马篇》贯注着为国尽忠、视死如归的信念,鲍照的“侠气”则贯注着寒士的不平,乃为富贵功名而发。境界的差距是明显的,所以鲍照的“侠”已经呈现出来的是豪强气,有些脱离“义”的原则,这是二者出身不同导致的认识差异。此外鲍照又有《学刘公干体五首》,全效刘桢,方东树认为其“诗体仗气极似公干,特雕润过公干”。[3](p185)
曹植诗歌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发端有力,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等。[4](p400-409)谢脁诗歌善于发端的特点,明显有曹植的影响。其名句如“飞雪天山来,飘聚绳棂外。苍云暗九重,北风吹万籁”、“荆山嵸百里,汉广流无极”、“沧波不可望,望极与天平”[5](p200-336)。其名作《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发端更是得到评论家的交口称赞。孙鑛赞其“首二句,昔人谓压全古,信然”。[6]王夫之赞其“敻绝千古”,[7](p767)成书则为之叫屈:“起句俊伟,直欲上迈陈思,通体亦皆雄健。论诗者言体格卑下,动指齐梁,似此诗置之魏人中,岂复能辨! ”[5](p208)
谢脁诗歌亦有明显学刘桢地方。如“发端峻甚,遽欲一空今古声情”的《观朝雨》:“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既洒百常观,复集九层台。”[5](p215)明显是学习刘桢。刘桢诗已不可知,但鲍照《学刘公干体五首》其三:“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集君瑶台上,飞舞两楹前”展示了刘桢诗歌的某些特点。[1](p359)谢朓诗歌很明显学习了“刘公干体”的结构、力度和由远及近的审美视角。
曹植的《京洛篇》、《美女篇》表现出“词采华茂”的特点。《京洛篇》写景色彩斑斓,《美女篇》写服饰华丽。最典型的还是诗体赋《洛神赋》:“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中略)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裾。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踐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中略)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於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4](p283)举体明丽华美。 鲍照的《代陈思王〈京洛篇〉》、《采桑》即是学习曹植辞采华丽的作品。谢脁的《入朝曲》、《直中书省》也鲜明地表现出这个特点。
其实,曹植的作品也有明显学习楚辞的。如《怨歌行》抒发为臣忠信见疑的悲怨,让异代的谢安“泣下沾衿”。[8](p2119)《赠白马王彪》“全篇情真意挚,死生之戚,离别之思,洋溢于楮墨之外”,表现出“情兼雅怨”这个特点。[4](p301)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谢脁《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咏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父》等同样具有相近的特征。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曹植同样是鲍照、谢朓的主要学习对象。其实谢朓诗歌来源还有很多,像其山水诗题材,很明显与先辈谢灵运有承继关系。
二、《诗品》忽略鲍谢主要源头的原因
作为一个现实感极强的批评家,钟嵘对其所处时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极为关注,他认为,当时诗坛存在诸多混乱,导致这些混乱的主体是三种人。一是“士俗”之流,他们把诗歌创作看得很重,创作热情也非常高。踏入诗坛的年龄小得让人吃惊:“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富家子弟创作热情更是达到了“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的地步,从而导致“庸音杂体,人各为容”。二是“轻薄之徒”,他们“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从而导致“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三是“王公缙绅之士”,他们“随其嗜欲,商榷不同”,从而导致“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9](p54-62)
实际上,在钟嵘看来,在这三种人中,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只是风气的追随者和推动者。真正给当时诗坛带来混乱的是第二种人,即“永明体”的代表人物,他们才是风气的倡导者,正是他们推尊鲍照、谢朓,才导致了诗坛的混乱。具体说,这个混乱是由“永明体”作家大力提倡的两种创作方法造成的:一是“用事”,尤其是“竞须新事”;二是“声病”。
钟嵘《诗品》正是有感于当时诗坛批评标准混乱的局面,在刘绘“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而又“其文未遂”的情况下创作的,意在对于汉代以来的一批诗家作品,通过“辨彰清浊,掎摭利病”以达到“致流别”、“辨清浊”、“显优劣”的目的。[9](p62)也就是通过对已有的优秀诗歌遗产的清理树立一个标尺,让当代人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好诗,从而改变当前的创作状况。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此目的呢?钟嵘应对的策略是提出新的批评标准。
关于钟嵘的批评标准,尽管当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以为,其批评标准集中体现在他对曹植五言诗的评价中。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9](p97)
正如曹旭所言,钟嵘关于曹植五言诗的评价“包括了两组美学范畴:一是内容情感上的‘雅’、‘怨’;二是体制风格上的‘文’、‘质’,‘骨气’与‘词采’。 ‘雅’代表了雅正和高层次、高品味的美学原则;‘怨’代表了汉魏以来以悲为美的思想。钟嵘在情感上要求‘雅’与‘怨’的结合。在诗歌的体制风格上,他又要求‘质’与‘文’,‘风力’与‘丹采’,‘骨气’与‘词采’这些不同的,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美学要素统一在一起,使刚性的诗歌精神与柔性的词采高度融合,体现出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1](p16)可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可以说是钟嵘的诗歌批评标准。
总之,钟嵘创作《诗品》的目的就是要以曹植代表的“建安风力”去攻击“永明体”,批判“永明体”。
三、《诗品》写作目的对批评客观性的负面影响
钟嵘与鲍照时代接近,与谢朓同时代,当然了解二人的创作情况,他没有指出鲍照、谢朓与曹植的承继关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二人跟钟嵘反对的“永明体”关系太紧密。鲍照是沈约的源头,谢朓是“永明体”代表,二人是当时诗坛的偶像,要反对“永明体”,必然涉及如何认识他们的问题。由于钟嵘运用的批评方法是“追源溯流法”,否定当时追随者创作平庸、标准混乱,就必须否定其“源”鲍照、谢朓;否定鲍、谢,就必须否定他们与自己的诗坛偶像有承继关系,追溯时片面地从其不足处着手,其源也只能是中品诗人,这就使得他无法做出客观的认识。客观地说,沈约等人的“声病”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过于严格的要求限制了诗歌创作,但这也是他们诗歌创作的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他们的诗作也没有完全遵循自己的理论,所以自身的成就很高。就是钟嵘贬斥的沈约,魏征也评价非常高:“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10](p1730)关于梁代“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现象的产生,唐代皎然明确指出,这是学习者的问题,主要责任不在沈约等人:“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11](p26)所以,由于“追源溯流法”的局限,批评“士俗”、“王公缙绅”的主观意图造成了钟嵘批评持有双重标准,评价“永明体”诗人时,使用现实需要标准,忽略审美标准;评价其他诗人时,使用审美标准,尽量摆脱主观倾向的干扰。这自然会造成批评的混乱。
这种现实性目的让钟嵘无法客观认识鲍照、谢朓的文学地位,分析他们尚气、用事、注重声韵在诗歌发展上有什么意义。由于谢朓在隋唐地位非常高,也使得隋唐人因此而全面否定《诗品》。隋刘善经就钟嵘贬低谢朓指责他:“嵘徒见口吻之为工,不知调和之有术。”[12](p93)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踳驳之论,纷然遂多。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品》,议论蜂起,高谈不息。 ”[13](p317)
由于不能正确认识“永明体”作家本身的成功与不足,钟嵘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当时诗坛的主要弊病,开出疗救的药方。钟嵘意识到了当时诗坛片面学鲍照和谢朓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但他并未就此研究出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梁代诗歌创作问题出现严重情况是在钟嵘去世后十七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中略)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 ”[10]p(1730)所谓“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就是隋李谔所云“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10](p1544)这虽与“永明体”有一定联系,但主要责任并不在它,所以魏征等对“永明体”作家与“宫体”作家的评价也有着天壤之别。
同时,因为“三品论人”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所以钟嵘在评价张华时就感到有些问题,这也导致他给曹操、陶渊明等人的品第引起了后人的颇多不满。这有审美标准的不完善的因素,但钟嵘反对“永明体”的主观意图,更加放大了理论上的缺陷。
钟嵘的主观需要使得他在评论与“永明体”有关的诗人时,使用了不同的语气与句法。上品诗人且不论,就看同属于中品的诗人评价,鲍照、谢朓、沈约的批评明显有别于其他人。评论其他人主要是挖掘、肯定其优长,指出其配得上中品的原因,语气上以肯定为基调,语法上常常先抑后扬。如曹丕,先指出其缺点“率皆鄙直如偶语”,然后指出其有成就的十余首诗的特点,最后肯定起地位:“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评嵇康亦先指出缺点,后肯定其地位。评张华指出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弊端后,末尾更表明张华地位虽低于上品,但高于中品。其他像何晏、孙楚、王赞、张翰、潘尼、应璩、陆云、石崇等三十二人,均是先说不足,以肯定其成就结尾定调。就是在“用事”上存在很大问题的颜延年,钟嵘也为其“弥见拘束”辩护,认为他“虽乖秀逸,固是经纶文雅;才减若人,则陷于困踬矣”。
评论鲍照时,钟嵘先大段赞扬之词,但最后从“然贵尚巧似”到结束,则批驳其缺点,并指出其不良影响:“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评价谢朓,是先抑、中扬、后抑。首先指出其源不好,而且谢朓还在此之上添了新的毛病。然后说他有句无篇。接着赞扬其优秀之处。但在赞扬其发端有力时,马上批评他结尾“多踬”。最后批评其过于注重声调的抑扬顿挫。评论沈约,后面更是大量篇幅言沈约文坛领袖地位不过是恰逢青黄不接所致,跟当时的江淹、谢朓、范云都有差距。
这两种语气和句法表现的作者态度显然有别,前者意在肯定,其虽有某些不足,但配得上中品地位,后者意在否定,其虽够得上中品地位,但总体缺点明显。这种有意贬低更加放大了“三品论人”的理论缺陷。
综上所述,由于钟嵘批评的基本出发点是想消解“永明体”的影响,因此有意忽视“永明体”代表作家与自己确立的审美典范的源流关系,这种批评态度不但使他在“永明体”的批评上不能一分为二、客观具体,而且导致了其“追源溯流”批评方法的不彻底。这种主观意图凌驾于客观标准之上的批评态度,也使他有意忽视“永明体”有关的诗人的重要学习对象——曹植,而是只追溯那些成就有限的源头,这更加放大了三品论人的理论缺陷。因此,可以这样说,钟嵘的主观需要与客观标准的对立损害了“追源溯流”批评方法运用中的客观性。
[1][南朝宋]鲍照.钱钟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清]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6.
[3][清]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魏]曹植.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南朝齐]谢朓.曹融南校注集说[M].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清]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M].南京:江苏书局,清同治11 年:卷六.
[7][清]王夫之.古诗评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6.
[8][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梁]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0][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唐]皎然.诗式[M]//[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12][日]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M].王利器,校 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3][唐]卢照邻,卢照邻集校注[M].李云逸,校 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I207
A
1003-8477(2012)01-0127-03
陶春林(1975—),男,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周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