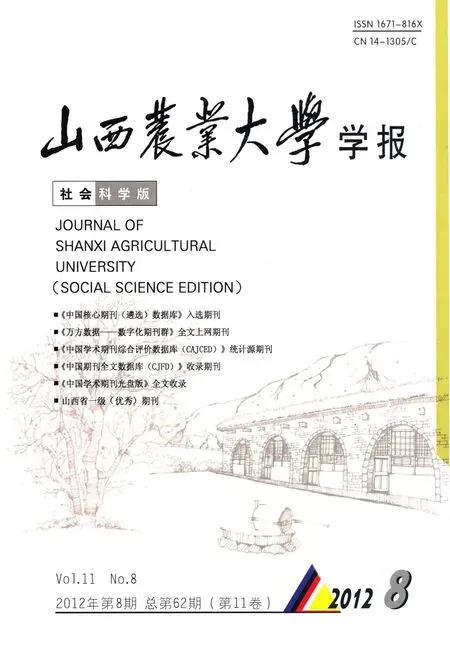章克标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和借鉴
2012-04-12陈利娟黎跃进
陈利娟,黎跃进
(1.山西大同大学 文史学院,山西 大同037009;2.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384)
一、章克标①和谷崎润一郎的因缘
① 章克标 (1900~2007),浙江海宁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长寿的作家。早年留学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科,但他爱好文学,曾与同学方光焘、程祥荣等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一起读书、讨论,并开始创作。回国后,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写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上一位非常活跃的作家、翻译家、编辑。也是狮吼社的主要成员,狮吼——金屋作家群的重要作家。著述颇丰、文体多样,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现代杂文创作以及日本文学的译介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小说集 《银蛇》、《恋爱四象》、《一个人的结婚》、 《蜃楼》等,杂文集 《文坛登龙术》、《风凉话》等,以及百岁高龄创作的回忆录, 《九十自述》和 《世纪挥手》。
刚踏上文坛,章克标就走近了唯美主义,他跟腾固、方光焘等同人一起组织了狮吼社,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在倾向于唯美主义的众多作家中,章克标对谷崎润一郎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翻译和介绍他的早期作品。
谷崎润一郎和永井荷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公认的代表作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谷崎润一郎作品在我国文坛的传播 “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1]且有多个译本,评论文章也随之大量涌现。其中,“章克标是译介谷崎润一郎作品最为用力也最有成就的”。他不断地翻译介绍谷崎的作品,1929年到1930年间,章克标翻译的谷崎润一郎的著名短篇 《刺青》、 《萝洞先生》、《杀艳》,分别在 《狮吼》半月刊、《金屋月刊》、《新文艺》等刊物上刊载,1929年11月开明书店还出版了章克标选译的 《谷崎润一郎集》,收入 《刺青》、《麒麟》、《恶魔》、《续恶魔》、《富美子的脚》、《二沙弥》共六篇小说。
这段译介高潮过去后,章克标还在不断地关注谷崎润一郎的作品。1941年1月,三通书局出版了章克标翻译的 《富美子的脚》(谷崎润一郎著);随后又出版了章的译作 《恶魔》和 《人面疮》;到1957年2月,章克标译出了谷崎润一郎的 《细雪》,准备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但随后赶上了整风运动,他被判为 “反革命分子”,接受改造,出书的事就不了了之。章克标不仅热情地译介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而且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他深深地理解了谷崎润一郎,理解了他的热情、他的追求、他的主张甚至是他的恶魔主义。对于谷崎润一郎的创作偏至于官能美的极端,他是有清醒认识的,但他更热心于用唯美的观点来为谷崎润一郎辩护,坚决反对用人生和社会学的文学观来批判其创作的颓废倾向:“他有丰富的空想世界,而这个空想像陶醉于鸦片之后,所见的幻美奇怪的梦。在他不要什么人生,也不要什么现实,他的世界是超越了现实和人生而存在的世界。人间有切切实实在社会上做事的时间,却也有耽于空想和睡着了做梦的时刻,他的文学便是后者,不能用人生什么来批判的。在他没有什么革命不革命、思想不思想的,他的作品中只有感情情调,并不是要用知识去理解的。”[2]
二、章克标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和借鉴
正是在不断地阅读、翻译、理解中,谷崎润一郎的唯美——颓废情调不知不觉渗透到章克标的创作中。对此,章克标有过如下叙述:“这几天,我的神经好像颇有些两样了。……第一,我连续翻译了几篇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头脑中被他的恶魔的色彩唯美的情调充塞满了。”[3]
(一)主人公形象的 “恶魔色彩”
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世界是由 “一切皆以美为强者,丑为弱者”的审美主张所统领,绝对排斥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也把这一抽象的主张具体对应到人类世界中,一方是作为美的象征的女性,另一方则是崇拜美、崇拜女性的男性。谷崎文学中的女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美女”,而是一批骄妇、毒妇形象。她们貌美如花、体态丰腴,但是肉体中却藏着巨大的魔性,就像艳丽非凡的罂粟花,既给人官能的美感,又能使人上瘾。而他笔下的男性,也不是普通的崇拜者,他们被女性的官能美、肉体美征服,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服服帖帖地爬在毒妇们的脚下,任其欺凌、折磨,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是悖于常理的受虐狂。
章克标作品中也塑造了这样的 “骄妇、毒妇”和受虐狂形象,只不过在程度上不及谷崎润一郎的疯狂和极端。章克标毕竟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所以在接受谷崎润一郎的影响时,不自觉的进行了文化过滤,这样他创造出来的形象也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
《银蛇》中的伍昭雪刚从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年轻美貌,浑身散发者迷人的魅力。在她身后,有一大群追随者,邵逸人、许谓渔、庄耀丹等等争相献媚,攻势凶猛;卞元寿、胜图、沈培根等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垂涎三尺、蠢蠢欲动。其中邵逸人最为痴迷,也最大胆,以至丑态百出。邵逸人曾这样分析:“她有媚态。女士所顶要紧的媚态,她的眼睛里放出她全个妖艳的灵魂,”他深感惑溺于她的魔力,而不仅是由于她的美,但他发现她对于自己的魔力还不曾自觉,也不能充分发挥,所以决定教导她、指点她、造就她,“若是我能够成功,我一定可以使她变成一个理想的妖妇,把一切男子玩在股掌之上的妖艳女人。……使她在无形之中,完成了一个又骚又辣又艳又恶的可爱的女人”。[3]他完全被这个 “美人”勾去了魂,成了风筝、木偶,被人操纵着。伍女士带给邵逸人只是难耐的痛苦、煎熬、折磨,但邵逸人一如继往地痴心不改,无法摆脱她的 “魔掌”,心甘情愿地受其摆布,活脱脱是一个受虐狂。这里的邵逸人、伍女士形象,以及邵逸人计划造就一个 “又骚又辣又艳又恶的可爱的女人”的构思,跟谷崎润一郎的 《刺青》何其相似,《刺青》中,刺青师在他理想的美女背上倾注了自己的灵魂,刺出了一只硕大的蜘蛛,也为美女注入了无穷的魔力,使她成了威力无比的女郎蜘蛛,可以任意驱使男性,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养料。邵逸人的计划无疑受此影响。
章克标在他的另一篇小说 《马车马》中,也塑造了类似的形象。《马车马》的主人公明波对现实的婚姻深感失望,觉得自己就像是拉着马车的马,内心充满了悲哀、苦痛,但是他却没办法象马一样脱缰而去。最后,他哀叹道:“我己是一个没办法的人了,是被她征服了的。以前说做马车马的苦,现在却又知道马车马而没有马车,却是更加不行,我是也要像别个人来驯良地服役了。”[4]他也是非常清醒得做她的奴隶,身不由己地拖着沉重的马车,一步步往前走,他身上的“受虐”倾向也很明显,象马一样被人驱使,但无力自拔。
章克标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同于一般的情爱小说中人物的温情脉脉,互相吸引。到章克标这里,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等的,是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美的一方 (往往是女性)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她们高高在上,傲视一切,威风凛凛,冷酷又残忍地肆意折磨匍匐在她们脚下地另一方 (男性),而这些拜倒在她们脚下的奴隶,被她们的美艳的魔力所吸引,任其凌辱,无力挣扎,反而以此为乐。这样一些有别于传统的形象,带上了鲜明的谷崎润一郎式的恶魔色彩,谷崎润一郎的早期作品,受王尔德的影响,多塑造一些 “莎乐美”式的人物,放荡、妖艳、冷酷,男人无不拜倒在她们脚下。章克标追随谷崎润一郎,也塑造了类似的 “骄妇”形象以及对应的有 “受虐”倾向的男性形象。
(二)浓郁的官能享乐主义色彩
谷崎润一郎文学早期的审美倾向主要表现为感官享乐的艺术化、唯美化,追求官能享乐和声色刺激。 《文身》 (也译作 《刺青》)、 《麒麟》、《春琴抄》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对官能美、感性美的追求是一种本能满足主义,但是由于追求者的态度过分极端,成为一种形而下的本能宣泄。在谷崎的唯美世界中,唯官能美的狂热与肉欲的耽迷合二为一。美的本体落实在官能刺激上,美的极致就是醉生梦死的感官享乐。所以对于谷崎来说,“美”仅仅是感官刺激带来的享乐感受,远非什么深刻的思想或精神。他对美的这种偏执的追求,显然是带有缺憾的——缺乏艺术的严肃性。“他摒弃了西方唯美主义文学所具有的人本主义内涵,仅取其感官享乐的一面,缺乏对人生意义、人本困境的深刻思考。他的作品就只剩下一幅幅在性、官能、肉欲的世界尽情享乐的狂欢者形象,缺乏西方唯美主义文学那种深刻的人本意蕴。而且,他绝对排斥伦理道德、世俗常规的合理性,走上了反理性主义的迷途,陷入偏邪的境地。”[5]
在追求官能享乐这一点上,章克标与谷崎润一郎有太多的相通之处,解志熙在 《“颓加荡”的耽迷——十里洋场的艺术狂欢》中,指出章克标所主张的 “艺术自足论和美感至上论,看来同北方唯美——颓废派作家们的主张一样高雅。但由于章克标把它们同醉生梦死的感官快乐主义相结合,便从形而上的高空跌入到形而下的深渊。换言之,在章克标那里,唯美即是唯乐,而唯乐又等于唯官能之乐。”[1]
章克标不断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在 《银蛇》、《蜃楼》、《做不成的小说》等作品中,突出官能美的描写随处可见,一切激动视觉、听觉、触觉的美他都毫不犹豫地猎取。这些作品中的活动的人物都是十里洋场的颓废文人,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文人的自我清高,在品茶、吟诗等雅致的艺术趣味中追求高雅脱俗的精神享受,而是投身于现实的都市,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中寻求自我生存和感情的需求。尽管时局动荡,战乱不断,他们仍然可以躲在外国租界里面安享太平。他们无所事事,除了聊天打牌,就是留恋于歌楼酒店,徘徊于花街柳巷,搜奇猎艳,在 “为艺术”的名义下满足感官享乐的欲望。如 《银蛇》中的邵逸人,已有妻女却疯狂地追逐美女——伍昭云和陈素秋,整天跟在美人的背后团团转,无所不为,丑态毕露。把恋爱作为创作灵感的源泉,得不到,便酒店买醉,妓院买笑,颓废又放荡,是一个十足的沉溺于感官享乐的颓废文人。《文坛登龙术》里所描述的文人的丑态,都集中在他身上。
《蜃楼》中作者不惜笔墨,不遗余力地描述建筑的富丽堂皇,室内陈设的精致奢华,人物的美貌绝伦,舞姿的轻盈优美,管弦丝竹之声的悦耳动听…… “她四肢百骸的抖动,衣袖裳角的飞扬,还有歌喉的振颤,这声色光影的大舞动,像天雨百花地喷彩泉。”[3]《做不成的小说》中,“我”为了做小说,与朋友去各色肉欲场所搜奇猎艳,看那些 “打扮得妖妖娆娆花花绿绿漂漂亮亮的”女人。在章克标的这些作品中,人物目之所及,最受关注的还是美的肉体:鲜红润泽的嘴唇,勾魂摄魄的眼睛,芙蓉花般艳丽天鹅绒般软和的面孔,灼灼的桃腮,丰隆的鼻子,丰丽的肩膀,俊秀的手臂,微突的乳峰,丰艳的肌肉等女性美的极致,无不让人心醉神迷。这样,章克标就把谷崎早期抽象化的官能世界现实化和都市化了,在对十里洋场颓废文人诗酒风流生活的恣意描述中,在 “颓加荡”的旗帜下纵情狂欢时,他把本来不乏严肃和深度的唯美——颓废主义引向了轻浮和浅薄,把唯美——颓废主义感官化、官能化了,或者说把唯美——颓废主义庸俗化,卑俗化了。
三、接受影响的原因
在众多文学流派,众多的作家、作品中,章克标为什么对唯美主义和谷崎润一郎情有独钟?章克标对唯美主义文学的选择和接受不是偶然的。“艺术,是艺术家从自己的审美主体出发,通过审美感知、审美理想,对审美对象进行重新铸造的结晶,因此艺术创造的过程是主客体相融的过程,其中审美主体居于主动地位。”[6]作家不是像镜子、照相机一样被动地再现审美客体,也不可能在吸收和借鉴外来艺术思潮时全盘照搬,作家对外来艺术思潮的选择、接受都和自身的审美需求相密切相关。这种对外来文学思潮的审美选择总是以接受者自己的独特个性、气质、人生经历为出发点,接受者总是选择和接受那些与他们精神上的近亲者。同时,作家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等因素,也为作家的选择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一)客观原因
1、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发展
“日本唯美主义是在20世纪初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作为对自然主义的反动而兴起的一种文学思潮。到1916、1917年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发展到巅峰,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潮。”[7]而章克标是在1918年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取了官费,继续学业。这时的日本文坛,唯美主义思潮正在盛期,唯美主义的作品在报纸、杂志、书刊等地方大量存在,他为了学习日语,每天读日报上连载的通俗长篇小说,那么他接触到唯美主义也是必然的了。章克标在他的回忆录《世纪挥手》中提到:田汉对当时正流行唯美派作品 (王尔德等人的作品)非常热心。
2、动荡的时局
二、三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战乱不断。军阀混战曾经激起过知识分子的愤怒,而1927年随着东北易帜,北伐结束,蒋介石在南京定都,又掀起新一轮白色恐怖。政治的低气压让文人们陷入颓唐的心境,对现实无奈而绝望,转而投入纯文艺的研究与写作之中。
章克标踏上文坛,就是在二十年代中期。面对时局的动荡,政治低压,社会的黑暗让章克标深感不满,但又找不到救世的良方,无力又无奈;面对自己的无力,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又让他感到苦闷压抑,只能做些 “幽默滑稽的小明堂”吐吐闷气。所以,唯美主义的反叛色彩让他兴奋。正如解志熙所言:“他们最欣赏的其实是唯美——颓废主义者那种冲决一切传统道德网罗的反叛精神以及无条件地献身于美和艺术的漂亮姿态,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唯美的深层基础——一种绝非美妙的人生观。”[1]而这时中国文坛上,对谷崎润一郎的译介正达到了 “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谷崎润一郎作品绚丽的色彩,大胆的想象,奇崛的幻想,以及人物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这些都让章克标折服。
(二)主观原因
1、个人的性格
章克标性格内向、拘谨、怯懦,他自己提到“受到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习惯规行矩步,谨小慎微,有时连自己也感到气恼”。[3]而章克标生活的小环境——上海大都市,在二、三十年代已经非常繁华了,商业发达,娱乐业发达 (舞厅、赌场等娱乐场所不断引进西方的现代化设备)。五光十色的生活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让他们迷醉。到处充满了诱惑,他身边的朋友们 (颓废文人),或者追逐 “顶时髦、顶出风头的恋爱”,或者混迹于花街柳巷,放荡又颓废,这让章克标艳羡不已。也想投身其中,然而伦理道德不自觉地约束着他的行动,想放荡一回,却又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旧的观念始终拖拉着新的观念,他们乐此不疲地探险着各式 ‘肉欲’市场,却又始终以 ‘灵肉一至’相标榜。”[8]也就是说,既想迎合外界的诱惑,又无法忘怀平常的道德准则。而通常人们对得不到的东西,无法实现的梦想,往往念念不忘,渴望不已,这种渴望郁结于心,徘徊不去。非常需要寻找一个替代品,读书是很好的消遣。这样,谷崎润一郎作品的享乐主义倾向,特别是感官享乐倾向,非常适合这样的胃口。
2、难忘的经历
其一、冒险的遗憾1926年寒假期间章克标去了一次上海,途中要在嘉兴中转。在旅馆住了一晚,“接待了”一位姑娘。这一夜的冒险,带给他的是难言的隐痛——身染恶疾。求医问药,甚至住院治疗,仍然不见好转,让他心情沉重了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他深知旅馆藏污纳垢,他 “接待”的并不是良家妇女,但是一个青年第一次接触未知的世界,第一次与女性交往,就受到这样的惩罚,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足以让他心有余悸。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女性的看法,即使不能把所有的女性统统归入 “肮脏、恶毒”一类,也对他们纯洁、善良充满了怀疑。而且,在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他笔下的 “美玲”形象——美貌、清纯、贤淑、善良。而理想与现实一碰撞,落差却如此之大,多少会有些理想破灭之感。
其二、牵涉郁、王恋爱 刚从大学毕业,清纯美丽的王映霞,身后有一大批的追求者。其中,已有妻室的郁达夫最为痴迷,郁达夫曾把章克标当作 “假想情敌”。一次,他请章克标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向章克标坦露他失魂落魄、异常痛苦的心迹:他对王映霞 “入了迷,着了魔”,被她 “勾了魂,慑了魄”,并请求章承诺“放弃王映霞,不要主动去追求她,放他一条生路”。郁达夫的绝望、痛苦无疑深深地印在了章克标的心里。郁达夫的失魂落魄也会让章克标感觉到女性的魅力,或者说是美的魔力——它可以统治一个人的灵魂。
其三、“相亲”的失望。一次,王映霞准备把她的姐妹介绍给章克标,要他到家里去相亲。这让他很不愉快,因为那时他坚持 “灵肉一致”的恋爱观,希望一见钟情的天作之合,而人造出来的会晤,同旧时的相亲一样,是一种交易,不是他希望的自由恋爱。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去“相亲”,自然不会有好感,而女方又 “特别不漂亮”,所以又是一次遗憾的经历。
尽管章克标对 “相亲”,没有好感,但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带着几分美好的理想。因为他的好朋友滕固的经历多少影响了他的恋爱观,不再固执地坚持 “一见钟情”,(腾固没娶到文君而娶了红娘,相濡以沫的生活也很美满)。但结果却是 “很伤脑筋”,尤其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女方 “不漂亮”,这对他的理想又是一次打击。
在章克标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没有给年轻人提供自由交往的机会,只有五四时期是个例外,但当时他在日本留学,没赶上,等他留学归来,时机已过。而且章克标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仅有的一些交往留给他的是尴尬、痛苦的回忆。对于女性的欺诈、恶毒他领教过;对于女性的魅力,他看到过,听说过;而对于现实中得不到美女的青睐,又会激起他无限的渴望。这些经历、印象在他心里不断地深化,所以读到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虽然谈不上什么思想或精神,却有着特殊的魔力,不仅让章克标倾倒,也让一大批人倾倒。诚如评论家V·H·威廉所说,“读谷崎作品的人会完全被谷崎的感觉美的魅力迷住,被引入谷崎独特的世界。谷崎文学的弱点和长处以不可思义的程度交织在一起。”[9]
[1]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53,233,66.
[2]章克标.谷崎润一郎集·序 [M].上海:开明书店,1929:3.
[3]陈福康,蒋山青.章克标文集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77,120,295-308,100.
[4]章克标.马车马 [J].金屋月刊,1(3):42.
[5]齐珮.日本唯美派文学研究 [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19.
[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74.
[7]叶谓渠,唐月梅.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 [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82-83.
[8]许道明.海派文学论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73.
[9]李媛.谷崎润一郎 “嗜美”探幽 [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7.